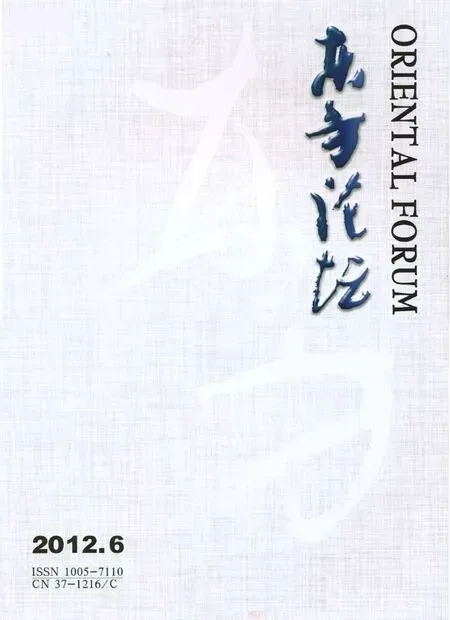论厉鹗诗歌的创作个性
张 然
论厉鹗诗歌的创作个性
张 然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清代诗人厉鹗反对为诗人和诗歌划分派别。现今大部分文学史著作将厉鹗树为浙派诗的代表人物,有碍于对其人其诗特立性的认识。厉鹗诗并非以师从某一派风格并将其推至极致取胜。他孜孜追求诗歌的艺术质量,表现为诗意的新奇和诗句的精整。
厉鹗;特立;“不谐于俗”
一
清代中期的诗坛,门户各张,各树旗纛,不但有宗唐宗宋之别,且各派诗说纷纭而立。严迪昌的《清诗史》则以“朝野”之分认辨清代中期的“诗界群星的坐标”。[1](P654)
诗人厉鹗,被视为清中期浙派诗的领袖, 《杭州府志·文苑传》称其“数十年大江南北,所至多争设坛坫,皆奉为盟主焉。”吴锡麒《墓田碑记》称其“一时推为祭酒,末学迎其津逮。”[2](P1728,1741)曾与厉鹗同在浙江志馆修书,而“诗派不合”[3](P823)的沈德潜“诮浙诗,谓沿宋习、 败唐风者,自樊榭为厉阶。”[4](P283)至今的文学史与文论史著作仍将厉鹗视为宋诗派的代表作家,如说“康、 雍、 乾时期,浙诗派最重要的诗人是厉鹗,他的诗论构成了该阶段宋诗派诗歌理论的主干,而与沈德潜的‘格调说’形成对照。”[5](P272)如说厉鹗“沿续了查慎行所标举的宋诗派方向”。[6](P493)厉鹗本人反对为诗人和诗歌划分派别,他曾辨“体”与“派”,明确指出:“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所谓“体”,不仅指诗体形式,其指涉相当宽泛: “诗之有体,成于时代,关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淘冶得也。”“少陵所云‘多师为师’,荆公所谓‘博观约取’。皆于体是辨。”对于诗歌流派的出现,厉鹗也作了解释: “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他追溯“派”形成的因由并指出结“派”的弊病: “自吕紫微作江西诗派,谢皋羽序睦州诗派,而诗于是乎有派。然犹后人瓣香所在,强为胪列耳,在诸公当日未尝龂龂然以派自居也。迨铁雅滥觞,已开陋习。有明中叶,李、 何扬波于前,王、 李承流于后,动以派别概天下之才俊,噉名者靡然从之,七子、 五子,叠床架屋。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 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钜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于此有卓然不为所惑者,岂非特立之士哉?”[2](P735)
厉鹗本人即为“卓然不为所惑”的“特立之士”。厉鹗祖籍浙江慈溪,生于浙江钱塘(杭州)。他在两浙诗人名士中交游甚广,袁枚《随园诗话》记述: “乾隆初,杭州诗酒之会最盛”,厉鹗与诗友们“每到西湖堤上,掎裳联襼,若屏风然。有明中、 让山两诗僧留宿古寺,诗成传抄,纸价为贵。”[3](P93-94)从地域角度介入文学现象,早就是将作家划分流派的依据之一。尤其在交通工具仍然相当原始的时代,同一地域的诗人便于交游与唱和,也因此难以避免相互影响,于是被视作一个群体。但是,倘若以“浙派诗”来为厉鹗归“派”,即使奉他为浙派诗的领袖人物,也多少有碍于对其人其诗“特立”性的认识。
厉鹗的著述理念也具有明显的特立性。他精研宋诗,历20余载,著《宋诗纪事》100卷。“暝写晨书,缉一朝之风雅。有集者,存其本事之诗,更为补逸;无集者,采厥散亡之什,如获全编。”[2](P731)200年后,钱钟书仍认可“不用说是部渊博伟大的著作”,至于“有些书籍它没有采用到,有些书籍这采用得没有彻底,有些书籍它说采用了而其实只是不可靠的转引”,[7](P23)则应归因于条件的限制。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可能排拒前人的影响,特别是在“诗分唐宋”已成为定论的清中期,对“唐”、 “宋”分别代表的审美风格的概括,已经形成供写诗者选择的二种规范。从厉鹗对诗句精警的追求,对“俗”的刻意躲避,确能读出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派的影响。但哪一个优秀诗人甘愿只做既往某一派的追随者和效仿者?正如厉鹗论宗唐诗人时所说:“夫诗之道不可以有所穷也。诸君言为唐诗,工矣;拙者为之,得貌遗神,而唐诗穷。于是能者参之苏、黄、 范、 陆,时出新意,末流遂澜倒无复绳检,而不为唐诗者又穷。物穷则变,变则通。”[2](P734)厉鹗正是怀着“诗之道不可有所穷”的信念,走出了一条“特立”的诗歌之路。
将厉鹗划归“浙派”,划归“宋诗派”,并封其为首领式人物,正如厉鹗当年所说,“是强为胪列耳”,作为诗人的他“未尝龂龂然以派自居耳。”
二
厉鹗逝世前以“不谐于俗”概括自己的人生和作品: “予生平不谐于俗,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2](P704)“不谐于俗”的自诩和自况,与宋诗派景仰的黄庭坚有所契合。黄庭坚曾为“不俗”作过界定: “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8](P1562)
厉鹗与黄庭坚所述“不俗人”并不相符。他“平居”即异于常人。其友全祖望为其所作《厉樊榭墓碣铭》云: “其人孤瘦枯寒,于世事绝不谙,又卞急不能随人曲折,率意而行,毕生以觅句为自得。其为诸生也,李穆堂阁学主试事,闱中见其谢表而异之曰:‘是必诗人也。’因录之。计车北上,汤侍郎西崖大赏其诗。会报罢,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馆焉,樊榭襆被潜出京。翌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复入长安。及以词科荐,同人强之始出,穆堂阁
学欲为道地,又报罢,而樊榭亦且老矣。乃忽有宦情,会选部之期近,遂赴之。同人皆谓:‘君非有簿书之才,何孟浪思一掷?’樊榭曰:‘吾思以薄禄养母也。’然樊榭竟至津门兴尽而返。予谐之曰:‘是不上竿之鱼也。’”[9](P364)厉鹗并非没有试图踏上对于当时诗书人来说被视为人生正路的仕途,但几次机会都被他放弃,甚至可以说是“逃”掉。时人叹其“寂寞”。“寂寞”一词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只是“不仕”的指代。厉鹗生活在诗歌氛围浓郁的江浙,交游广泛,唱和频繁,不无崇拜者和赞助者。他被“扬州马秋玉兄弟延为上客”,“马氏小玲珑馆多藏旧书善本,间以古器名画,因得端居探讨。”[10](P6)厉鹗在杭州南湖居所,闹中取静,简素而清雅,自号“南湖花隐”。时人王茨檐以专文叙其居“倚城北陴陑,舍喧而即静,水树明瑟,有敞而堂,有折而庑,有华散生盘门藩落而延接于櫺槛,是为樊榭山民南湖花隐。”原址曾为宋代豪门之豪宅,记述者对比今昔,迭发议论,而对厉鹗之羡慕溢于字句间: “今茨所见,远峦云浮,卉木翳荟,禅棲盂瓶之扣食,泠泠水次。物不停固,与为豪侈者之役于物也,其终不如寂寞者之适吾素已矣。题以‘花隐’,樊榭殆欲佩兰餐菊,以终老于斯矣!”但南湖居所只是“赁居”,居住八年后,不得不“移居东城”,时人又叹其“贫”,“所居在城东仓巷,破屋萧然,粝餐自给,竟困于缝掖以老。”[2](P1747-1754)而他却能于“破屋萧然,粝餐自给”的生活中找到一份自由的感觉。他在《移居四首》中叙述“南湖结隐八年余,又向东城赋卜居”,对他人眼中“破屋”的环境颇为满意: “颇爱平桥通小市,也多乔木暯清渠。”“莎径梅坪密复斜,百弓堪作小园夸。”他想象着“稍待芟除荒秽了,一轩风景任支分。”他可以享有一份相对平稳的诗人生活: “从人画出村夫子,旧事它时一笑。”“仰屋著书聊耳耳,闭门种菜漫云云。”[2](P985-986)实际上,他的“贫”是相对的,在友人的资助下,他尚能“以求子故,累买妾而卒不育”[9](P365)。厉鹗往来于杭州、扬州之间,得以在社会夹缝中做一个专业的诗人、词人、 文人,并在生前即获得相当大的声名。这使他的“不谐于俗”能“特立”于世俗社会,并难得地享有较多的行为自由和精神自由。据乡人记载:“厉樊榭徵君制意拙率,不修威仪,尝曳步缓行,仰天摇首,虽在忂巷,时见吟咏意。市人望见遥避之,呼为‘诗魔’。”“厉徵君之诗词,与金农冬心书画,乡里齐名,人称髯金、 瘦厉。”[2](P1752)不少研究者认为厉鹗“终竟潦倒一生”,“这是个畸行诗人而落魄江湖者”[1](P878),中国古代文论强调“文如其人”、 “诗如其人”,因“其人孤瘦枯寒”[9](P364),于是人们往往以“瘦”、 “寒”之类的词概括厉鹗的诗风。笔者则认为,形体与处境的“孤瘦枯寒”并未造就厉鹗“如其人”的诗风。厉鹗“生平不谐于俗”,是体现于异于常人的行为方式,而其“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却并不依仗特异的风格,而是孜孜追求诗歌的艺术质量,表现为诗意和诗句的精整。
三
在厉鹗写作的年代,作为诗人要表现出诗的“特立”性已非常艰难。袁枚曾在《随园诗话》中记下寒士丁珠的诗句“著书翻恨古人多”。丁珠又有《遣怀》诗一首,诉说晚生者的不平: “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后。”[3](P174)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使诗人们感受着处于古人笼罩下的无奈感。恽敬在《坚白石斋诗集序》中两次感慨“言诗于今日难矣哉”,他回顾唐以来诗的发展变化,且叙且叹:“古近之体备于唐,唐之诗人盖数十变焉,宋较之唐溢矣,亦数十变焉。元较之宋敛矣,且屡变焉。明较之元充矣,又屡变焉。本朝顺治中诗赡而宕,康熙则适而远,雍正则浏而整。”那么,身处清中期的诗人还能怎样写诗?恽敬鸟瞰诗坛: “于是自乾隆以来凡能于诗者,不得不自辟町畦,各尊坛坫。是故秦权汉尺以为质古,山经水注以为博雅,牦轩竭陀以为诡逸,街弹春相以为真率,博徒淫舍以为纵丽。”[11](P250)分别以几个字去概括某派诗风,当然不可能准确,而恽敬所说各派风格被推向极端的趋向确有具体指涉。风格被推向极端必显其偏,而有所偏,甚至偏到极致才易于立说,也才容易实现“不蹈袭,不规摹”的创新效应。
在“乾隆以来凡能于诗者,不得不自避町畦,各尊坛坫”的诗坛背景下,厉鹗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诗歌道路。
厉鹗在为友人余茁村诗集所作“序”中,对“寒”做过精彩的议论和阐释: “集中诗大都皆彫年急景,冰雪峥嵘,触于怀而托于音者也。初出以眎予,标其首曰‘销寒’,予献疑曰:‘气之游者寒则敛,景之蒙者寒则清,材之柔者寒则坚。其在人也,寒女有机丝,人赖其用;寒士有特操,世资其道。寒亦何可竟销耶?’”厉鹗又诘问道: “寒亦何必遽销耶?若君之耸‘山’字肩,踞炉画残灰,作惊人语,如是以忍寒可矣,奚至效小儿女,骨脆不能凌吹,亟俟煦和,点梅图以脂为九九数,而反名曰销寒乎?”厉鹗认为,自古以来,“顾未有耽玩寒事而吟不辍如吾友拙村者”,[2](P741)余茁村“少日颇饶于赀”,有钱而有闲,因此得以“耽玩寒事”。而对于厉鹗来说,“寒”则是其真实的人生处境,他的作品中不乏写“寒”者,但他既非“耽玩寒事”也非借诗“销寒”。“寒”只是厉鹗的诗材之一,他追求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歌艺术效果。如作于晚年的《槜李舟中春寒》[2](P1417),以“寒”为题,感受着“三朝天气腝翻寒”的寒冷,他期望的是能写出超越前人的诗句: “漫首单棲最惆怅,陆家赋后咏尤难。”用陆龟蒙《春寒赋》句,“寒中之人,有异于寒冬,其来也低迷,其往也惆怅。”及陆《自遣》诗句:“天意最饶惆怅事,单棲分付与春寒”。厉鹗分明很欣赏陆龟蒙所咏寒中“单棲”之“惆怅”,而陆之诗句所唤起的不仅是认同感,更是前人笼罩下的无奈和希望超越前人的艺术追求。厉鹗此诗颈联“周遮莺语依前涩,禁勒桃花不放残”极为精警而精妙,非信手拈来而稍带斧痕,而其句之精、 之新,不得不令人赞叹他在“陆家赋后咏尤难”的背景下所做出的艺术努力。又如《信宿溪上巢夜复大雪晓望有作》[2](P975)以“清寒山梦惊”开篇,夜间大雪之后的拂晓,最为寒冷,但厉鹗并未抒写寒冷中的感受,相反,他似乎忘记自己置身于“寒”中,更没有借身之“寒”而联想心之“寒”。他将令人惊叹的雪景凝化为新警的诗句: “乱迷荒塗踪,深罨春流响。稍稍杂雾霭,冥冥失诸嶂。”显而易见,诗句非脱口而出而是推求得来,他力求以不落前人套路的诗句描述雪中山水的奇美。而厉鹗又以眼前的雪景引发充满诗意的联想和想象: “窙寥观太空,眩花本无象。一庭虚白光,湛寂生妙想。”这几句诗都有出处,“窙寥观太空”出自潘岳《登虎牢关赋》“幽谷豁以窙寥”,“一庭虚白光,湛寂生妙想”出自收入《中州集》的朱之才《水月有兴》诗“人生湛寂初,与月同清质”。依仗着对诗歌艺术的执着,厉鹗能够翻新出奇,这或许是人们将他归类于宋诗派的理由,但是,如果只据诗句中的字词是否有“来处”判断其宗唐还是宗宋,过于浮面了。在厉鹗生活的时代,诗人写诗已经不可能完全躲避前人用过的字词,从前人诗句中去“偷”吗?“偷”,即蹈袭似乎早已成为诗人难以回避的手段。
唐代诗僧皎然把诗人的蹈袭行径分为偷语、偷意、 偷势三个品级: “偷语最为钝贼,……此辈无处逃刑”,“其次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其次偷势,才巧意精”[12](P59)。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引皎然语,说明自宋代以来,“偷窃”已与诗学融合: “在宋代诗人里,偷窃变成师徒公开传授的专门学问。”[7](P18)厉鹗也认同“偷”吗?相反,他竭力躲避落到“偷”的陷阱——虽然前人留给他的创新空间已相当窄仄。
总之,厉鹗诗不是以师从某一派风格并将其推至极致取胜,而是“毕生以觅句为自得”,他在林立的诗派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厉鹗曾在《赵谷林爱日堂诗集序》中感叹自古以来诗作往往借名位以流传: “自汉魏迄今,诗歌之传于代者,往往有名位人为多,而顦顇偃蹇之士,十不得二三焉。其故何也?有名位人势力既盛,门生故吏不惮謄写模印,四方希风望景之徒,又多流布述诵,虽无良友朋、 佳子孙,而其传也恒易。若士之顦顇偃蹇者则异是。”[2](P731)甚至发出了“呜呼!是非命也哉!”的呼喊,其中隐含着对自己诗作能否传世的担忧。以当时标准来看,终生未仕的厉鹗确属“士之顦顇偃蹇者”,但他却于生前即已蜚声诗坛。在他身后,创“肌理说”的翁方纲和标举“性灵说”的袁枚分帜立派,却都认可厉鹗的诗歌成就。翁方纲“于近从中颇许樊榭、 萚石两家”[13](P51),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摘引厉鹗的如下诗句,称之为“绝调”: “身披絮帽寒犹薄,才上篮舆趣便生。”“压枝梅子多难数,过雨杨花贴地飞。”“白日如年娱我老,绿阴似水送春归”。“荒村已是裁春帖,茅店还闻索酒钱”。“烛为留人迟见跋,鸡防失旦故争先。”[3](P823)在厉鹗的《樊榭山房集》中,堪称“绝调”的诗句随处可见。在厉鹗身后,由于学其诗者渐多,甚至出现了“近来浙派入人深,樊榭家家欲铸金”(洪亮吉《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14](P132)的现象。厉鹗本人既不愿“袭一二钜公之遗貌”,又“未尝龂龂然以派自居”,而“欲铸金”的景从者仍然要强为其划“派”,违背了他本人的主张,也说明了厉鹗批评过的“动以派别概天下之才俊”的习俗根深蒂固。
[1] 严迪昌. 清诗史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2] 厉鹗. 樊榭山房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3] 袁枚. 随园诗话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4] 袁枚. 小仓山房文集 [M]. 王英志. 袁枚全集: 第二集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5] 王运熙, 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下册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6] 章培恒, 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 下卷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7] 钱钟书. 宋诗选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8] 黄庭坚. 黄庭坚全集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9] 朱铸禹.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0] 周维德. 蒲褐山房诗话新编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
[11] 恽敬. 大云山房文稿 [M].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续修四库全书: 第1482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12] 李壮鹰. 诗式校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13] 法式善. 梧门诗话: [M].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续修四库全书:第1705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14] 洪亮吉. 更生斋诗 [M].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续修四库全书:第1468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潘文竹
Uniqueness of Li E's Poetic Creation
ZHANG R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Li E, a poet in the Qing Dynasty, objected to the division of poets and poems into schools. But the present works of literary history still regard him as a representative of Zhejiang School of poems. This viewpoin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his poetic uniqueness. Rather than learn and promote a specific school, he was devoted to the artistic quality of poems, i.e., the novelty of poetic meaning and the properness of lines.
Li E; unique; “inharmonious with the vulgar”
I207
A
1005-7110(2012)06-0098-04
2012-10-19
张然(1975-),男,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