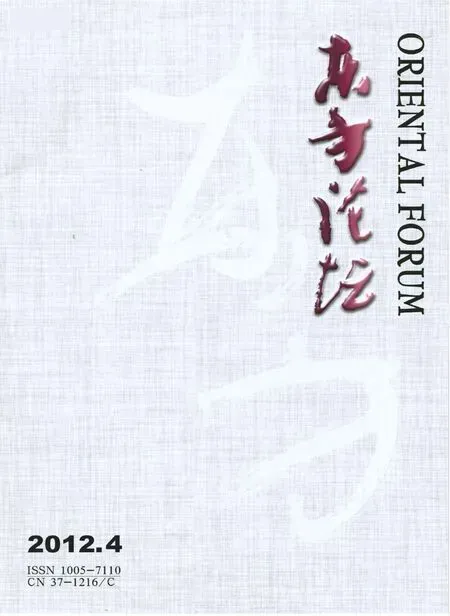读《大日经》心得
薛 克 翘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100007)
读《大日经》心得
薛 克 翘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100007)
《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分属两个系统,一个代表真言乘,一个代表金刚乘,前者倾向于“右道”而后者倾向于“左道”。《大日经》一方面在维护大乘佛教,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印度教的多方渗透。
大日经;佛教密宗;真言乘;胎藏界曼荼罗
《大日经》(全名《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学界已经有了定论。如,日本学者中村元先生认为,“《大日经》是体系化了的真言密教的最重要的根本经典。”[1](P125)中国学者黄心川先生认为,“密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思想系统开始出现于《大日经》”。[2](P40)吕建福先生也说,“《大日经》是真言乘的根本经典,也是中期密教的两部代表经典之一。”[3](P58)也就是说,这部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佛教真言乘的基本要领和内容。
而关于《大日经》的翻译和编纂年代,学界还有一些大同小异的看法。如,中村元先生认为,《大日经》约于7世纪前半至中叶成于印度;由善无畏译、弟子一行笔受的《大日经》完成于西历724年。[1](P126)日本学者长部和雄先生则提出,《大日经》先后有两个译本:第一个是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善无畏“奉诏译”的,其梵文底本被称为“善无畏本”;第二个是客死北印度的无行禅师搜集、于7世纪末被送回(长安的)梵文本,由善无畏和一行合作于开元十二乃至十三年(公元724—725年)“私译”的,[4](P117-118)即现行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关于《大日经》的成书地,有中印度那烂陀寺说、西印度说、南印度说、北印度说和西北印度说诸种,松长友庆先生认为“成立于那烂陀或者西印度的可能性大。”[5](P58)
吕建福先生综合上述意见,经考证,认为“编纂《大日经》的地方或许就在那烂陀寺或附近。”“《大日经》的形成时间放在六世纪末七世纪初,比较接近事实。”[3](P59)
总之,《大日经》在密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中国密教如此,对日本密教如此,对印度密教亦是如此。
下面,谈谈笔者读《大日经》的几点体会。
一、《大日经》的中心思想
学界公认,《大日经》卷一《入真言门住心品》(简称《住心品》)提出的三句话“菩提心为因,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是《大日经》的思想核心。
对此,参与翻译此经的一行阿阇梨在《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简称《大日经疏》)卷一里作了解释,认为这是一个因果循环的体系,“犹如世间种子,籍四大众缘,故得生根,如是次第,乃至果实成熟,名为究竟。”“如从种子生果,果还成种,故以为名也。”此间,一行对菩提心、因、大悲、根、方便和究竟六个概念一一予以解说:菩提心是深信不疑之心,白净坚牢之心。因是种子(相当于内因),同时又是后二句的缘起。悲为慈悲,“慈如广植嘉苗,悲如芸除草秽”。“根是能执持义,犹树根执持茎叶花果,使不倾拔也”。“拔一切苦施无量乐,由自善根。”“方便为究竟者,谓万行圆极,无可复增,应物之权,究尽能事。”这是一行作为信仰者对信众的解说。如果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解释字面意思,是为了让信众理解并产生敬仰崇拜之心的话,那么,当代学者吕建福先生则站在哲学的立场对此作出现代解读,他说:“《大日经》把它的全部教义概括为因、根、究竟三句……因句是它的本体论,讲清净平等的菩提心为成佛之内在根据,佛心自心平等无二,如实知自心即是菩提。根句是它的实践论,讲大悲胎藏密法,以入此曼荼罗为成佛之基本条件。究竟句是它的方法论,讲三密为成佛之捷径、趣入究竟之方便,以手结印契为身密,口诵真言为语密,心作观想为意密。三密相应,即身成佛。”[3](P60)可知,《大日经》的这个思想核心虽然仅仅三句话,却是一整套真言乘义理和修法的概括和总结。
《住心品》在提出核心思想的同时,也明确了真言乘的理论归属,即大乘佛学。经中在解释菩提心时还说,“诸法无相,谓虚空相”。这显然是大乘佛学的观点。例如,龙树《中论》第五品(鸠摩罗什译文)说:“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若先有虚空,即为是无相。是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于无相法中,相则无所相。”①北京大学叶少勇先生给出了现代汉译:“在有虚空相之前,任何虚空不可得。若相之前有‘虚空’,‘虚空’则成为无相。没有无相之事物,无论何者于何处。既无无相之事物,则相当行于何处?”见叶少勇:《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81页。
《住心品》又说,“所谓空性,离于根境。无相无境界,越诸戏论。等虚空无边一切佛法,依此相续生。离有为、无为界,离诸造作,离眼耳鼻舌身意。极无自性心生。”同样,这也与大乘佛教思想相一致。例如,龙树《中论颂》第十七品(鸠摩罗什译文)说:“如是从初心,心法相续生,从是而有果,离心无相续。”[6](P273)
《大日经》在讲空的同时也强调幻。其《住心品》中说有“十幻”,即“幻、阳焰、梦、影、乾闼婆城、响、水月、浮泡、虚空花、旋火轮。”这些都是佛典中,尤其是大乘佛典中常用的表示空幻的比喻。例如,龙树《中论颂》第七品(鸠摩罗什译文)中就提到其中的三个:“如幻亦如梦,如乾达婆城,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6](P129)
此外,《大日经》中还多次使用了“阿赖耶”的概念。如卷一《真言品》提到“若识,若阿赖耶”。还说道,“大乘行,发无缘乘,法无我性。何以故,如彼往昔如是修行者,观察蕴阿赖耶,知自性如幻”。“阿赖耶”是大乘瑜伽行派提出的“八识”之一。其余七识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瑜伽行派认为,客观世界的本质是“识”,即人的感知。而人的感知是不真实的。实际上,人所感知的一切都是“识”,所以说“万法唯识,唯识无境”。阿赖耶识被认为是“种子识”,其活动生出世间万象。②参见姚卫群:《印度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不烦举证,已可看出,《大日经》中显然也融有大乘瑜伽行派的理论。
总之,在义理上,《大日经》不仅依附于大乘,还兼容空有两宗,这是其菩提心论的基础。
二、真言乘与大乘的关系
《大日经》卷一《曼荼罗具缘真言品》(简称《真言品》)有这样一段偈颂:“佛子此大乘,真言行道法。我今正开演,为彼大乘器。过去等正觉,及与未来世,现在诸世尊,住饶益众生。如是诸贤者,解真言妙法。”还说:“此殊胜愿道,大心摩诃衍,汝今能志求,当成就如来。”如此,《大日经》屡屡明确宣称自己属于大乘佛教。由此则更加证明,上文所说的“虚空”,就是大乘佛教中观派所主张的“空”。
《大日经》在提出自己理论归属的同时,也称自己的修行体系为“真言乘”。如《真言品》中所说:“秘密主,无大乘宿习,未曾思惟真言乘行,彼不能少分,见闻欢喜信受;又金刚萨埵,若彼有情,昔于大乘,真言乘道无量门进趣,已曾修行,为彼等故,限此造立名数。彼阿阇梨亦当以大悲心立如是誓愿,为度无余众生界故。”大乘佛教讲究以慈悲之心度无量众生,真言乘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真言乘有更多的法门可供进入,以此强调真言乘比传统的大乘更为殊胜。
那么,真言乘殊胜在哪里?其特别之处在哪里?就在于通过建立曼荼罗,并在每一个步骤上念诵真言,使其修行获得种种悉地(siddhi,成就),并最终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也就是说,建立曼荼罗是真言乘区别于以往大乘佛教的最重要的修行方式,而念诵真言与建立曼荼罗是同步进行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既然以真言乘自称,就要突出真言的地位。于是,真言占据了全经的很大比重。卷二《真言品》的后半部分、卷二《真言藏品》和卷四《密印品》几乎全部、卷五《字轮品》的开头部分、卷六《八印品》几乎全部,都是各种名目的真言。卷七为《供养次第法》,似为原典的附录部分,其中《净行品》、《仪式品》、《持诵法则品》偈颂与真言约略参半。
《大日经》中的真言名目繁多,例如,卷一中出现的两条真言,是在建立曼荼罗之初,一于洒扫场地时使用,一于冥想诸神下降时使用。其后,除卷三仅出8条真言外,卷二及以后各卷,各种名目的真言便接踵而来,而其基本用意都在于向诸神表示赞美、皈依和祈请,表示修行者内心对佛、菩萨、天神等的观想。因此,每一位神明都有相对应的真言。这些真言强调的是念诵,而不必究其原意。特别是传入中土以后,一般信众更无法知其所以。但它们的梵文原文仍然是有含义的,所以今人还是对它们作出了研究和解读。例如,“一切诸佛”真言:南么 三曼多勃驮喃 萨婆他 微么底 微枳罗宁 达摩 驮睹涅阇多 参 参 诃 莎诃。译为现代汉语为:皈依普遍诸佛,依一切法除无慧呀,法界生呀(依一切法除无慧,于法界生者呀),参 参 诃 莎
诃。[7](P80)
在修炼中,真言乘密教强调身、口、意三业和合。为此,《大日经》卷四《密印品》则将真言与手印相应,即每一手印都有一相对应的真言,做手印时必诵真言。手印为身业,真言为口业,观想为意业。这样,一面做出手印,一面口诵真言,一面心中冥想,就达到了三业合一的境地。这就是真言乘修法的关键要领。而建立曼荼罗,只是其前奏和铺垫,是营造一个富于氛围的场所。
三、胎藏界曼荼罗
曼荼罗的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吠陀时代。即由当时供奉神位和祭品的祭坛发展而来。吠陀祭祀通常以火祭,以火为沟通人神关系的纽带和桥梁,所以火神阿耆尼就成为人神的共同见证。火祭也是后来密教中“护摩”祭的前身。
“曼荼罗坛法是《金刚道场经》和《灌顶道场经》中新出现的”[3](P48),时间约在四五世纪。但曼荼罗法并非密教的发明,在上座部佛教各部中已经相当常见,其相关律书中多有记载。[3](P48)虽然建立曼荼罗的做法并非自《大日经》始,但《大日经》对建立曼荼罗所作的描述和解释却是空前的周全详尽,其轨则已经发展到十分完备的地步。
首先,对曼荼罗的主持人(阿阇梨)要求极为严格。如《真言品》说:“应发菩提心;妙慧慈悲兼综众艺,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通达三乘,善解真言实义;知众生心,信诸佛菩萨,得传教灌顶等。”还要“妙解曼荼罗画;其性调柔,离于我执,于真言行善得决定;究习瑜伽,住勇健菩提心。”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能成为阿阇梨,也就不能主持曼荼罗坛场传法,不能为弟子灌顶。
其次,在画曼荼罗前要先选址。《真言品》说:“彼坚住受教,当为择平地,山林多华果,悦意诸清泉,诸佛所称叹。应作圆坛事,或在河流处,鹅雁等庄严,彼应作慧解,悲生曼荼罗。正觉缘导师,圣者声闻众,曾游此地分,佛常所称誉。及余诸方所,僧坊阿练若,华房高楼阁,胜妙诸池苑,制底火神祠,牛栏河潬中,诸天庙空室,仙人得道处。如上之所说,或所意乐处。利益弟子故,当画曼荼罗。”又说,“彼拣择地,除去砾石、碎瓦、破器、髑髅、毛发、糠糟、灰炭、刺骨、朽木等,及虫蚁、蜣蜋、毒螫之类。”这使人们想起,后期金刚乘阿阇梨常在寒林中修习,并以髑髅为严饰和食器,显然是对真言乘的颠覆。
再次,是选择吉日良辰、礼佛、念偈颂告地神、香花供养等程序。
最后开始画曼荼罗。大日如来居中,其次是四方佛,再次是诸菩萨及其眷属,还有各路护法神明,不一而足。他们的名位都是依据方位安置的,大体是中心为主尊大日如来,然后是“东方以为首”,以东南西北的顺序右旋,安置四佛:宝幢、开敷华、阿弥陀、鼓音声。又在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个位置安置四大菩萨:普贤、文殊、弥勒、观音。这样,八个方位就形成了“八叶莲花”,又称“中台八叶”。外围还有多重(一般为三到四重)。总之,曼荼罗就是这样一个万神殿,诸佛、菩萨、金刚、护法、天龙八部及其眷属等咸集,各擅其位。阿阇梨要带领弟子按照“右旋”的次序一一礼拜。
《大日经》卷一《真言品》把这种曼荼罗叫做“大悲胎藏生大曼荼罗王”,所以称王者,以其规模最宏、诸神毕集、最为严丽、供养最丰。
但现在的问题是,《大日经》为什么把这种曼荼罗叫胎藏界?对此,历来颇多解释。日本学者长部和雄先生解读说,《大日经》中的“胎藏界曼荼罗的根本无疑是被称为‘大悲胎藏生’的生命来自母性的原理。……说到底,是作为象征生育的存在论图形的最高表现形式。”[4](P26)他指出了胎藏界曼荼罗的象征意义,这是很重要的。
《真言品》还说:“内心妙白莲,胎藏正均等,藏中造一切,悲生曼荼罗。”据此理解,心如白莲,是比喻其纯净洁白,不受污染,它正如母体的胎藏,能孕育生发一切,而孕育和生发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慈悲。也就是说,这个曼荼罗之所以叫做胎藏,是因为,第一,它象征着心,象征着白莲一样纯净之心,此心即菩提之心;第二,它有生育能力,由它产生慈悲,由慈悲可以普度众生。正如一行《大日经疏》卷十五所说:“从大悲根本生发,大乘无上诸佛最秘者,谓此漫荼罗,即是无上大乘根原也。谓此菩提之心,以大悲而为根本,亦如胎藏,故言根本也。”由此可知,胎藏曼荼罗不仅是真言乘的修行场所,也是真言乘核心思想的外在形式。
四、莲花与金刚
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女神的加入
我们知道,佛教有一整套的诸神谱系,至晚在五世纪昙无谶等人译的《金光明经》中就已经趋于完备①见《金光明经》第六至十品。。《大日经》则提出了一整套更加完备的神谱。这个神谱有三个特点:第一,确立了大日如来的独尊地位。第二,在这个谱系里,金刚的名目繁多,而且升格为菩萨,其中为首的是执金刚,又叫持金刚,又叫金刚手秘密主。他的地位很重要、很特别。世尊毗卢遮那是直接向执金刚宣说大乘佛教中最高机密的。他悉心谛听,并不时发问。从大乘佛教的观点来看,执金刚的身份是菩萨,世尊将秘密说给他,是让他肩负起普度众生的使命。但从密教的观点来看,他又被称为秘密主,似乎是秘密的掌管者、执行者。这样,指导修行、主持曼荼罗仪轨的阿阇梨仿佛就是他的代表或化身。第三,女神众多。应当说,到了真言乘的阶段,所有的金刚,都代表着坚固勇猛的阳性力量。但是,仅仅有阳刚力量显然是有缺失、不平衡的,于是,女神也纷纷出现。佛部有佛眼佛母(梵文Buddhaloca),莲花部有白衣佛母(《真言品》作“白处尊”,梵文Pandara-vasini),金刚部有金刚母(《真言品》又作“忙莽鸡”,梵文Mamaki )。还有诸多女神分别与男神配对,如菩萨们都有明妃在侧,等等。而且,经中对她们的形象也有所描绘。例如,《真言品》说,在观世音的右边是多罗尊(梵文Tara),“青白色相杂,中年女人状,合掌持青莲,圆光靡不遍,晖发犹净金,微笑鲜白衣。”观世音的左边是毗俱胝(梵文Bhrkuti),“左边毘俱胝,手垂数珠鬘,三目持发髻,尊形犹皓素,圆光色无主,黄赤白相入。”而大势至的“明妃在其侧,号持名称者②据一行《大日经疏》卷五,大势至的明妃“号持名称者”的名字叫耶输陀罗(梵文Yashodhara)。。一切妙璎珞,庄严金色身,执鲜妙华枝,左持钵胤遇③钵胤遇,同偈又作钵孕遇,花名。一行《大日经疏》卷五:“亦西方胜上之花。”。”
女神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度教的影响。早期佛教并没有这种情况,而印度教的主要神明却都是有配偶的,至少在史诗时代就已如此。这些印度教的神明都纷纷被请入佛教的神殿——曼荼罗中,出于外围的位置,属于护法神。这也是真言乘有意迎合社会大众生活习惯的表现。如《真言品》所说,阎摩王、帝释天、日天等,皆有后妃。
(二)胎藏界的暗示
这里还要再次提到胎藏界曼荼罗。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先生曾说:“曼荼罗分胎藏界曼荼罗和金刚界曼荼罗。‘胎藏界’的胎即是母胎,胎藏界曼荼罗是基于女性原理的,而金刚界曼荼罗是基于男性原理的。胎藏界曼荼罗是用母性的慈悲来突出佛的慈悲。”[1](P75)他道出了男女两性的原理,然而强调的却是母性内心柔和慈善的一面。
《大日经》所宣称的曼荼罗既然冠以胎藏之名,我们不妨从词源学角度来分析一下“胎藏界”一词——Garbha-dhatu。这是一个复合词,由garbha和dhatu组成。garbha有胎和坯胎等意思,但也有子宫的意思;dhaatu有金属、元素、身体要素等意思,但也有精液的意思。如果都取后一个意思,就是子宫加上精液,那就是要怀胎了,并将要生产了。当时来华的印度阿阇梨们,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也许对于印度人来说不需要解释。所以,汉译《大日经》中只强调了它“生”的功能,但也就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解释。而一行的《大日经疏》卷三说得明白:“次说修真言行,大悲胎藏生,大漫荼罗王也。今且约胎藏为喻,行者初发一切智心,如父母和合因缘,识种子初托胎中,尔时渐次增长,为行业巧风之所匠成,乃至始诞育时,诸根百体皆悉备足。始于父母种姓中生,犹如依真言门,学大悲万行,净心显现。又此婴童,渐具人法,习诸伎艺,伎艺已通,施行事业,如于净心中发起方便,修治自地,随缘利物,济度众生,故名大悲胎藏生也。复次,初入净菩提心门,见法明道,如识种子歌罗罗④歌罗罗,梵文kalala,义同garbha。时,前七地以来,为大悲万行之所含养,如在胎藏,无功用以去渐学如来方便。如婴童已生,习诸伎艺,至如来一切智地。如伎艺已成,施于从政,故名大悲胎藏生。又是一重秘密漫荼罗也。”一行的解释让我们知道,之所以以胎藏为喻,就是取男女和合的本义,即如“识种子初托胎中”。不过,他是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场,始终把握的是“随缘利物,济度众生”的原则。
笔者以为,《大日经》之所以使用“胎藏”这个词,原本就包含着男女和合的意思。这与女神进入曼荼罗神殿的意义是一样的,表现出真言乘迎合民众的心理,也预示着无上瑜伽的来临。
(三)六字真言的隐喻
《大日经》中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六字真言。
《真言品》中说:“真陀摩尼珠,住于白莲上。”这里的真陀摩尼珠就是如意宝珠或如意宝,梵文cinta-mani。如意宝珠住于白莲上,与六字真言已经很接近了。人们熟悉的六字真言为:唵嘛尼叭弥吽。其梵文为Om mani padme hum。其实是六个音节,翻译为汉文是六个字,所以叫六字真言。其字面的意义就是“祈愿宝珠在莲花上!”这是我国学者张保胜先生译出的原义。他说:“这显然是一句隐语。这句隐语如果再仔细追寻,就会发现,在印度密教巫术中,‘么尼’被视为男根的象征物;‘莲花’被视为女阴的象征物。所以,这个句子应译为‘祈愿两性和合!’”他认为,这来自于古代先民的生殖崇拜,古人不以为怪,今人却有所忌讳;在先民看来,“万事万物无不产生于两性和合。提升到哲学的高度,阴阳和合就成了万物的生因。这种认识属于原始唯物论范畴。”[8](P22)无论是在梵文原文的翻译上,还是对其隐语的破解上,他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大日经》中的这句“真陀摩尼珠,住于白莲上”自然也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也是一句隐语,只不过它是一句偈颂,而不是一句咒语而已。
印度古人一向崇拜莲花,佛教更是将莲花神圣化。《大日经》也不例外。诸神坐于莲花台,有许多还手执莲花,有开敷的,有未开敷的,有半开敷的。其胎藏曼荼罗有莲花部,甚至将整个曼荼罗喻为莲花。对此,一行在《大日经疏》卷四予以解说和引申:“今以莲花喻此漫荼罗义,如莲种在坚壳之中,枝条花叶之性已宛然具足,犹若世间种子心,从此渐次增长,乃至初生花苞时,莲台果实隐于叶藏之内,如出世间心尚在蕴中,又由此叶藏所包,不为风寒众缘之所伤坏。净色须蕊日夜滋荣,犹如大悲胎藏。既成就已,于日光中显照开敷,如方便满足。今此中妙法莲花漫荼罗义。”所以,如果说胎藏界曼荼罗的创立基于女性原理的话,那么,莲花曼荼罗也是基于一样的原理。
再说金刚一词,在汉语中有诸多含义,有时指一类神明,有时指金刚杵,有时指金刚石。梵语中也是一样,vajra、kulisha、hira、drdha,等等。[9](P867)其中,伐折罗(vajra)最常用,兼有金刚杵、金刚石和雷等多义。单说这金刚石,即钻石,属于宝石(摩尼)一类,所以有时也被称为摩尼宝王,梵文为mani-raja。这样,vajra和mani就有了共同点。仍如一行所说,“金刚喻实相智。过一切语言、心、行、道,适无所依,不示诸法,无初、中、后,不尽不坏,离诸过罪,不可变易,不可破毁,故名金刚。如世间金刚宝,有三事最胜:一者不可坏故,二者宝中之上故,三者战具中胜故。”(《大日经疏》卷一)如前文提到,摩尼既然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自然就代表着男性。金刚则不管是神、兵器还是宝石,都是牢固、坚硬、能破、阳刚的象征,也代表男性。由此可以推知,莲花与金刚就分别代表了阴阳两性。与六字真言的隐喻是一样的。
五、结语
通过对《大日经》的阅读,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男女合和的蛛丝马迹。
从以上举例已经可以看出,不管是胎藏界的象征意义,还是莲花与金刚的象征意义,以及六字真言的隐喻,都能证明这一点,即两性和合的问题已经在《大日经》中被隐晦地提出,这也许正是《大日经》与《金刚顶经》关系中的重要一点,也是后来无上瑜伽的一个前奏。
第二,《大日经》与《金刚顶经》的关系。
基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大日经》与《金刚顶经》虽然是两个系统,一个是代表言乘,一个代表金刚乘。从内容看两者似乎又有关联,但不能说后者是由前者过渡而来的。因为学界公认,《大日经》是在北印度或西北印度编成的,而《金刚顶经》是在南印度编成的。那么,真言乘与金刚乘、胎藏界曼荼罗与金刚界曼荼罗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是相互关联、并行发展的关系。但是后来,约九世纪,情形就不同了,真言乘在印度似乎并没有大的发展,而金刚乘却显示出日益旺盛的强势,那背后的原因可能主要来自印度教的强大攻势。这个问题需要以后论证,这里先不谈。
第三,对印度教的包容。
从《大日经》已经可以清楚看到,佛教对印度教的吸纳,或者说印度教对佛教的渗透,已经愈来愈烈。应当说,在佛教和印度教的发展过程中,相互间是互有影响的。例如,“大乘瑜伽行派所强调的‘识’或‘心’在婆罗门教中就早有类似的论述。一些奥义书就把‘识’看作万有的根本”。[10](P470)到《大日经》中,情况更是如此。义理、神明、修法等诸方面都有印度教的影响。《住心品》中讲到“幻”,其实和吠檀多派哲学中的“幻”(梵文Maya,音译摩耶)是一样的意思。至于进入曼荼罗中的印度教神明,那就更多了,除印度教三大主神梵天、湿婆、毗湿奴及其眷属外,甚至连“大围陀论师”都在供养之列。而到了金刚乘时期,佛教和印度教更是难分难解,几乎是混沌一片了。那是后话。
第四,维护大乘佛教的最后努力。
佛教发展到《大日经》这个时期,即公元7世纪的时候,其在印度的颓势已经显露。学者们在研究玄奘巡礼印度佛教圣地的记载中得出了这一看法,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
这里要说的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既然是两个系统,如果按照“右道”和“左道”的说法,则《大日经》倾向于右道,而《金刚顶经》倾向于左道。
一方面,为了维护佛教的戒律《大日经》明确强调了不杀生、不食肉,也强调了不淫欲等。如卷六《学处品》讲菩萨戒,其中说道:“菩萨持不邪淫戒。若他所摄,自妻、自种族,标相所护,不发贪心,况复非道。二身交会,有余方便,随所应度,摄护众生。” 再如前面提到,《大日经》还主张远离髑髅、污秽等。这些都与旁门左道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为争取外道皈依佛门,《大日经》中采取了一些迎合与变通的做法。如一行《大日经疏》卷四所说,在曼荼罗选址以及画曼荼罗时,“但发心求五通持明仙道,或愿长寿成就世间种种悉地,亦可随彼情机而诱接之也。复次,有诸异学,深乐围陀火祠之法,愿生梵世,闻佛秘藏中亦有火天真言行,法旨趣甚深故,即从此门而入正法。复有奉事自在、毘纽那罗延、日、月尊等种种世天,若闻佛秘藏中亦有彼等诸天真言行法,乃至毘卢遮那大我之身,即便信受而入正法。或有志愿生三界诸天者,闻佛秘藏中,具有诸天乘真言行法,能令于无量世生彼天中,不复退堕终成第一义天,由此深心愿乐得入正法者,或有宗习世间五通仙法者,闻佛秘藏中具有迦叶、瞿昙大仙等种种真言,能令获得不思议神通,乃至如毘卢遮那住寿长远,彼便踊跃志求,得入正法。以如是等种种门故,佛说火神诸处皆可造漫荼罗也。偈云:‘如上之所说,或所意乐处,利益弟子故,当画漫荼罗’者,乃至求诸胜地,皆不能得,不可令此密教遂无所传,但随阿阇梨心所好乐,谓有利益之地,即可造漫荼罗也。”由这段文字所列的种种情况可知,为了“诱接”外道皈依正法,为了密教的传播,不仅在曼荼罗的选址上可以采取权变措施,即便是修法上也要多方借镜印度教。因此可以说,在面临印度教强大压力的情势下,《大日经》及真言乘的佛子们,为挽救佛教的颓势,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2011年岁末于京东太阳宫)
[1]中村元.密教经典及其他[M].东京:东京书籍,2004.
[2]黄心川.东方佛教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吕建福.中国密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宫坂宥胜,梅原猛,金冈秀友编.密教的历史[M].东京:春秋社,1981.
[5]松长友庆.密教的历史[M],京都:平乐寺书店,1974.
[6]叶少勇.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A].上海:中西书局,2011.
[7]吉田惠弘.胎藏界咒语解记[M].林光明,林胜仪译.台北:嘉丰出版社,2011.
[8]张保胜.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林光明等编.汉梵佛教语大辞典[M].台北:嘉丰出版社,2011.
[10]姚卫群:佛学概论[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Few Findings from Reading The Vairochana Sultra
Xue Ke-Qiao
TheVairochana SultraandAdamantine Pinnacle Sultrabelong to different systems, the former representing the Mantrayana and inclining towards the “Right Way” and latter the Mahayana and inclining towards the “Left Way”.On the one hand,The Vairochana Sultramaintains the Mahayana; on the other, it has been permeated by Hinduism in many ways.
The Vairochana Sultra;Buddhism Tantrism;Mantrayana;Garbha-Dhatu Mandala
I106
A
1005-7110(2012)04-0074-06
2012-03-22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研究中心课题“印度密教与中国神怪小说研究”(10JJD750002)的阶段性成果。
薛克翘(1945-),男,辽宁金县人,北京大学东方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印度文化与文学研究。
冯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