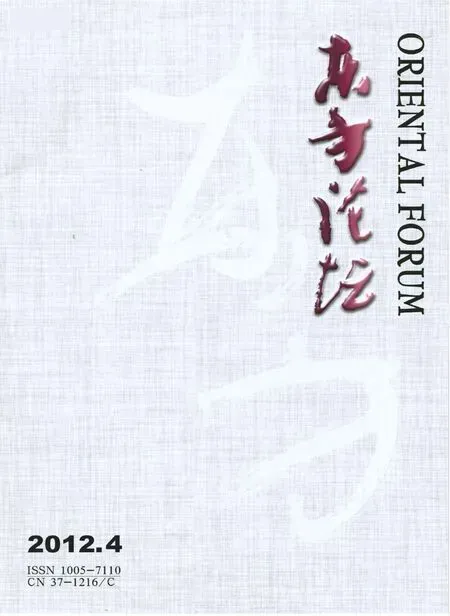近代自然法论者的自由观及其方法论局限
罗 朝 慧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近代自然法论者的自由观及其方法论局限
罗 朝 慧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17世纪以来的近代自然法论者如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和康德等,真正开始根据人自身内自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自由本性来解释和建构理性的政治共同体。然而由于他们静止地固执于某种单一的人类本性,或者自然的、或者道德的、或者理性的自由本性来认识和解释个人、国家及法律的实践准则,将个人自身内作为有机整体存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自由本性分离或对立起来,因而在理论或实践上造成一种自由排斥、僭越或压迫另外一种自由,在方法论上则造成事实、价值及逻辑三种必然性原则的相互对立和分离、或者相互混淆和僭越。
自然法论者;政治思想;自由观;方法论局限
真正从个人自身出发论证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必然性和现实性理性根基、建构政治社会及其法律和道德实践的价值准则,是从17世纪以来的近代自然法政治哲学开始的,如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和康德等,他们真正开始根据人自身内存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根本的存在本性来解释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而不再根据外在的自然或神灵,来建构国家及其法律实践原则的政治社会理论。尽管古代自然法包含着政治和法律实践公正无私的价值准则,包含着对人的精神与理性、自由与平等的尊重与承认,但是这种尊重和承认的基础或根据是来自外部自然或神灵的理性权威,从而个人自由与权利是从外面、并且是偶然性地得到承认和理解的,人对自身内在的精神或主体性自由本质并没有形成独立、自觉的自我意识。
一、霍布斯和洛克自然主义的自由观
霍布斯坚信自然科学原理和几何学推理对于人类政治生活领域的适用,他认为个人在经验世界中的理性意志及其自由活动,从其终极的合理性或价值必然性上是源于自然法则或上帝理性。在他看来,“人的自由……就是他在从事自己具有意志、欲望或意向的事情上不受阻碍。”[1](P163)“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1](P97)可见,他所讲的自由是从个人原始存在的利己天性出发的“自然”权利,即人在自然状态下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任个人的各种偏私、自傲、贪婪、复仇等等自然激情自由发挥的自由。这样,霍布斯就将自然法内蕴的自由和理性精神,经验地或唯物地解释为个人普遍的自然天性,即自我保全的利己天性,个人自由就是这种自然的普遍性利己天性不受阻碍地实现。因而,霍布斯所说的自由和权利,仅仅是个人满足自我保全之需求与利益出发的“自然的”权利或“自然的”自由,他所构建的国家和法律之责就在于保证所有个人的这种“自然”自由之实现时彼此间相安无事、互不侵害,保持一种外在的和平秩序。所以“在霍布斯那里,国家没有积极的功能,它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维护和平与秩序是利维坦得以建立的理由和存在的依据。利维坦是一个警察,而不是一个导师。”[2](P244)
然而,根据人的自然天性所建构的国家和法律,往往将其公民成员当作桀骜不驯、贪婪自私的自然性动物来管理,时时防范和压制个人的自然天性;同时,个人对国家也天然地存在恐惧、妒忌与仇恨。这导致无论在国家及其法律的政治共同体统治之下,还是在此之外的特殊性社会活动领域,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都难免处于“自然的” 强制与“自然的”特权压制之下。这种基于自然基础上建构的国家或政府与个人之间始终是相互敌意的、对抗的,从而这种外在强制下的统一也必然是偶然的和不稳定的。如果自由只是经验的和外在的,那么它必然是受强制的。因为自然的东西始终是个别性和排他性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直接的、敌意的对抗,故而自由主义者至今仍然将国家看作个体自由的大敌,国家与个人之间主要是基于自然需要满足及自我保全利益的契约或委托代理关系,淹没了公民与国家之间内在的本质同一,个人无论对自身还是对国家都只有一种自然的主观意识。正是由于“霍布斯将理性、自由、意志等人类精神的范畴归于自然力量的具体显示”[3],所以“霍布斯不能使理性从古典的自然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不能完成他所发起的摆脱自然的转变,不能建立一种基于主体创造性模式的政治哲学。”[4](P179)
如果说霍布斯以自然科学的理智必然性、以及几何推理方法的逻辑必然性,来建构自然法政治理论体系及其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权威。那么,洛克则并没有运用多少自然科学知识及严格的逻辑推理来建构和解释他的政治学说,而是更多地根据英国政治历史状况及其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实际上,洛克的政治学说基本上是依据一种对几何学自明公理的理性确信,以及对人性尊严、自由和道德的直接信念,同时还夹杂着一种对《圣经》权威的信仰,这三种因素成为洛克构建其政治自由理论的基础与根据。洛克与霍布斯一样,仍然坚持个人自我保全之利己天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主张个人所有权绝对至上原则,认为个体自由及其财产所有权是任何人不可干预的,国家及其法律只是一种保护个人生命、自由与财产安全的工具主义理性实体。霍布斯和洛克基于个人原始既定的自然利己天性来解释和建构的理性政治共同体或政治社会,可以说是相当于后来黑格尔所论证的市民社会,即建立在需要体系之上的外部国家或契约式法理国家,即任由个人尽情施展自己在自然和主观理智方面的特殊性与任意性,最大化他们自己的财富积累,国家只是保护这种特殊性需要无障碍地得到满足和实现的必要工具、条件。
二、休谟对自然法政治体系的方法论批判
休谟率先批判了霍布斯和洛克自然法政治体系的方法论缺陷,指出其推理的理性或逻辑必然与事实的和价值的必然相混淆。休谟认为自然法政治学说体系中的理性原则包含或混淆了三种不同的意义和用法:第一,严格意义的演绎或推理;第二,经验关系或自然事实的必然性;第三,关于权利、公正及正义的价值必然性。休谟认为后两类作用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理性,它们都包含着无法加以证明的因素。然而,在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政治体系中,理性既是严格的演绎或推理,又充当了经验事实或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还充当了道德或价值领域的必然性。
在休谟看来,关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和道德领域的必然性知识或价值标准,并不能由理性主义的逻辑必然性、或自然事实的因果必然性来决定,亦即不能把政治社会领域的必然性知识简单地还原为形式命题的逻辑推理。因为“必然性是有规则的、确定的,人类行为是不规则的、不确定的。因此,人类行为并非必然发生的。”[5](P403)所以人们的价值判断并不以理性为真理必然性依据,道德或价值的判断将取决于人们的特殊习惯和情感感受。休谟以观念的习惯性联想为基础,否定并代替了数学或演绎推理的逻辑理性在因果关系和价值观念上的运用,认为所谓的因果关系与权利、自由和公正等价值观念,与人们的理智能力是根本无关的,而是源于人类的习惯性联想,以及对快乐和痛苦的情绪感受,是人们长期活动而约定俗成的传统、习俗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普遍性观念。因此,道德的根源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根本不可能由推理得出道德的结论,“理性决不能单独成为任何有意志行为的动机;其次,在指导意志方面,理性也决不能反对情感。”[5](P413)
休谟要求将理性与自然(事实)和道德(价值)必然性相区分,第一次提出关于人自身精神世界的政治学、伦理学及法学等人类社会科学领域的必然性知识和原则,不能用传统的先验理性或逻辑主义的理性思维来解释,并第一次尝试根据人自身自然的和原始的倾向,诉诸个人的真实感觉、情感、感受,以及民族习俗和事物自身的功用,作为道德或价值判断的必然性来源与依据。这样,休谟就将政治和道德领域中理论知识与实践原则的必然性,置于个人直接的主观经验、感受、习惯以及事物本身的实际效用中,否认道德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可以说“休谟的哲学给了自然权力以致命的一击,并且取消了对价值进行理性判断的可能性。因而休谟的理论被描述为向政治哲学的存在本身发出了挑战,而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挑战。”[6](P617)同时,休谟也由此洞察到了将经验主义在人类社会科学领域贯彻到底的结果,就是取消理性在人类精神和道德领域必然性知识解释的科学地位,从而必然走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结局。实际上,休谟对自然法的理性批判与改造,只是将理性逐出了自然和道德领域必然性知识的解释地位,主张个人自身自然情感、主观感觉、以及原始倾向和功利目的的真实性价值地位。然而,他仍然将自然和道德的必然性相混淆,以个人的自然感觉和原始倾向、以及事物功效,来代替或解释道德与价值的必然性,仍然加剧了自然与道德、或理性与道德的隔阂和矛盾。
三、卢梭和康德道德主义的自由观
1.卢梭基于自然道德的浪漫主义自由
紧随休谟之后,卢梭继续发起了对自然法政治体系中科学理性主义的攻击,继续求索对于人自身的自由精神及道德本性的认识与理解,即从精神和道德方面研究人,认为基于个人自然主义利己天性解释的自由与权利,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政治和法律实践原则,严重损害了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天然的自由本性。卢梭感慨“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7](P4),他认为这正是因为人类理智教育和法律之下的文明社会,破坏了人在自然状态下那种自然同自由或自然同精神的直接同一与和谐,使人的自然本性与精神和道德相分离。而且随着理智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进步,人们的自然情欲或私人物欲湮没了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自由天性。所以,卢梭将理智知识和科学技术以及在此之上建立的法律,看作是束缚人的精神和道德自由的枷锁。 “社会和法律,给弱者戴上了新的镣铐,使富人获得了新的权力,并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天然的自由,制定了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现象的法律,把巧取豪夺的行径变成一种不可改变的权利,此外还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终日劳苦,陷于奴役和贫困的境地。”[8](P101)
根据卢梭,如果个人行为及政治和法律实践原则的价值标准,皆由自然科学的理智知识、以及基于个人利己天性的实用主义功利或效用来决定,那么这不仅使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相互之间缺乏内在的情感和道德统一的基础。人们对于国家的服从不过是出于私人利益和情欲的满足,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因此也不过是个人对自己自然情欲和私人利益的忠诚。这样,作为人类政治组织和最高权力的国家,便失去了它自身的神圣性质与独立尊严,个人对国家忠诚与服从的义务,因缺乏内在的精神和情感纽带,而变得并非神圣的和绝对的,国家和法律缺乏道德与伦理的必然性基础。因此,卢梭从人自然的善感或道德天性出发,根据“社会公约”形式和“公意”原则,试图建立一个道德人格的政治联合体,将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同一、公共意志与个人意志同一,这种同一性规定着个人的理性和意志。然而,卢梭并没有清楚地界定作为普遍意志的“公意”与个人确定性的自由意志。他的“公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道德规定,与个人理性意志的规定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循环论证。从人自然的道德天性和自由意志出发建立“公意”的政治联合体;同时又根据这个作为道德人格的“公意”政治共同体,规定个人的理性意志。这样,个人理性意志与“公意”共同体就成为直接同一的,它们都将私人利益或私有财产以及个人的特殊目的和意志排除在外,个人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就成了为道德而道德的统一,个人自然需要和主观目的的特殊性被排除在外。
卢梭在清除掉个人特殊的和主观的自然需要及自私的物质利益之后,在自然的道德原则基础上,将作为国家及其法律的“公意”与个人自由意志直接同一起来,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这无疑反映了卢梭浪漫主义的政治理想。然而,“公意”与个人意志的直接同一,必将造成两种相对的局面:一方面,“公意”名义下的道德共同体——国家或政府及其立法的普遍意志,走向专制性的强迫,压制个人自由的自然性、主观性和特殊性。正如卢梭所言:“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7](P24-25)。另一方面,个人意志以“公意”或普遍意志的名义,拥有绝对的否定性地位和自由,他可以否定一切现存的理性权威或实体性权力组织,反对一切特殊形态的权力或权利实体性存在。
如果说霍布斯和洛克及其追随者,主要把自由看作是基于个人自然的利己天性,及其满足需要、占有财富的理智活动,败坏了人在精神方面的自由和道德;那么卢梭则率先把自由与人的精神和道德联系起来,把自由看作内在于人精神中的东西。但是卢梭只把自由视作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自然天性,即一种心灵的直觉理性,而把个人特殊的自然欲求和理智能力排除在道德主义的自由之外。美国政治思想史学者萨拜因(George J.Sabine)认为卢梭“只是抨击了自然法体系一个有限的局部,即抨击人为地把社会仅仅视为保障个人财富的工具和把人性仅仅视为盘算利益能力的观点”[9](P670),他将道德或“心灵的理性”与自然以及“头脑的理性”对立起来,就有些走得过远了[9](P656)。卢梭基于自然主义道德原则建立的浪漫主义自由政治理想,排斥个人利己的自然需求及私有财产,否定个人特殊性和主观性自由,这实际上正是对个人自然必然性自由本性的压制,这本身也是不道德的、非理性的和不自由的,因为人的精神和道德与其自然的生命、身体及其私人的、特殊的物质需要,原本就是不可分离的有机统一体。
2.康德理性主义的道德自由
休谟批判自然法理性对于自然领域和道德领域必然性知识的僭越,反对先天的自然法理性准则以及纯粹先验的理性思维对于自然和道德必然性的说明与解释,由此打断了康德理性独断论的迷梦。卢梭注意到个人自然欲求满足的功利计算或理智理性,以及自然法政治体系对于个人利益和私有财产权利的优先承认,对于人类纯粹自然的精神和道德天性的破坏,因而主张自由意志和道德至上的国家原则,这深深鼓舞了康德对人类自由意志与道德法则的沉思。
实际上,无论是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主义自由观、休谟怀疑主义的理性批判,还是卢梭的自然主义道德,都没能真正认识和了解人自身的精神及其自由本性,他们只是先天地或直觉地知道自由。正如康德所指出的,“自由是我们先天地知道其可能性却仍然不理解的唯一理念,因为它是我们所知道的道德法则的条件。”[10](P2)康德指出,自由作为一种先天意识或观念,是道德法则的必然条件,不能从自然和经验现象中推论出来,因为那种经验证明和推论的结果,必然导致自然与道德,或理性与道德的矛盾。所以,康德将先天的自由和道德概念归入实践理性,而将自然事实或经验现象的认知归入理论理性适用范围,同时区分人的自然本性和道德本性,即人既是感性世界的一员,具有服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同时,人作为精神的理性存在者,属于知性世界的一员,他是自由的,服从绝对必然性的道德法则。“当我们称某人为自由的时候,与当我们认为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要服从于自然规律的时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11](P149)康德所规定和解释的自由完全属于个人内在的理性精神和道德领域,主张自由与道德及理性三者是同一的,认为这是任何外在权威和个人都不可侵犯的人之为人的道德尊严。“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对自己和所有其他人,从不应该只当作手段,而应该在任何情况下,也当作其自身即是目的。[11](P95)根据康德纯粹理性的道德法则,每个人都根据自己自身内在的理性意志行为,这就是实践理性,就是自由,就是道德律,任何他人、社会和国家及其法律都必须尊重个人这种理性和自由的主体性地位与尊严,否则就是不道德的、非理性的。
如果说,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都没有将个人自由和权利与人类精神自身的理性本质同一起来,即没有真正将“普遍性”的人的概念纳入国家的伦理政治制度之中,那么黑格尔认为康德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第一次提出了个人权利和义务与人类理性精神或自由意志相同一的等式,第一次提出了所有人拥有普遍的做人尊严、自由资格及其普遍平等的权利。因此,康德“这个原则的建立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即认自由为人所赖以旋转的枢纽,并认自由为最后的顶点,再也不能强加任何东西在它上面。所以人不能承认任何违反他的自由的东西,他不能承认任何权威。”[12](P289)斯特劳斯也认为,“康德将人的意志自由的道德法则作为政治实践的基础,以捍卫人的理性尊严和自由意志,这无疑是具有伟大的积极意义的。”[6](P673)康德在区分个人的自然与自由本性的基础上,严格区分了法权领域与道德领域,把道德、义务完全置于个人的主观意志领域,即完全依靠一种道德上的个人自律或主观自由,而将权利完全置于强制性的法制领域,这样国家和法律可能因此丧失精神性的伦理要素,而仅仅成为控制和管理个人权利领域的外在权威与理性工具。康德将个人自由和理性的绝对本质,停留在道德的“应当”或自我的道德良心,亦即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自我确信或信念当中。这就是说,我们通过康德,仅仅是主观上知道、意识到并确信普遍性的善和义务,但是对于知道什么、确信什么以及应该尽些什么义务等等,并没有客观普遍性的牢固基础或理性根据,而是一切依赖于个人的道德自律或道德良心的主观判断,即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普遍性理智知识上、道德或义务的应当上。然而,黑格尔认为“一个人必须做些什么,应该尽些什么义务,才能成为有德的人,这在伦理性的共同体中是容易谈出的:他只须做在他的环境中所已指出的、明确的和他所熟知的事就行了。正直是在法律上和伦理上对他要求的普遍物。”[13](P168)显然,康德理性主义道德自由的政治理想缺乏客观的伦理要素,它对于个人自由的现实性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改观,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自律、道德良知、慈善之心来达到个体权利的真正实现是远远不够的。
如同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法政治体系那样,科学主义理性或逻辑主义理性不能代替或僭越事实的和道德或价值的必然,卢梭和康德的纯粹道德,无论自然主义道德还是理性主义道德,同样不能排斥或吞没自然或事实的必然。可以说,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和康德等近代自然法论者,对于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解释、以及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建构,其理论内容及其论证方法,始终徘徊于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原则的混淆与僭越、或者分离与排斥的困境之中。它们将人自身内作为整体存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必然性自由本性分离开来或对立起来,固执于人身上直接存在着的某种单一的、静止不变的普遍性本质,如个人自然的利己天性,或者是自然的道德情感,或者是先天的道德理性,因而无论从自然还是精神本性出发解释和建构的政治体系,或多或少都会造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造成一种自由排斥、僭越或湮没另一种自由。
对此,美国政治思想史学者萨拜因(George H.Sabine)提出:“如果能把理性、事实和价值三者融为一体,或者说倘若能把理性解释为同时包含三者,那么一种新的逻辑、新的形而上学以及对绝对价值的新辩护也许可能产生。这就是哲学在康德的指引下并最完整地体现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所选择的道路”[9](P679)。黑格尔之所以主张将三者历史地和逻辑地综合统一起来,并不是按照某种外在的既定规则或技术方法,而是三者本身事实上就是内在地统一于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自由和理性本性之中,人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根本存在本性正是他自身自由和理性精神的外在化和具体化,国家和法的伦理政治世界正是人类为实现自身三种根本自由本性或存在方式而不断认识和实践改造的创造物。黑格尔坚持了自由和理性这两个属于现代社会人类最基本的自我意识,并将它作为现代政治国家建立的基本原则,认为作为世界真理的“绝对精神”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中实现为人类自由本质的全面实现。关于法和伦理政治世界认知和解释的理性、事实和价值三种方法论的必然性原则,事实上正是源于人类自身自由和理性精神不断实现、证明和显现自身的永恒运动,亦即人类寻求自身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及客观权利在法和伦理政治世界中获得全面发展的历史实践与创造活动。简言之,法和伦理政治世界的真理和正义,在于人类自身内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存在本性及其客观权利的实现,从而对于真理和正义的理性认知及论证方法,便是事实、价值和理性三种必然性原则的历史性辩证统一,从而不可能再仅仅坚持某种单一静止的必然性原则或自由本性。政治世界的真理之知,即是对人类自身的真理之知。黑格尔“这一新的理性以空前的概括性、普遍性和抽象性,不仅重聚逻辑、自然和道德于一体,而且集社会、历史和传统、国家、政府与权利于一身,这就是占据19世纪政治哲学重要地位的新的理性主义”[14]。
[1][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高建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三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3]Arbis B.Collins (ed.), Introduction to Hegel On the Modern Worl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xix.
[4]Andrew Buchwalter, Hegel, Hobbes, Kant, and the Scienticizatio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Arbis B.Collins (ed.), Hegel On the Modern Worl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5][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下)[M].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M].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0][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序言,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M].孙少伟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1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4]张桂琳.理性与传统:谁是权利的基础——伯克政治哲学解读[J].政治学研究,2002,(2).
On the Ideas of Freedom and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 of Hobbes,Locke, Rousseau and Kant
LUO Chao-hui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s:It is such modern natural-law theorists as Hobbes, Locke, Rousseau and Kant since the 1600s who constructed political society and its law and moral practical principles.They interpreted the necessity and actuality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right on the basis of human nature such as natural, moral and rational freedom.However, they realized and interpreted practical behavioral principles or right foundation of individual, state and law only according to Metaphysic reason principle, i.e., fixedly insisting on some specific human nature, or natural, moral or reasonable nature.They made the three necessary free natures like nature, moral and reason which exist in human nature as a whole organism separate or opposite to each other, lea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one freedom excluding the other freedom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and the situation of fact, value and logical reason, the three necessity principles, opposite, separate, mixed up or arrogating to one another methodologically.
natural law theorist; political thought; idea of freedom;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
D033.3
A
1005-7110(2012)04-0046-06
2012-05-28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人类自然、道德和理性自由本性及权利的现实性——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研究》),立项编号为:11XJC810001。
罗朝慧(1974-),女,四川泸州人,法学博士,副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
侯德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