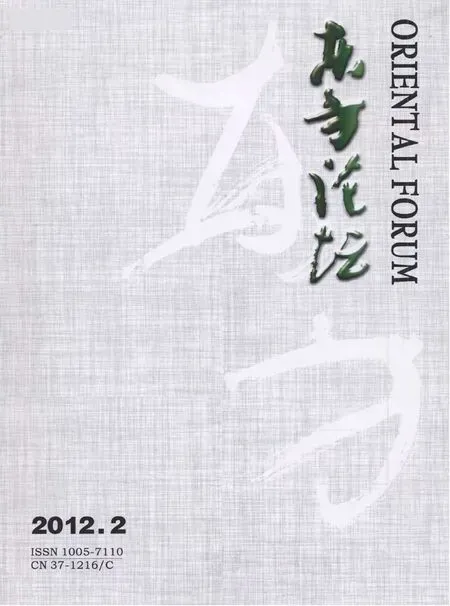美国产品责任法上的售后义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产品责任法上的售后义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董 春 华
(华东政法大学 科学研究院,上海200042)
生产商售后义务是产品责任法中的一项新制度,它起源于美国。该制度在美国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它对所包含的售后警告和售后召回产品义务的具体判断都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标准。对生产商售后义务与工艺水平抗辩、产品改进的特殊关系,以及违反售后义务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上,美国司法判决都已经比较完善。这些经验对我国当下《侵权责任法》第46条售后义务条款的实施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售后警告义务;售后召回产品的义务;工艺水平抗辩;归责原则
售后义务并非指销售者的售后服务,而是指产品投入流通后,产品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产品存在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损害危险,经营者应当采取警示或者召回措施以避免损害。若未采取相关措施或者采取措施不利造成损害,仍然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的售后行为已经成为现代产品责任法中越来越重要的事项。美国产品责任法最先发展了售后义务理论,从1959年的Comstock v. General Motors Corp.案至今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在其著名的《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 (第三版)①《法律重述》是美国法律学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并非立法文件,是对美国现存法律的展示,也有超前的意义。它集法官、律师和教授、学者等法律精英的智慧于一身,在美国法律届赢得了很高的权威。《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是侵权法的第三次重述,在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中占有重要地位,于1997年5月通过。以下简称《重述》(第三版)。中确认了司法中发展并扩张的售后义务。中国《侵权责任法》第46条也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售后义务,对于该制度如何实施,如何处理其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关系,是当下我国产品责任法亟待解决的问题。故研究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售后义务,探究其渊源、理论基础及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普通法中的售后义务之发展
在美国,售后产品责任诉讼已并不新奇。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在50多年前就确认,生产商警告消费者产品危险的义务在产品出售之后并未必然结束。20世纪七八十代,一些法院开始承认售后警告义务,特别是在一些危险药品案件中。20世纪90年代,法院和立法机关已经开始比较经常地适用售后警告义务,还扩大售后义务的范畴,不仅要求生产商售后警告义务,还要求生产商售后召回产品的义务,但普通法的召回义务始终未普遍建立。
(一)早期售后义务在普通法中的发展
Comstock v. General Motors Corp.②Comstock v. General Motors Corp., 99 N.W.2d 627(Mich. 1959).案一般被认为是售后警告义务具有开创意义的案例,法院和评论家都将该案作为售后警告义务的起源。该案中,通用公司在1953年款别克车投入流通后不久,得知其刹车存在问题。某技工被该款车撞了之后提起诉讼。虽然生产商警告了经销商,密歇根州最高法院仍然确定,当发现汽车刹车潜在危险时,生产商有额外义务采取合理手段警告53别克的购买者。法院推理道,当存在危及生命的潜在缺陷,若生产商在产品被投入流通后不久发现了该缺陷,他就有义务提出警告。
在Noel v. United Aircraft Corp.①Noel v. United Aircraft Corp., 342 F.2d 232(3d Cir. 1964).案中,飞机生产商供应螺旋桨装置设计,他知道该设计已经有过10起退耦(decoupling)、起火或者分离事故发生,有57起发动机起火或者不启动状况。第三巡回上诉法院认定,被告生产商因未警告可利用的新安全设备而违反持续性义务。故生产商有持续性义务改善产品的安全。
在4年后的Braniff Airways Inc. v. Curtis-Wright Corp.②Braniff Airways, Inc. v. Curtis-Wright Corp., 411 F.2d 451(2d Cir. 1969).案中,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明确拒绝适用Noel案规则,但承认,当生产商发现产品存在危险时,生产商有维修危险产品的义务。
在1979年的Bell Helicopter v. Bradshaw③Bell Helicopter v. Bradshaw, 594 S.W.2d 519(Tex. Civ. App. 1979).案中,德克萨斯州民事上诉法院利用了一个相对不同的原则进行判决,即生产商自愿承担改善产品的义务,会导致承担提供完全改进的义务。贝尔直升机公司开发了一种新的桨片系统,该系统比先前系统需要更少的维护,它通知了所有的购买者新系统的可使用性。法院认为,贝尔公司的行为不充分,不能满足它的法律义务。该义务要求公司强制撤回旧桨片系统,或者合理地预测并告知使用者危险的严重性,应该实施撤回。法院判决,一旦贝尔公司制造出一个更安全的设计,生产商就对直升机使用者产生义务,以阻止他们继续使用旧系统。
Comstock案后的这三个早期扩大生产商售后义务的案例涉及的被告都属于航空领域。因飞机部件很小的缺陷都会带来严重死亡,航空领域对人类伤害的潜力异乎寻常。这说明,安全是法院扩大生产商售后义务的强大动力。[1](P1036)与Comstock案相比,Cover v. Cohen④Cover v. Cohen,461 N.E.2d 864(N.Y. 1984).案在适用售后义务上使用相对较自由的方式,扩大了售后警告的义务,也发展了售后义务。首先,Comstock案为在出售前就已经存在的潜在缺陷适用责任。而Cover案表明,即使产品销售时是合理安全的,生产商仍然可能负责任。既定缺陷的存在并非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其次,Comstock案仅涉及生产商,Cover案明确表示包括经销商和零售商。通过这种方式,Cover案通过让产品链上所有潜在主体负责任,来追寻传统产品责任理论。再次,Comstock案要求生产商投入流通后不久发现缺陷,Cover案并未明确限制生产商义务产生的时间。[2](P21)
(二)《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第三版)通过后主要法域对售后义务的态度
对判例的考察表明,少数法院已经通过《重述》(第三版)以过失为基础的售后警告义务,并依据第10节来确定义务何时产生;有些法院在通过《重述》(第三版)之前就已经采纳了第10节的理性生产商标准;在采纳了《重述》(第三版)后,有些法院已经确认售后警告的义务,却并未提到《重述》;有些法院明确拒绝《重述》(第三版),而有些法院在未提及《重述》(第三版)的情况下拒绝售后义务。[3](P974)以下考察部分州及部分联邦法院的具体情况。
1.主要州适用售后义务的典型案例。1999年早期,爱荷华州最高法院在Lovick v. Wil-Rich⑤Lovick v. Wil-Rich,588 N.W.2d 688 (Iowa 1999).案中采纳了《重述》(第三版)与生产商售后警告义务相关的第10节。法院认为,虽然售后警告的义务扎根于一般过失原则中,在考虑售后警告义务的范畴和性质时,有些区别就显得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生产商警告使用者的义务在产品出售之时已经发生变化,生产者对产品不再有控制权。最有争议的是,产品出售之后生产商获悉产品缺陷,在分析生产商行为是否合适时,是否有必要考虑不同的要件。该法院认为,初审法院给陪审团一般过失的指示,对如何衡量生产商售后行为的合理性不能给予足够的指导,陪审团必须被指导考虑那些使提供售后警告成为过分负担和不切实际的因素。
Lewis v. Ariens Company⑥Lewis v. Ariens Company, 751 N.E.2d 862, 864 (Mass. 2001).案中,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采纳了《重述》(第三版)提出的关于生产商持续警告消费者产品售后发现的风险或者危险的原则。该法院认为,第10节的原则是马萨诸塞州售后警告义务规则逻辑和平衡的体现。
路易斯安纳州上诉法院发现,《路易斯安纳州产品责任法》有如下规定:产品脱离生产者控制后,生产者获知可能导致伤害或危险的产品特性,或者作为理性谨慎生产商而行为的人获知该种信息,要为未尽合理注意向使用者和产品操作者提供该种危险特性提供足够警告而负责任。
有些法院采纳了售后警告义务,但范畴有限,生产商只有义务警告那些产品出售时即存在但那时并未合理发现的缺陷。当生产商发现或者应该发现这样的潜在风险,即发生警告该风险的义务。[3](P982-983)
2.联邦法院发展售后义务的典型案例。在Robinson v. Brandtjen & Kluge, Inc.①Robinson v. Brandtjen & Kluge, Inc., 500 F.3d 691 (8th Cir. 2007).案中,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再次确认了它先前的判决,在那一判决中该法院确认,南达科他州法律允许因为过失售后警告义务而获得赔偿。该法院特别提到第10节并下结论,生产商在本案中并未违反售后警告义务。该案涉及20世纪40年代出售的印刷机,50多年以后受害人的雇主才获得该印刷机。之所以认定该案不存在售后警告义务,主要是考虑漫长的时间段,生产商很难找到那些需要警告的使用者。
联邦地区法院在Brown v. Crown Equipment Corp.②Brown v. Crown Equipment Corp., 460 F. Supp. 2d 188 (D. Me. 2006).案中下结论,缅因州将确认以过失为基础的售后警告义务,在出售产品时,生产商的产品并不具有缺陷,主要是因为使用者环境的改变造成后来的危险。它随后确认,在陪审团做出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后、反对被告提出的简易判决的观点时,它的观点特别依据第10节。该案中,原告在仓库中操作产于1989年的叉车时死亡。1995年,生产商得知,很多仓库中的新支架设计会置毫无保护的操作者于风险之中,并严重伤害操作者。生产商开发了一个叉车升级的配套元件,提高了操作者的靠背高度,能减少风险。但生产商并未将此信息告知叉车的所有者——原告的雇主。上诉中,美国上诉第一巡回法院认为,其他法域不同意该问题,缅因州最高司法法院也未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该争点应提交给缅因州法院证实。在反馈中,缅因州最高司法法院认为,“在有限情形下,可以认定对非直接购买者的售后警告义务,但我们未采纳、现在也不会采纳第10节”。该法院继续分析道,在缅因州过失法律的一般普通法的原则之下,生产商在本案事实之下负有对原告的售后警告义务。
二、《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第三版)对售后义务的规定
在美国,售后义务已经通过法院判例和立法而得以扩大。《重述》(第三版)确认了这种扩张,某种程度上扩大了生产商普通法上的售后责任。生产商必须建立合适的售后监控系统和委员会,培训能够收集信息决定是否采取售后行动的人员。[3](P986)在制定《重述》过程中,美国法律学会倾向于原告的成员希望保留售后义务部分,而倾向于被告的成员希望删除或者严重删除该部分。《侵权法重述》(第二版)402A条款并不包含售后义务的条款,生产商只需要为投入流通时存在的缺陷负责任。《重述》(第三版)明确了规定生产商售后警告和召回产品的义务。
(一)对售后警告义务的规定及其判断标准
1.对售后义务的规定。《重述》(第三版)起草人考察了1997年全美国的案例,认为判例法和常识已经足够支持规定“售后警告义务”。该节明确规定:(a)如果销售者未能在产品销售或者分销之后提出警示,而一个在销售者地位的符合理性的人应该会提出这样的警示,因这样的不作为而导致他人财产或人身伤害的,从事销售或者其他分销产品的商业行为者,应承担民事责任。(b)在下列情形下,一个符合理性的处于销售者地位的人,应该会提出警示:(1)销售者知道或者理应知道产品对于人身或财产具有重大的伤害风险;而且(2)那些可能应该被提供警示的人能够确定,并且可以推断他们对于该伤害风险并不知悉;而且(3)警示能够有效地传递给那些可能应该被提供警示的人,并且他们能够在收到警示之后采取相应行动;并且(4)伤害的风险足够大,因而有必要为提供这样的警示付出必要的费用成本。[5](P272-273)
2.判断售后警告义务的标准。普通法已经发展了一套标准来衡量并确定在每一特定案件中是否存在生产商售后义务及其性质为何。这些因素包括:
(1)危险的程度。危险的严重程度是法院确定是否存在售后义务的重要依据。通常情况下,危险的程度越高,生产商承担责任的可能性越大。
(2)市场的大小和性质。在确定是否存在售后义务及其性质时,大众消费(mass-marketed)产品的生产商很明显不能与出卖特殊产品且市场有限的生产商适用同样的标准。后者比前者有更有利的地位去定位并通知产品的现在使用者。有些法院已经指出,日用品生产商应该从法律上被排除该种售后义务。
(3)与产品使用者是否存在持续性关系。很多案例中,生产者是否与产品使用者存在持续性关系是确定是否追究未提供售后警告责任的关键因素。如生产商在出售产品之后,仍然对产品使用者提供售后服务,或者继续向该产品使用者提供产品等。对前者的责任要求更高,因为生产商不仅与产品使用者存在特殊关系,而且与他出售的产品也存在“密切”联系。[6]
(4)获得危险信息的途径。在衡量生产商售后警告义务时,确定生产商是从工艺的新发展中获得信息,还是从危险事故的发生或投诉获得信息,这至关重要。法院一般不情愿将持续通知消费者工艺进步的义务强加给生产商。
(5)产品使用者是否可被识别。确认有售后警告的义务后,警告谁就成为重要问题。警告谁的问题要根据每个案例的事实情况来确定。《重述》(第三版)第10节也要求证明,应该向其作售后警告的人们,他们在售后义务产生之前是否是可被识别的。这些特别要求可依据:产品的类型、出售零部件的数目、潜在使用者的数目、记录的可能性以及追踪产品使用者可以采取的措施等。评注e阐明,当记录并不能识别消费者,售后义务将不会产生。
(二)对召回产品义务的规定及其评价
1. 对召回产品义务的规定。《重述》(第三版)第11节规定,销售商或分销商不需要为未召回产品而负责任,除非成文法或者法规要求,或者即便销售商或分销商自愿承担召回产品的义务,但存在过失。“凡从事产品销售或者分销商业经营活动,在下列情形下,应对销售者未能在产品出售或分销后追回该产品从而导致的人身或财产损害承担责任:(a)(1)依据成文法或者行政法规所颁发的政府命令,具体要求销售者或分销者追回该产品;或者(2)在没有(a)(1)追回要求的情况下,销售者或分销者主动决定追回该产品;而且(b)销售者或分销者未能在追回产品的过程中合理谨慎地行事。”[5](P285-286)
规定第11节的主要目的是明确第10节并不包含召回产品的义务。这一受到限制的义务很大程度上以政府指令为依据,要求生产商召回产品。不幸的是,第11节引进了“行善人原则”,承担救助义务之人的行为必须合理,不使将被救助者陷入更糟糕的境地。[7](P35)若他们采取的自愿召回措施存在过失,要负责任。
2.售后召回产品义务之评价。售后召回产品义务既具有公法性质也有私法性质。召回产品的义务具有私法属性,是侵权法上的义务,并非通过合同当事人之间进行约定。违反售后召回产品的义务不仅可能导致民事上的赔偿责任,还有可能导致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故美国法院及行政机关都认可,售后召回产品的义务一般不属于普通法上的义务,由行政机关通过国会立法、法规进行规定。虽然原告的律师努力扩大这一义务适用的范畴,很多法院都拒绝确认召回或者撤回产品的普通法义务,认定其为政府管理的领域。①Stranger v. Smith & Nephew, Inc., 401 F. Supp. 2d 974,982(E.D.Mo.2005).
虽然《重述》(第三版)规定了售后召回产品之义务,但正是这样的规定,巧妙地拒绝了普通法上召回产品的义务,虽然出售者可能承担召回义务或者政府或者行政机构强制该义务。[2](P78)在拒绝普通法上的召回义务时,它承认召回给生产商施加了的负担,政府机构最合适来检验与召回相关的争点。伊利诺斯州上诉法院曾根据第11节支持自己判决拒绝普通法上追回产品的义务。②Modelski v. Navistar Int'l Transp. Corp., 707 N.E.2d 239, 247 (Ill. App. Ct. 1999).
但第11节所认定的责任原则是不公平的,也是很糟糕的政策。如果生产商或者分销商自愿召回产品,召回行为存在过失,会导致承担责任。理性的生产商因此不可能自愿召回产品,该节实际上阻碍了自愿召回的发生。召回产品的前提是产品存在缺陷,而召回产品的行为,并不必然带来承担普通法上的赔偿责任。在美国,有些产品的召回可能完全出于环保考虑。如受害人在诉讼中主张,导致他伤害的产品,此前是政府强制召回的产品,这也不必然导致该生产商承担普通法上的赔偿责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仍然根据传统产品责任法中对产品缺陷的判断,而非政府指令。
三、售后义务与工艺水平的抗辩
1.售后义务与工艺水平的抗辩。工艺水平的抗辩是指产品投入流通时,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不能发现产品存在的缺陷,生产商可在诉讼中主张免责。有些国家称之为发展风险的抗辩。售后义务的宗旨是要求生产商在产品投入流通后,跟踪产品的安全状况。若随后通过一些途径发现产品具有危险性,生产商应该采取措施防止或减少危害的发生。故当售后义务与工艺水平抗辩相遇时,会出现两种情况:售后义务击败了工艺水平抗辩,生产商依然承担赔偿责任;售后义务责任不成立,生产商不承担赔偿责任。二者看似非此即彼,存在冲突。
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受害人起诉后,他在完成一般产品责任法中所有的举证责任后,生产商仍可提出工艺水平的抗辩。若受害人主张生产商要承担违反售后义务的致害责任,受害人要进行举证。虽然法律规定了售后义务,但何时需要采取警告或者召回产品的措施,用何种标准来判断,应该由法官在审判中进行判断。因此,受害人不仅要证明生产商有采取警告或者召回产品的必要性,还要证明生产商应采取而未采取该种措施,或采取该种措施不利,由此导致伤害。若受害人举证成功,他不仅可以击败生产商工艺水平的抗辩,还可以获得赔偿。因此,售后义务并不必然导致工艺水平抗辩的无效。
在美国,一些州虽然在成文法中认可了生产商工艺水平的抗辩,但通常并不明确提出二者的冲突。如作为近期产品责任改革立法的一部分,密歇根州已经制定了工艺水平抗辩的立法,阻止生产商或者销售者为未提供警告而负责任。除非原告能够证明,根据科学、技术或者医学信息,在特定产品部件脱离生产商控制时,生产商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伤害的风险。然而,立法明确规定,这一抗辩并不影响,在产品脱离生产商或者销售者的控制后,适用合理注意的义务,基本上确认Comstock案关于潜在缺陷规则的合理性。
但爱荷华州立法机关于1986年制定立法规定了产品责任中工艺水平的抗辩,规定“本节不能减少警告知悉缺陷或危险状况的义务,不减轻未提供警告的责任。”当然,有些法域因为成文法中规定了工艺水平的抗辩,提出不承认售后义务的合理性,拒绝给受害人以赔偿。
美国产品责任法中,只有在过失侵权之诉中,被告才被赋予“工艺水平”之抗辩的权利,即对于产品投入流通时的工艺水平不能发现的缺陷、或虽已发现却无法以现有技术消除的危险,生产商可主张免责。这类诉讼中受害人可以获得巨额惩罚性赔偿,前提是他们能够通过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被告的行为非常不合理、粗鲁或恶劣。
2.售后义务与产品安全改进。与工艺水平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产品安全改进是否会导致售后义务的发生。美国大多数法院认为,当初始产品设计和生产都合理时,就不存在告知顾客产品改进的义务。到目前为止,少数法院仅仅在特定事实情况下要求生产商告知产品使用者安全改进的义务。多数法院包括密歇根州上诉法院,都已经拒绝要求生产商给产品使用者提供与安全有关的工艺方面的更新。这些法院通常都强调,确认这种义务会阻碍生产商努力改善设计的安全,担心他们有义务寻找并通知现在的产品使用者每一个新的改进。如在Lynch v. McStome and Linsoln Plaza Associates①Lynch v. McStome and Linsoln Plaza Associates,548 A.2d 1276(Pa. Super. Ct. 1988)案中,宾夕法尼亚州高级法院判决,产品出售时不存在缺陷,就不存在售后警告的义务。原告因乘坐的电梯突然停止而受到伤害,对有利于被告的陪审团裁决提起上诉,主张她应该被允许引进证据证明,生产商并未通知电梯所有人,他们已将新电梯制动系统使用于新电梯,它本可以阻止突然的停止。但法院判决,如果产品在出售时没有缺陷,技术的进步不会导致售后义务的发生。因此,法院通常对涉及生产商是否知悉产品危险时,是因为产品安全设计的改进,还是通过伤害或死亡报告,抑或是消费者投诉而获得,后者通常更容易导致生产商负责任。只有很少数法院要求生产商提供工艺进步的信息。
具体来说,虽然售后警告的性质和范畴可能在不同法域有很大不同,但都不应该包括警告工艺进步的义务。适用这样的责任是给生产商施加不合理的负担,会阻碍生产商改进产品,成为安全的不利诱因。[2](P80)《重述》(第三版)第11节评注a还明确指出,产品安全的改进并不导致召回先前产品,那样会阻碍生产商制造更安全的产品。一些法院还认为,只有在以下条件下生产商告知买者安全改进才是合理的:(1)生产商与购买者有持续的关系;(2)市场有限;(3)提供安全改进通知的成本极其微小。
四、违反售后义务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生产商就其未履行售后义务导致损害承担的侵权责任是严格责任还是过失责任?《重述》(第三版)第10节规定售后义务属于过失理论的范畴,但法院并不会因为受害人以严格责任理论为依据提起诉讼而驳回起诉。第10节明确规定,以售后义务为根据提起诉讼属于过失,因为产品提供者的行为是售后义务所要探究的焦点。[3](P968)视行为人的行为为考察焦点,属于过失范畴,售后义务取决于生产商行为的合理性。根据第10节,生产商不需要为售后行为负严格责任。Lovick v. Wil-Rich①Lovick v. Wil-Rich,588 N.W.2d 688(Iowa 1999).案法官也同意“过失是解决售后警告产品责任诉讼合适的理论”。
在严格责任情况下构建售后警示义务,将使生产商处于两难境地:改进产品将使其售出的产品变得有缺陷,因而要负严格责任,不改进产品则产品没有竞争力。售后警示义务背景之下,过失分析比适用严格责任更加合适,因为严格责任强调产品的危险状态,而非生产商的行为。②Patton v. Hutchinson Wil-Rich Manufacturing Co.,861 P.2d 1299,1310(Kan.1993).
可见,因为产品提供者行为的合理性是售后义务的核心,故以售后义务为基础的诉讼必须以过失为基础。当生产商的行为是核心时,过失就是正确的法律理论。《重述》(第三版)第10节创造了产品供应商发现产品售后安全问题的合理注意的义务。另外,评注c还规定,一般注意义务要求,当销售商有合理依据怀疑未知风险的存在时,生产商要进行调查。然而,该评注还明确,除了处方药和医疗器械,“持续地监督观察该产品的行为”通常都意味着过于沉重的负担,并不能支持售后义务。生产商未建立信息收集系统,但又主张不知晓风险,这可能被陪审团认定为行为“不合理”,特别是当建立这种系统成本不需要太高时。这些判断都在过失理论之下发生的。
五、美国售后义务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无论法院是否更经常地适用售后义务,售后义务在美国法律界并未获得一致认可,有些学者称其为洪水猛兽,认为其责任是极度扩大的责任,工业界的反对则更强烈。这些观点的表达不仅是因为立场不同,也在于售后义务本身确实存在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尽管售后义务有扩大的趋势,但很多州仍然严格限制。如有些州明确限制售后警告义务在产品投入流通时存在缺陷的情形。但是,售后义务作为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在美国已经根深蒂固,并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并扩张。在美国本土,售后义务的理论和司法实践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6条明确规定了售后义务,却并未提及与售后义务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法院也无可资借鉴的判例。因此,无论是在具体司法操作还是价值理念指导上,美国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借鉴。
1.违反售后义务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在美国,违反售后义务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主流观点是适用过失理论,《重述》(第三版)也持该种观点。目前我国学界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是过失理论,有学者认为是严格责任。对于过失理论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杨立新教授在药品召回义务致害领域持严格责任观点,即在药品召回产品导致侵权中,归责原则应该是严格责任,主要依据是药品侵权责任属于产品责任,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笔者认为不妥。在以上分析中已经指出,售后义务并非一般产品责任义务,而且即使在产品责任法发达的美国,对其很多理念和价值也并未完全确定。售后义务关注的焦点是生产商之行为,而非产品的缺陷状态。在我国,产品责任法确实适用严格责任,但并不意味着违反售后义务导致的责任也应该适用严格责任。这样会导致生产商负担过重,特别是在药品、医疗器械领域更不应该如此,这样有剥夺病危病人获得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权利之嫌。
2.售后义务与工艺水平的抗辩。在美国,有些法院认为,工艺水平的抗辩可能导致不发生售后义务,但有些法院并不认为二者存在冲突,要根据案情具体判断。中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3款规定,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生产商可主张不承担责任。该条规定与售后义务也并不冲突。产品责任诉讼中,受害人在完成一般产品责任法中所有的举证后,生产商仍可提出并举证工艺水平的抗辩。如果受害人主张生产商承担违反售后义务侵权责任,他必须进行举证。虽然《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售后义务,但何时需采取警告或召回产品措施,用何种标准来判断,需要法官根据证据进行衡量和判断。受害人还要证明,生产商有采取警告或者召回产品的必要性,且生产商应该采取而未采取该种措施,或者采取措施不利,由此导致原告伤害。若受害人举证成功,他不仅可以击败生产商的抗辩,还可以获得赔偿。因此,《侵权责任法》第46条售后跟踪义务的规定,并不必然导致《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3款的无效。
3.关于产品安全改进与售后义务。在美国,多数法院并不倾向于认定生产商有将产品安全改进信息告知消费者的义务。在中国,产品改进也是提高产品安全的一种重要方式,且是事前预防的方式,是根本性的,不宜认定生产商改进产品会导致其承担售后义务。因产品改进导致生产商承担违反售后义务的侵权责任,实际上是阻碍生产商改进产品安全,这不是产品责任法的初衷,也不是要求生产商承担售后义务的价值目标。因此,必须在改进产品安全与生产商售后义务之间作出区分。
4.关于售后警告与召回产品的区分。售后警告义务与召回产品的义务是售后义务的两种情况,前者成本比后者小得多。召回产品的义务对生产商是相对较沉重的负担。这也是美国法院一般不追究生产商召回产品的普通法义务的原因所在。鉴于此,相比较生产商违反售后警告义务致害,生产商违反召回产品义务导致侵权责任的适用条件自然要严格得多。一般情况下,若召回产品的行为已经发生,也发生了人身或财产损害,与一般产品责任相比,产品缺陷已经不需要由法院认定,因为召回产品本身就足以说明缺陷的存在。但在特殊情况下,每一起产品召回并不意味着当然具有证明缺陷存在的证据效力,这要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判断。
[1] Kevin R. Boyle, The Expanding Post-Sale Duty of a Manufacturer:Does a Manufacturer Have a Duty to Retrofit Its Products?[J].38 Ariz. L. Rev. 1033(Fall,1996).
[2] Douglas R. Richmond, Expanding Products Liability:Manufactures’ Post-Sale Duties to Warn, Retrofit and Recall[J].36 Idaho L.Rev.7(1999).
[3] Kenneth Ross & J. David Prince, Post-Sale Duties: The Most Expansive Theory in Products Liability[J]. 74 Brooklyn L.Rev. 963(Spring, 2009).
[4] James A.Henderson, Jr. & Aaron Twerski, The Politics of the Products Liability Restatement[J]. 26 Hofstra L.Rev.667(1998). [5] 美国法律研究院.侵权法重述第三版:产品责任[M].肖永平、龚乐凡、汪雪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6] Edward J.Higgins, Feature: Tort Law: Gone but not Forgotten:Manufactures’ Post-Sale Duties to Warn of Recall[J].78 MI Bar Jnl. 570 (June,1999).
[7] M. Stuart Madden, Modern Post-Sale Warnings and Related Obligations[J].27 Wm.Mitchell L.Rev.33(2000).
责任编辑:侯德彤
After-sales Duties under American Product Liability Law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on China
DONG Chun-hua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fter-sales duties of producers are a new system under the product liability law. Having its origin in the USA, it is relatively mature with a set of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judgment of after-sales warning and recalling sold products. Hence, the judicial judgment in the US is also mature in terms of counterplea of after-sales duties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product improvemen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violating after-sales duties. Therefore,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an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fter-sales duties under Article 46 of Tort Liability Law in China.
after-sales warning duty; after-sales product-recalling duty; counterplea of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principle of imputation
DF045
A
1005-7110(2012)02-0039-07
2012-02-09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缺陷医疗器械侵权责任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0CFX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得到上海市人文社科基地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的资助(基地编号:SJ0709);本文为上海高校优青专项基金项目“中美食品责任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编号:hzf09020)的阶段性成果。
董春华(1980-),女,山东青岛人,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