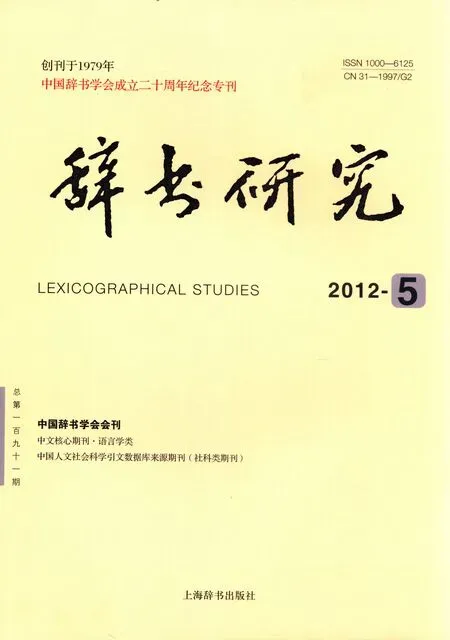打假批劣显精神
徐庆凯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200040)
在中国辞书学会的二十年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个学会的鲜明特点是,在组织学术研究、开展学术讨论、加强学科建设的同时,十分关注、积极参与净化辞书园地和提高辞书质量的实际工作,做了揭批伪劣辞书和举办中国辞书奖这两大实事,从而对中国的辞书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2年10月,我赴京参加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在分组讨论时,我揭批了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等严重错误,希望学会关注这类现象,为净化辞书园地尽一份力。此事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和学会领导的重视。学会第一副会长巢峰在大会的闭幕词中对辞书界的打假批劣发表了看法,主要内容如下:
现在辞书界剽窃成风,差错成风,拼凑成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被人抄袭不计其数。辞书编纂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掮客,他们把编辞书当作捞取政治资本和金钱的手段,不管坑害广大读者与否。有一本《语言大典》,公然把《辞海》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和《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两个附录加以影印,当作自己的附录。这本书许多条目照搬《现代汉语词典》。我社有的同志翻阅《语言大典》,发现其收词和释义简直不可思议。例如在“一”字头下,大部分词目是任意凑合的自由词组,既无查阅的必要,也无查阅的可能,根本不成其为词目,如“一袋”、“一盘”、“一箱”、“一茶杯”、“一个铅字”、“一段台词”、“一截粗木头”、“一套房间”、“一声喊叫”、“一次又一次的损失”、“一天干两天的活”、“一股劲儿地呜嘟呜嘟吹奏”等等。释义则如:“一胖一瘦”释为“一个胖的一个瘦的”;“一直被人叫着”释为“在一段时间中保持粘着和固定,看来像由于粘合力或粘着力或粘住”;在“一部分”这一条中甚至出现“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的消灭宗教”这样的例句。这样的词典,怎么能不加批判、抵制而任其流传?我以为我们的辞书编纂和出版中有一种堕落行为。评劣就是要与辞书编纂与出版中的堕落现象作斗争。我们要促使辞书事业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就一定要做好打假打劣的工作。
这一段话,义正词严,吹响了中国辞书学会打假批劣的号角,拉开了其后中国辞书界“三大战役”的序幕(见2003年12月17日《中华读书报》载巢峰的《中国辞书界的“三大战役”》一文)。
三大战役
返沪后,我进一步检查了《语言大典》,又发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问题,于是写成《如此词典,匪夷所思——评〈语言大典〉》一文在《辞书研究》1993年第3期上发表。刊出前,《文汇读书周报》根据该文校样于5月15日以头版头条发表《〈语言大典〉竟是“谬误大全”》的报道,披露了该文的要点。5月22日该报又以头版头条发表《杜绝谬种》的报道,说该报上期揭批《语言大典》的报道“在读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此后,于光远、曾彦修、巢峰、王宁等知名人士相继发表了批评《语言大典》的文章。批评的对象陆续扩展到王同亿主编的其他词典,如《现代汉语大词典》、《新现代汉语词典》、《新编新华字典》、《英汉辞海》、《英汉科技词天》、《法汉科技词汇大全》、《俄汉科技词汇大全》等。
在开展批评的同时,由于《新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大量抄袭《现代汉语词典》和《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又由于《语言大典》抄袭《辞海》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和《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两个附录(共二十多万字),《语言大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大量抄袭《中国成语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辞海编辑委员会、上海辞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五个单位和部分作者于1993年7月至9月先后对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提起诉讼。这五起案件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审理后判决被告败诉。被告不服,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经分别审理,最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是我国最大的辞书著作权诉讼案件。此案的审理和判决,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也扩大了对王同亿系列词典集体性批评的影响。
在这次集体性批评中,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为数更多的以杂文为主的短评(其中瓜田的《无知却有胆 快去编辞典》最出色)成为一大特色,还有一批评论性报道(其中庄建的《我们丢失了什么?——从王同亿、海南出版社涉及的五起著作权侵权案说开去》分量最重),再加上华君武的漫画;广播电台、电视台也施展了他们特有的手段。这一场规模大、气势足、内容扎实、形式多样、持续数年的集体性批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99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选录了六十五篇批评《语言大典》的短评,编成《发人深思的笑话——〈语言大典〉短评集》一书出版。印数两千册,很快销售一空。
1997年,中国辞书学会秘书处将批评王同亿系列词典的论文四十三篇编成《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在1999年出版,对打假批劣的第一战役做了总结。
但王同亿并不甘于失败,他回到湖南家乡继续炮制劣质词典。2001年,他抛出了由他主编、京华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并用改头换面的手法,对该书略加增补,又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高级现代汉语大词典》。这两部词典,除抄袭剽窃有所收敛外,胡编乱造依然如故。词目中充满着污言秽语,如“狗日的”、“狗娘养的”、“狗杂种”、“放狗屁”等等。释义则信口雌黄,如“不破不立”释为“现多指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暴卒”释为“凶暴的士兵”,等等。例证不仅堆砌得不可思议,如“一”字条第二个义项“最小的正整数”就有八十个例证;而且许多例证的内容令人不可容忍:思想荒谬的如“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黄色下流的如“有色心无色胆的只能色迷迷地看”,恶俗不堪的如“屙屎带放屁——顺便”,如此这般,不胜枚举。
对于王同亿再造伪劣词典的行为,中国辞书学会常务理事会在2001年6月决定予以批评。该会辞书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在同年8月举行的研讨会上落实了这一决定。同年10月,中国辞书学会又联合中国教育学会举行座谈会继续展开批评。两次会上的发言都整理成文并先后发表。此外,报刊上还发表了其他批评文章和评论性报道。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把这些文章编成《需要批评 需要反思》一书,在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汇集了打假批劣第二战役的成果。
自称为“王同亿重出江湖”的事件发生后,中国辞书学会加大了对辞书市场调查研究的力度。2002年底,向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提供了六十种有问题辞书的名单,并报告了这些书中的主要问题。不久,图书司司长阎晓宏约见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曹先擢、副会长韩敬体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告知他们总署在市场检查中发现了一些可能有问题的辞书,又接到学会提供的有问题辞书的名单和许多读者对伪劣辞书的投诉,决定开展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委托中国辞书学会承办。由总署确定的对二十一种辞书的专项检查随即启动。2003年10月,总署公布了不合格辞书的名单。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内容相同、字数相同、定价也相同仅书名不同、开本不同的两部书。一部叫做《中华辞海》(32开),一部叫做《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16开)。它们是孪生出来的一对怪胎,不伦不类,抄袭剽窃,胡编乱造,差错泛滥。不合格辞书的名单公布后,发表了《“非常态”的伪劣辞书》、《有名无实的“百科全书”》等一批评论文章。这就是打假批劣第三战役的大致经过。
在三大战役中,不仅揭批了伪劣辞书,而且还对从源头上遏制伪劣辞书提出了不少建议。鉴于伪劣辞书都是由不具备辞书出版资质的出版社出笼的,因此建议出版行政部门实行辞书出版准入制,规定出版辞书必须具备的条件,不具备条件的出版社不得出版辞书。条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定数量合格的辞书编辑,为此建议举办辞书编辑培训班,编辑经过培训并通过考试取得证书后方可持证上岗。建议建立出版社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考核制度,防止为了追逐利润而出版伪劣辞书。建议出版行政部门组织辞书专家定期进行辞书质量检查,发现伪劣辞书及时处理。建议对伪劣辞书的出版者给予行政处罚,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对伪劣辞书的编纂者追缴其稿费,不让他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建议立法保护精神产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购买伪劣辞书的读者应有权索赔。建议新闻媒体介绍辞书应认真审核,力求合乎实际,不能让伪劣辞书的编纂者、出版者自吹自擂,欺骗读者;同时对伪劣辞书加强舆论监督,使之原形毕露。
以上种种建议,有些已被采纳。早在1994年2月24日新闻出版署召开的提高辞书质量、促进辞书繁荣的座谈会上,时任新闻出版署党组成员、图书司司长的杨牧之即已表示赞同与会专家提出的加强辞书质量检查、辞书编辑须经培训获得资格方可上岗、出版社须具备条件才能出版辞书等项建议。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先后发出《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开展辞书出版人员资格培训工作的通知》,从2006年到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和中国辞书学会合作,已举办七期培训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国辞书学会还在2008年发布《辞书工作者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自律准则》(载《辞书研究》2008年第2期),其中,“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不择手段追逐暴利的行为”、“反对抄袭和变相抄袭”、“确保辞书质量、杜绝劣质辞书进入市场”等准则都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伪劣辞书。
两位代表
中国辞书学会的打假批劣,参与者甚多。他们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能容忍宝贵的国家资产被用来制造文化垃圾,败坏祖国文化,愚弄和毒害广大读者。同时,他们对辞书事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不能容忍辞书的园地被糟蹋,辞书的名声被玷污。因此,他们坚持不懈地投入打假批劣的斗争。其中有两位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有必要在此略加记述,以便于学习和发扬他们正气凛然、祛邪不止的精神。
一位是历任学会第一副会长、代会长、名誉会长的巢峰。1992年他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上吹响了打假批劣的号角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组织开展这项工作为己任,运筹帷幄,精心部署,逐步推进。他在各种大小会议上都会提及打假批劣。重要的如:1993年在中国辞书学会第一届年会上题为“《语言大典》的教训”的开幕词;1994年在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上题为“‘王同亿现象’剖析”的讲话;1995年在首届中国辞书奖颁奖大会暨中国辞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的两次讲话;等等。他一再建议实行辞书出版准入制和培训辞书编辑,作为遏制伪劣辞书的手段。
他还写了一批相关的文章。主要的有:1994年发表的《刹一刹著书出书中的粗制滥造风——兼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2001年发表的《辞书编纂必须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2003年发表的《中国辞书界的“三大战役”》、《辞书出版准入制势在必行》和《净化辞书市场的五大措施》。这些文章在辞书界、出版界、文化界有较大影响。
另一位是长期担任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副会长、现任顾问的周明鉴。他对优质辞书爱护有加,多方帮助;对劣质辞书则绝不容忍,务必铲除。他住在北京,常到甜水园图书市场浏览,发现可疑的辞书,就自己掏钱买回去检查,从而发现了许多问题,积累了大量资料,通过学会向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报告。拿到王同亿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后,他随机检查了该书的五分之一,每页都有红笔划出的条条杠杠,贴着密密麻麻的浮签。后来他又发现王同亿的《高级现代汉语大词典》其实是此书的翻版。批评这两部词典时,他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评析》、《词典都是“东抄西改”编出来的吗?》、《可悲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底中国辞书学会向新闻出版总署提供的六十种有问题辞书的名单,许多都是他的发现。如前所述,这是新闻出版总署开展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时确定书目的三个来源之一。检查结果公布后,他发表《有名无实的“百科全书”》一文,揭批了煌煌四十六册、用大礼品盒包装、定价五千八百元而内容一塌糊涂的《现代生活实用百科全书》。
影响深远
中国辞书学会打假批劣的壮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致力于推动开展学术批评的杨玉圣,曾经两次论及辞书界的打假批劣。他说:“围绕《语言大典》等王同亿现象的集体性批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辞书界的‘无法无天’态势,其积极意义无疑是历史性的。”又说:对王同亿现象的批评,“不仅给辞书论坛注入了生气和活力,而且强有力地显示了学术批评的魅力与威力;它不仅张扬了辞书界的正气之歌,而且为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批评开启了一条阳光大道。”(见1996年10月2日和1997年10月8日的《中华读书报》)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是还可以看得更广更深一些。于光远在《值得重视的一个消极文化现象——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一文中说:“它(按:指《语言大典》)的用处看来只是为研究当前我国文化现象提供一个对象。它使我们去想不少问题,它也使我们通过这种思索了解不少问题。”这样的词典为什么能够出版?为什么被吹捧和抬举得那么高?为什么被揭批后还可以发行?“这就要深思一番了。这不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接着我们还可以问,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风气?并且进一步要问这种社会风气是如何造成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一个问下去,得出行动方面的结论,进行教育,改进工作,我想对于我们的国家的文化事业是大有好处的。”(载1994年第2期《辞书研究》)对于后来揭批的伪劣辞书,也都可以做这样的深思。
从辞书编纂出版的角度说,打假批劣,对所有的辞书编纂者、出版者都有警示作用,告诫他们决不可造假制劣,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当然,无视警告、敢于冒险的大有人在,但终究少得多了。尤其是由打假批劣引出的辞书出版准入制、辞书编辑培训和持证上岗制以及辞书质量专项检查的实行,对于整顿辞书出版秩序、从源头上遏制伪劣辞书、提高辞书质量、建设辞书编辑队伍已经起了并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从辞书研究的角度说,这些年不仅揭批了伪劣辞书,而且揭批了伪劣辞书的炮制者为自己开脱的种种奇谈怪论,光是关于抄袭行为的就有一大堆。被人揭发其抄袭行为如整个词条的注释、例句一字不动地照抄,照抄注、例,仅增删个别无关紧要的字等五种手法后,王同亿竟答辩说:“凡编词典,都离不开这‘五种手法’。”他又说:“词典具有承继性强烈的特点,按照传统模式,东抄西改而已。”他还说:“作为语言构成成分的语词,人们应有共同的认识。……以‘抄袭’为名,将‘共识’据为‘专利’的作法是不适当的,也是行不通的。”(按:王同亿将“共识”绝对化,并将“共识”和“对共识的表述”混为一谈。)他又说,词典的条目是“记录”的结果,不是“创作”的成果,没有独创性,因此不是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按:歪曲别人所用的“记录”一词,毫无根据地抹煞词典的独创性和著作权。)他还说,他的行为是对他人词典的“适当引用”。(按:他的行为和著作权法规定的“适当引用”毫无共同之处。)对于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严加驳斥,这是辞书研究的一个成果。另一方面,伪劣辞书为辞书研究提供了大量反面素材,也对辞书研究的深入开展甚为有益。
现在,辞书界的打假批劣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斗争还将继续下去,永无尽期。希望中国辞书学会始终站在这个斗争的前列,为净化辞书园地、提高辞书质量、繁荣辞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