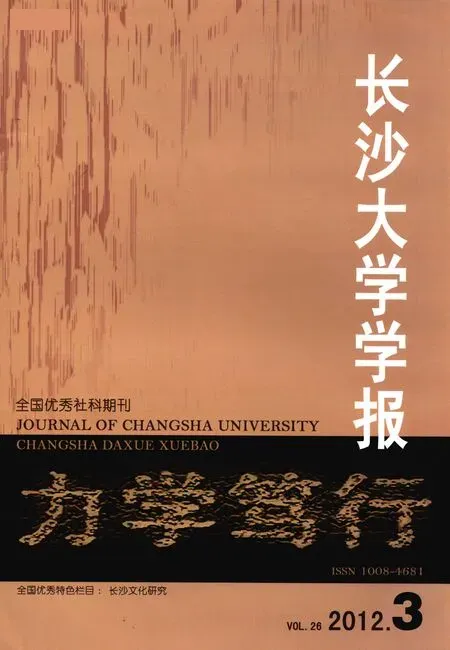跨越性与文学性:比较文学学科话语的基石*
李夫生
(长沙大学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湖南长沙 410003)
跨越性与文学性:比较文学学科话语的基石*
李夫生
(长沙大学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湖南长沙 410003)
比较文学的学科话语实际上就是指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及学术规范等问题。跨越性是决定比较文学成其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性要点,是其作为开放性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文学性是保持比较文学成其为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观念。比较文学的学科话语简而言之有两个基本点:跨越性和文学性。
跨越性;文学性;比较文学
一 比较文学的学科话语
“比较文学的学科话语”,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范围和边界、内涵和外延以及相关学术规范等等问题,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比较文学研究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路径和准则。
比较文学虽然长期被当作一门正式学科,但其学科的正当性却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自比较文学诞生以来的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这种强烈的质疑未曾间歇,从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到美国知名学者华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U.S.A)教授苏珊·巴丝尼特(Susan Bassnett,1945-),学界不断有人指责比较文学的“不合法性”。以至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危机”。可以说,比较文学发展到今天,是不断从“危机”中找到“转机”的。这是各学科门类中绝无仅有的现象。
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2)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的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1]
韦勒克的这个警告,其实说的正是比较文学学科话语的问题,也就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要明确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及独特的研究范式。
与此相应的是,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主要在于两方面:比较文学作为研究方法还是一种文学鉴赏、辨析、比较、研究的视野?
大多数研究者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三大块综合起来构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基本内容和理论模式。早期研究基本上是前两个板块为主。在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框架下,下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等法国学派常用并激赏的具体研究方法;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理论框架下,又细分为“主题学”、“题材史”、“类型学”、“文体学”、“比较诗学”等文学学科范围之内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学与宗教”等跨学科的研究范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晚近的一些比较文学研究又加入了第三板块,即所谓的“跨文化研究”(曹顺庆先生则在其《比较文学论》等著作中将它称之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2]。这三大板块构筑起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也是时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模式。
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建构,无论是两个板块还是三个板块,其最根本的缺陷是历时性理论描述带来的一系列困惑:第一个问题是在几个理论发展阶段中,或者说是几个理论模块中,各自理论言说规则不一,难免形成自说自话,分类混乱的现象。比如同样是对主题的探究,在法国学派的所谓“影响研究”中,着重关注的是作品主题如何从A国流传、转变为B国作品中的同类主题。换句话说,就是A国作品的主题如何影响到B国作品中的同类主题。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平行研究”中,关注的重心则是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不同作品的同类主题的研究,即所谓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的“主题”研究。这样,同为对“主题”的研究,但实质内容却大不一样。另外的问题就是理论重叠,相互叠合的问题。同样是关于“主题学”,究竟是归诸于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中,或者既放在影响研究中,又放在平行研究中,花开数枝,各表一点,面面俱倒却又浅尝辄止?这样一来,理论凌乱,容易使人莫衷一是。如前所述,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中,“主题学”关注是的“材料”的寻根溯源,但在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平行研究”中,则是强调没有事实影响关系的不同文学体系间的主题研究。正因为各有偏重,又都属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关注范畴,因此,给“主题学”准确定位——它是属于影响研究呢,还是平行研究,竟成了不少研究者难以解决的问题。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每位研究者都试图说清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结果却始终没有真正地说清楚它的理论体系。
怎么样才能梳理清楚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整合、建构完整的比较文学学科话语?我们认为,唯有从比较文学的最根本的学理——“跨越性”和“文学性”这两个基点来进行融通,才能真正把握住比较文学的理论内核。
二 比较文学是一种跨越性的研究
无论在比较文学发展的哪一个阶段,比较文学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这就是它所具有的开放性的眼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跨越性”。对于“跨越性”的学科特征,应该说在比较文学界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但是,在“跨越性”这个问题上,各家阐释又众说纷纭。其中传播最广的要数“四跨说”,即指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3]。
可以说,在比较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开放性眼光的“跨越性”成就了比较文学学科,也造成比较文学学科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四跨说”虽然都在法美学派的定义中的有所超越,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澄清或者说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这是因为:
有关“跨民族”的问题。法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跨国文学研究的观念给出了比较文学最初的学科界限,但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中这个界定并不精准。比较文学是为了突破民族文学的界限而兴起的,它的着眼点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国家”是政治地缘概念。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是一个民族的,也可以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因此,比较文学的界限,应该是跨越民族的,而不是国家的界限。其实,在法国学派兴起的时候,在欧洲各国,民族和国家总体而言是重合的,只有极少数国家和民族不相吻合。而且,比较文学兴盛之时,欧洲民族国家尚未大量崛起。因此,更加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这样“跨国”与“跨民族”并无实质上的二致。但是,当比较文学兴起之后,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问题就显得复杂了。一是大量民族国家的崛起,另一个是比较文学开始越过法国边界,拓展到西欧以外的地方。现代国家大多是多民族的,比如中国,就有56个民族组成,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民族多样性更加丰富。如果每个国家内部的几十上百种民族之间都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那么难免造成文学研究领域的混乱。而且跟比较文学的创始者们提出的比较文学要具有国际眼光的学科初始宗旨也不相符合。所以,尊重比较文学学科实践,把一国内部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仅仅当作一种大的民族范畴文学来研究应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中国有56个民族,美利坚合众国差不多集中了世界各种民族在一起,但在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我们仍然将中国、美国等这样的民族国家的文学当作一个国别文学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集合概念。
有关“跨语言”的问题。以语言界限来限定比较文学的学科同样存在一些问题。语言和国家的界限是难相吻合的,英国和美国、澳大利亚及世界很多说英语的国家之间,虽然语言发音、表述习惯等方面略有区别,但总体而言是没有语言界限的。那它们之间的比较是否就不能算是比较文学了呢?反过来说,同一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语言,比如南美的一些国家,同一国家内部可能既说西班牙语又说法语,甚至还可以说英语,这些国家的文学研究就不能算是比较文学的范畴吗?还有一种现象更让人迷惑,如一些跨语际写作的作家,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写作,这让“跨语言”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充分展示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效果呢?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着眼于“世界性”的学科情怀。虽然各个发展阶段的理论表述各有偏重,但“世界性”始终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终极关怀。法国学派强调文学关系的重要性,强调“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研究“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4]。基亚(Marius Francois Guyard,1921-)更是明确地说比较文学是一种“国际文学的关系史”[5]。这些学科开创者的理论表述,其实都有一种国际眼光,即强调将跨国文学史的关系研究触角伸到国别文学史的研究之外。美国学派的学科理论更加务实,将比较文学开疆拓土的视界投得更深更远,提出超越文学史的限制,可以将文学性(美学价值)纳入比较文学的法眼中来,格外重视没有实际事实联系的文学比较研究。这样,比较文学研究的“跨越性”就不再仅限于文学关系史的比较研究中,视野更加广阔得多。
在此基础上,美国学派更进一步提出了跨学科研究,从而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更向前推进了一步。雷马克(Henry H.H.Renmak)在其著名的《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认为,比较文学可以“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6]。雷马克实际上说的就是指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为规避跨学科比较研究在可比性上“大而无当”的风险,雷马克提出了可比性的“系统性”原则,即只有当文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比较时,比较文学的学理性才能确立。但是,雷马克虽然注意到了比较研究可比性“系统性”法则,但并没有作出非常严格的逻辑界定,因此,这个“系统性”仍然显得比较空泛无定。即使这样,跨学科研究仍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比如诗与画、文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等等。
近些年,中国比较文学界更进一步提出了比较文学话语的“跨异质文化”论。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的时候,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文学内部的很多东西。曹顺庆先生在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学科特征是“跨异质文化”。“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线,沟通了各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关系的各国文学,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7]近些年来,曹顺庆对其“跨异质文化”略有修正,进一步升级为“跨文明研究”。在他看来,“文化”一词涵义过于混乱,难免有理解上的误区。实际上“跨异质文化”和有些学者提出的“跨文化”研究是不太相同的。“跨异质文化”更加注重中西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是文化差异的最大包容点”,所以以“跨文明”取代“跨异质文化”表述更为妥当[8]。
从比较文学学科创立之初法国影响研究学派的“跨国”至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跨学科”再到当下的比较文学界的“跨文化”,万变不离其宗,比较文学始终具有“跨越性”,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石,是比较文学学科开放性的、世界性的学科特征最根本的保证。
三 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关系”的研究
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从法国学派有关国际文学系史的实证性研究开始的。前面我们提到,比较文学刚刚创立的时候,就遭到了来自著名美学家克罗齐等人的非难。为了应对这种理论质疑,法国学派必须考虑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具备的科学基础。所以基亚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只不过是一门名字没取好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9]法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实证性的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公允地说,这种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奠定了比较文学学科的严谨的科学性研究基础。
但是,由于在实际操过过程中,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过于强调实证的影响研究,束缚了研究的有效展开,逐渐使后人对这种研究范式产生怀疑和反思:首先是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作出激烈批评。在著名的教堂山会议上,美国学者认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是僵硬的外部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在当时文学研究由社会学的外部研究向关于文学性的内部研究转向的历史语境下,韦勒克提出比较文学研究要“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10],应该把美学价值重新引进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来。因为“文学性”问题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作品得以存在的内部规律性。相应地,比较文学应该从简单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的定位中重新回到文学本身。比较文学不应该只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同时它也应该包括文学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内容。
美国学派韦勒克等人的质疑和责难当然自有它的道理。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科,比较文学学科话语不应有自我束缚和限制。而且,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对文学内部规律的重视也是应有的题中之义。但是,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责难也有它的一些片面性。作为学科发展第一阶段的重要理论,“影响研究”有其充分的学科理论价值。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的“影响研究”,首先是一种文学关系学研究。就其最初的学科定位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强调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它继续追求一种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的文学关系研究实际上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波斯奈特(H.M.Posnett,1855-1927)在1886年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文学的专著《比较文学》,实际上就是一部关于文学的进化史著作。波斯奈特用进化论的观点来检讨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探讨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她提出:
“我们采用社会逐步进展的方法,从氏族到城市,从城市到国家,从以上两种到世界大同,作为我们研究比较文学的适当顺序。”[11]
氏族——城市——国家——世界的文学进化图式实质上使比较文学在其最初发展阶段着重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就是文学的进化史。法国学派在波斯奈特的定义之下有所拓展。梵·第根(Paul Van Teighem,1891-1958)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可以在各个方面延长一个国家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能够“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上,纺织一个更为普遍的文学史的网”[12]。其意在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于不同国家的文学史之间,是国别文学史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是一种弥补国别文学史视野片面性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这样,比较文学的这种国际文学关系史就共同编织出国际文学发展的总体网络,从而形成一种总体国际视野。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互相交流、对话、融合是形成文学发展的重要途径。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了文学横向发展的新动力,促进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进步。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的文学关系研究特别强调实证研究。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文学的实证研究。它力图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法国文学对其他国家的文学的影响力量,从而证明法国文学的重要性。应该说,法国学派的这种理论起源,深层意识中含有一定的文学沙文主义,但是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它逐渐摒弃了这种观念,而向着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开放。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影响研究的实证性方法,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形成了一整套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包括:渊源学、流传学和媒介学等实证性的文学研究范畴。渊源学主要通过溯本求源的方式来探讨一种或多种文学现象的横向来源;流传学主要研究一个文学现象在另外的文学体系中获得的影响和传播的情态;媒介学研究不同国家文学之间文学影响得以形成的中介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及其它所提供的种种研究方法,在用实证性的科学研究方法来求证法国文学在国际文学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的时候,虽然注意到了文学在传播和影响的过程中的种种变异现象,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美国“平行研究”为主流的阶段,文学现象之间的变异现象也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从“文学性”出发,来研究不同体系内文学现象的共同点。它注重强调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某种关系性”[13]。这种关联性在韦斯坦因那里就是所谓的类同或者平行研究中存在的“亲和性”[14]。无论是“关联性”也好,“亲和性”也罢,其实都是求同思维范式的体现。这在单一的西方文学体系中是很有效的一种研究方法,但是,在世界文学的范围看来,这种理论并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除一些基本的文学原理大致相同外,在不同文化体系内,文学现象表现为更多的是不同状况,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
除了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的变异性之外,我们还应看到异质文化中文学的差异性。也就是除一些基本的文学原理外,在文学表现形式、表现习惯,审美观念等具体的文学形态上,不同文化体系内的文学都会存在不同的样态。我们将这种样态称之为文学的差异性。这种文学差异性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是存在的,在强调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的今天,更是色彩斑斓。这种状况的出现,给比较文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比较文学作为研究文学关系的一门学科,比须面对这种新的状态。
怎样处理这种不同文学变异甚至差异?比较文学的世界性眼光要求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必须具有博大的胸怀。因为,正如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所说的,在文论多元化的语境下,“人们发现有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15]。这就告诉我们,比较文学研究不仅要关注一种文学现象的影响形式,更要关注它的变异形式,同时还要关注它的差异之所在。只在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才有真正进入“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埃柯的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作为居于欧洲文明中心的他,不仅意识到了不同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并且对这种差异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睿智的洞见。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文学要以各民族异质文化的相互尊重和理解为前提,比较文学要从“异”出发。因为,只有容得下各种不同文化的“变异性”、“差异性”的胸怀,才真正会有文学“世界性”的天空[16]。
但是,我们强调比较文学“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变异”、“差异”问题,又必须警惕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极端化的文化相对主义;一是将文化“他者”乌托邦化。文化相对主义固然超越了对“化者”文化高低优劣的划分,超越了以某种中心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偏见,但它如发展到极端,极易走入另一个“自我中心”,从而缺少宽容性,与“世界文学”理想背道而驰;而将“他者”文化或文学乌托邦化的结果是陷入到一种对“差异”或者“变异”的梦幻迷恋之中,将“他者”镜像化为一种理想模式,从而缺少一种识别与批判的勇气[17]。
四 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总体)性的研究
比较文学从它创立学科起就致力于文学的总体性研究。但是在比较文学草创时期,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却有着纠缠不休的关系。
法国学派主将基亚就曾指出:
“人们曾想,现在也还在想把比较文学发展成为一种‘总体文学’来研究,找出‘多种文学的共同点’(梵·第根),来看看它们之间存在的是主从关系抑或只是一种偶合。为了纪念‘世界文学’这个词的发明者——歌德,人们还想撰写一部‘世界文学’,目的是要说明‘人们共同喜爱的作品的主体’。1951年时,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打算,对大部分法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些形而上学的或无益的工作。”[18]
基亚的这种批评,是针对梵·第根的“总体文学”观,力图维护以他的老师伽列等人的比较文学学科观念的纯洁性的。因为,在伽列等人看来,比较文学什么地方的“联系”消失了,那么那里的比较工作也就不存在了。
事实上,梵·第根与基亚的争歧,仅仅在于梵·第根在强调比较文学“关系”的同时,还设想过“总体文学”:
“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之间的‘二元的’关系……所谓‘文学之总体的历史’,或更简单些‘总体文学’,就是一种对于许多国文学所共有的那些事实的探讨。”[19]
比基亚学科眼界稍微开阔一些,在梵第根看来,“总体文学是比较文学的一种自然的展开和一种必要的补充。”[20]他提出的“总体文学”实际上是在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启迪下对文学整体性的一种最初把握。事实上,它冲击了法国学派其他代表人物如基亚等人刻板固守的一国对一国的关系,冲击了法国学派的根本立场,即比较文学非“比较”而是“关系”、“贸易”。因此,他所提出的“总体文学”,启发了后人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
之后美国学者韦勒克、雷马克等人进一步修正了梵·第根的比较文学学科观念。韦勒克说:
“我怀疑梵·第根区分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意图是否行得通。他认为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个文学之间的互相关系,而总体文学则着眼于席卷几国文学的运动和风尚。这一区分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无疑是不恰当的。”[21]
这样,在韦勒克看来,“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术语,指的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文学研究。”[22]
雷马克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更加直截了当:
“比较文学研究超越一国范围的文学,并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的关系。”“简而言之,它把一国文学同另一国或多国文学进行比较,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23]。
雷马克的“比较文学”定义几乎成了金科玉律。但依然遭到来自韦勒克等人的质疑。韦勒克认为:
“内容和方法之间的人为界线、渊源和影响的机械主义概念,以及尽管是十分慷慨的但极属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是比较文学研究中持久危机的症状。所有这三个方面都需要彻底加以调整。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线应当废除。……(比较文学)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干脆就称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研究。”[24]
雷马克和韦勒克等人对比较文学的重新定义,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纠正了法国学派的文学沙文主义倾向,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从狭隘的文学“贸易”关系转而为文学性之间的研究,无疑挽救了比较文学局促的颓势。但是,雷马克、韦勒克等人却又为比较文学危机打开了另一个口子,即比较文学疆界的无限化,使比较文学限于到“无边的比较文学”新危机中。特别是近些年来,文学研究界“文化研究”热潮的崛起,“文化研究”渗入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使得比较文学研究更加拓宽了视野,也使得比较文学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中来,即当一个学科没有一定的学术界限时,这个学科存在价值等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认为,比较文学学科话语,有其自身产生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所决定的。完全否认学科发展历史和拒斥发展现状一样,都是对学科本身不负责任的一种偏颇做法。因此,比较文学的学科话语,既应尊重学科发展历史过程,又要吸纳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研究新成就。比较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是有别于一般的文学研究方式而出现的,“比较”是其基本的法则,那么我们始终要将“比较”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不二法门。但是“比较”的内容和形式不是一承不变的,从“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不仅是学科发展阶段的变更,更是比较文学之“比较”在内涵和形式上的更新、换代。但无论比较文学如何发展,“文学”始终应是这门学科的核心部分,应是其关键词。因此,无论研究方法如何,我们始终应坚守“文学”这条边界和底线。不然,“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或就真的可以寿终正寝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话语简而言之有两个基本点:跨越性和文学性。跨越性是决定比较文学成其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性要点,是其作为开放性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文学性是保持比较文学成其为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果说,“可比性”是“文学关系”或“文学和其他知识信仰”之间可供比较研究之处,而“文学性”则是比较对象之间与文学之间的本质联系,那么,“跨越性”则是则是比较文学学科“世界性”的学科属性表现。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可比性”或“文学性”还是“跨越性”都会随历史时代的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是一承不变的。
[1][10][21][22][24][美]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A].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3]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4][法]伽列.比较文学·初版序言[A].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资料[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18][法]基亚.比较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6][23][美]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A].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7]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J].中国比较文学,1995,(1).
[8]曹顺庆.比较文学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9]基亚.比较文学·前言(第6版)[A].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1][英]波斯奈特.比较法和文学[A].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比较文学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2][19][20][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A].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比较文学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3][美]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A].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资料[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4][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5][意]恩贝托·埃柯.寻求沟通的语言[A].跨文化对话(第1辑)[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16][17]李夫生.比较文学:从“异”出发[J].求索,2004,(12).
I1
A
1008-4681(2012)03-0070-05
2012-04-28
李夫生(1964-),男,湖南浏阳人,长沙大学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作者本人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