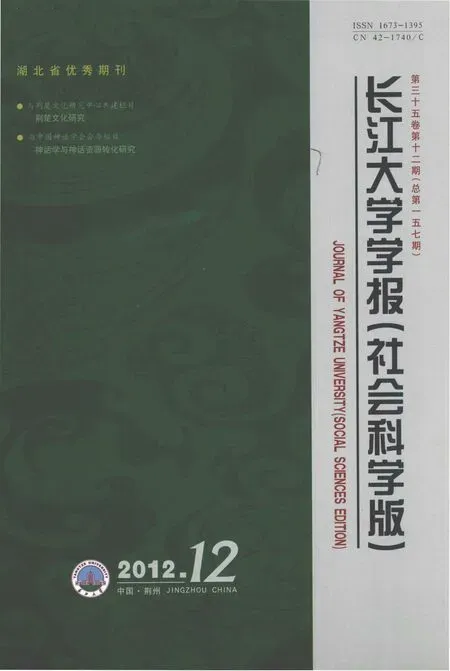神话思维与原始绘画
凌晓星
(安庆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0)
责任编辑 胡号寰 E-mail:huhaohuan2@126.com
18世纪的意大利人扬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a),率先提出原始人的思维状态是神话思维。[1](P35)他认为,神话思维带给人的是诗性智慧,而诗的活动就是想象的活动。后来卡西尔在维科观点的基础上清晰地解析出图像获得艺术意义的发展进程。他指出作为想象产物的神话,本身就象征着对既成物的超越,伴随着精神解放的进程,图像被附加于图像上的生命涵义也日益脱落,当图像作为形象本身在精神的自由活动中获得自身的逻各斯和独立的精神形式时,便以自在的方式构成了自身,并转而进入了艺术的领域。[2](P27)而绘画的过程既需要想象也需要求真,而经年累月的图式矫正和以图言意,也刺激了原始人思辨能力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原始绘画最明显的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以最具特点的角度描绘形象
从发掘出来的洞窟壁画看,史前的动物画造型一般都是取侧面;人物造型通常是各部位不同角度的组合,头部一般取正面或正侧面,躯干取正面,脚和男性生殖器以及女性乳房取侧面,就整体而言,静止站立的取正面,奔跑的取侧面。显然,原始人选取的都是最具标识度的信息进行描绘。
对此,艺术史家埃马努埃尔·勒维(Emanuel Loewy)的解释是:原始人之所以“从正面再现人体,从侧面再现马匹,从上面再现蜥蜴”,乃是记忆对感觉印象优化重组的结果。[3](P13)但他的学生贡布里希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贡布里希指出:“任何人的头脑中都没有勒维的理论所假定的那种人体、马匹和蜥蜴的图式性画面,这些在我们头脑中唤起的画面将因人而异,但它永远是难以捉摸的一批杂乱无章、转瞬即逝的东西,绝不可能完全传达出来。”[3](P13)在贡布里希看来,画家只能“见其所欲画”,而不能“画其所已见”,人类依靠固有的心理图式整理自然,画家所作的只能以一个原初的图式为出发点,将对象进行解释性转换。由于人类需要借助一些“路标”将印象和经验分节化和特殊化,“便于区分”这一自发性能力就使这些“路标”自然集中于最具特色的关键点上,而“‘原始艺术’工具般的精确性常常伴随着把物像简缩为有限要素的做法”。[3](P62)
贡布里希的这种观点与康德的“图型论”存有某种渊源,康德把“想象力为一个概念提供其图像的普遍做法的表象”称为该概念的“图型”。以野牛为例,按照康德的理论,根本不会有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牛的图像与牛的概念相符,而只能依据一定规则,在想象中构建出一般意义上的牛的“草样”,牛的图像在现实中有多种可能,但这些图像只有与牛的概念“草样”相符,才成其为牛的图像。这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心中或在手上呈现的具体图像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概念图型之上,原始人能再现出动物的形象,这说明他们已经能够区分人与动物,能够辨清一个标记或一个痕迹的明确含义,具备这两点,原始人才有意识地制作标记、矫正图式和传递信息。这就意味着在神话思维中已经萌生了理性的种子,而仅仅选取最具标识性的角度进行组合,说明他们在形式方面的要求处于较低的限度之内。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阿尔伯蒂所言:“艺术的起源是从人类发现事物间惊人的相似性开始的,比如在一棵树干或一块岩壁上发现人的脸或一个动物的形象,人就有可能会尝试通过简单的加工以强化某些特征使之更像,这样就激发了人类原初的艺术本能,艺术就诞生了,而那些被强化的特征往往是事物最具标志性之处”。
二、早期岩画动物形象自然写实
卡西尔指出,作为想象产物的神话,本身就象征着对既成物的超越,也就是说“神话在精神上超越了物的世界”,在神话意识中所引发的图像创作虽然会被原始人误判为物质实体,但它毕竟具有了精神的意义,伴随着精神解放的进程,图像越来越多地摆脱开表象者与被表象者的等价关系,被附加于图像上的生命涵义也日益脱落,当图像作为形象本身在精神的自由活动中获得自身的逻各斯和独立的精神形式时,图像就“第一次获得了纯粹内在固有的合法性和真理”,以自在的方式构成了自身,并转而进入了艺术的领域。[2](P28)无论是维科 还是卡 西尔,他们都强调了想象在神话思维中所起的作用,并且指出想象是促成原始绘画产生的重要力量。的确,对于原始人来说,每一个新鲜所得,每一种陌生境况都能激发惊奇和想象,而想象则会把这种现象归之于神秘力量的介入,并给这种力量赋以人格化的外形。正是出于想象,原始人在岩石上发现了“动物”,并把它当作有效验的生命实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介乎于直观思维和概念思维之间的神话思维虽然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但当原始人试图把岩壁上的“动物”绘制出来时,就说明他们已经萌生出求真的欲望。而早期狩猎者时代岩画上动物形象的自然写实,则是那个时期人们求真欲望的写照。
早期狩猎者时代岩画上的动物形象自然写实,“较少几何学的生硬感”。中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岩画与陶器上人物、动物形象明显具有几何化和符号化倾向。虽然原始绘画在各个时期都或多或少存在几何化的痕迹,但从旧石器时期的奥瑞纳、索鲁特和马格德林三个文化期的岩画看,其中的动物形象大都写实生动,较少有几何学的生硬感,如拉斯科内洞右壁上的“中国马”,马的头部、腹部和各关节部位都勾勒的自然流畅、看不出规划的痕迹。中石器和新石器时期,艺术形象的写实性逐渐淡化,不仅出现了宏大的围猎场面,而且抽象化和符号化倾向比较明显,人类自身形象也被更多地表现出来。以列文特岩画为例,列文特岩画早期比较写实,对动物和人物的运动描绘比较多,但到了后来,造型越来越抽象,生动的表现性及运动感消失了,代之以一种简单的隐喻符号。新石器时期的伊比利亚半岛岩画,人物、动物的符号化意味都比较明显。
对此,贡布里希的解释是,原始社会的早期狩猎者时代由于将野牛等动物作为食物来源,所以很容易把牛马鹿等动物的形象投射到岩壁的花纹或裂缝上,于是,在他们眼里,为了“牛和马”更清楚地凸现出来,他们先是用实涂法,后来发展到用线把关键点勾连起来以成轮廓,这样的一种呈像方式更符合人类的天然视觉,因而就显得生动自然,而几何学的筹划是随着理性的萌生才在绘画中发展起来的。如贡布里希所说,原始人凭借心理图式和强大的想象力创作出绘画,但另一方面,艺术创造又促使他们必须去观察实物,比较异同,增减取舍,分析结构,从而发展出逻辑能力。随着思维的发展,原始人表达意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先是具体写实的形象组合,如牛马组合、鹿象组合,后来出现了符号化的象征系统,如在“牛”身上画上平行线或交叉线可能表示“打”或“杀”,在“牛”旁边画一组方格可能表示陷阱或栅栏等。这说明,对于原始人来说,图像越来越承担起象征、隐喻和传递信息的功能,理性的光芒在艺术行为之中也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
总之,原始绘画的产生与原始人所特有的神话思维密切相关,原始人强大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使艺术得以可能,艺术在自觉地模仿宇宙之时又将自然力予以恰切转化,理性在这种转化中逐渐生长起来,而绘画就是人类因特定生存目的转化自然时而产生的特殊艺术样态,它一方面加速了理性的成长,另一方面又在理性的驱使下逐渐摆脱开“像”与“物”的等价关系,由此而获得了独立的精神形式和自身的逻格斯。
[1](意)维柯.维柯著作选[M].陆晓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M].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