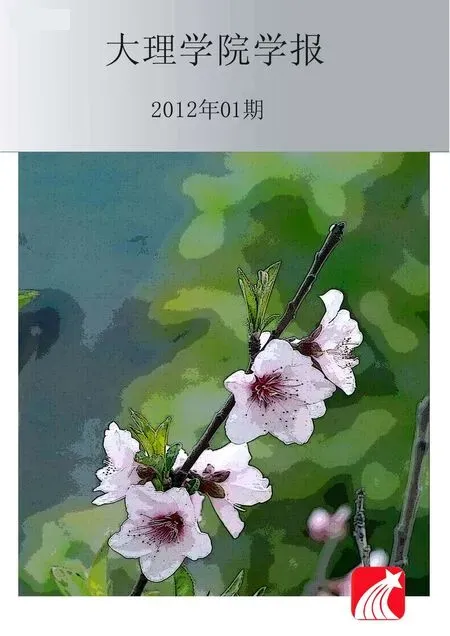清人的健讼与缠讼
——以《冕宁县清代档案》吴华诉谢昌达案为例
李艳君
(大理学院政法与经管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清人的健讼与缠讼
——以《冕宁县清代档案》吴华诉谢昌达案为例
李艳君
(大理学院政法与经管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在《冕宁县清代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吴华与谢昌达因孩童口角而互控在案,在此过程中,文人吴华不依不饶,以各种理由九次控县、三次控府,充分展示了清人的健讼与缠讼。事实告诉我们,在以“无讼”思想为主宰的传统社会,当事人一旦卷入纠纷进入诉讼,其不但不畏惧打官司,而且为达目的,甚至表现出健讼与缠讼。此外,通过此案也可以看出隐藏在案件背后的强权政治、官府的不作为以及当事人自身因素等,正是这些导致健讼、缠讼的出现;同时,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健讼、缠讼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冕宁县清代档案》;健讼;缠讼
“无讼是求”是中国古代延续几千年的主流思想,然而也有少数当事人出于各种因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成为所谓的“健讼、缠讼”者,在《冕宁县清代档案》(现存冕宁县档案局)中,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吴华与谢昌达的案子。
一、案件起因与审结
(一)吴华其人
吴华为冕宁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人氏,是一位文人(可以自己书写书状,而这也许是他不断告状的一个原因,因为写书状对他来说,可谓信手拈来)。据他说“:民五十岁时丧明(这也是他在状式中自称瞽民的原因,按照清律的规定,残疾之人打官司必须由抱告代为投递书状。也正因为如此,其子文童吴世龙便成为他的抱告),数载设身教子,世读诗书,片纸未曾入衙。”也就是说,吴华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在五十岁时丧失了视力。多年来,设身教子,世读诗书,从未与人打过官司。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知书达理之人,却走进官府,打起了官司。且一发而不可收,从一个“片纸未曾入衙”之人,一跃而成为其时所谓健讼、缠讼之人。其间所思所行及其经历可谓耐人寻味。
(二)案件起因
案件发生于光绪十四年正月,吴华的儿子与谢昌达的儿子同在一起读书。有一天,两个孩子因口角而打了起来。这本是小孩之间嬉戏之事,正如吴华在诉状中所说“乳子口角本属鼠牙”,想必不需多时两个孩子就会和好如初。可不想就是这样本为“鼠牙雀角”之事,却由于两家大人的参与,越闹越大,一发而不可收。
(三)诉讼的兴起与审结
官司首先是由谢昌达所挑起。谢昌达时为官府的吏书,他大概是想借工作之便,抢先告状,以便为自己赢取更多的利益。于是谢昌达便以抢劫之名指控吴华:“殊吏书谢昌达不惟毁门入室,反以抢劫诬民”,两家的官司由此开始。但是谢昌达没有想到,自己却撞上了枪口,吴华虽为一介书生——普通百姓且已残疾,但其应诉打官司的情绪一旦引燃,就一发而不可收。其间吴华不但转被告而为原告,且其告状的气势早已远远超过谢昌达,不依不饶,控县控府,且一告再告,大有不告倒谢昌达誓不罢休之势。下面,我们看一看在此过程中,吴华是如何一次次控告的:
第一次,吴华以谢昌达毁门入室,且反以抢劫对其进行诬告为名控告到县。知县批词“:已于谢昌达词内批示矣,并勘验伤开期集讯”。
第二次,吴华门外拦轿,知县亲勘并批:“候讯”。
第三次,吴华又到县控告,知县仍批“候讯”。
第四次,吴华仍然控县,知县批词:“鼠牙雀角耳,数语可了,何必如此剌剌不休,姑候集讯”。
第五次,吴华改名再次控告到县,知县批词:“以混名告人本属不合,惟彼此以混名控告则尔不得谓之理真矣。其实官司之是非何在乎此,不过恶习相沿耳,殊属无谓。谢昌达词内拖欠街邻,是何的名?著谢昌达指实另呈”。
第六次,吴华又控告到县,知县批示:“街邻口角竟以毁门抄家控告,抑知轻事重报之咎乎?所控刑吏买案卖案有谁凭证?隐禀舞弊有谁何见识?满口糊言是何意见?仰原差即将人证刻日带候质讯”〔1〕。
从上述批词中,我们看出吴华虽然在县控告六次,但知县并没有对他的控告有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实际上,也正是由于知县的不作为,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矛盾,才促使吴华屡屡控告,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健讼、缠讼”之人的出现正是官府的不作为所造成的,或者至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六次控县都没有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吴华开始向宁远府上控。宁远府在接到上诉后则将案件批复由冕宁县审理。由于吴华已对冕宁县知县能否公正审理此案不再信任,于是请求宁远府将案件批由西昌县审理。此案于是又被转到西昌县,西昌县审理的结果是“将谢昌达笞责,令出诬告切结”,即谢昌达诬告罪名成立,判处笞刑,并令其具结悔过。同时吴华也应要求出具了遵断甘结,此案至此结束。
二、健讼与缠讼
(一)再起讼端
前述,我们看到,在一年的时间里,吴华六次控县两次控府,终于结束了与谢昌达的争端。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吴华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告状理由——一张贴在钟鼓楼上的诽谤吴华是抢匪的匿名谣歌帖。
据吴华在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冕宁县的投状所述:“伊讼棍等不忿,日串恶棍寻害四次”,即谢昌达等讼棍对于西昌县的判决不服,经常与恶棍在一起密谋寻害吴华共计四次。尤其是“今四月二十三,撞帖谣歌钟鼓楼县门西札各一张,民即请文武查役看实,当查役等扯回一张”。在这份题为“冕邑文童知之”的谣歌中,说吴华是抢匪。按照清律,抢匪的儿子是不准应试的:“朝廷重乎功名所以设其例也,凡刑丧匿冒一切抢匪子孙不准应试”。而吴华的儿子吴世龙即将参加考试。吴华又进一步指出:谣歌还号召“冕邑文童若准吴姓子孙应试是开地方抢匪能试之端,不准吴姓应试,不惟王法相宜即风俗亦端”。
为此,吴华在投状中“恳恩拿获以对笔记”。最后他说:“皇城中王法地,四门有堆卡,四街有巡查。再伊等以为毁谤民家,殊不知目无官长,戏玩国典。只得恳恩拿获,以正地方,伏乞。”
对于吴华的再次告状,冕宁县知县表现得很有耐心,他在吴华的书状上写到:“查该呈控案早已在府讯结完案,再查例载投贴匿名文,查见者即便烧毁等语,所抄之词,律不准理,应毋庸议”。可见知县并没有受理他的控告。
吴华并不甘心,继上次告状仅过两天即四月二十五日,吴华再次控告到县,这次他告状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是“孰伊等不忿,已串更夫李象茂寻害一次,又今岁三月二十五日有文生侯应爵,来南街程姓茶铺内亲对民言,云县主对伊说有文生陆启荣进街对县主言,民家告刑吏刑书即是告县主,请县主要叫廪棚中不认保民子,又叫人串地方乱童生将民子阻考,民即对伊言后日有此事真假伊要与民对审”;二是“四月二十三日,伊等擅帖无名谣歌,民恳严拿占抄在案”;三是“四月二十四日,有学差许奉前来对民言数次,今又来家言县主实恨民家如骨血,去岁告刑书吏书即是告县主,叫民家可不要进场以免凶打”。
上述三点内容可归结为:吴华告刑吏刑书(即谢昌达)就是告知县;号召地方乱童生阻止吴华之子应考。吴华说“民思朝廷开科取士非是戏玩,民家又是城内大粮户,房内街坊无半点越理犯分案件事情”,“又欲不上控皇城中抢匪声名难当,欲得上控不惟互相阴害,且不准考,此二人言真假”。其子能否参加考试,对吴华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他继续告状的主要原因。他请求“恳恩唤齐与民对审”“,今民子考不为荣,不考不为辱。但事关大典,岂有以此清白之童生而用挟仇阻塞之蠹谋。恳恩讯实为何事不保何情不考,不然十载寒窗罔费劳苦,只得恳恩作主”。
四是“今二十五日民在南街茶铺,忽来白玉兴言,廪保戴钦位至天佑店茶铺内,民至天佑店问及何事,戴钦位言帮说铜钱二十千文即考,搕索为名民比即拉戴钦位大堂喊冤,呈恳在案恳恩作主,伏乞”。
对于吴华的再一次呈控,知县批示:“无名白帖律不准理,昨已明白批示。尔等府控之案如何讯断,所有缘由本县尚未奉到行知,俟卷宗发下亦不难查核。吴世龙有人认保与否(即吴华之子参加考试需要有廪生为其认保),其事责在廪生。其余拉杂之词尤为空言无据,候试场完竣传唤案内应讯人证来案,照例严究以肃助令而儆刁风”〔2〕。
可是时间仅仅刚过两天,即四月二十七日,吴华又呈状到县:具告状瞽民吴华抱告文童吴世龙为二堂拉住开条阻考事。情去岁吏书谢昌达捏名诬抢,沐府断清,将伊笞责令出诬告切结。今逢皇王大典考其清白取其真才,有陆启荣等二堂穿逼阻考,被民子拉住喊冤,沐恩二堂讯断,叫民二次复去投保朱保师言点名时当堂恳保民子去候点名。有文生陆启荣等统率数十余人,将民子逐出场外。民城内粮户前已考过五考,民子前已考过二考。今诬刑童无故阻考,戏玩国典,娼疾人才。今考门已开,恳提调申覆伏乞林大宗师台前赏准作主施行。
针对吴华的状词,知县一一批驳:本县二十五日早堂问案,尔等率领妇子在大堂喊冤,随即吩谕站堂差人当即带案讯问。据廪生戴钦位供称,前曾在尔家教读,尔夫妇二人将该生辫子揪扭致辱师长,例应惩责。姑念该呈瞽目,从宽免究。乃该呈又与陆启荣等揪扭,况陆启荣非廪非童,廪生愿保与否与伊何干。尔等与陆启荣在大堂前口角,众目共见,该呈所称在二堂拉住,是何意见,殊属糊涂。点名之时该呈又称陆启荣等统率数十人阻挡入场,须传出保廪生及头门当凭人役并未见有阻挡之人。该呈随竟妄言,岂盲于目而亦盲于心乎!俟场毕后卷宗下县并将所控之谢昌达及应讯之人证并传。
综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在仅仅五天的时间里,吴华即三次呈控到冕宁县。其缘由主要是吴华被诬为抢匪,使其子参加科举考试受阻。虽然冕宁县知县对其呈控内容一一批驳,但由于事关其子之前途,所以吴华继续上控。
(二)控府结案
吴华并没有等待知县的传讯,很快上控到府。他说:“今四月二十六幸值县试,民子吴世龙投册赶考,讵生童藉口诬称民子系谢昌达所控抢匪刑童,临点名时将子挪出,阻不容考”,在此情形下,“……情迫莫何,惟奔恳仁天恩施格外曲赐矜怜,赏移林主察明补考,……”。宁远府知府批示由西昌县审理。西昌县审完后行文冕宁县,将此案的审理结果及卷宗一并移交冕宁县。下面是西昌县的移文:
钦加同知衔特授宁远府西昌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许为移知事。案据贵县民吴华呈称“:为藉诬阻考,恳怜作主事。情去正民幼子与冕宁吏书谢昌达之子因细故口角,殊昌达即捏诬抄抢重情朦控林主案下,民稍有衣食不甘负抢名污辱,奔府控伸,沐批恩辕提讯明确,昌达诬抢情真,已沐笞责饬具诬告甘结备案。民同子回家午夜顶焚。今四月二十六幸值县试,民子吴世龙投册赶考,讵生童藉口诬称民子系谢昌达所控抢匪刑童,临点名时将子挪出,阻不容考。比民再三哀恳,奈林主仁慈,下情难能上达。惨民子寒窗辛苦三载方得一试,况案经恩讯,谢昌达现有诬抢切结,何为抢匪,明明藉诬阻考,情迫莫何,惟奔恳仁天恩施格外曲赐矜怜,赏移林主察明补考,庶免生童等借口朋阻,不但民子顶焚终身,即全家老幼亦颂祝不朽。为此恳乞施行等情。”据此查此案该民吴华前以遵批息讼冤诬不明等情上控谢昌达等,奉府宪于檄饬敝县移提人证卷宗到案讯明,该两造委因幼孩口角控经贵县讯断,乃吴华抗不具结,辄行捏词叠次上控,实属刁健,其谢昌达妄告抄毁亦属不合。当将抱告子吴世龙同谢昌达各子戒责示儆,并饬各具诬告切结在案。兹据前情除呈批示外,所有此案讯结缘由拟合备文移知,为此合移贵县,请烦查照外,还原卷二宗即祈查收归档,至吴世龙应否收录补考并请衡夺施行,须至移者。计移还原卷二宗
右移
四川宁远府冕宁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林
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3〕
从上述移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吴华的控告,西昌县知县对吴华和谢昌达各打五十大板,均予以指责“:……乃吴华抗不具结,辄行捏词叠次上控,实属刁健,其谢昌达妄告抄毁亦属不合。”同时判决“当将抱告子吴世龙同谢昌达各子戒责示儆,并饬各具诬告切结在案。”即对引起事端的吴华及谢昌达之子给予责打,并要求双方各自出具诬告切结,“至吴世龙应否收录补考”,则由冕宁县知县“衡夺施行”。此案到此结束。
三、案件启示
上述,我们记录了发生在清光绪十四、十五年冕宁县的一个案例,在冕宁县档案中,这虽属特例(整个《冕宁县清代档案》中,这样的案件仅此一例),但仍能说明问题。那么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清代的民众(或至少说一部分)并不忌讼,更不畏讼
众所周知,受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无讼思想的影响,即使到了清代,不论是从官方还是从大众心理,鄙视诉讼追求无讼仍然是整个社会的主流。然而档案资料却也告诉我们:虽然当时整个社会环境都不利于民众进行诉讼,但是当关系到自己的利益时,许多人并未因此而忌讼、畏讼,相反更多的人选择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个别当事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法律的空子频频告状,可谓是官府所指责的“好讼、健讼”之徒。
当然,上述案件只是个别的特例。在当时,大多数当事人选择打官司还只是为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官司一旦判决,即使小有亏欠,多数当事人也是接受判决,很少再有上控的。
(二)隐藏在案件背后的强权政治
在本案中,我们始终看到的是被官府指责为“刁健”之人的吴华,却很少提及本案的另一当事人——谢昌达。实际上,案件的发生、发展及使吴华成为健讼、缠讼之人,无不与谢昌达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而且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可以发现案件背后所隐藏的强大的封建势力。
案件的导火索是两个孩童之争。而引起诉案发生的则是吴华被诬告为抢劫;引起诉案进一步发展的是吴华之子参考受阻。那么这一切事件背后的推手是谁呢?实际上正是本案的另一当事人谢昌达。谢昌达是何许人也,原来是官府的吏书。吏书不过是衙门当中的小人物而已,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小人物,由于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告刑书吏书即是告县主”,却能够使冕宁县知县面对吴华的六次控告而不作出任何实质性的结论;在败诉的情况下却能在冕宁县制造事端,阻止吴华之子参考。由此我们不得不慨叹封建强权的巨大势力。
难道这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健讼、缠讼的出现没有关系吗!
(三)正确看待清代的健讼、缠讼现象
在古人的笔下,无论是好讼、健讼、缠讼都不是好事,是为官方、民众所抨击指责之现象。然而,以今人眼光来看,健讼、缠讼的出现绝非偶然;健讼、缠讼也未必都是坏事,对此,我们应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首先,健讼、缠讼的出现是有原因的,绝非偶然。从司法档案来看,当事人选择缠讼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官府裁决确实不公,使得当事人感到正义未申。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平民百姓,当其面临不公的判决,除了不停地控告、一遍遍主张自己的“权利”外,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可以选择呢!“缠讼基本上是贫弱阶层的诉讼心态和行动策略;也可以说,缠讼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可以利用,惟有‘缠’或‘闹’一途”〔4〕。另一种情况则是有些当事人将无理缠讼作为一种图赖的手段。不能否认确实有些当事人无视案情及法官断案的公正与否,只是考虑自己的目的是否达到。如法官判决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那么他就会利用各种理由与机会不停地控告。
具体到本案,则主要是由于:第一,官府的轻视与不作为。为此,我们首先看看官府在吴华最初六次控县中,冕宁县知县的六次批词:
第一次批词:已于谢昌达词内批示矣,并勘验伤开期集讯。
第二次批词:候讯。
第三次批词:候讯。
第四次批词:鼠牙雀角耳,数语可了,何必如此剌剌不休,姑候集讯。
第五次批词:以混名告人本属不合,惟彼此以混名控告则尔不得谓之理真矣。其实官司之是非何在乎此,不过恶习相沿耳,殊属无谓。谢昌达词内拖欠街邻,是何的名?著谢昌达指实另呈。
第六次批词:街邻口角竟以毁门抄家控告,抑知轻事重报之咎乎?所控刑吏买案卖案有谁凭证?隐禀舞弊有谁何见识?满口糊言是何意见?仰原差即将人证刻日带候质讯。
从上述批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官方对民间纠纷的轻视与蔑视,认为双方的争执不过是“鼠牙雀角耳”、“数语可了,何必如此剌剌不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六次批词中,我们看不到一次实质性的结论,或要求当事人“候讯、集讯”,或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另呈”,直至最后仍然批示“质讯”。由此可见,有些当事人的所谓健讼、好讼、缠讼,除其本身原因外,官方的态度与不作为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官方的不作为,才造就了所谓的好讼、健讼之徒。
此外,由于大清法律并没有对诉讼的次数加以限制,这样就使得当事人只要感觉不满意或者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就可以不受限制地一再呈诉、上控,可以说清代法律的漏洞也是造就好讼、健讼甚至缠讼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第二,案件确实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所在。从本案的当事人之一吴华来说,可以说他是被逼成为健讼、缠讼之人的。我们看在此案的第一阶段,吴华因谢昌达诬告其为抢劫而进行告状。抢劫,这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尤其是此罪名还关系到当事人的下一代的前途问题。因为按照大清律例,抢匪的儿子是不能参加科考的,而吴华的儿子已经寒窗苦读几载,正欲参加即将来临的考试呢!令人遗憾的是其六次上告,冕宁县知县却都没有作出实质性的判决,直至上控到宁远府,才由西昌县作出谢昌达诬告罪名成立的判决。
案件之所以能够继续发生进入到第二阶段,是因为吴华的儿子吴世龙因此案受到牵连(即抢匪的儿子不能参加考试)科考受阻,这在时人来看可算是一件大事,况此事的发生又与吴华被诬告为抢劫相关。所以我们看到在此关键时刻(其子将于四月二十六日参加考试),吴华先后于四月二十三、二十五和二十七日三次呈控冕宁县,希望其子能够顺利参加考试或在受阻之后能够补考。然而冕宁县知县仍然没有作出明确的判决。在此情形下,吴华不得不再次上控到宁远府。
第三,当事人——吴华自身的因素。吴华之所以能够不断告状,还和其自身相关,那就是他是一位文人,能够自书诉状。打官司需要向官府呈递书状,试想如果当事人没有文化,不能自书诉状而是请人代书,那么作为普通百姓,他能够支付起代书的费用吗?即使他支付得起,那么他也不会像吴华一样迅速、及时、多次地做出行动。正是由于吴华本身有文化,还有一位寒窗苦读时刻准备应考的儿子的帮助,才使他在此案的第一阶段六次控县,两次控府;在案件的第二阶段在很短的时间(五天)内三次控县,之后又上控到府。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当事人自身有无文化,也是决定其能否成为健讼、缠讼之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四,健讼、缠讼未必不是一种好事。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两面。虽然健讼、缠讼一直为时人所抨击。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健讼、缠讼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那就是,正是这些好讼之人在警醒、推动着官府积极作为、公正行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正是这些好讼健讼之人在推动着法律、社会的进步吗!
〔1〕冕宁县档案局.冕宁县清代档案:轴号31〔Z〕.卷号:389-69.
〔2〕冕宁县档案局.冕宁县清代档案:轴号31〔Z〕.卷号:389-74.
〔3〕冕宁县档案局.冕宁县清代档案:轴号31〔Z〕.卷号:389-72.
〔4〕徐忠明.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J〕.社会科学论坛,2004(10):44.
Litigiosity and Vexatiousness Made by People in Qing Dynasty——Taking the Case that Wu Hua accused Xie Changda as an Example Recorded in Mianning County Archives of Qing Dynasty
LI Yanjun
(College of Politics,Law,Economics and Management,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There was a case recorded in Mianning County Archives of Qing Dynast,and the two lawsuit main bodies,bodies Wu Hua and Xie Changda accused each other because their children had a quarrel.Intellectual Wu Hua accused county government for 9 times and state government for 3 times,which manifested clearly his character of litigiosity and vexatiousness.Once people were involved in lawsuit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non-litigation dominated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they not only faced bravely the lawsuits,but also did their efforts to win it.Besides,we could see power politics,government nonfeasance and parties'own factors hidden behind the case.It was these factors that caused litigiosity and vexatiousness.At the same time,litigiosity and vexatiousness may be a good thing in modern view.
Mianning County Archives of Qing Dynasty;litigiosity;vexatiousness
D91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2345(2012)01-0070-06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IOBFX015)
2011-09-26
李艳君,副教授,主要从事清代司法制度研究.
(责任编辑 袁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