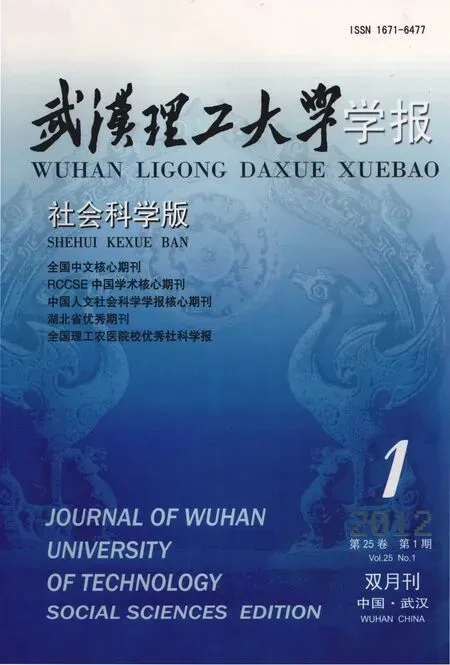社会水泥中的希望——阿多诺文化工业思想中的积极性
魏艳芳,姚 燕
(1.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100080)
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文化不是大众的文化,相反,它是控制大众的社会水泥。大众文化通过对大众的欺骗和麻痹,使大众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的思维,并进而把大众牢牢黏合在现存秩序里。由此,统治阶级通过大众文化实现了对社会大众的隐形控制。这一论断无疑极具哲理和智慧,阿多诺也因其这一论断而被视为立场坚定的大众文化批判者。
那么,在他对大众文化长达一生的关注之中,他关于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大众被完全控制的思想,是否发生过改变或动摇?研读阿多诺主要的大众文化著作,在他对大众文化一贯的批判中,我们可以零星地发现他这一总体悲观思想中的积极性。
本文通过梳理阿多诺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文本,呈现出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及大众的积极性判,以期对合理评判阿多诺及其文化工业思想提供一点材料。
需要说明的是,当代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在含义上显然是不完全相同的,但在阿多诺的行文中,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一词经常更替使用。因此,本文忽略了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两词之间的差异,把二者等同使用。
一、大众文化转化成艺术的可能性
阿多诺一贯在文化工业与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的对比中批判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标准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他看来,大众文化与现代艺术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早在1936年3月,阿多诺就在写给本雅明的一封信中论及了大众文化与艺术的关系。阿多诺指出,伟大的艺术作品与电影都打上了资本主义的印记,都包含了变化的因素[1]123。可见,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文化具有历史性,它的无否定、无超越和无变化等非艺术性特征是随着某些历史条件的出现而出现的,也必定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当代大众文化的无冲突性和它所处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联。在《大众文化的图示》一文中,阿多诺指出大众文化的无冲突性不是天然就有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硬生生地制造出来的,它与资产阶级在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有关。资产阶级文化也曾经包含阴谋、冲突等变化的因素,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冲突、阴谋和发展,这些自律文学和音乐中的关键因素,也必定是资产阶级的”[2]65。在资产阶级尚未取得稳固的地位的时候,“作为无权力的一方通过自己的智力获取权力的一种努力,阴谋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体制、算计和金钱战胜土地不动产及直接军事压迫的审美密码”[1]66。而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稳固并且是垄断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已经不再需要像当初那样使用阴谋去战胜什么东西。“现在已没有谁再会被阴谋欺骗,因为它已在社会中无所不在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则”[2]66。因而在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众文化中已没有冲突和变化。即使有冲突和变化,这种冲突和变化也不会造成任何紧张,因为冲突和变化的结果都是处于人们预料之中的,是被预先规定的。
大众文化也能变成艺术。既然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即无冲突、无矛盾的文化工业,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出现的,那么它就有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可能性。这应该可以看作是阿多诺思想中的一个隐含的结论。在《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一文中,阿多诺强调,“认为以前的艺术是完全纯正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只从艺术品的内在联系,而不从它对观众的影响来考虑问题,这是浪漫的幻想。相反地,审美所要求的一些自律性的特点,自为世界的美学要求的残余,甚至存在于大众文化的最微不足道的产品中”[2]136-137。在阿多诺看来,所谓艺术的自律性质就是指艺术内在地具有超越、否定既存现实的性质。显然,阿多诺在此处承认,大众文化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真正的艺术特质,即超越、否定的性质。以电影为例。在早期《启蒙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旗帜鲜明地指出电影已不再是艺术,而是统治阶级用来欺骗大众、控制大众的意识形态工具。“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企业,而转变成了连它有意制造出的废品,也被认可的意识形态”[3]113。但是在晚期,在《电影的透明性》一文中,他认为电影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对人类的经验进行客观性的重建,因而,“电影也能成为艺术”[2]156。
与对大众文化粉饰太平掩饰矛盾这一无矛盾性的尖锐批判相比,阿多诺关于“大众文化也能变成艺术”的论述显然更加宽容。他把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变化放入一个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貌似对大众文化的一些消极影响和作用有了更深沉的历史性分析和态度。但笔者认为,阿多诺此处的确是用社会历史的眼光来打量、分析大众文化的无冲突性,与他对大众文化一贯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相异,但并不能因此就说阿多诺改变了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而只能说这是他总体批判态度上的一点更客观更宽容的思考。因为在他有了这一分析和判断之后,他对大众文化的总体态度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
二、大众文化瓦解自身谎言的可能性
早期的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一种全新的控制形式,它凭借大众传播媒介渗透进社会所有方面,用娱乐麻痹大众,用虚假的满足欺骗大众。“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教的,心理学的影片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够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3]135。文化工业已充斥社会所有领域,它利用日益更新的技术复制经验的对象,这些复制越是密切和完整,就越容易欺骗、麻痹大众,越使大众误以为外面的世界就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个世界的不断延长。于是,大众文化成了社会水泥,它牢牢地把大众控制起来,把大众粘合在社会体制里。显而易见,早期的阿多诺认为电影用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内容的完美配合,达到了整合大众的目的。那么,这种完美的整合是否能一直完美?
在其晚期的《电影的透明性》一文中,阿多诺通过对电影为了吸引大众注意力、控制大众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的论述,得出了“大众文化本身包含着自身谎言的解毒剂”的结论。他关于“大众文化本身包含着自身谎言的解毒剂”的论述,是从分析电影这一大众文化的典型模式之意图和其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开始,并进而推广至整个大众文化领域的。
阿多诺指出,以往对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所进行的分析,总是依靠传播媒介的意图,却忽略了传播媒介的意图和它们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然而这种差距却是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传媒所固有的。大众文化按照它们的意图去影响大众,但即使这些意图的设计完全是为了大众量身定做的,意图也总是和实际效果有差距。大众并非一定会完全接受文化工业的影响,按照文化工业的意图去行事。“对电视作为意识形态电影的分析包含了多种行为反应模式,这将暗示着工业提供的意识形态的官方目标模式也许是绝不会自动对应于那些能影响观众的模式”[2]156。文化工业为了达到其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所采取的宣传模式,不会恰恰就是那种能契合观众并能影响观众的模式。换句话说就是,文化工业意欲用官方的、正式化的意识形态模式来影响和控制大众,不一定能收到预期效果。
当宣传者明白赤裸裸的、生硬的意识形态宣传不会达到它预期的效果时,“为了抓住消费者,提供给他们替代性满足,非官方的、非传统的意识形态必须在一个更宽广更丰富多彩的模式里被描绘,而不是简单地适应于故事的道德内容”[2]156。“今天,如果你在德国、布拉格,甚至是保守的瑞士和天主教罗马,随处看见男孩和女孩过马路时手挽手,豪不尴尬地亲吻对方,那么他们或许更多地是从那种将巴黎玩乐者当作民俗学兜售的影片中学到的”[2]157。阿多诺认为,相较毫不隐秘、直接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控制,这种隐秘的、非官方的变换多种姿态出现的大众文化产品不易引起消费者的反感和拒绝,更能达到预期目的,起到灌输意识形态的作用。
因此,为了吸引消费者,打消消费者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警惕和抗拒,让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控制更有效,更隐秘,大众文化的产品就必须包含一些非正统的、非官方的,甚至是异己的意识形态内容。就这样,“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本身,在它试图控制大众时,变得像它旨在控制的那个社会一样,内在地具有对抗性了。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包含着对自己的谎言的解毒剂。没有其他理由可以抗辩”[2]157。“通过选择想必已被清洗了主观意义的对象,这些电影注入了有着准确意义的对象,而这些意义正是电影试图抵制的”[2]157。
于是,大众文化这一社会粘合剂本身变得不再是铁板一块,它自身内在地包含否定自己,突破自己的因素。这看似是阿多诺对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的分析结果,是阿多诺晚期对自己早期关于文化工业的悲观思想的反思,其实这一结论早就蕴含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里面了。按照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否定是绝对的,每一事物都包含否定自身和超越自身的因素。那么,大众文化包含自身的“谎言的解毒剂“就是必然的结论。
三、大众反抗的可能性
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立场坚定地批判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用娱乐和消费同化乃至麻痹大众,使大众甘心依附于这个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同在该文中,阿多诺又指出:“但是只有因为这些娱乐消遣作品充斥了整个社会过程,消费者已经变得愚昧无知,从一开始就顺从地放弃对一切作品(包括极无意义的作品)的渴求,按照它们的限制来反思整体,这种盲目的心满意足的情况才会出现”[3]135。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阿多诺并不认为消费者是很容易就能被完全控制的,消费者盲目的心满意足这种情况不会轻易出现。
而且,现实情况是,随着知识的进展和统计学的普及,公众也不再是容易被愚弄的了。即使是在支持它们(指文化工业)的公众那里,要想对公众进行欺骗,使他们对这个社会心满意足也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对公众的愚化不能落后于同时期知识的进展。在普遍运用统计学的时代,在银幕上还把群众与百万富翁等同一致起来,真是莫大的讽刺;在法律上迷惑大多数的群众是莫大的愚蠢。因为或然率的计算已表明了意识形态”[3]136。阿多诺接着指出,随着技术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胜利,文化工业的生产和传播的效率有了提高,文化工业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成了家庭中的文化用品。人们有了接受它们的良好机会,但是人们也可以不接受它们。总之,只有当人们接受它们时,它们才会发生作用,否则,它们就不能发生作用。这即是说大众有选择的能动性。尽管文化工业的产品已经多到触手可及,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已经无路可逃,必须接受它们的影响。如果大众选择不接受它们,它们就无法影响大众。
因此,“在今天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体系本身决定的要重视消费者的要求,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消费者反抗的可能性”[3]132-133。阿多诺认为,从根本上看,消费者可以认识到,文化工业一方面可以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但另一方面的情况是,他被满足的这些需求,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他永远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一旦消费者对自己作为文化工业整合的对象的地位不满意,反抗就可能发生。
到了他写作《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的时候,阿多诺依然认为大众是大众文化控制的对象,缺乏明确的反抗意识。“这个体制以进步的名义施加在人们身上一种生产的技术力量的调整,通过这种调整,人们变成了没有反抗意识的、可以操纵的对象,以至于他们远远落后于生产技术力量中蕴含的潜能”[2]80。但他也同时指出,“尽管作为主体的人仍然代表物化的极限,大众文化必须试图一遍又一遍地控制他们:包含在这种无效重复中的恶的无限性是唯一的一丝希望,即这种重复可能是无效的,人毕竟是不能被完全控制的”[2]80。人是不能被完全控制的,人的自发意识也还没有完全被物化所掌握。因此,在目前解放民主的秩序之内,个人仍然拥有足够的自由,而这使得个人有条件为了矫正这个体制做一点微薄的贡献。个人因此得以处于一个这样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发现一些不同于纯粹管理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什么,阿多诺没有说明。但他明确指出,这些因素与管理文化之间存在着差距,“正是在这种差距之中,存在着希望”[2]113。
在其晚期的《论闲暇》一文中,阿多诺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大众从大众文化这一社会水泥渗透下反抗并获得自由的可能性。他指出:“如果我的结论不是太草率的话,那么文化工业在闲暇时间提供给民众的,确实是被消费和易于接受的,但是,民众对它们的接受和消费一定是有所保留的,即使是那些最幼稚的戏迷和影迷也不会简单地把这些都当作是真的。或许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说,这些都是非常不可信的。很明显,对意识和闲暇的整合还没有完全成功。在一定限度内,个人的真实利益仍然足够强大,可以抵制这种整合。”[2]170因此,“尤其是非闲暇领域,社会不能使一切都按照它的模式运转……我应该避免写出后果,但我想在这里我能够发现一个成熟的机会,一个或许最终有助于将闲暇时间适当地变成真正的自由的机会”[2]170。
四、简评及启示
一般认为,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激烈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家,他的文化工业思想被认为是对当代大众文化最彻底的批判。笔者指出阿多诺这一总体上悲观态度之中的希望之光,只是想表明阿多诺这一理论思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非意欲用他只言片语的述说来颠覆他本人的主流观点。从阿多诺关于大众文化、大众积极转变可能性的论述中,虽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早期文化工业结论的反思,但不能因此说阿多诺的这些反思改变了他对作为整体的文化工业的反对态度。“这并不能为阿多诺的民粹主义立场提供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松动他的‘文化整合说’的巨大底座。……文化工业对人的整合、操纵、收编与改造则是贯穿他整个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中的一条主线”[4]。那么又该如何理解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转化及大众积极反抗可能性的一点带过?其实,阿多诺的这一积极性判断早就蕴含在其非同一性哲学思想之中了。按照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思想的内涵和逻辑,每一事物本身都应含有否定自身的抵抗要素。那么,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包含有自己谎言的解毒剂应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可是阿多诺为什么没有在这一合乎逻辑的结论上大做文章呢?很明显,因为这一结论与其对大众文化的尖锐批判相矛盾。但我们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阿多诺所处的时代,大众文化的弊端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大众文化对社会和大众的危害是更加迫切需要批判的。所以,他选择了对大众文化的大力批判。
总体看来,阿多诺的关于文化工业是控制大众的社会水泥、大众是完全被动的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观点对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影响更深远,即使是对它的质疑和批判也正好凸显了阿多诺这一思想的重要性。针对阿多诺文化工业思想中的这一主流观点,许多西方理论家提出了质疑和反驳,风头最盛的是大众文化理论家费斯克。与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积极性、大众主动性的匆匆掠过不同,费斯克大张旗鼓地提出了平民主义的大众文化理论。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并不等于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控制大众的商品,而是由大众促成的文化形式,因此,大众文化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大众也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处境和需要利用和改造大众文化。不可否认,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纠正了阿多诺对于大众文化以及大众过于悲观的缺陷,但他的作法有些矫枉过正,从而滑入过于乐观的极端。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本身存在着必须加以批判的消极现象,大众也并不像费斯克所说的那样,可以无所不能地利用和改造大众文化。
对于大众文化,阿多诺过于悲观,而以费斯克为代表的平民主义大众文化观又过于乐观。因此,对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建设和发展来说,我们不能完全倾向一方而抛弃另一方。正确的作法应该是,既要运用阿多诺所提出的大众文化和大众的悲观理论审视和批判我国大众文化,又要利用费斯克所提出的乐观大众文化理论积极发展大众文化,从而避免和克服我国方兴未艾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的非理性现象。
[1] Theodor W.Adorno.“Letters to Walter Benjamin”[M]∥Ronald Taylor,ed.,Aesthetics and politics.London:Verso,1986.
[2]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al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1.
[3]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4] 赵 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1.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