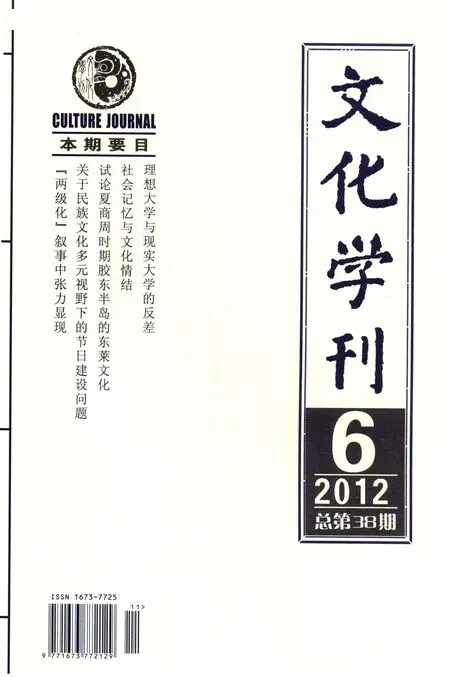陇南白马藏族美术文化概论
余永红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甘肃 成县 742500)
从白马藏族居住的地域范围以及语言、服饰以及其他民俗文化等方面综合考察,多数学者认为白马藏族系古代氐族后裔,[1]这是近年来对白马藏族族属以及文化研究的基本结论,之所以还有少数不同看法,是由于他们在与比邻的汉族、藏族、羌族的长期交流中,融合了其他民族的一些文化属性。解放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白马藏族在族属问题上归于藏族,所以也称白马藏族。西北高原地域是古代氐羌民族的发祥地,学界一致认为他们也是甘肃境内的马家窑文化以及后来的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的主人,[2]所以他们很早就已步入发达的农耕文明。大约4000年以前由于甘肃中部地区气候的变化,[3]迫使氐羌民族向南发展,以彩陶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农耕文化逐渐趋于衰落,而代之以游牧文化以及半耕半牧型文化。有文献记载以来,可知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眠山以北的一大片地区,乃是氏人比较稳定的居住区,也就是现在的甘肃东南部,以及与其相邻近的陕西西南,四川北部沿边一带,从自然地理位置来说,包括渭河、汉水、嘉陵江、岷江诸水的源头,秦岭以西及岷山以北的地区。而陇南地区曾是古代氐羌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带,赵逵夫先生考证认为,氐人就发祥于陇南西和的仇池,《山海经》中“形天葬首”的“常羊山”即今西和的仇池山,[4]魏晋时期氐人在陇南地域则建立了前后仇池、武都、武兴、阴平等政权。后来由于中原民族统治者的压迫,氐人在陇南地域的活动范围也逐渐缩小,而且是从陇南北部开始逐渐南移,之后有一部分氐人在陇南南部和四川北部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定居下来,即目前的白马藏族。
根据赵逵夫先生的观点,西和仇池一带的居民中已没有一点白马民俗的踪影,而四川平武的白马人又是经文县南迁的,现在要研究白马人的民俗文化,实际上也就只能追溯至甘肃文县的铁楼、石鸡坝等地。应该说,这里是白马人民俗文化的博物馆。[5]陇南的白马藏族主要聚居在甘肃南部文县白马河流域的铁楼藏族乡,另外还有石鸡坝乡的民堡沟也有两个村寨,总人口约2万多人,白马村寨的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的半山腰,高寒阴湿,生活条件艰苦。据白马人讲这是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迫使其居住于人迹罕至的险恶环境中。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之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所以使白马藏族的民俗文化基本保留了原始古朴的特色,这也是众多的氐人被杀戮、迁徙、融合后,仅仅遗留在汉、藏、羌民族夹缝中的古代氐人文化,所以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中美术文化最为丰富独特,既有造型独特而神秘诡异的木雕傩面具,也有华丽精美的民族服饰和刺绣;既有古朴原始的民居建筑艺术,也包括文化寓意深厚的宗教绘画,同时还包括富有白马藏族民俗文化意味的家具以及其它装饰品等。综合起来考察,白马藏族的美术文化又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即艺术形态的综合性,形式因素的独特性,文化寓意的深刻性,制作工艺的原生态性,同时也体现出美术类型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一、艺术形态的综合性
由于白马藏族特殊的居住环境以及延续了古老民族的文化习俗,从而形成他们相对封闭独立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使白马藏族的民族文化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有机整体,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相互融合,并且都与白马藏族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美术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原始形态的美术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几乎没有区分的界限,处于一种相互包容、渗透、混沌未分的状态[6],当它发展到纯艺术的成熟阶段后,形式因素得到凸显,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建立在“艺术的反映”基础之上的 “既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关系,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独立分支,这也是现代美术与原始美术的本质区别。白马藏族的民族文化延续了古老民族艺术文化的基本特征,民族艺术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艺术文化与其它文化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美术作为白马藏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融合在白马藏族的现实生活与文化大系统之中,没有作为民族的纯艺术形态存在,而这正体现了白马藏族美术的基本特征,以及与民族风俗与文化的有机统一。
二、形式因素的独特性
美术作为视觉艺术,独特的形式感是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文化符号,由于白马藏族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生存环境的影响,其民族艺术也体现出独特的形式感,是白马藏族区别于藏族、羌族和汉族等其他邻近民族的主要文化符号。将白马人划归藏族,有白马藏族民俗文化受藏文化影响的因素,但这并不能说白马人就是藏族,在白马藏族美术文化中有其自身独立的民族个性品质。这其中以服饰文化最为典型,尤其是服饰中的图案,不仅形式与其他民族迥异,而且包含了白马藏族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综合文化信息。白马藏族的“沙嘠帽”是民族服饰的典型符号,别致的造型,洁白的色彩,独特的白鸡尾羽装饰都体现了民族服饰文化的独特个性。羽毛在我国的民族服饰中被广泛应用,但白马藏族“沙嘠帽”的装饰最为特别,以其素净、神秘、淳朴以及别致的形式结构,成为白马山寨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民族风情,我们在藏族服饰文化中难以找到相似的因素。白马藏族妇女的服饰“百褶衣”色彩华丽、结构巧妙、装饰图案精美而富有民族文化寓意,既不同于藏族服饰,更不同于羌族、彝族等民族的服饰,例如彝族亦有“百褶裙”,但结构和裙褶没有特别之处,而白马藏族“百褶衣”则将上衣和裙子有机结合,并且裙褶位于身后,褶数为24折,代表一年的24节气,体现了半耕半牧民族服饰文化中的农耕文化意蕴。坎肩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也较为普遍,但白马藏族的坎肩则以其后背月亮纹、星星纹、太阳纹等独特的图案显示出民族个性。另外白马藏族妇女的鱼骨牌头饰也十分特别,圆润洁白的鱼骨和鲜红的毛线巧妙搭配,形成独特的头饰效果。再如他们的民族傩面具,以怪异的造型、神秘的色彩和强烈精神意味突出了面具的民族文化个性,尤其凸出的双目以及额头正中的纵目更为特别,成为其民族美术文化的典型符号。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也体现出“土墙板屋”的原始结构,造型古朴,结构独特,装饰别致;他们居住在高海拔的大山之中,民居建筑依山势而排列[7],层层叠叠,形成自然而又独特的村落布局,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白马藏族的民族宗教绘画由于受其民族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的影响,也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造型稚朴,色彩强烈,人物形象面色凝重,双目凸显,既有白马藏人的生活原型与现实基础,又折射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符号特征。
三、文化寓意的深刻性
由于白马藏族民族文化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美术与文化的一体性,可以说他们的美术就是视觉形象化的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形式和符号,是我们解读和研究白马藏族民族文化的主要依据之一。白马藏族美术的文化意蕴一方面体现在其美术本身就是该民族的一种独特视觉文化,鲜活艳丽的色彩、神秘怪异的造型、粗犷质朴的线条,形成独特的白马藏族美术的视觉形式,另一方面更表现在其美术形式背后蕴含的深层民族文化寓意。例如,怪异神秘的白马藏族傩面具中,其实体现了深厚的民族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的痕迹,尤其是面具中的“纵目”和“凸目”造型,是氐人先祖“雕题”遗俗以及形天“以乳为目”的形象化体现,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另外,白马藏族妇女服饰上的刺绣图案,也具有民族文化符号的特征,是写在民族服饰上的民族文化,其中也包含了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农耕崇拜等文化寓意,这些图案的内容除了太阳、月亮、星星、自然花卉形象以外,还有“纵目”和“凸目”的民族文化符号痕迹,同时还通过数字的形式隐含了农耕文化意蕴。这种深刻的文化寓意以及独特的视觉形式达到了有机融合,使其民族美术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达到了形式与精神、文化的高度统一。
四、制作工艺的原生态性%
陇南白马藏族聚居区域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滞后,交通不发达,与外界的交流十分有限,所以好多原生态文化资源不为学术界所关注,受现代文明的冲击相对较少,也避免了大规模的商业性开发,这种劣势反而使白马藏族的许多民间艺术保留了原生态性,对考察研究提供了最真实的范本,为专业研究者的考察研究提供了最真实的图像资料。白马藏族的民族服饰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和优美的形式感,不仅结构方面传承了民族传统形态,而且服饰上的装饰图案也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属于古老的民族文化符号;白马藏族民族服饰的制作虽然也受现代商业文化和汉文化的冲击,但其民族服饰的款式始终保持着民族个性,制作方法和工艺也保留了传统的制作程序,而且服饰图案的基本格式也相对固定,代表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含义,可以说其民族服饰无论结构、样式方面,还是文化寓意方面,都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态特征。再如白马藏人系的腰带,目前还用传统的织机来编织,长度达4米,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白马藏族民族服饰的标志 “沙嘠帽”,目前依然运用传统的制作方法,制作工具、工艺、程序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装饰形式、内容也固定。白马藏族的傩面具虽然在色彩方面有现代因素,但其造型符号却始终不变,民族文化的基因一直流传,目前白马藏族的傩面具制作有专门的传承人,基本造型和样式、色彩有特殊的规格,代表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含义,也是地域美术文化中的亮点。
五、美术类型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由于白马藏族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民族美术对现实生活的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民族经济、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发展与变迁,与他们现实生活紧密关联的美术文化会随之变化。白马藏族在历史上曾长期与汉族、藏族、羌族等民族杂居,所以在民族文化方面也长期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尤其上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因素、以及随后的全球化、工业文明等,都对白马藏族民族文化形成强有力的影响和冲击,致使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被同化或流失,但他们以宗教文化为主流和核心的民族文化却得以长期传承。鉴于以上原因,致使他们的美术文化也体现出类型的不平衡性,具体表现在:民族傩面具及其装饰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由于宗教活动的主体地位世代传承,所以使傩面具体现出长盛不衰的发展状态;服饰文化虽然受以上因素影响,男子服饰和儿童服饰濒临消失,但妇女服饰基本保留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以上两个类型形成白马藏族美术文化的主体,总体上代表了民族美术文化的面貌。由于长期与汉族比邻而居,所以目前的建筑风格与当地汉族基本趋于一致,但从民族历史来宏观考察,这一带是古代氐族活动的中心地带,所以当地汉人也大多为汉化的氐人,民居建筑风格应为白马藏族的民族传统风格,从当地遗存的较为古老的民居来看,基本结构和装饰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民居建筑也是白马藏族美术文化的主要类型之一。宗教绘画和雕塑中,也有较为强烈的白马藏族民族风格,但近年来白马藏族民间画师十分稀少,大多数宗教美术由汉族民间画师来完成,致使一些民族美术文化的符号特征被淡化,总体上已趋于衰退。白马藏人的家具、生活用品、小型装饰品等类型,则民族特征已十分模糊,体现出白马藏族目前的生活状态,传统民族文化的成分已很少。
所以,和陇南汉族民间美术文化相比,尽管白马人的美术文化仍然具有较为鲜明的民族特色,但也标志着白马藏族民俗文化的衰变与退化,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正是由于民族文化的衰变与蜕化所导致的。这种现象既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共同处境,也是全人类都必须面临的文化多样性与文明进步两难处境。如何在促进白马人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同时,又能有效保护和传承白马人民族文化,是同时关系到行政、文化、学术的综合问题,需要借助各种力量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1][1]段丽波,龚卿.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溯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4).
[2]安成邦,等.甘肃中部4000年前环境变化与古文化变迁[J].地理学报,2003,(5).
[3]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J].历史研究,1965,(2).
[4]赵逵夫.三目神与氐族渊源[A].西和县志办公室.仇池论集[C].2010.54.
[5]邱正保,邱雷生,田佐.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论文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8.
[6]刘峻骧.中华艺术通史·原始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
[7]刘光华.先秦时期甘肃的民族(一)[J].西北民族研究,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