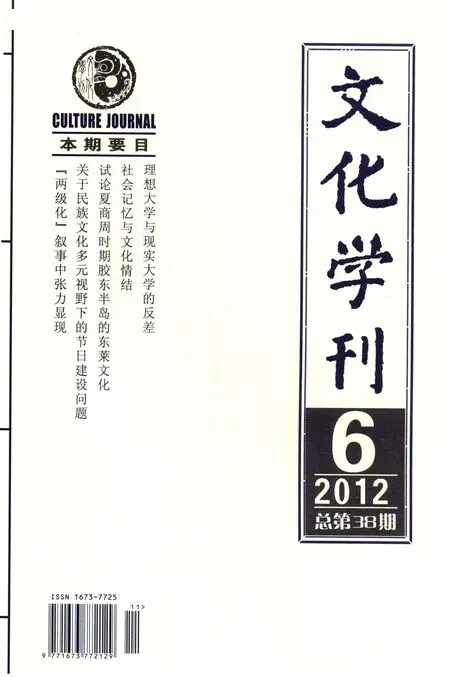隐语行话研究与公安言语识别
董丽娟
(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1)
隐语行话,即所谓秘密语,是作为世界大多数民族都具有的一种语言变异现象而存在的。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秘密语的使用源远流长。中国的秘密语起源于先秦,发达于唐宋,盛行于明清, 传承至现今。
一、隐语行话的涵义及其特征分析
(一)何为“隐语行话”
隐语行话,又称 “隐语”、“秘密语”、“行话”、“市语”、“春点”、“锦语”、“市语”、 杂话”或“黑话”等,是一种封闭性、半封闭性的符号系统,其主要特征在于遁辞隐义或者谲譬指事。它的使用目的主要是满足某些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维护其内部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的需要。
(二)隐语行话的普遍特征
作为一种特定的语言文化现象和一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特殊的言语习俗,隐语行话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口头性。就表达方式来说,口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举例来说,“秘密语”作为语言出现,“市语”作为口头表达的方式出现,“杂话”和“黑话”也主要是通过口语表达出来的。
其次,就表达主体来说,无论“秘密语”、“市语”、“黑话”还是“杂话”,都有其特定的使用对象,隐语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因人设隐的,离开了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隐语就不能够成功地表达其所蕴含的意思。
第三,就表达的时效性而言,其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间性,超过一定的时间,特定的隐语就有可能被替代或抛弃,不能再被完全正确地理解。
二、犯罪活动中的隐语行话分析
犯罪团伙或组织往往将隐语行话作为犯罪的工具,以秘密进行其违法犯罪活动。因此正确识别和判断犯罪活动中的隐语行话,对于公安机关迅速识别预谋犯罪,打击、惩治违法犯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犯罪隐语的涵义
作为隐语行话的重要组成部分,犯罪隐语特指犯罪集团或犯罪群体内部成员用于沟通和交流、特殊的、具有隐讳性的语言。犯罪隐语中蕴含着大量涉及犯罪性质、内容以及犯罪人员身份等各方面有意义的信息。
(二)犯罪隐语的独特属性
隐语不是独立的语言系统,是某些社会群体所使用的故意不让外人知晓的秘密词语,是常见的社会方言之一。从民俗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犯罪隐语作为一个复杂的封闭系统,有着不同于自然语言的特殊属性。
1.犯罪隐语中存在着大量的一词多义、异名同指现象,且存在“万能词”。从语法意义上分析,犯罪隐语中的绝大多数多义词是相互联系的。举例来说,双义词“鬼”说的是警察或者卧底警察;三义词“爆甲”和“爆格”分别说的是入屋盗窃、撬盗保险柜和破锁盗窃。在异名同指的词语中,指代“警察”的词语是最多的。比如,“鬼、针、枪、差佬”等词都特指警察。若要细细地分析,“鬼、针、国宝”专指卧底警察;“车、灯、军装”专指巡警;“花狗、老保、看门狗”专指门卫。作为万能词出现的,比如“开工”一词,在不同的案件和犯罪团伙中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它既可以笼统地理解为准备作案,也可以理解为去盗窃、去抢劫、去卖淫等犯罪活动。
2.犯罪隐语中涉及钱和重量的表达在不同类型的犯罪团伙中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不一致性,并且用来表示的数词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贩毒集团的交易中,由于钱的数额一般相对较大,因此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数字都有被缩小的趋势:比如,一个太阳指代1亿元,1毫子指代1万元,一文指代10万元;而在一般的零售毒品犯罪中,1毫指代100元,与前述相比缩小了一百倍。在涉及毒品交易重量的表达中,以海洛因为例,根据海洛因的加工惯例,出现了如下隐语:350克海洛因被称为1块、1番、半件或者半套;700克则有了1只、1对、1件或1套的隐语称呼。
3.不同案件类型的隐语分别呈现出了萎缩和发展的相对状态。由于历史比较长,盗窃案件的隐语非常丰富。从对公安干警的称呼到对社会上各类其他人员的称呼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自己的称呼;从警械到盗窃的各种不同动作以及犯罪分子间相互提醒的话语,所涉隐语几乎无所不包。举例来看,“钳手、钳工”指一般盗窃分子;“高人、老鬼、老雀”指盗窃高手;“新仔、茄子”是对扒窃新手的称呼。对于盗窃动作的指代也极为丰富,先后出现了“搜廊、开柜、探路、反板、挤档、捞面”等二十多个词汇。关于盗窃时相互提醒的话语也涉及了“散水、风大了、爆机”等相关隐语。但是,由于盗窃方面的隐语流传久远,多年以来,新生盗窃行业隐语极少,呈现出萎缩的状态。
与其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涉毒案件的隐语却呈现出了积极的蓬勃发展态势,这与毒品犯罪本身的高风险性、高秘密性是分不开的。从对吸毒人员、戒毒人员和贩毒人员的称呼到对毒品的名称、吸食方法、毒品评价、以及戒毒过程、制贩毒过程等的称谓都有了非常细致完备的发展,其丰富程度令人瞠目。在毒品交易中涉及到的隐语主要有:贩卖毒品的“出米、出货、派米”等;购买毒品的“拿货、买米、海鲜”等;毒瘾发作时的“师傅到、老点、点瘾”等。毒品犯罪中隐语行话的发展不仅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体系,而且呈现出明显的继续发展变化的态势。
4.犯罪隐语的封闭性。犯罪隐语狭隘地流行于各种黑社会集团或组织之中,再加上不同黑社会组织间严密的利害关系冲突性,不同黑社会间,其犯罪隐语也是彼此封闭、各不相同的,这要求成员必须充分地保守各自的秘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绝不会使用同一套隐语,从这个角度看,黑社会组织越是隐秘,其犯罪隐语的封闭性就越强。一旦有秘密语不慎被外人所知便失去了它的保密功能,因此这些隐语往往会被立即放弃或者重新翻造。80年代澳门赌场的职员曾把运气极差的赌客称作“灯”,而当这个词慢慢被赌客所熟知后,该词则马上被“闪闪亮”所替代了。
5.犯罪隐语的口头约定俗成性。犯罪隐语具有浓重的口语化色彩,它们只是口头流传而无正规的书面表达形式。再加上其使用上的频繁性,因此,犯罪隐语的字面意思往往很简单,其秘密性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字面意思以外的隐性意义上。
另外,犯罪隐语的创造和使用过程也是经过严格的内部约定的,而并非随意创造使用的。由于犯罪行为总是涉及黄、赌、毒等社会违法活动,因此犯罪隐语在表现风格上往往带有无耻、露骨和玩世不恭的特点。举例来说,“抢大米”是对“轮奸”的代称,“咬老软”则指的是“靠妓女为生的人”,这些词均带有戏谑意味。
6.犯罪隐语的语言组织上的寄生性和传承性。犯罪隐语大多是传统方言的基础上变异发展而来的,并且这种变异仅仅局限于词义的语用层面上,因此,它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语音、语义和语法系统。犯罪隐语的传承性又称连续性,是说不同时代或地方的犯罪隐语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诸多犯罪隐语的来源是相当复杂的,它结合了一定的历史遗留也传承了一定的地域特点。
(三)犯罪隐语的类别
1.黑话。黑话大都以一个短句作为符号单位,是用来清晰明了的识别对方身份和描述情况的。举例说明,旧时的中国东北曾经用“报报蔓”来问姓氏, 若回答者说“虎头蔓”则表示姓王、回答“顺水蔓”则表示姓刘。然而,现行的黑话则往往是以一个词组为符号单位的。例如“打群架”则称为“开片”,“单挑”则称呼为“只秋”、“用刀砍人”称呼为“劈友”等等。
2.暗语。暗语的表达和使用范围都非常狭小,它仅仅局限于约定的双方,具有突出的专用性和定向认同性。暗语往往使用常见的词汇,冠以借代、双关的修辞,来影射交际双方心照不宣的本意, 以进行秘密的沟通联系。
(四)犯罪隐语的功能
《武经总要后集·隐语》中这样描述军中的秘密交流:“军中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号隐语以喻之”。由此可知,隐语行话的使用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守秘密,以达到沟通成功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其使用功能:
1.内部交际。用于行业的内部交际以保守秘密是犯罪隐语行话使用的最根本属性,同时也是其创制的首要目的,是犯罪集团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伴随地域、风俗的不同,隐语中对同一事物的称呼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举例来说,对于小扒手,北京地区称为“小弟”、青岛地区称为“小皮子”等各具特色。
2.身份验证。懂得并会使用某一行业的犯罪隐语,即说明是该行当的人,不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因此犯罪隐语都可以用来验证对方的身份。犯罪团伙中还存在着一种对话式隐语,以达到在特殊情况下立即验证对方真实身份的目的,保密性相当高。
三、犯罪隐语研究与公安言语识别
犯罪隐语是违法犯罪人员预谋犯罪、实施犯罪的重要工具,犯罪隐语中包含了大量关于犯罪活动、内容、罪犯身份等的各方面信息。要想及时准确的破解犯罪隐语中的各种信息,对于民俗隐语行话的常识了解至关重要。
首先,犯罪隐语仍然遵循着语言的基本语法结构,但是其中已经包含了丰富的联想因素。比如,将“人贩子”称呼为“长线红娘”的隐语、将“相机”称呼为“咔嚓”的隐语等等都形象的蕴含了民众的想象。再如 “娼妓”,北京、辽宁、上海、云南等地分别有了“暗门子”、“抽子”、“拉彩”、“马马”等的称呼;对于“嫖娼活动”,北京地区称“挂蜜”,云南地区称“钩旦”,辽宁地区称“挂点”,河南地区称“挂癞子”等等。对于“扒窃自行车”的犯罪行为的称呼则更加形象,比如“登轮”、“拍轮”等等。
其次,犯罪隐语的构成规则是合乎词语组合的语法结构的。虽然犯罪隐语数量繁杂、内容多样并且不断的发展变化,但是实际上它们都与具体的事物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根据将扒窃行为称作“吃”的隐语称呼就衍生出了诸多类似的隐语词汇:北京地区称 “扒窃”为“吃现成的”;山西地区称其为“吃小钱”;“扒窃成功”成都地区称为“吃到”,如果扒窃的钱物比较可观,则称为“吃到肥的”。根据扒窃的方式的不同,不同地域也有着不同的隐语称呼。例如,在火车上扒窃,北京人称“吃大轮”、四川人称“吃滚滚钱”;扒窃裤兜,北京人称“吃地道”;夜间入室扒窃,河北人称“吃黑道的”、昆明人称“吃露水钱”;在人流中行窃,重庆人称“吃活的”等等。
第三,公安言语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近年来,随着以匿名信或纸条等方式进行勒索、恐吓案件的日益增多,社会恶劣影响日益严重。广泛应用民俗语言学的言语识别技术根据恐吓信、敲诈信、诬陷信等作案工具中所反映出来的方音、方言词汇、地方习俗字及其语法结构来初步判断犯罪嫌疑人的所在地、籍贯等因素,对于进一步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地域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缩小侦查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同的犯罪信件、犯罪标语或传单能够表现出不同的言语特征,这对进一步辨识嫌疑人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以及精神状况和生理状况,从而对嫌疑人进行“画像”,以更准确、具体的查找嫌疑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事实上,言语识别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作为证据,进而指正作案人。
四、犯罪隐语研究的重大功能性作用
要想及时准确地发现犯罪线索,提高侦查效率,熟知特定的犯罪隐语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犯罪隐语的熟悉直接有益于公安干警迅速及时地收集犯罪情报,知晓预谋犯罪活动。在嫌犯审讯方面,公安干警艺术、策略地穿插运用嫌犯熟悉且适用范围不大的隐语行话,更容易使嫌犯无处遁形,突破其心理防线,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找到破案突破口。
将民俗语言学的知识作为刑事技术手段应用于破案侦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在科学技术水平迅猛发展、人类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今天,该理论体系仍然需要不断的丰富与完善。随着科技化、智能化犯罪的增多,破案难度的大大增加,也对警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增加知识含量的广度和深度,掌握现代化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熟识民间隐语和风俗,对于公安执法人员极为重要的。
[1]李迎春.犯罪中的言语现象与犯罪言语识别[J].公安大学学报,1992,(1).
[2]陈健蒙.涉毒隐语、行话释义[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0,(2).
[3]郝志伦.汉语隐语论纲[J].巴蜀书社,2001,(2).
[4]黄娟娟,肖辉,韩莉.言语识别技术在侦破恐吓勒索案中的应用[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