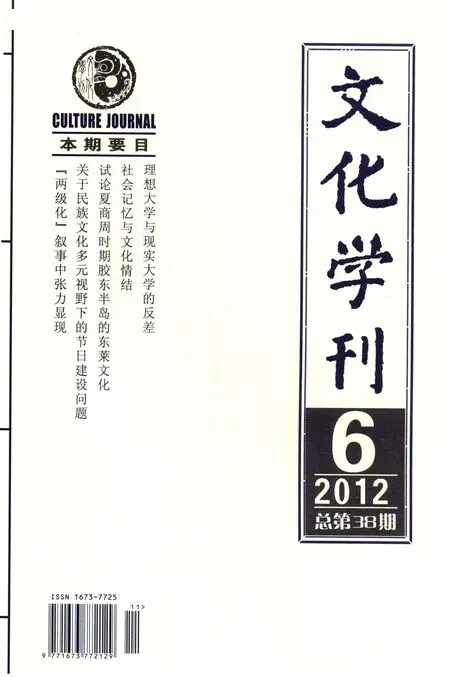史华慈的文化观及比较文化思想
徐 强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3)
众所周知,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长期从事近现代中国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所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的崛起》(1951)、《共产主义在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1968)、《中国及其他问题》(1996)、《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1964)以及《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引人瞩目、影响深远。但我们也知道,史华慈并不仅仅是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已,实际上他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一位具有深厚人文关切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思想史研究、比较文化研究背后隐藏着他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s)和人文精神。本文一方面将尝试着发掘史华慈本人的文化观和比较文化思想,阐明这种文化观同他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试图理解他的文化观和比较文化思想又如何影响了他对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的解读。这样做的目的是一种不同的文化观和比较文化理念,从而为当今时代研究、文化比较等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和思路;同时也希望能够推动我们在新的情境下重新反思、梳理和阐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使之能展现出应对当下的、普世性问题所具有的新意义和新价值。
一、史华慈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切
依解释学的观点,思想的解释者总是生存和生活于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之中,因而他必然会被他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和语言等等塑造,这决定了每一种解读都处于某种受历史制约的视域之中,他总是带着已经形成的前理解、前见解进入解释或解读。[1]史华慈自然也摆脱不了这种限制。其实,在史华慈的文化观、比较文化思想中,包括他的中国思想解读背后,隐藏了或预设了他深刻的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这种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知识背景决定了他对文化、文化比较的整体理解,所以对这种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的把握实际上就构成理解史华慈的文化观和比较文化思想的前提。那么,这种问题意识或人文关怀是什么?
首先,从根本上讲史华慈本人终其一生都对人类命运、人性奥秘有一种深切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史华慈能够成为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原因。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背后隐藏的深刻意图是努力探索人的复杂的思想世界,去理解人的奥秘及其命运,其中包括“生死爱欲这类人生头等大事的奥秘”、“个人之间与群体之间人际关系无法穷尽的奥秘”、“人和他周围的浩瀚的不属人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个无底洞般的奥秘”等。[2]林同奇曾指出:“人性的奥秘实是史氏人文主义的出发点或基石”,[3]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决定着他的思想史、文化研究的取向。
其次,对于人,史华慈从年轻时就形成了一种基本的观念,即人根本就是一个矛盾结合体,一个活生生的吊诡,“一种充满 ‘悲剧性、复杂性’的受造物”[4]。他认为,人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可堕失性(fallibility);另一方面却有一种自主的、超越的能力。人的自主性展示了人的灿烂辉煌,人的可堕失性则造成人的无知与卑贱,人的吊诡性在于自主性与可堕失性不仅并存,而且共生。借用帕斯卡(B.Pascal)的看法,人是“万物的裁决者,同时又是一个低能儿,一条泥土中的爬虫”。[5]正是基于对人的这种吊诡性的理解和体认,史华慈在文化研究中特别关注“人的有限的自由”或“有限而脆弱的自主性(autonomy)”,不断追问 “同一个人是如何可能一方面被束缚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时空、自己的社会阶层和自己的心理历史之中,另一方面又可以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和看法可以建立在事物之本然和应然之上。”[6]可以说,史华慈的整个文化研究都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并一直试图对此做出有效的回应。
再次,基于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人的吊诡性存在的体认,史华慈对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横行的 “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深致不满,这种精神最珍视的价值是自我肯定、积极行动、无限扩张和无止境的控制主宰。此种精神激荡起了诸如“化约主义的自然观”、“人类中心的主体主义”、“社会技术工程取向”等文化思潮。史华慈对这些精神的横行深存警觉,认为“化约主义的自然观”和“人类中心的主体主义”片面重视人的工具理性,把人做简单化、平面化处理,切断了人和超越的联系,断绝了人间价值的超越源头,而“社会工程取向”则将人机械化,消除了个人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提升人的精神与道德素质的必要性。[7]对这些精神的批评和反思,构成其文化研究的直接动力,他努力要做的工作是从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可供借鉴的资源,以克服西方文化自身存在的不足。
最后,带着对人性及人类命运奥秘的追问、对人类自身吊诡性存在(“自由又受限”)的体认,以及对于化约主义、社会技术工程取向将人类简单化、粗暴化处理的不满,史华慈让自己的研究进入到人类的丰富的意识活动的领域,从这样一个细致、复杂的角度探讨人类思想、人类文化。林同奇曾指出:“史的终生志业就在于尽可能穷究这个错综复杂、气象万千的人的意识世界,尽可能去理解(而不是破解)这个无法破解的人性之谜。”[8]正是因为史华慈坚持人的意识活动的复杂性,并从这个角度探讨文化,所以,他对于结构主义等种种文化解读模式深致不满,而他的文化研究就要对这种将文化结构化、固化的文化观进行反省,思考真正“理想的‘多元文化社会’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图景”,[9]真正理解文化,从而也是真正理解人、理解人的奥秘、理解人的“全部复杂性”。
总之,以上便是对贯穿史华慈本人整个学术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和问题意识的简单概括,他的文化观或比较文化思想实际上都是以此为根基和前提的。这些问题和意识根本上决定了他如何看待文化、如何做出文化的比较研究,而他的文化观、文化比较思想可以说都是在回应着他的根本的问题和人文关怀。
二、文化观
正是因为史华慈带着如上独特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展开他的文化研究,所以,他的文化观展现出颇为不同的特色。概括的说,史华慈在文化观上提出了如下看法。
(一)弱势的、谦虚的文化整体观
基于对人的奥秘及人的意识活动的复杂性的理解,史华慈自然地倾向于从如下的角度把握文化,即认为立足于人的复杂的意识活动的人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 “围绕着一些 ‘无法确解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s)所展开的持续的会话或辩论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往往是众声喧哗的对话和辩论过程”。[10]那么,这样看来人类文化就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已确定的、固定的整体,而只能是一种未经决定的“不稳定的、相当松散的整体”,它对于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和未来的种种可能是完全敞开的,它“是一个在人的主动参与下形成的动态发展的整体,并且随时会受其内部和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差异——地区、时间的差异,不同文化群体的差异,乃至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差异,而绝不会是铁板一块的封闭整体。”[11]对于这种文化整体,我们只能说是“远为松散、脆弱的大有问题的一种整体”,这便是史华慈所说的“弱势的、谦虚的文化整体观”。
立足于对人的复杂性和吊诡性存在的深刻体验,史华慈不满于文化人类学把人类文化结构化、模型化、静止化处理的做法。在这种文化观中,文化被看成是隐藏在人群背后的固定结构或系统,他们通常认为,一种文化有其独特的稳定结构,它决定处于该文化中的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在一种文化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依照范式所决定的、稳定的深层机制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样人类活动便只不过是普遍的文化模式或内在结构的表面的“具体例示物”[12]罢了。这便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哪怕是有限的)自由,这与史华慈对人的基本预设是不符的。史华慈认为文化不可能是这样一种状态,它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是一个“非化约”,也是不能“化约”的思想世界。它不像某些研究者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一个由许多有争议,甚至互相矛盾的方面组成的综合体。文化内部经常存在着各种张力,一种“问题性”,或称为“富有成果的含混性”,从而构成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多元格局。史华慈的这种文化观显然应和了上文所分析的他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
(二)“文化导向”或“文化取向”
在此基础上,史华慈提出他的 “文化导向”说。史华慈认为人类历史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每种文化中都存在着一种或几种占统治地位的、持久不衰的主导性文化取向,他把此称之为 “文化导向”或 “文化取向”(culture orientations),比如,他认为普世王权、整体主义的内在秩序等构成中国传统的文化导向。史华慈这里用“文化导向”一词,一方面表明了他同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结构”或“文化蓝图”不同;另一方面又同他所秉持的“弱势的、谦虚的文化整体观”统一起来。“文化结构”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Levi-Strauss)的观点,而“文化蓝图”则是格尔茨(Geertz)的看法,他们都倾向于认为文化是一种稳定的、体系化的结构或模式,文化隐藏在人类活动的背后,构成人类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人的所有活动都被这种文化结构或蓝图内在地决定了,人的活动无自由可言。但是“导向”(orientations)一词却不同于此,它不像“结构”或“蓝图”那样刻板,它是相对弱势的,作为“导向”它一方面表明文化对人的思想与行动具有一定的诱导与塑造作用;另一方面却也给人的自主性留下了活动的空间。史华慈认为,文化导向虽然限定了人的可能的选择范围,但是在剩下的若干可能中,如何选择仍取决于个人。虽然文化导向对人有所限定和指引,但是这种文化导向内部绝非铁板一块,而是有深刻的张力,并且总有一些人或思想派别能够对这些文化导向做出自觉地思考和反省。他们围绕各自不同的思考进路对共享的“文化取向”作出极具对话性的解释,并在思想派别间展开积极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创造出范围更广阔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的层级在对话甚至辩讦中获得提升,而整体的“文化取向”则因此被丰富和强化。显然,基于对人的有限的自由的理解,使史华慈不倾向于“文化结构”或“文化蓝图”说,而主张相对弱势的“文化导向”观;也因此他特别关注人在文化导向中的自由,特别关注文化活动中的有创造性的人,虽然这些人是少数的,探讨有才华的头脑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表现“有限的自由”,他说:“我主要处理的不是全体人民匿名的‘心态’(mentalities),而是其思想已记载于文本之中的少数人的深刻思考。这项事业看来不仅是不合时宜的,甚至还有可能被人称为是精英主义的。”[13]他甚至乐意接受人们对他的“精英主义”的判定,也正是立足于他的“文化导向”观。
总而言之,“文化导向”不同于 “文化结构”或“文化蓝图”,它相对自由,作为一种引导方向,它比较灵活,既为此后文化思想的探讨提供了某些方向性的指引,又并非死板的律条,它不但不会限制内部的对话和争论,反而在不断的驳难、反思中形成的“问题意识”而得以推动其自身的丰富和扩展。[14]
三、比较文化思想
正是因为史华慈秉持“弱势的、谦虚的文化整体观”,以及“文化导向”说,所以很自然地他对诸如“西方文化是x,中国文化是y”之类鲁莽的、固化的文化比较理念保持着深刻的怀疑,[15]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文化比较,而是对文化在凝固化理解基础上的粗暴论断。从根本上说,史华慈认为不同文化实际上往往共享了基于普世性生存经验或感受的共同关切,所以,存在在深层次上比较的必要和可能。
(一)为何比较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 “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盛行,这种精神主张自我肯定、积极行动、无限扩张和对外无止境的控制主宰,与此相适应,“化约主义的自然观”、“人类中心的主体主义”思潮充斥近代西方社会。这些精神和思潮的盛行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比如,他们对于人及一切所做的还原主义的、机械化的理解,使人走向平面化,切断了人与超越的价值源头之间的联系,人类中心的盲目冲动则给自然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史华慈深刻地感受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他认为,通过比较文化研究,发现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从不同文化中获得更多的人文主义资源来补救当前西方文化的单维度的、偏颇的弊病,以及回应当今人类向何处去这个涉及人类命运的大问题。他相信“以各种不同形态出现的人类的一切经验对于人生的悲惨渺小和辉煌灿烂都有其意义”,[16]通过比较所获得的这些经验越多,人类在响应环境挑战时的选择余地就越多。比如,针对西方思想界中盛行的“化约主义”一元论思维,史华慈认为在中国思想世界中存在“非化约”的、多元的思想格局,它不“抹杀宇宙中千差万别的现象,将它们全部化约成牛顿式的物质,并把一切意义和价值从宇宙中排除干净。‘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宇宙绝不是一堆死物、一架大钟表,而是充满生机和意义的过程或秩序”,[17]这正可以作为对“化约主义”一元论进行纠正的有益经验。
总之,史华慈认为不同文化虽然具有不同的主导性倾向,但是它们却都可以为解决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通过对它们的比较研究,就可以把握这些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可以丰富人类共同的经验,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比较的可能性
当然,如果要对不同的文化进行比较,那么前提是它们之间是可以做比较的,否则比较就没有意义。史华慈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进行比较的,或者说他“深信对他人的信念系统进行韦伯式理解 (the Weberian Verstehen)的可能性”,[18]关键在于,他认为人类尽管受到不同的文化、语言与历史的限制,但仍然拥有某些共同的关切和经验,或说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正是因为处于不同文化、语言和历史中的人类拥有共同的关切或关怀,并都尝试着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所以,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也正是因为文化体现的是人类面对共同的关切时做出的不同回应,所以,文化与文化之间,甚至文化内部就充满了深刻的内在张力,史华慈尖锐地指出真正的文化比较不能是仅仅得出“西方文化是x,中国文化是y”之类的粗糙的总括性提法,文化比较必须深入到文化内部,观察不同文化中的人或思想派别在面对共同的关切时所作出的不同的努力。用史华慈的话说:“只有当我们从整个文化取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意识的层面上时,跨文化的比较就会变得激动人心和富于启发性。真理往往存在于精细的差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对于x文化和y文化的全球性概括之中。”“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又再次找到了建立普遍人类话语的可能希望。”[19]这里的“问题意识”层面或细微的差别即表明文化比较是关注人们在面对问题或关切时所展开的细致的、持续不断的辩论和对话,史华慈认为只有这样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史华慈的文化观的影响,显然他的这种文化比较思想是与他“弱势的、松散的文化整体观”密切相关的。
(三)文化比较的方法
史华慈的文化比较方法当然是和以上所分析的他的比较文化思想相一致,他首先认为真正的文化比较应深入到问题意识的层面,关注不同文化之间,以及文化内部围绕共同的问题意识展开的细致的思考,并在这个层面上寻找那些细微的差别,从而丰富人类共同的经验。
葛瑞汉在评价史华慈的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比较方法,“一种倾向是运用那些超越文化和语言差异的概念,透过所有表面的不同,去发现中国思想中对普遍问题的探索。另一种倾向是透过所有的相同点,去揭示那些与受文化制约的概念系统相关的,以及与汉语和印欧语言结构差异相关的关键词汇间的差别。”[20]这里葛瑞汉所说的前一种学者就是史华慈,后一种则是指自己。他的确指出了史华慈在文化比较的特别之处,他不是对不同文化的整体做出粗糙的论断,而是深入内部去发掘人们面对共同的关切或问题意识时所展开的对话和思路的细微差别,这恰恰是史华慈文化比较的独特方法。
再者,史华慈认为既然不同文化之间往往分享了共同的关切和经验,所以,我们可以以韦伯式理解来把握其他文化、展开文化比较。史华慈说:“我认为在研究西方社会和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交遇时,必须尽可能深入地把自己沉浸(immerse)在两个世界的种种特殊具体的情况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途。”[21]在文化比较的方法上,史华慈不满于盛行于西方的“科学模式”,认为这些模式僵化封闭,无法适应复杂流变的人类经验。他认为文化比较研究者不能把自己先验地当做“科学家”,任由自己的理论去宰割他的研究对象,即有自己的思想与感情、苦难与希望的巨大的人的集体。“作为一位富有人文关切的史学家,他只能带着同情、尊敬乃至惊奇的心情走进这一片人类经验的茫茫大海。”[22]
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怀着对人性奥秘和人的意识的复杂性的深刻关注,秉持着如上所说的文化观,史华慈深入中国文化思想的世界。他始终强调,自己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的思想世界,所关注的是古今、中外人类面临一系列普世性的问题意识时的持续不断的探索,丰富整个人类应对挑战的普世经验。这是他的目的,也是他的方法。
立足于其文化观,史华慈认为借助对古老中国思想世界的观照和审视,有益于解决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价值危机。他确信中国文化中所埋藏的思想资源足以成为透视、反思当下人类思想困境的宝贵经验,比如,中国文化中的“非化约主义”倾向、整体主义的“内在论”的秩序观等等。史华慈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中西方人类分享了某些共同的、普世性关切,这样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比较和沟通就是可能的。因此,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等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本质上可看做比较文化的产物,其中始终渗透着史华慈本人的问题意识。林同奇对此曾有一个评价,他说在史华慈的作品中,“我们几乎随时可以听到孔子和苏格拉底、墨子和霍布斯、老子和奥义书、孟子和卢梭、荀子和柏拉图、韩非子和马基雅维利等等之间的对话。”[23]虽然他们基于自身的背景、文化、历史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对于应对普世性问题都是宝贵财富。
因为史华慈持一种“弱势的、谦虚的文化整体观”和“文化导向”观,所以,他对给予中国文化某种僵化、固定论断的做法保持怀疑。他自己在研究中则试图探讨 “在后世一直占据中国思想史主导地位的主要思想趋向”、“持续的文化主导趋向”,并探讨其形成过程。史华慈认为中国自上古而来的祖先崇拜、家庭崇拜而塑造的秩序观念,以宇宙论为基础的、普世王权为中心的、普遍的、包含一切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观念,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整体主义的“内在论”的秩序观等,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取向;进而他认为,主导中国文明数千年发展的持续文化趋向,是以维护和阐发传统价值观念为己任的儒家思想;而对于“为何人类偏离了天的规范”、“规范性秩序又该如何恢复”的追问,则构成基本的问题意识,这些文化取向或问题意识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发展方向。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派别大都在这样的导向中思考问题。
当然,史华慈毕竟认为既然只是导向,那么它还会给人留下自由的空间,所以在史华慈的研究中,就不仅仅是揭示这些文化导向,而是同时关注历史上有头脑的那些人如何在这种导向中发挥展示的自由能力,从而不断改变或丰富这个文化导向。所以,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去挖掘那些丰富的细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仅仅关注“中国的思想”,而要关注“中国人在他们的历史处境的框架里如何不断地想而又想。”[24]史华慈认为先秦诸子百家实际上都是有反思能力的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享的文化导向做出了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因此,中国古代文化导向内部就充满了深刻的张力,展现出丰富、活跃的局面。
五、小结
史华慈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思想者,他终其一生都试图去探寻人性的奥秘,他对于人的吊诡性存在,对于人的有限的自由有深刻的体认,他把探讨人的复杂的意识生活作为重要的目标,这些构成史华慈根本的人文关切和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意识和人文关切构成史华慈文化观和文化比较思想的基石,他的文化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都在回应他这些根本的关切,我们也必须在这些关切的前提下把握他的文化观和比较文化思想。
基于史华慈对人的意识生活之复杂性的坚持,他自然地对于那些把文化做简单化、固定化、僵化的处理模式和做法深致不满。他认为正是因为人的意识的复杂性,所以,立足于此的文化必定是 “不稳定的、相当松散的整体”,内部充满着种种差异和张力,必定是在人的主动参与下形成的动态发展的整体,我们不能对此作出类似x文化、y文化的粗暴概括,由此构成他 “弱势的、谦虚的文化整体观”。针对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结构”或“文化蓝图”说,史华慈认为文化不能作为一种稳定的、持续的结构,内在地决定着人的所有行为,使人毫无自由;他认为文化只能是一种主导性倾向,作为一种导向,它对于人的活动有所指导或限定,但是它一定会为人的活动留下一定的自由,人可以发挥这个有限的自由,对文化导向本身作出反省,使文化导向本身获得丰富和扩展。这种文化导向说显然是立足于他对人的有限的自由的体认。
在比较文化思想方面,史华慈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是存在着比较和沟通的可能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古今中外的人分享了某些共同的关切和经验。他认为也正是因为这点,通过跨文化的比较,了解不同文化在解决普世性关切时的不同思路,就可以丰富人们在应对一些共同挑战时的经验和资源,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他认为文化的比较不能停留在表面上对不同文化做出粗浅的僵化概括,真正的文化比较应该深入到问题意识的层面、深入到文化导向内部,展现围绕某些问题而体现出的细微差别,这样的比较才会有启示意义。进而,他认为要了解一种不同文化,我们不能带着科学家的傲慢态度去审视它、肢解它,而只能带着同情、尊敬乃至惊奇的心情走进它,也就是说韦伯式的同情的理解更合适。
秉持着如上的文化观和比较文化思想,史华慈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做出了有意思的梳理,他详尽地探索了中国基本的文化导向,分析了其形成过程;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真正深入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内部,特别是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非常有见地地分析了先秦儒、道、墨、法家那些有思想的人或派别,如何一方面继承了一种文化导向,同时又积极对此做出反省,并彼此之间展开持续的、有创造性的对话,不仅展现了古代思想史的活跃局面,而且为我们应对当今的一些普世性问题提供了有用的资源。
可以说,史华慈的文化观和比较文化思想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根本上是由于他独特的人文关怀和问题意识,他使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的把握文化的方式,而且或许是一种更好的方式;他在文化比较上的独特思路能够使对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进入细致、根本的层面,从而获得更有启示的成果。史华慈在他的文化观和比较文化思想基础上的中国文化研究,则向我们展现了不甚相同的中国古代思想局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如何重新反思古代文化,如何展现它的普世价值,如何让它走向世界从而为当今人类面临的一些共同挑战提供宝贵的经验和资源,实际上也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
[1]李建盛.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46.
[2][3][4][7][8][10][17][18][21][22][23]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A].许纪霖.史华慈论中国[C].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58.292.260.285.266.253.281.287.271.268.278.
[5][16]B.Schwartz.China and other matter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88.16.
[6]B.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Introduction)[M].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5.
[9][14]项念东.史华慈论中国思想世界中的“秩序感”及其文化意义[J].东方丛刊,2008,(3):210.211-212.
[11]刘玉宇.对两种思想史研究的考察——史华慈与葛瑞汉先秦思想史研究比较[A].许纪霖.史华慈论中国[C].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75.
[12][13][15][19]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程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7.3.13.13,
[20]Graham,A.C.Making out the Way:a Review of TheWorldofThoughtinAncientChinaby Benjamin Schwartz”[J].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86.
[24]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A].许纪霖.史华慈论中国[C].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