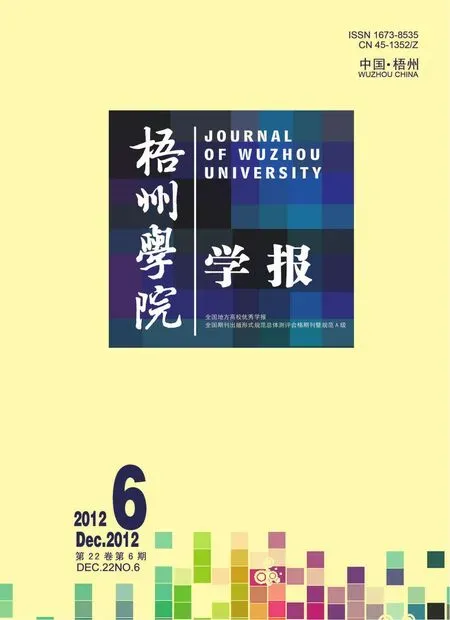精神生态失衡的悲剧
——精神生态视域下的《逾矩的罪人》
席战强
精神生态失衡的悲剧
——精神生态视域下的《逾矩的罪人》
席战强
(河池学院中文系,广西宜州 546300)
《逾矩的罪人》是劳伦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国内对其研究较少。小说讲述一个婚外情故事。劳伦斯在小说中书写了比特丽丝、海伦娜和男主人公西格蒙德精神生态的失衡,特别是对西格蒙德精神生态失衡造成的悲剧人生的书写,彰显了其精神生态观。即和谐的精神生态应当是抛弃占有和征服欲望,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同时要更改彰显个体生命的自然天性以达到灵与肉的和谐统一。人精神生态的和谐有赖于社会生态(人与人之间、男女两性之间)和谐,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相互依存。
劳伦斯;精神生态;《逾矩的罪人》;和谐;启示
一、精神生态与劳伦斯
所谓生态,简单地说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对生态问题的研究从最早对自然生态的研究渐渐延伸到对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层面上的研究。因为,随着自然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生态危机与人类的思想文化观念所操控的行为密不可分。因为人类也是生物的一种,而且人类这一生物种类是所有生物种类中唯一具有控制、支配并决定其他生物种类生存状态的一个高级灵性物种,对于其他生物的生存状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即人类的思想意识、文化理念对于自然界其他生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1973年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Naess)提出了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在关注自然环境生态的同时也把人纳入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从而对人类个体本身的关注也进入了生态学研究的范畴,并将生态学发展到哲学与伦理学领域,提出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特别是生态共生理念更具当代价值,包含人与自然平等共生、共在共容的重要哲学与伦理学内涵。我国学者鲁枢元先生认为在“生态”这一大系统中包含有“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三个子系统。在这三个子系统中,自然生态指的是自然界,社会生态指的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精神生态指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生活状态。鲁枢元先生认为,自然生态的破坏必然影响到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但精神生态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鲁枢元先生指出了“精神生态学”这一概念并定义为: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1]148。随着自然生态的破坏,人类失去了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的环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支配欲和占有欲延伸到了人类社会自身,从而在造成自然生态破坏之时也同时造成了社会生态的异化和精神生态的失衡。生态学者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却没有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水平,并且随着物质财富的累积、市场化的全面推进,人类的精神生活反而出现急剧下滑的趋势”[2]。为此,对人类精神生态的研究愈加迫切。
由于生态危机(包含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的出现,相应地出现了反映生态危机或关注生态问题的文学创作(生态文学),20世纪初期的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文学创作就猎涉到生态问题。其创作背景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工业化社会,此时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自然、社会、精神生态都急剧变化,濒临危机。劳伦斯在小说创作中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主旨是对现代工业文明下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进行书写与剖析,并在其中蕴含其生态前瞻意识。对于劳伦斯小说的研究,国内学者多集中在其《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几部长篇小说,而对于《逾矩的罪人》这部小说的研究甚少。《逾矩的罪人》是劳伦斯继《白孔雀》之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因婚外情而导致的悲剧:小说主人公西格蒙德是一位小提琴师,是家庭的经济之柱。由于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开支难以为继而兼职做家庭教师。由于生活拮据,妻子比特丽丝对他颇多抱怨和不满。家庭沉重的负担和精神压力最终使他陷入与学生海伦娜婚外恋从中寻求精神寄托,最后因对家庭的内疚和情人的不可捉摸而痛苦不堪,最终悬梁自尽以求解脱。笔者认为,在小说中,劳伦斯讲述的这一个婚外情故事并非是在做道德上的、伦理上的评判,而是借此对人类精神生态问题进行剖析,体现了劳伦斯生态意识的前瞻性。
二、《逾矩的罪人》对精神生态的书写
在《逾矩的罪人》中,对于人类精神生态失衡的揭示,主要体现在比特丽丝、海伦娜和西格蒙德这三个人物身上。
从小说着墨不多的叙述中我们知道,比特丽丝出身于一个殷实的家庭,自小就在法国新教学校读书,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和西格蒙德也是因为相爱而结合在一起,甚至为了与西格蒙德的爱而与家里人不和并在家中失宠。然而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爱情是浪漫的,而婚姻则是现实的。婚后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们互相指责抱怨,彼此心中留下的是怨恨和不满,爱情早已消失。比特丽丝常常因为西格蒙德微薄的收入而大发脾气,在得知丈夫的移情别恋后,比特丽丝从内心到言语都充满对他的厌恶与反感,并将情感转移到孩子身上,以弥补夫妻情爱的缺失。海伦娜是一个外表美丽、娇媚迷人的女人,深深地吸引着西格蒙德,“她那双像大海一样蕴含着风暴的蓝眼睛,也像大海那样永远充满了自信、孤独;她那厚实、雪白的喉部是世上最结实、最美妙的东西;还有她那双像丝绸一样柔软、像银莲花一样轻巧的小手,这一切连同大海和丘陵就是他的明天”[3]17。她身体丰腴,金发如阳光灿烂,眼睛如同大海般蔚蓝。然而,海伦娜的内心深处又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她不仅想完全拥有西格蒙德的肉体、而且她渴求占有他的精神和属于他的一切。而且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她置身于冷漠之中,在她与一切自然的日常事物间存在着一种隔阂,好像她属于一个未知的种族,永远不能讲述自身的故事。”[3]142
有论者认为比特丽丝和海伦娜这两个女人是劳伦斯笔下的“悍妇”和“大女人”形象[4]。但如果从劳伦斯对人类精神生态问题的探讨这一主题构成的一贯创作风格来看,她们同样是属于精神生态失衡的典型人物。因为比特丽丝无疑是一个“怨妇”形象,怨妇必然涉及到精神生态失衡的问题。而海伦娜所追求的只是充满梦幻色彩的爱,而不是现实中真实的爱。因而海伦娜也是一个精神生态存在严重问题的人物。
劳伦斯对精神生态失衡的书写重点是男主人公西格蒙德。有评论认为:“男主人公西格蒙德就是一个‘自然人’形象。他英俊健壮、感情细腻、有知识、懂艺术;他的内心充溢着摆脱一切枷锁,从而获取自由,即恢复其自然本性的渴望。但这样一个所谓的‘自然人’一出场便显出与社会、与家庭、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个正常人的一切极不和谐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一面,从而也注定了其悲剧性的结局”[5]。“西格蒙德的悲剧又是劳伦斯所崇尚的‘自然人’的必然结局。在劳伦斯的眼里,西格蒙德是一个符合他的理想的‘自然人’。他体格健壮,感情丰富、深沉,又有很高的音乐素养;他的内心充满了摆脱一切束缚,从而得到自由,即恢复其自然本性的渴望。”[6]但笔者认为,西格蒙德并不是什么“自然人”或“文明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现代人,是一个因精神生活压抑而导致精神生态严重失衡的男人。他的移情别恋完全是因为精神生活的压抑所致,为精神生活的压抑而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小说中并没有描写或暗示西格蒙德品性浪漫,也没有描写他与妻子性爱的矛盾,更没有描写他与社会的脱节,不适宜在这个社会生存。相反,他如同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一样谋求生存,只是生活的紧张,收入不能满足家里几个孩子的教育及生活的开销,操持家务的妻子难免有不满的说辞和脸色。为此,一对经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妻因生活重负而造成家庭不和谐,从而导致精神上的痛苦与压抑。他与学生海伦娜产生的“爱情”只能说是一种因精神生活压抑而产生的一种压抑情感的迁移,从小说中写到他们海滨度假来看,西格蒙德对海伦娜的情感并非是一种爱情,他对海伦娜的情感仍然是一种矛盾复杂的情感,是借对方来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因而西格蒙德的移情别恋既是对生活压力的释放,又是其作为精神主体的精神人格不健全的一种体现,是其精神生态失衡后的一个美丽的错误。西格蒙德的移情别恋并不是什么追求完美的爱情而是因为生活压抑所致,在其移情别恋的过程中始终充满了矛盾与痛苦,才会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占据其灵魂深处。这种负罪感就是追求个人灵魂的自由解脱与家庭责任的冲突。为了摆脱精神生活的压抑苦闷,他恋上海伦娜,但在内心世界里,海伦娜也并非是他心中的唯一,并非是他要追求的完美。所以,想着自己给妻子和孩子们带来的痛苦就使其负罪之感陡然而生,同时又因为海伦娜的无辜而觉得对不起海伦娜,这种矛盾心理,这种负罪感一直在陪伴着他,从而更加剧了他精神生态的进一步不平衡,这种精神生态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他最后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精神痛苦的一生。在小说中,作者有意识地不断强化死亡这一阴影,这不是劳伦斯有意安排的结局,而是生活的正常法则,试想,一个并非大奸大恶的人,一个有着高度家庭责任感的人,不可能是一个随意寻花问柳之人,在痛苦之时寻找情感的排泄必然是更加痛苦的,罪孽感也加深,因而自杀必然成了唯一的解脱之法。死亡无疑就是精神生态严重失衡的必然结果。这种死亡在劳伦斯笔下并非少见。如《恋爱中的女人》中的杰拉尔德就是一个因精神生态严重失衡而死亡的绝好例证。
由此可见,西格蒙德不愿受到家庭婚姻生活的束缚而移情别恋于自己的学生海伦娜,以期在与情人的浓情蜜意中获得自由,获得精神生态的平衡。然而在与情人的交往中同样感觉到精神的不平衡和不自由。因为情人对他的爱也是一种肉体的和精神的占有。从此徘徊于情感与责任的矛盾当中,最后因对家庭的内疚对情感及自由的无望而自缢身亡。由此我们可以勾画出西格蒙德的悲剧人生轨迹:“移情别恋”——“负罪感”——“死亡”。为了摆脱生活的压力而移情别恋,因移情别恋而产生痛苦的负罪感,因负罪感而自杀以彻底摆脱痛苦。三个阶段环环相扣,入情入理,演绎了一出悲凄动人而又令人惆怅怜悯的悲剧。可以说,西格蒙德是一个精神生态严重失衡的悲剧性人物。
劳伦斯的小说创作常常将笔锋指向人物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以探讨人类精神生态失衡这一严重问题。而其对人类精神生态的揭示从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里就初见端倪。从此,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关注和探讨贯穿其整部小说创作。劳伦斯对精神生态危机的关注与劳伦斯当时所处的生态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工业文明高速发展时期,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自然生态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断裂,人性受到压抑,西方社会出现了信仰真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关系出现了断裂。因而劳伦斯在其创作中总是紧紧抓住人的自然本性如何遭受到摧残,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如何遭受到破坏和人的精神生态如何走向崩溃甚至于死亡这一中心点来切入,以期揭示“在工业化和机械文明渐成为主宰一切的社会力量的时期,人们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相互关系上的变化”[3]3。可见,精神生态学者从自然的、社会的、人类个体的道德、伦理等方面阐释了精神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如何治理这一危机,而劳伦斯则是以文学的语言、生动的形象揭示人类社会精神生态危机并提出了其独特的生态观。因而,精神生态之于劳伦斯或劳伦斯之于精神生态是一种不谋而合的关系。
三、《逾矩的罪人》对构建和谐精神生态的启示
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是密切相关的,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人类世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生态学者们认为,是人类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导致了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因而精神生态的危机才是更深层的生态危机。在《逾矩的罪人》中,劳伦斯对精神生态失衡的书写及其蕴含其中的精神生态哲思,无不对当今构建和谐精神生态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人类精神生态的和谐源自于社会生态的和谐,同时社会生态的和谐也离不开精神生态的和谐。两者相互依存共生。在小说中,社会生态是不和谐的,夫妻之间没有相知、宽容与谅解,正是恶化的夫妻关系和家庭的压抑促使西格蒙德移情别恋,也正是妻子的唠叨和责骂彻底摧毁了西格蒙德的男性意志并在家庭中失去了男性应有的权势和地位。而西格蒙德与海伦娜的关系也是不和谐的,他们同样是互不了解,海伦娜对西格蒙德的爱只是一种占有,她“追求的是充满梦幻色彩的爱,而不是现实中真实的爱,即劳伦斯所倡导的理想的爱:精神与肉体的合二为一”[4]。正是这种社会生态的不和谐使西格蒙德在精神上和心灵上受尽折磨,从而一步一步走向悲剧。
其次,个体精神生态的平衡与否,与个体生命自然天性的彰显密不可分。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在于个体自然性的理智彰显。生命主体的自然天性得不到彰显,生命之花不但不能结果反而会很快地凋谢,但这种彰显必须是理智的。从西格蒙德悲剧性的一生来看,生命之花过早凋谢与其自然天性的压抑紧密相关。作为一个颇具天赋的艺术家,其天性中潜在的东西,或者说是艺术基因必须会使得他豁达、大度、开朗,其禀性应该是诗意浪漫的,然而,生活的琐屑事务,家庭柴米油盐却要系于其一生,这就必然抑制其天性的彰显。西格蒙德的移情别恋似乎是其天性的彰显,要寻找心灵栖息的港湾,而这一栖息的港湾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就是所谓的爱情,只有在所谓的爱情天堂里才能使一颗受伤的灵魂得到安慰。然而,海伦娜实则并非是他的知音,而是一个没有理想追求庸俗的女性,对他并不是理解而是只想将对方占为己有。在此,西格蒙德的自然天性并没有得到彰显反而因此陷于矛盾痛苦的境地,这就为他后来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其三,个体自然天性的彰显往往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及传统习俗。人,作为社会集团成员的一分子,离不开社会集团这一社会系统。社会的组成往往有其共同的游戏规则,人的主体活动往往受限于社会集团。社会生态系统有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丛林法则,作为生命个体的自然天性是追求自由独立,真诚率性、无欺。但社会这一复杂的生物圈相对于自然生物圈而言则更具“动物性的野蛮”。西格蒙德要想保持其率性而为,自然为社会法则所不容。而人作为个体存在于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中同样潜移默化地打上社会法则的烙印,如家庭责任感,对所爱的人负责、对子女的责任,还有内心世界里产生的社会认同感。如他人如何看待我,我在他人心目中会如何如何等等。社会生态圈内显性的、隐性的法则无不左右着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自然天性的舒展。
四、结语
总之,在《逾矩的罪人》这部小说中,劳伦斯侧重于精神生态的揭示,人的精神生态的和谐同时还有赖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两性关系的和谐),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相互依存。这一生态思想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当今世界,尤其是当今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同时也向人类的精神世界弥漫,造成精神生态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人的物化、类化、单一化、表浅化’,人的‘道德感、历史感的丧失,审美能力,爱的能力的丧失’”[2]。因而对于精神生态的重视与治理刻不容缓。
[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朱鹏杰.中国“精神生态”研究二十年[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3]劳伦斯.逾矩的罪人[M].程爱民,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4.
[4]苏燕.解读劳伦斯《逾矩的罪人》中的女性[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5]张锦.“自然人”的悲剧——劳伦斯《逾矩的罪人》评析[J].文史纵横,2007(1).
[6]王正文,程爱民.试论《逾矩的罪人》的社会意义及创作特色[J].外国文学研究,1998(3).
I106.4
A
1673-8535(2012)06-0030-05
席战强(1966-),男,广西天峨人,河池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现代文学和劳伦斯。
(责任编辑:覃华巧)
2012-09-12
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201010LX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