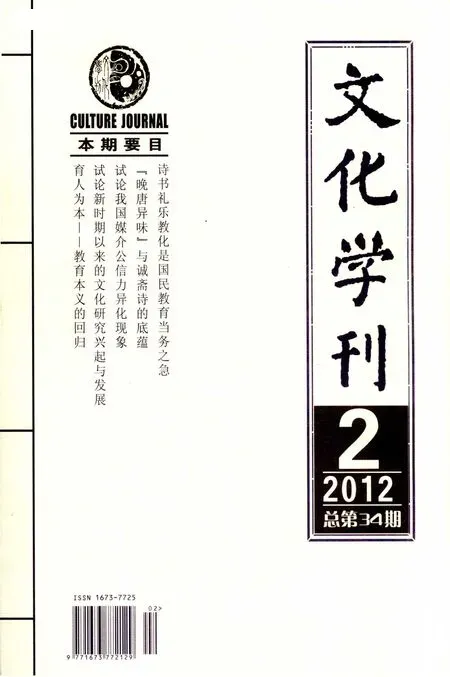杨万里“性灵”观的诗学旨归
郭艳华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是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飞跃,自此之后,“性灵”这一体现主体情感的诗学术语开始广泛出现在诗学理论中。如庾信《赵国公集序》云:“含吐性灵,抑扬词气”;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有:“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宅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七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高适《答侯少府》有:“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论。”以上只举几家之言,从中即可看出,“性灵”的情感内涵已由魏晋时期注重表现主体生命本源的探索,发展为唐代以自然感发内心的真情。不论其具体内涵有着怎样的演变,“性灵”都是以“缘情”的诗学本体观念作为其理论基础。但到了宋代,由于性理思想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情”逐渐被“理”所取代,诗学也被赋予过多的道德和社会功能,而审美和情感功能却被理学家和文人们所忽视。因此,随着中唐“文以载道”思想在宋代的承续和深化,诗文理论中的“性灵”遂不多见。直至杨万里,其创作中明显的“性灵”观念不仅体现了他文学思想的特质,而且突破了宋诗理性化、议论化、文字化的诗学品格,成为宋代文学思想转变的标志。学术界大都认为,杨万里是中国性灵文学思想的重要环节,如郭绍虞先生在阐释“性灵说”的内涵时说:“近人言性灵说者,每以杨万里、袁宏道、袁枚3人为言,这3人诚足为性灵说的代表”,[1]肯定了杨万里是明清“性灵说”的先声。此外,亦有学者认为“性灵之说,实由杨诚斋生发出来”;[2]吴兆路在《中国性灵文学思想》一书在考察性灵文学思想流变过程中,将杨万里作为性灵文学的先驱人物来看待。可以说杨万里作为明清“性灵”说的先声在文学史上似乎已是定论,但对其“性灵”观的诗学内涵却缺乏具体剖析与论证。本文认为,追求内心自适与精神超越是杨万里“性灵”观的本质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儒家重视美刺、强调礼乐教化的传统诗学观念,这是时代环境与哲学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儒道互补是中国古代士人人格模式的集中体现,当经世致用的济世理想受到外在环境的阻滞后,文人难免产生避世情绪,自然由对外部事功的追求转向精神的自适与超越,这似乎成为封建文人人格追求的必由之路。杨万里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此期的南宋王朝虽然在金与蒙古步步逼近的夹缝中生存,但却依然不思进取,苟安于半壁江山。面对家国命运面临严重威胁,文人和理学家们的忧患意识与家国责任感空前高涨,政治上的共同诉求超越了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的论争,并紧密团结在一起与主和派进行抗争,这也招致了近悻势力对道学的攻击,“道学”与“反道学”之争由此成为当时党争的主要形态。在此现实境况下,杨万里所构建的君主与臣子间理想的和谐关系也化为泡影。他希望“在下者,以进退之节而发诸身,凛凛然如执玉而忧其坠。在上者,养其下,恤恤然如艺苗而望其成。”然而,现实却与之截然相反。自隆兴和议后,宋孝宗不但意志沉沦,而且借助于投降势力的支持,以期将半壁江山的苟安局面维持下去。面对国势的日益衰微与君主的无所作为,以及自身经受党争打击的命运遭际,杨万里的人生价值取向开始由“兼济”的济世情怀向“独善”的自我完善倾斜,这使得经世致用的思想中始终潜伏着独善其身的价值因素;晚年明哲保身之际,亦未完全泯灭入世之心。多重心态交织在一起,并且升沉起伏,反映出他思想的多变及复杂性,精神自由与心灵超越的向往始终占据其人生价值追求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其创作价值取向。经历宦海浮沉、仕途失意的文人“由于不能在现实政治中成就其现实人生,便不能不转而追求个体适意的艺术人生,而这种艺术人生的物化形态便是诗文书画”。[3]杨万里同样如此。在外部政治环境的挤压下,诗人无力把握自我命运,转而将诗歌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达则振斯文以饰天下,穷则卷斯文以饰一身”。[4]显然,杨万里对文学的现实功能与抒情功能的生成背景,以及价值归属有着明确的认识,因而,在其人生价值取向的波动中,他能够随着外部环境与自身需求不断地调整其创作心态,从中可以看出他力图实现自我超越的心灵轨迹。
杨万里一生三度立朝,每一次都怀着“得君行道”的愿望去为国尽忠,时人对他的秉义忠正非常叹服。其好友周必大称他 “立朝谔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当求之古人真所谓浩然之气,至刚至大,以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5]朱熹谓其“清德雅望,朝野属心”;[6]赵蕃亦认为:“先生力学自诚明,忠信今知蛮貊行。”[7]然而,他的清正直言、忠心义胆却被孝宗认为是“直不中律”。自南渡后,不论是高宗还是孝宗,他们内心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苟且偷安,在南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中享乐度日。他们在内心中非常惧怕主战派的力争反抗,以及理学家的道义劝讲,孝宗视杨万里为“直不中律”与其刚正不阿的个性直接有关,并最终因为张浚力争配飨之事而遭贬谪。次年(公元1189年),孝宗内禅,光宗即位,杨万里又被召回京城。抱着辅佐新主的愿望,他再度立朝,这也成为其最后一段政治生涯。在此期间,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刚毅狷介、直言纳谏的风格,并因此得罪权臣。朝廷上下的昏聩使他彻底绝望,他也意识到“某不幸,平生多以忠信获罪”[8]的必然命运。此后,杨万里自请离职,他的政治生涯也由此结束。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杨万里从京城回到故里,开始了他晚年的退休生活。在回乡的路上,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两岸万山如走马,一帆千里送归舟。出笼病鹤孤飞后,回首金陵始欲愁。”[9]可以看出,杨万里此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他一方面流露出辞官归里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又回首京城,内心充满了对朝廷局面的忧虑,从中可见其对报国事君的政治理难以割舍,但又无从实现的内心哀痛。这种哀痛已不是他一己仕途失意之痛,而是一代文人普遍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时代悲痛!
处在南宋小朝廷苟安于半壁江山,南北分治已成定局的时代,儒家的三不朽思想已经无法平衡诗人失落的内心。正因如此,杨万里对建功立业的事功观念相对淡泊,他更着意于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以心灵的宁静安然来抵御外在现实环境的冲击。由此,杨万里经世致用思想中潜伏的独善因素随之逐渐上升,并流露于创作中:“山无人迹草长青,异彩奇香不识名。只是苔花兼藓叶,也无半点俗尘生。”(《山中草木》)在他看来,长在山间的草木虽然不被人所欣赏,但它也因此免遭被人随意采摘践踏的危险,始终保持葱郁繁盛的生命力,这其中隐含着 “祸可避,则命可避”[10]的生存体验。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杨万里“性灵”观包含的对赤子之心的向往,对内心真性情流露的情感内涵于此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他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转化到创作思想中,并形成 “达则振斯文以饰天下,穷则卷斯文以饰一身”的诗学理念,以此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其实质是把诗歌创作视为自我精神补偿和心灵自适的重要方式。
事实上,人在现实生活中会遭受种种束缚,这会使心灵受到压抑,从而陷入苦闷当中。当面对如此境况,排解忧愁苦闷的最好方式就是走入自然之中,把自然万物看做是有生命的存在,在与它们的交流融合中,身心自然得到放松,心情亦会怡然自乐,这在儒家与道家那里都已达成共识。正如庄子在 《知北游》中所云:“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就连以道德伦理关照人与自然关系的孔子亦向往“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疏放悠闲,虽然宇宙自然在先贤那里尚未脱离附在其上的道德属性成为独立的审美关照对象,但却已经向人们昭示着放身自然当中,心灵就会得到自由沐浴的价值方式。杨万里对此深有感触,其诗云:“诗人家在木犀林,万顷湖光一径深。夹路两行森翠盖,西风半夜散麸金。邀宾把酒杯浮玉,擘水庖霜脍落砧。掇取仙山入京洛,不妨冷眼看升沉。”(《木犀初发呈张功父》)他在诗中虚构了一个万顷湖光,如仙境一般的地方。他想象如果诗人能够经历如此胜境,心灵得到洗刷,那么当再次面对名利升沉时,自是另一番心胸。杨万里的感受之所以如此鲜明,是因为他自己亦有着“软红尘里眼曾开,苦被新诗猛换回”(《张尉惠诗和韵谢之》)的创作经历。因而,在他看来,“诗家不愁吟不彻,只愁天地无风月”(《云龙歌调陆务观》);“随分哦诗足散愁,老怀何用更冥搜”(《秋怀》)。只要自己主动与自然万象建立联系,以“万物一体”的眼光去看待自然,将万物看做是自己身心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把其当做流连观赏之物,就能够抛却世俗之形骸,与物交融,与大化同流,最终达到“一句能销万古愁”(《题山庄小集》)的心灵解脱,并因此脱离世俗社会的评价机制,通过自我肯定、自我认同,实现自我超越与自身价值。其早期“诗也者,矫天下之具”的诗教观念在此时已经转向对内心世界和自我超越的关注,以自适的创作方式作为自我解脱的途径,并流露于诗歌创作中。如:“清风明月行乐耳,布袜青鞋随所之。颠倒壶觞留落日,翻腾山水入新诗”(《送颜几圣龙学尚书出守泉州》);“今日风光定自佳,不寒不热恰清和。百年人世行乐耳,一岁春归奈老何。”(《初夏即事》)这其中流露出的“行乐”思想,显然渗透着禅宗超越世俗的生存智慧,并成为他寻求心理平衡的依托。其“何如闭目坐斋房,下帘扫地自焚香。听风听雨都有味,健来即行倦来睡”[11]的自适心态显然是受禅宗“穿衣吃饭、困来即卧”思想的影响,并与理学家逍遥安乐、吟风弄月的内心安顿融合在一起。
从此意义上讲,杨万里注重“心”与“物”关系的“性灵”观念,与自适的人生追求密切相关,其“小吟聊适意”的创作意旨与“妙句忽从天上落”的自得创作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关系,类似于白居易的“但对松与竹,如在山中时。情性聊自适,吟咏偶成诗”(《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他们的共同感受是:只要抛却世俗束缚,敞开心灵,用心去感受自然,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就会自然从中流出。作诗与个人身世的穷通无关,它只是让自身获得内心愉悦、精神自主的一种自适方式。因此,杨万里醉心于自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 “观天地,见吾心”,即在纷纭变化的大千世界中使自己的内心不受外物的牵制,从而达到内心的超脱与旷达,因而,其“性灵”观念最终成为一种悠然自得的生命情调,体现着其生命价值的皈依与诗歌创作的最终旨归。
二
除了诗人的身份以外,杨万里还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理学家,他所生活的乾淳年间是南宋理学最为繁盛,也是思想界论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他与湖湘学派、程朱学派以及陆九渊的心学学派都有学术上的交流。在朱、陆之辩后,他的思想明显转向了心学学派,但又不废弃程朱思想,而是吸取了他们为学方法、精神境界中更有利于心性修养、心灵安顿的真精神,这使得他将自我心灵超越和悠然自适生命情调的追求作为诗歌创作的主导思想。因此,作为一位理学家,他并没有重蹈宋儒“文以载道”或“作文害道”的旧辙,而是将文学的目的和功用成为其实现心灵内在超越的方式和途径。这也是他不遗余力地对诗歌创作进行探索的重要原因,并最终将理学、心学与诗学在思维、审美、情感领域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改变了宋诗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诗学局面,给宋诗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构建起抒写自适自得的“性灵”世界。
儒家的文化性格总体上是内敛型的,他们始终将自我的内心修养与政治责任、道德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抑制个性自由的张扬。在对平和、淡泊心境的持守中,其人格心态随之向超然旷达、随缘自适的方向发展。对于杨万里而言,心学思想的介入给他提供了在压抑中调节处世心态的广阔空间,从而使主体之心从道德之“理”中解放出来。杨万里的“性灵”观与宋诗“吟咏性情”的最大区别就是:宋诗的“吟咏性情之正”的诗学观念要求主体之“性情”要符合道德涵养的要求,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始终保持一种理性的和谐关系,从而忽视了“心”与物之间的联系,反映在创作中则缺乏物我无间、情景交融、情景相生的审美质素,因而,呈现出一种平和、理智的老境美。杨万里的“性灵”观所蕴涵的主体内涵与情感内涵均与之不同。不论是从道德主体向情感主体的转换,还是对心学、对主体精神的强调,以及对内心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渗透到杨万里的文学思想之中,成为其“性灵”观念产生的思想根源。
在确认了诗歌的超功利价值后,杨万里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诗人言之不足与嗟叹之,不足而作也”。[12]虽然他把《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诗歌艺术发生论简化了,但其所言的“不足而作”足以说明诗歌创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艺术本质,而且是“感于物”而发之情。其自云:“红尘不解送诗来,身在烟波句自佳”(《再登垂虹亭》);“不是风烟好,何缘句子香。”(《过池阳舟中望九华》)在与自然的深入交流中,杨万里所注重的“心”、“物”之关系也由主体对“物”的主动关照而逐渐变为物、我的融合无间。不仅是“我”主动“观物”、“感物”,而且“物”亦主动“触乎我”。如其诗云:“泊舟梅堰日微升,一径深深唤我登”(《小泊梅堰登明孝寺》);“久雨令人不出门,新晴唤我到西园。”(《新晴西园散步》)人与物在杨万里那里已经变成了双向互动的关系,我不离物,物不离我,而将二者沟通起来的则恰恰是主体自然真实的内心情感。这一情感由于他自身淡泊名利而显得纯净自然,并带有一丝山林之人的清逸之气。与一般隐逸诗总是透着淡淡的感伤情绪相比,其“吟咏性灵”之作则融合着诗人内心的真挚之情和闲适之趣,并且在平淡清远的审美情趣中透发着清新可喜、幽默风趣的自得情调,这是其追求独立人格与精神自主的必然结果。
因此,杨万里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和审美情趣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它与心学对人在万物中的超越地位与潜在的无限价值之肯定有着直接关系。人除了作为道德自我以外,同时也是一个感性的自我、情感的自我。道德自我需要通过存养本心来实现,而感性自我与情感自我则需要主体自身去主动发现,并用心去感受和体验,如此才能实现自我心灵的超越。应该说,心学所提倡的就是人自身的觉解,这一觉解则需要依靠主体内心的感受和体验去获得。正如程颢所云:“言天地之化,已剩一体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与天地。”[13]他认为,人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其有超越性的心灵活动,即使是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亦能体会到生命的自得之乐。有了这样的人生目标,作起诗来自然也会“下笔生波便百川,字间句里总超然。”(《张尉惠诗和韵谢之》)从此意义上讲,杨万里的“性灵”观念中所包含的悠然自得之生命情调与心学,对人生之价值意义的确认极为契合。从追求自我心灵超越的生命意义出发,杨万里对读书穷理,并以此得取功名的价值实现方式是不予认同的,因为,这会造成生命情调的萎缩和理性的偏执,从而淹没了自我适意的生命情趣。
在他看来,“霜松雪竹,生我灵囿,世谓今人不如古,其然乎哉?”[14]这句话意在说明,每个人都身处宇宙万象当中,同为宇宙的一部分,只要用心去感受,去体会大自然的美好,就会得到人生的快乐与满足,又何必去叹羡追慕古人呢?在与自然的融合中,杨万里越来越体味到自然山水娱情乐性的审美价值。如其诗云:“病眼看书痛不胜,落花千朵唤双明”(《谢张功父送牡丹》);“万壑松风和涧水,鸣琴漱玉自相娱。”(《和巩采若逰蒲涧》)可以看出,自然界的和谐与生机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与自然的沟通中,杨万里展露了自我情感世界中最率真的一面,自然景物也因被赋予了人的灵性与感知而变得善解人意,富有感情。当然,这种方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艺术构思与修辞手法的统一,而是诗人的自我生命意趣在创作中的流露,具有明显的主观情感色彩,体现了杨万里“性灵”观的情感内涵,即注重对自我生命的把握,淡化道德心性和政治事功对主体内心本然情感的牵制,其中渗透着他对自我适意之生命情调的追求。正因如此,杨万里构建了一个前所少见,且具有生命灵性、知觉情感的自然世界。在他的笔下,自然界的山川风物并不是无生命、无意识的客观存在物,而是具有灵性、知觉、意欲和情感。他之所以能够感受到自然万物的灵性,并赋予自然界以生命知觉,是因为在与自然的交感中能够获得心灵的完全放松,实现主体心灵的自由与超越。与宋代大多数诗人以“性情”为本的创作观念相比,杨万里之“性灵”观更加注重用主体灵动并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思维表现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内心体验,同时,又以不着世俗尘见的纯净之情去体察流行于宇宙自然中的生生之“性”,具有哲学上的超越意味。因此,他的“性灵”观是出于道德情感而又超越道德情感的心灵感悟,是一种对符合道德美感的自由追求,可以视为创作主体之“性情”和艺术灵感的结合体。
结 语
杨万里的“性灵”观念标志着宋代诗学创作主体意识的转型,即注重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主体在与外物的交融中实现自我人生的价值追求。对杨万里而言,理学是其思想的根基,而心学思想以及禅宗境界的介入,又导致他以理性取代激越,以智慧寻求解脱,以境界实现超越。从其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宇宙自然的归依,对尘世功名的淡漠,对自我生命的彻悟。可以说,他把宇宙自然作为一种生存的智慧和精神的安顿之所,是自己心灵的栖息地。因而,杨万里对自由之境的获得是一种主观性的行为,其内心的自由情怀往往在与自然景物的碰撞中一触即发,这就需要他去寻、去探、去索,靠自己的主观意识去捕捉和把握“物”的自在性,一旦获取了这样的机缘,其内心的本真情感就会被触发,并流溢出无限的自由与畅快。因而,在他看来,不论处在何种境遇中,自由就在自己心中,只要用心去感受,就能获得心灵的超越。因此,不论是在思想境界上,还是在抒情结构上,杨万里的自然山水诗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而是深深打着宋代文化思想的烙印。
[1]郭绍虞.郭绍虞说文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75.
[2](日)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187.
[3]左东岭.国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1,(3).
[4]杨万里.诚斋易传[M].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六.
[5]周必大.题杨廷秀浩斋记[A].周必大.文忠集[C].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九.
[6]朱熹.答杨廷秀[A].朱熹.晦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八.
[7]赵蕃.次韵杨廷秀太和万安道中所寄七首[A].赵蕃.淳熙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
[8]杨万里.与材翁弟书[A].杨万里.诚斋集[M].四部丛刊本.卷六十七.
[9]杨万里.发赵屯得风宿杨林池是日行二百里[A].杨万里.诚斋集[C].四部丛刊本.卷三十五.
[10]杨万里.庸言七[A].杨万里.诚斋集[C].四部丛刊本.卷九十三.
[11]杨万里.书莫读[A].杨万里.诚斋集[C].四部丛刊本.卷十二.
[12]杨万里.答张子仪尚书[A].杨万里.诚斋集[C].四部丛刊本.卷六十八.
[13]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8.
[14]杨万里.跋主管乃祖忠节录[A].杨万里.诚斋集[C].四部丛刊本.卷一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