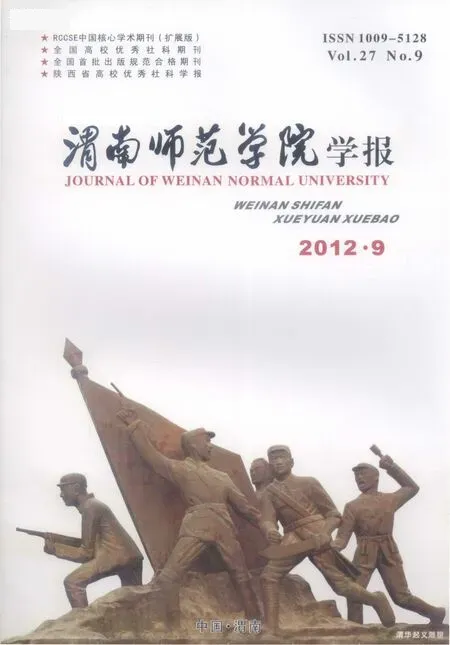陈白露与茶花女的艺术形象比较
张 蕻
(渭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处,陕西渭南714000)
陈白露与茶花女的艺术形象比较
张 蕻
(渭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处,陕西渭南714000)
陈白露和茶花女分别是曹禺《日出》和小仲马《茶花女》中的人物。她们两人都是文学中典型的妓女形象,都经历了几近相同的悲剧命运。文章把陈白露与茶花女这两个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着相似的境遇而又有着不同个性的文学形象放在同一视角下进行审视和比较,通过这两个悲剧形象所呈现的复杂的社会内涵来剖析其悲剧意义上的差异。
陈白露;茶花女;艺术形象;比较
陈白露是曹禺《日出》中的女主人公,是我国19世纪30年代都市生活中的高级交际花,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最后服药自杀。茶花女是19世纪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在自我堕落中死亡。陈白露和茶花女的生活遭遇十分相似,一个是红极一时的都市歌女、舞女、高级交际花,一个是首都名妓。我们仅在此做以比较分析,从中可看出一些东西方文学的异同。
一
陈白露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的30年代的都市中,她有着美好的少女时代,但由于父亲的突然病故而使其生活陷入困顿。后来和一位诗人有过一段浪漫的婚姻,婚后却感生活平淡,不久她和诗人离了婚,标志着她的罗曼蒂克时代的结束,再后来成了名歌星、舞女,过着春风得意、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在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里,她不甘堕落却又不能不堕落,她的良心尚未泯灭,但又不能自拔,痛苦不得解脱。[1]84方达生的到来,在陈白露的感情生活上激起了千层浪,她既甜蜜又痛苦,体现了她内心矛盾的复杂性。方达生对她的指责,她有一番似乎是“很自负”的答辩,而那番答辩其实质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对罪恶的社会制度的控诉,其中蕴含着复杂而矛盾、痛苦而心酸、倔强自负而又软弱无力的心理特征以及她厌倦屈辱而又摆脱不了生活陷阱的呻吟与呼唤。然而光怪陆离的社会,其邪恶黑暗的势力太强大了,那口残酷的井太深了。拯救“小东西”终归失败,这是悲剧,是社会的悲剧,也使得陈白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性,在日出前结束了自己年轻美丽的生命。
《茶花女》中的主人公就出身于贫苦的农家。她原名玛格丽特·戈蒂叶,因为她喜爱茶花,故称茶花女。她是法国首都巴黎红极一时的高级妓女。她外貌漂亮,智慧过人,心地善良。但是美貌和善良并没有使她过上真正独立的生活,没有自由和个人追求的幸福。茶花女像一只无辜的羔羊,她漂亮的外貌只是提高了她作为商品的价格,她整天被巴黎的那些达官贵人、老爷少爷包围,追逐和玩弄,即使肺病恶化也还要强颜欢笑,她深感卖笑生涯的痛苦,感触颇深地说:“我们已经身不由己了,我们不再是人,而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我们这种人,一天换不到情人们的欢笑,一天满足不了他们的虚荣心,他们就会抛弃我们。”[2]55虽然茶花女有时会用狂饮纵欲来麻醉自己,但她对美好的人生理想始终未泯灭,像陈白露一样,也想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追求一个正常的幸福的爱情生活,遇到阿尔芒后,她内心蕴藏的爱情被唤醒,决心向奢侈糜烂的生活告别,她毅然决然打发掉老公爵、N伯爵,把首饰、珠宝等统统变卖,和阿尔芒去乡下过简朴而幸福的生活。但阿尔芒的父亲迪瓦尔这个资产阶级道德化身的代表,却以下贱的妓女茶花女是“榨钱机器”、“玷辱门楣”等种种理由扼杀了她纯朴的爱情生活,使她再次落入巴黎社会的火坑“重操旧业”,最后在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玩弄、债主的逼债以及情人的折磨的联合打击下,贫病交迫地“像狗似地”死在公寓里。
小仲马控诉了万恶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如何吞噬了一个年轻善良的妇女,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社会风气的堕落,指责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公子少爷平时把茶花女作为一个妓女玩弄蹂躏,在这个可怜的女人临死之前,这批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又吸干了她身上的最后一滴血。陈白露和茶花女所受的屈辱经历何其相似,当潘月亭破产后,金八又为她付账单时,她无疑感到又一个毒蜘蛛张大爪牙向她围捕过来,她想挣扎却无力挣扎,最终没有逃脱毁灭的命运。尽管她们死的方式不同,但都有同样的悲惨结局,这种命运是与各自所处的剥削阶级吃人的社会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二
由于曹禺和小仲马所处的国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也由于剧作家和小说家的思想认识和艺术修养的不同,陈白露和茶花女又是两个存在着许多个性差异的典型艺术形象。
1.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受奴役受剥削的方式不同
陈白露生活的都市是以30年代天津为模型的。民族危机加剧,官僚资本和金融买办资本控制着市场,社会、都市生活瞬息万变,各种人物矛盾激烈,金钱万能,整个社会在金钱势力制约下,呈畸形形态,表现为“鬼的天堂”和“可怜的动物的地狱”。这是一个金钱的社会,是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控制的社会,人和人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现金交易外,什么都不存在了,人们发疯似地追逐钱财,尔虞我诈,金钱控制着一切,并且由于在都市社会里还存在着像金八那样的封建帮会和买办,注定了陈白露在失去了潘月亭这个靠山后,又要受金八的控制。陈白露是已经被腐化了的快要剩下空壳的躯体,她变得玩世不恭,逐渐失去灵魂,却又对太阳和光明怀着憧憬、希望,陈白露表面上有更大的自由,实则被“有余者”控制于手心,被金钱左右;陈白露不仅身受卖淫生活的迫害侮辱,饱尝被出卖的痛苦,而且这种迫害还同时使她陷入腐朽生活的桎梏,陈白露是一个知识女性,但她抛弃了思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推翻黑暗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找到自我解放的道路,被黎明前的黑暗淹没,吞噬了她的生命和爱情。
茶花女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关系已经高度发展的法国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金融资产阶级靠着巧取豪夺积累了巨额财富,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卖淫也就成为这个制度和风尚下的特定产物,类似茶花女那样的大批农家姑娘,就不得不出卖肉体,沦为妓女。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取消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法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人身自由,平等博爱,在形式上妓女是有人身自由的,但在被金钱完全支配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失业、饥饿、虚伪的道德是她们不得不“自愿”接受资产阶级贵族的享乐淫逸。有着伪善面孔的迪瓦尔用娓娓动听的说教和鳄鱼般的眼泪打动心地善良的玛格丽特放弃对真正爱情的享受,甘心情愿地一次又一次跳进巴黎上层社会的淫窟,在自我折磨和煎熬中慢慢地枯尽自己鲜花般的生命。这种“自由”比起中国30年代的陈白露来说,只能说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是看不到什么希望和光明的。
2.个性性格特征和形象塑造的社会意义不同
作者从陈白露过去的“竹筠时代”的纯真、美好的生活和现时的“白露时代”的邪恶、黑暗的处境的对比映衬中,特别是从金钱统治的社会和罪恶卖笑生涯对她精神的腐蚀与毒害中,多方面、多层次地刻画其内心世界的悲剧性冲突和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她一直在寻求一个皈依之所,尽管她对方达生说:“上哪儿去呢?我是卖给这个地方的。”但她不甘于在人生的旅店中度过一生。她怀着个人奋斗、追求个性解放的动机,结果就“闯”进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金钱统治的罪恶社会的泥潭中。在这个泥潭中,她成为红极一时的高级交际花,饱尝着卖淫生活的辛酸与痛苦,以牺牲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换取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堕落生涯,她沦落于风尘之中且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她的灵魂、她的人性被金钱的邪恶势力腐蚀着,异化着。但是,她又厌恶这种生活,不甘心过着被奴役的屈辱生活。陈白露对她所生存的那个泥潭有着愤懑,进行抗争、反抗,而她的抗争和反抗却因看不清未来的前途而采取了特殊的方式。
陈白露的悲剧是中国30年代都市社会所固有的“制度和道德”的悲剧,它作为一种法则潜伏于不人道与不公平的社会中,它的恐怖和危害力已在女性的心灵上有了传统的积淀,并以此向女性证明:你别无选择地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中艰难地生活。她的自杀也说明了脱离社会的解放,单靠个人奋斗和追求个性解放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才能使知识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3]
茶花女在放荡之中有忠贞,任性之中有善良,日日夜夜的放纵淫乐,使她的精神极度疲劳、烦闷和空虚。生活里到处都是虚情假意,冷酷自私,没有欢乐,没有温暖,她感到极度苦闷,感情容易冲动,反复无常,狂热任性。她狂饮纵乐,没有积蓄,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她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她的谈笑粗鲁得就像一个脚夫,别人讲的话越下流,她就笑得越起劲”[2]68。作者满怀同情地说:“可怜的姑娘在放荡、酗酒和失眠中逃避生活的现实。”[2]72即使她同意成为阿尔芒的情人后,也还强装欢笑来接待其他情人,她被彻底地捆绑在现金交易的战车上。她内心的痛苦无以伦比。小仲马塑造茶花女是怀着同情赞美被侮辱受损害的女性的,但在整个小说中没有十分强烈的控诉意义,因而作品的战斗性不强,只是对资本主义上流社会中的这种客观现实做了逼真的描绘,但也能引起人们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抗议。
3.反抗精神的不同和自我拯救意义的不同
陈白露的反抗精神可通过拯救小东西一事反映出来。面对金八的爪牙,她机智巧妙而又义正辞严地打发走了他们。她对小东西敢于打金八的耳光表示赞赏,拯救小东西是她对黑暗社会的挑战,抒发她久积心中的痛苦。在被禁锢、被压抑的的社会里,她想反抗却力不从心。方达生使陈白露相信了人间还有自由和爱情,相信了自己还是竹筠,越是这样,便越加剧了陈白露内心的精神矛盾,越更深切地体验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她只得选择自杀这个最消极的反抗方式向社会做出有力的控诉。陈白露没有走上积极的反抗道路,是因为她缺乏自觉的精神拯救意识,她是受过“五四”影响的知识女性,但她不思考自我的精神拯救,她在那种花天酒地的商品爱中不再为自己的精神与灵魂的解放而苦斗了,这种精神麻醉与困扰进而使陈白露无法有自觉的自我拯救。[4]
与陈白露相比,茶花女却显得更有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她对这个社会没有清醒的认识,始终没有觉醒,甚至没有反抗。她能摆脱公爵老的控制,寻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有着反抗的一面。但是茶花女心肠太软,过于舍己为人,对于门第和等级观念又太忍让、屈从,最后慢性自杀含恨而死,采取了比陈白露更为消极的方式。这种怯懦性格只能引人怜悯和同情。这是资产阶级发达社会更虚伪、更残酷的对一个下层妇女的精神极度戕害的结果。
总之,陈白露和茶花女是东西方两个不同类型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悲剧的命运,分别遭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贵族的蹂躏,通过描写她们的不幸遭遇,作者愤怒地控诉了吃人社会的罪恶和虚伪,激起了人们对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的愤慨,对光明社会的向往。
[1]曹禺.曹禺经典作品[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2][法]小仲马.茶花女[M].李登福,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3]宫玉静,齐子萍.同途殊归:陈白露与玛格丽特形象之比较[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39-43.
[4]孙展.陈白露与玛格丽特悲剧命运及其成因[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10):38 -40.
【责任编辑 朱正平】
Art Image Comparison of Chen Bailu and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ZHANG H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0,China)
Chen Bailu and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are figures of Sunrise by Cao Yu and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by Alexandre Dumas Fils,who are the classic images of prostitute with similar fate.In the same perspective,the paper surveys and compares the two figures that lived in different tim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had similar experiences but different characters.And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ir different tragic fates with the complicated social connotations presented from the two tragic figures.
Chen Bailu;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art image;comparison
I206
A
1009—5128(2012)09—0074—03
2012—03—27
张蕻(1970—),女,陕西华阴人,渭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