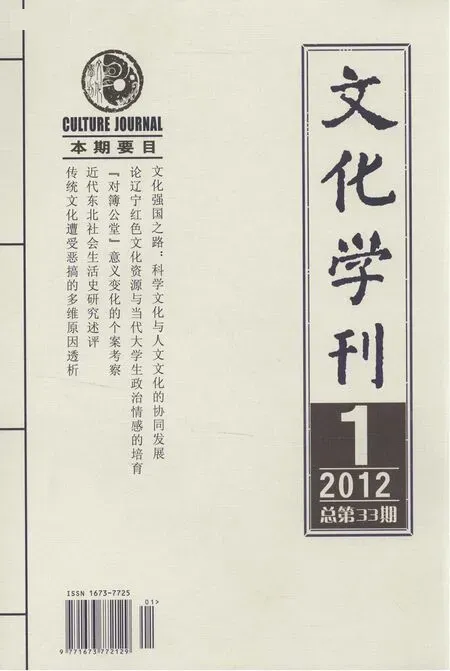扫帚成精故事的演化及中西文化比较
李索穆晶
(大连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日常生活中,扫帚只是一种清洁工具。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会看到很多成了精的扫帚,西方文学中也经常出现会飞的扫帚。无论是扫帚精,还是飞天扫帚,在东西方的传统中,扫帚都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具有一定的魔力。然而,由于中西方在文化、历史、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进而导致二者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文学作品中同样披着神奇之光的扫帚,其特征和作用也迥然不同。
一、中国文学中的扫帚精
南朝刘敬叔的《异苑》中较早记载了扫帚成精的故事:“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复。”[1]这则《徐氏婢》后来被收在《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八《精怪一》中,说的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年间,在今天江苏镇江——当时叫东海——这个地方,有一个姓徐的人家,家里的婢女兰香忽然患病,人日渐瘦弱,脸色发黄,打扫擦拭起家来与平时很不一样。家里人都觉得很奇怪,就暗地里观察她。忽然有一天,大家看见一把扫帚从墙角走过来,直奔兰香的床。于是大家把扫帚逮个正着,拿出去烧了,兰香的病随之也好了。显然,故事里的扫帚精是作为一个害人的反面角色而存在的。
到了唐代,扫帚更多地被赋予了驱凶除恶的魔力,在唐人牛僧孺的《玄怪录》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
毗陵有个叫滕庭俊的人,身患热病多年,每次发作,身上都如火烧般灼热,好多天才能恢复,看了很多名医都无方可治。后来他前往洛阳就医,天已经黑了,还没到达,就到路旁的人家投宿。但家中主人不在,庭俊便自己坐下来歇息。这时,从西屋出来一个头顶已经疏秃的老人。他自称是浑家的扫门之客,姓麻名来和,人称麻大。老人带着庭俊来到后馆,里面装饰华美,亭阁奇秀。后来又出来一个叫且耶的门客,开始与麻大对诗。麻大吟诗:“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静,人用去灰尘。”且耶良久答道:“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苻王笔端坐,尔来求食浑浑门。”庭俊虽不懂他们的意思,但看见这里门庭华丽,便有在这里暂留停歇之意,且耶、麻大互相看了看,笑着说:“假如公子真的住在这,一天就厌恶了。”主人回来了,派人四处喊庭俊。麻大和且耶二人却突然间不见了踪影,只见厕所旁边,有一只被一群苍蝇围绕着的大秃扫帚。庭俊本来患有热病,从那以后便痊愈了,并再也没有复发过。
在这则故事里,麻大就是一个扫帚精。显然,这里的扫帚精的形象较从前更丰满了,而且作者不再只让他以扫帚的本身面貌示人,而是为他赋予了新的形象,即幻化成人,并且对他进行了外貌、语言、动作以及神态的描写,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提升:他懂得诗词歌赋,能够与人相互酬唱,与客人相谈甚欢。“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已后顿愈,更不复发矣”,[3]可见,庭俊正是与扫帚精诗酒唱谈之后病情才得以根治的。故事中的扫帚精是一个善良的角色,他不仅热心接待了孤单劳累的庭俊,还好酒好菜招待庭俊,与他和朋友诗酒唱和,并把庭俊的顽固热疾祛走了。在这里,扫帚精被赋予了一种神性,具有一种可以祛除邪恶的神奇力量。
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一个名为铁扫帚的道士:“临安术士,失其姓名,常著道服,标榜曰铁扫帚。 ……”[4]《尔雅·释草》云:“荓,马帚也。 ”[5]铁扫帚是一种豆科植物,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蠡实》:“此即荔草,谓其可为马刷,故名。今河南北人呼为铁扫帚是矣。”[6]又有记载:“按此植物之茎,古以为筮。”[7]古代用来做扫帚的植物多选铁扫帚,而铁扫帚又常为占卜所用,这就使得扫帚披上了一层巫术的神秘外衣。元代人李衎在他的《竹谱》卷八《神翁竹》里就记载了宋徽宗宣和年间一个叫徐守素的算命先生,在泰州(今江苏)的一座万寿观里做洒扫一职,经常拿着一把竹扫帚穿街走巷,为人言吉凶祸福,非常灵验。更神的是,他死了以后,在他的墓地里,同一株竹根上生出了无数的竹子,砍了,拢起来就是一把扫帚。这样一来,扫帚就成了具有某种神秘象征的事物。这又可以说是从扫帚成精这一故事发展而来的,由最初的把扫帚人化到后来的扫帚本身成为一种象征,这正是《异苑》中扫帚成精故事的发展演化。
二、西方文学中的飞天扫帚
西方文学中,尤其是在童话故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巫师们骑着扫帚飞来飞去。格林童话中的《糖果屋》中就有骑着飞天扫帚的糖果女巫,“小女巫坐着飞天扫把在清晨呼啸而过,魔法手杖上挂满金属骷髅头作为饰物。穿越碳木森林上空时,在蘑菇园发现一个陌生的小女孩……”[8]曾经风靡全球的魔法小男孩——哈利波特也有一把飞天扫帚。扫帚虽然没有什么魔法,但是它和他的魔棒一样重要,因为这是他必不可少的一样交通工具,扫帚和他是不可分离的。在第三部《哈利波特和阿兹卡班囚徒》中也有一章《霹雳扫帚》专门讲述了他的扫帚。时下较为流行的英国芭贝·柯尔的绘本童话《我的妈妈真麻烦》中塑造了一个巫婆妈妈,她也有一把飞天扫帚,在学校失火那一天,巫婆妈妈骑着飞天扫帚疾速赶来,施咒语让乌云下雨,扑灭了学校的大火,如此等等。在西方的文学故事中,骑着飞天扫帚的巫师很多,也可以说,飞天扫帚已经成了巫师的一个象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传说,扫帚是巫师最常用的交通工具。
这种现象在诗歌里也有所反映。十九世纪美国很受人们喜爱的作家奥利弗·温戴尔·霍姆斯曾写过一首诗:
埃塞克斯郡有许多许多屋棱,
他知道那些都是巫魔的象征;
小小的方窗看得很清楚,
午夜的女巫就从那里飞出,
骑着训练有素的扫帚航行,
像影子一样掠过高高的天顶;
穿过猫头鹰和蝙蝠的轨道,
怀抱她们那煤炭般漆黑的猫。
正像早期出现于希腊《荷马史诗》中的巫师也以多种动物作为坐骑一样,这首诗里指出的 “扫帚”、“猫”等也都是巫师的法器,是巫魔的象征。
对于为什么巫师,尤其是女巫要骑飞天扫帚这个问题,历来说法不一,但是比较通行的说法有:第一,扫帚和彗星在外形上相似,所以女巫的扫帚也能像彗星一样在天空中飞。第二,扫把是女性致力于家务的象征。古时女性专主家庭内务,日常清理房屋最不可或缺的工具便是扫把。由于女性几乎人手一支扫帚,而大部分行巫术的都是女性,因此扫把便成了女巫的代表物。第三,远古时异教徒为使作物丰收而举行祈求土地肥沃的仪式,其间包括信徒跨骑扫把或干草叉并高跃、舞蹈的动作。这样一直推广并沿用,扫帚就成了巫师的一个象征。
三、中西方扫帚成精故事反映的文化差异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童话中扫帚成精的故事,都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思索追求,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认识的能力及其观念的局限。他们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相信万物有灵,相信灵魂和神灵的存在,同时,也与图腾崇拜、巫术信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组成当时人们世界观的因素密切相关。因此,肉体凡胎的人在一切日常事务上都要向诸神祷告,相信他们可以并且愿意插手凡间俗事。大部分不幸,比如疾病、饥荒、战乱都被当成是有敌意的超自然力联合了不怀好意的恶神在作祟,而人们则会向本族的保护神们祈求庇佑不受损害。[9]
但是,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扫帚形象又有所不同。中国文学故事中的成精的扫帚具备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成精、神化后的扫帚仍然带有人们赋予扫帚的原始功能特点。在汉语中,扫帚最初只称“帚”,甲骨文作“”,象扫帚形。 《说文·巾部》:“帚,粪也。……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 ”[10]段玉裁以为是“所以粪也”,[11]即用来扫除的工具(“粪”即扫除的意思)。也就是说,杜康当初制造扫帚是为了扫除,即“扫除”是帚最原始的功能。此功能泛化、虚化,可泛指清除。于是便具有了二重性——既可用来除去污秽,也可以用来损害有益的事物。如果不分是非一律清除,就有了破坏、毁坏的意思。所以在汉文化中,因其尾像扫帚的“慧星”俗称“扫帚星”,被认为主战乱和天灾,是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妖星,出现了就不吉利。用来除去污秽的扫帚,表现在文学中,就是正面形象,即善良的扫帚精;对人类带来损害或是搞破坏、毁坏的扫帚,表现在文学中,就成了反面形象,即邪恶的扫帚精。二是可以幻化为人,拥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可以像人一样说话、行动、思考,甚至富有人的情感,像人一样表达喜怒哀乐。在故事中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人类发生紧密的联系,推动故事的发展,共同构成故事的完整性,并且对整个故事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些时候甚至扮演着主角。如上文所举的麻大就是如此,故事中的麻大完全同人一样,言行举止看不出任何逊色于人类之处,有些才华甚至要更强。这则故事,乍一看滕庭俊是主角,实则引导故事发展的却是麻大,麻大才是故事的重点,不可代替。
西方故事中女巫的坐骑选择了扫帚,他们让扫帚飞上天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扫帚在外形上很像天空中的彗星,都拖着长长的尾巴。西方的飞天扫帚与中国古代的扫帚精虽然同样具有某些神秘色彩,但是飞天扫帚与扫帚本身的功能——打扫有较大差异,它们多是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而存在的,而且没有意识,只是巫师拥有法力的一种证明,只是人物形象的一种衬托。
要之,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扫帚精形象是扫帚自身功能的演化,二者具有内在功能上的联系;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飞天扫帚与扫帚自身只是形象上的相似,二者主要是外形上的近似。
同样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扫帚成精在东西方文学中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呢?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东西方地域差异以及社会传统、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人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主张人与万物等齐,天人合一,并重视现象背后的理据;西方人更乐于聚焦于具体的物体而忽略与背景的联系,并更加相信人对环境的控制能力。
美国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12]
这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必然出现了同一个文学素材产生不同文学形象、蕴涵不同文化传统的现象。因此,中国古代故事中的扫帚变成了人形的精怪参与人的活动,与人发生联系,成为人的朋友,或是敌人,有时候甚至具有超出人类的能力,引导人类做出某种行动。故事中的扫帚作为一个纯粹的自然事物,却堂而皇之地走进人类的世界,能动性地参与人的生活,这充分体现了故事背后的人们对自然的关注和重视。中国古代哲学主张“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万物有灵,相扶相生,天、地、人不可分离。《说文·一部》:“天,颠也。至高无上。”[13]引而申之,天即是最高的神,具有主宰万物的力量。虽然在天、地、人这个统一体中,人处于中心的地位,但也不能忤逆天意,无视自然,违背自然规律。为了更好地突出自然与人的平等关系,在故事或者传说中,自然事物便被人类人化、神化。所以,当扫帚被赋予了神的色彩时,它们便具有了某种超越人的力量。但善恶有报,因果相应,超人类的邪恶力量最终也会被人类用智慧征服,正义力量也终究会有益于人类。所以在扫帚成精、化神的故事中,隐隐透露出“天人合一”的汉文化气息。而在以后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如《聊斋志异》、《西游记》等,都出现了事物或动物成精的故事,而个中所蕴涵的深层文化内涵莫不与此相类。
西方人关注物体而不注重联系,倾向于把行为归因于做事的人的思维方式。西方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是分开的,没有必然的联系,人是上帝最高的创造物,人高于万物而存在。在西方的意识中,人与万物生来就不是平等的,万物都要服从人的意志,人可以支配、控制自然。所以,作为自然之一的扫帚,虽然被人类带进了生活,甚至作为巫师的坐骑飞向天空,但是,它也只是靠着巫师的法力才得以如此,它本身并不具备飞行的功能,而仅仅只是一个可以由人支配、控制的物体而已。所以,即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类意识比较低级的状态下,西方故事中的飞天扫帚也不会具有人类的意识,更不会超越于人类之上,控制人的行为。
扫帚成精在古代的小说中还有很多,我们这里只是拾取两个典型的例子来加以概述。扫帚成精这一故事不仅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同时,也使扫帚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蕴的文学意象而独立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而比较中西方文学中的扫帚形象及内蕴的不同,并非是为了分出高低优劣,只是要探究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以便更好地理解、鉴赏中西方文学的不同的美。
[1]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2927.
[2][3]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42-43.
[4]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73.
[5]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87.
[6]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938.
[7]洪迈.夷坚志选注[M].许逸民选注.北京:人民艺术出版社,1988.
[8]格林兄弟.格林童话全集[M].魏以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9]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女巫——神秘文化典藏系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
[10][1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59.3.
[1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361.
[12][美]理查德·尼斯贝特.思维的版图[M].李秀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1-1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