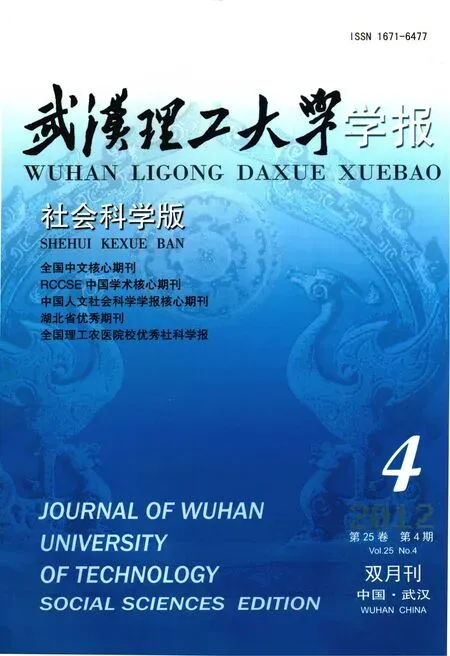基于网络自我伦理构建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
冯 荣,石变梅
(台州学院 党委学工部,浙江 临海317000)
基于网络自我伦理构建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
冯 荣,石变梅
(台州学院 党委学工部,浙江 临海317000)
自我伦理是人们对道德和伦理精神的切身感悟,是人在生活情境中的权衡和抉择,是开放的自我观下的自我约束。其构建的逻辑起点基于人有自我救赎的主观需要,人有全面发展的客观需求,人有主体实现的内在要求。构建目标则指向于自我实现的满足,真实人性的再现及精神境界的升华。因此网络舆情的引导应从明确网络伦理的责任主体,继承现实社会伦理的精髓,建立“慎独”的道德自律,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培植个体社会支持系统,强化网络主体的心理调适等方面进行治理。
自我伦理;网络舆情;引导
一、网络舆情成因的伦理审视
网络舆情,又称“网上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或者平台的社会舆情,是网民发表的意见和态度的总和,集中体现了一部分受众对象——网民的思想、情绪、意志、认知和行为。究其根源,其发生和发展都全过程渗透着网络主体的道德行为,并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
一是道德主体自我异化。大多数的网络主体身处于海量信息的互联网,没有充分意识到有些信息的危害性和腐蚀性,有害信息非但不能有助于自我的提高和自我发展,反而会让自己思想错乱,道德困惑甚至于沉湎于其中不能自拔,逐渐迷失自我。人性道德的“该不该”被网络技术的“能不能”所取代。
二是道德主体难以约束。网络传播的载体比较多,但绝大多数对用户开放注册的网络载体尚未实行实名制,也没有经过认证。即便是校园BBS论坛,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也没有要求网民实名注册,学生游弋其中,身穿多个“马甲”,较为自由、随便;另外,很多高校没有建立起网络信息员、管理员队伍,也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来约束道德主体的行为,客观上放任了道德主体行为的随意实施。
三是道德主体欠缺自律。网络道德寻求规范的最终目的不是向人们去昭示其某些标准,而是引导网民更好地投身于道德实践,以网民内心的信念和自知来约束自己以合乎网络的伦理,从而最终促成以自律来促成他律。尽管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大学生们普遍追求诚信、公平、正直,但从网络行为失范表征的情况来看,其并没有进行有效地自我约束和自我节制。
四是道德主体认识偏差。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便是对于可知的网络世界总也有暂时未知的部分。加之,网络信息包罗万象,多元而广泛,增加了其复杂性和多样性,极易在客观上加深作为实施道德主体行为的大学生们认识网络和甄别信息进而进行自我研判的难度,造成道德上的困惑。
五是道德主体行为失范。网络与生俱来的虚拟性、隐蔽性、随意性等特点,使得极具张扬个性,宣扬自我,追崇自由的大学生们在表达思想和观点的同时充分放任个性,淡化责任意识,凸显自我中心。主观意识的变化直接造就了网络主体行为的变化,结果则导致了网络用语失范,引发虚假泛滥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直接促成了网络伦理的失范,为网络舆情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六是道德客体他律滞后。在网络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道德主体通过自我设定,创造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形成道德客体。然而,在道德客体对象化重塑道德主体的双向互动中,却缺乏必要的道德规范。作为高校网络主体的大学生又是一个个体思维非常独立的群体,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个人习惯去看待事情和处理问题。他律的缺失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大学生自律意识的形成和提升,从而也间接导致了主体行为的失范。
二、网络自我伦理建构的现实逻辑
任何社会的存在对个人都有一种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既是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人寻求精神依附的需要[1]209。倘若这种约束力移嫁到人的思想精神领域,那便演化成了伦理。从这个角度讲,人是离不开伦理而单独存在的,这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同样地,即便是置身于网络世界亦不能例外,因为其主体是人。伦理是一种自然法则,是有关人类关系的自然法则。其涵义是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2]。与其概念相对应,自我伦理的重心在于自我关系。它指的是人们对道德和伦理精神的切身感悟,是人在生活情境中的权衡和抉择,是开放的自我观下的自我约束。
(一)网络自我伦理构建的逻辑前提
从伦理内在的本质剖析,“自我与自我伦理的调节,实际上是主体对自身意识和行为进行的积极主动的调节和控制,是个体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所必需的道德支撑”[3]。在其中,“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劳动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4]。因此,其建构的基点如下。
1.人有自我救赎的主观需要。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是自我负责的人,是自我把握命运的人。即便是在开放的网络社会中,同样蕴含着对自我的内在安宁与满足的追求。正如荷尔德林的诗句描述的那样,“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长着拯救者”。“我们”是自己的拯救者。所以,克尔凯郭尔指出:“伦理只与个体相关联,以至于每一个个体只能本质地在自身之内理解伦理。”[5]285关于这一点,康德在他的墓志铭上诗意地作了回答:“璀璨星空在我头顶,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它告诫我们,建立自我伦理是人应该无条件践履的一项绝对命令。
2.人有全面发展的客观需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273。它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正如先前所言,自我伦理的建构是自我完善所必需的道德支撑,那么伦理主客体关系调整的价值也就在于人的发展。网络虽没有直接地作用于人,但同时又在与人交流的客观活动中实实在在地促进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也理应成为包括网络社会在内的广义社会的目标价值追求,并成为其始终恪守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出发点,抑或逻辑起点。
3.人有主体实现的内在要求。“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现实中的个人绝不是消极地被动地接受外界和他人的塑造和教育;相反每个正常的人都能够‘自由’、‘自觉’地将自己本身、自己的生活及生命活动当做意识的对象,能动地支配自己的活动”[7]166。可以说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基础之上,是依靠人来实施的,以人为对象,它的出发点是人,落脚点也是人。网际自我的产生,正因为有了作为网络主体的“人”的主动参与和独立支配,才渗透着人的主体性,使其具有了某种主体性因素。这是与自我伦理所倡导的基于自主性、自我责任和自我创造的出发点相适应的。
(二)网络自我伦理构建的目标追求
网络自我伦理建构的目标是追求终极的价值,即个体有责任使自己成为自主的,有创造性的主体,同时应以自我生活的智慧追求幸福的生活。
1.自我实现的满足。人类行为的一切动力都源自于需要,需要是人动力的源泉。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原欲”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需要。当“已经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后又引起新的需要”[6]32。在此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最高层次的需要。如果一个人的“原欲”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满足时,他便会转而去虚拟的网络世界建立一个虚拟的“自我”去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潜能的发挥和自我能力的认可,其本质是自我实现的欲望的满足。
2.精神境界的升华。人是意义的存在物和精神的存在物,不仅有生物性的自然需要,更具有精神性的需要和意义性的追求[7]166。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甚或社会实践则很少直接为了追求精神的富庶。相反各种琐碎的物质的需要充斥着现实,何谈理想的实现和精神的追求。而网络恰恰为人们搭建了实践的场所,通过重塑虚拟的自我,参与主体表达,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心灵依托和精神慰藉。
3.真实人性的再现。人并不是完美的,人性中的全部也并不能完全在真实的社会中全部予以表征。相比现实的物理空间而言,网络的虚拟世界给了人们一个充分释放情怀,发泄自我,满足欲望的平台。这时候,重新建构的“自我”并不是完全虚拟的,其中也渗透着人的主体性,人的思想和人的情绪。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不能简单地独立或者割裂开来,相反则是有益的补充和人性的部分反映。“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真实的自我,一个完完全全的自我,并且促使着人们从多维的视角去重新诠释和解构人性。
4.虚拟真实的统一。“尽管网络人际传播条件下的印象失真显著高于面对面的传播”[8],但网络同样渗透着人的主体意识,看似没有灵魂的信息帧,在一定程度上也表征了人的伦理,不仅有对自我的认同和自我的节制,也有对自我的追求和满足,是一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准艺术表现形式。在虚拟网络社会里,人们找到了自我意愿和自我价值的最大体现。真实的生活也因由此满足而更加地“富庶”。网络虚拟相对于生活现实,不能简单地割裂,而是交互影响,对立统一的。
三、网络自我伦理构建的舆情引导
网络伦理是人类通过电子信息技术网络进行社会交往所表征出来的道德关系。一旦网络主体的主体性扩散和网络技术对主体的异化,必然会造成网际伦理的错乱和失范。舆情引导实质上也就是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网络主体的虚拟自我与真实自我互为统一。因为网络主体的异化,其根源在于人的自身缺陷。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人类更需要自己的道德责任。建构基于自我的网络伦理,就是要引进各种动态的内外力量,促进自我的调适,以至于让自我约束成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从而有效地去引导网络舆情。
(一)网络自我伦理构建的舆情引导机制
从根源上讲,网络舆情的始作俑者及“推手”——其主体自我与客体自我的需要是互为影响,互为协调,互为补充的。着眼于自我伦理基础上建构舆情引导机制就是要将虚拟自我与真实自我所导致的多元自我经过一定程度的整合,以此增强自我的自主选择能力,消除自我对虚拟生活的过度依赖,提高敏锐性和甄别力,变虚拟生活为现实生活的有益补充,从而有利于舆情的处置。
1.主动选择机制。网络传播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通过数字化的网络终端进行信息的虚拟交互。主体的人既是信息的发布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作为信息的受众者,他同样也可以主动地去海量的网络里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同样可以与信息的发布者进行交流,此时他已不再是受众的身份。网络使自我同时成为信息的收、授者,身份不再固定。即使作为受众,亦能成为信息收集和虚拟生活的主人,而不会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或沉溺于虚拟生活不能自拔。
2.自我调适机制。人之所区别于其他动物,在于能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适时对自我的行为和想法进行修正。主体的人在网上浏览海量信息的过程中,很可能就受其他交互信息的影响,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以此来比照当前的自我行为。一旦觉得过去的想法是“荒谬”的,就会从而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想法,而不至于让自己沉湎于“过去”,束缚于“旧往”。
3.适度克制机制。人是思维着的动物,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着自己的生活。即便是隐匿于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同样有着自我控制的能力。不仅可以从容地把信息收集量控制在自己的处理能力之内,不至于迷离于“信息场”;而且可以在网络世界里游刃有余,仅仅只会把虚拟的自我当做自我的一部分,把虚拟的生活仅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不会让自己迷失在虚拟世界里,也不会任由其侵蚀真实的生活。
4.虚实协调机制。自我伦理调节的是主体自我和客体自我道德行为的伦理关系,能够约束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作为自身生活经验的有益补充和改善真实生活质量的有效方式。借助于虚拟生活,真实生活得到更加全面的满足。同样地,真实生活也可以左右虚拟的网络活动。
(二)基于网络自我伦理构建的舆情引导策略
从现实的角度去探析,网络引发的道德滑坡现象已经有所显现,其根源在于伦理调整对象的变化,其中道德主体的自我已经具有了虚拟和真实的双重身份,主体角色逐渐模糊。因此,自我伦理视域下的网络舆情引导的途径必须突出自我的主体行为,着眼于个体的自律,通过显性的方式和手段,建立起自我的伦理来引导网络舆情。
1.明确网络伦理的责任主体。伦理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自然法则。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而且极富有创造性。网络是由人类的智慧发明的,从设计之初就蕴含了人的主体性因素。即便不是面对面的交流,鼠标和键盘也屏蔽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网络的主宰是人。人是网络中唯一的道德权威。他们想实现自我,唯一寄希望于通过权衡与选择体现自我的尊严,以证明“人作为人”的社会存在和价值意义。既然如此,“如果选择不可避免,那么,责任也是不可避免的”[5]284。以至于建构网络伦理,“自我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5]303。
2.继承现实社会伦理的精髓。历史从来都是延续的。人的伦理道德是历史的产物同样也不例外。现实中的社会伦理是经过长期实践的积累而逐渐形成的某种具有共性的道德规范,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约束并指导着人的活动。网络虽然是一种新生事物,但仍离不开人的主体性。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不管是网上网下,都必须统一。因而,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也必然在伦理构建上继承了现实社会的伦理。那种忽视网络伦理存在的必要性显然是错误的。当然,继承现实社会伦理,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于网络。只有充分考虑网络的特性,“通过吸收已有伦理道德的精神核质,利用伦理道德现成的生成和运行机制,在人们网络活动的实践中形成合理可行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既统一又不乏多样性的信息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1]214-215。
3.建立“慎独”的道德自律。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而且从未放弃过对此的不懈追求,即使是网络社会也不例外。然而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殊性,使得根植于现实社会的制度规范显得力不从心,那些刚性的,显现的,外延的“他律”就难以对网络传播的主体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从而在事实上凸显了自我道德节制的作用。不管有无他人在场,即使有做坏事的条件和机会,仍然会自觉不苟地按照约定俗成的道德原则或者信念去实施行为,而不至于违规。如同康德强调的“意志自律”,即“自己为自己立法”[9]。
4.加强网络伦理道德的教育。学生是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提高学生的伦理道德意识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更是网络化背景下,和谐社会赋予高校的重要任务和战略要求。解决了传播主体的意识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源上化解网络舆情,杜绝网络行为失范。为此必须创新形式,调整思路,积极依托思政教育的主阵地。通过在组织计算机教学过程的环节中引入网络伦理知识,甚至开设网络伦理选修课程等形式加强对学生网络伦理的道德教育和知识灌输,提高其在参与网络舆情过程的判断力和辨别力。如美国杜克大学对学生开设了“伦理学和国际互联网络”的高等教育必修课程。
5.建立客体的网络伦理规范。网络伦理规范是网络道德建设、网络意识培养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个体的人,学生的网络行为也是其参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此时,其网络行为是与社会行为统一的。当然,网络道德规范首先是立足于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在从事网络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相对合理并且被学生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制定“网络公约”,倡导“文明上网,上文明网”等形式,大力宣传网络道德规范,彰显效果。让学生网民自觉地变“行不行”的网络技术操作为“该不该”的网络道德规范要求,变网络行为主体外在的道德标准为内在的道德修养。诚如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所制定的“计算机伦理十诫”。
6.强化网络主体的心理调适。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中,很大一部分学生参与其中是盲从的,缺少认知的,主观上造成了道德行为的失范,客观上提升了舆情的“热度指数”,推动和放大了其效果。不难看出,从中心理感受力起了主导作用。为此,应当整合网络教育资源,开展“交互型”的教育工作。通过网络团体心理辅导、个体心理援助、网络咨询、网络心育等手段,加强对学生的正向体验,使其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遵守一定网络伦理的坚定信念,不至于盲从地参与舆情推动,被动地蜕变为“网络推手”。
7.培植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需要是一切行为的源动力。包括大学生的上网,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渴求与人交往的需求,渴求自我实现的价值感的需要。如果能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倡导鼓励他们走出自我的束缚,与人交往,与人为善,与人互助,从而在其中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自我的价值满足感,就可以形成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很大程度上会弱化对网络虚拟人际交往的依赖,不至于模糊“自我”的本来角色。
总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舆情已经切实地影响着高校的文化信息领域,直接关乎着社会和谐和校园稳定,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并且进一步从多维的视角去研究,积极地探寻其规律性,创新其工作方法,从而引导其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1]黄 寰.网络伦理危机及对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陈 绚.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
[3]郝文清.论自我的伦理调节——兼论自我道德规范的心理保健功能[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8(2):109-11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3.
[5]朱银端.网络伦理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万光侠.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张 放.虚幻与真实——网络人际传播中的印象形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人民出版社,2010:108.
[9]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86.
Guidance of Colleg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on Basis of Building Self Internet Ethics
FENG Rong,SHI Bian-mei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Committee,Taizhou College,Linhai 317000,Zhejiang,China )
Self ethics is an immediate experience of the spirit of morality and ethics,the weighing and choice in varied living circumstances,and a self restraint under an open conception of the self.Its logic outset is the subjective demand for a self-salvation,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human all round development,and the inner request for an actualization of subjectivity,while its aim includes the realization of self fulfillment,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 humanity and the sublimation of the spiritual realm.With this perspective in mind,the guidance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is prone to manage by identifying the internet responsibility subject,inheriting the existing spirit of the social ethics,building moral self discipline of“self restraining in privacy”(“shendu”in Chinese),strengthening individual moral and ethical education,cultivating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individuals,intensifying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internet ethics etc.
self ethics;internet public opinions;guidance
G41;B82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2.04.026
2012-03-05
冯 荣(1982—),男,浙江省临海市人,台州学院党委学工部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石变梅(1973—),女,山西省太谷县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台州学院思政部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GXSZ022YB)
(责任编辑 易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