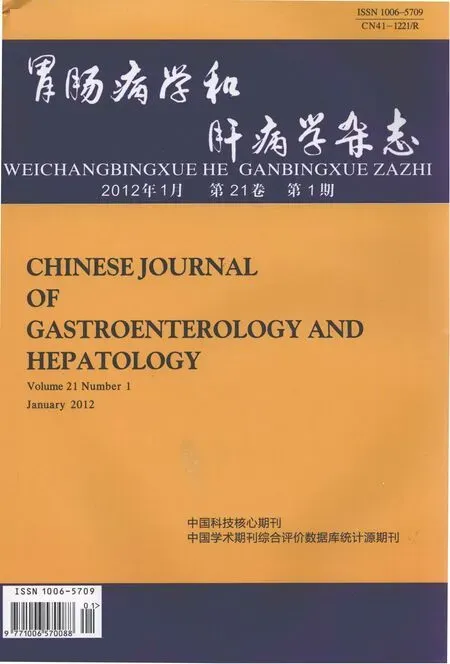胃癌研究及诊治新进展
王婕敏,林三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北京100191
胃癌目前是全球发病率第四位的恶性肿瘤,在肿瘤中致死率居第二位。我国是胃癌高发国家,每年新发病例占全球的40%[1],且早期胃癌诊断率低,在胃癌研究与诊治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本文仅就近年来胃癌的流行病学、病因及基础研究、诊断治疗等方面的新进展进行概述。
1 胃癌流行病学
2008 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再次对全球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进行统计[1],并于2010年公布数据:2008年胃癌的新发病例989 000人,发病率为14.1/10万,新发病例70%在发展中国家。全球胃癌死亡738 000人/年,死亡率为10.3/10万。其发病率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分布,高发地区包括东亚、东欧和中、南美,而亚洲南部、北非、东非、北美及欧洲发病率较低。男性发病率为女性的2倍,在东亚地区发病率为男性42.4/10万,女性18.3/10万,死亡率分别为男性28.1/10万,女性13.0/10万。2005年我国公布的数据[2]显示我国胃癌发病率在男性中达37.1/10万,女性中为17.4/10万,死亡率分别为15/10万和13.3/10万。胃癌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下降趋势,近10年间下降约 10%[1]。
胃癌的危险因素目前较明确的有:幽门螺杆菌(H.pylori)感染、高盐摄入、胃癌家族史、吸烟及大量饮酒;保护性因素为摄入非淀粉类新鲜蔬菜(尤其是葱属蔬菜)及水果;近期有文献报道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对胃癌的发生有预防作用,但此结论尚在进一步研究中。由于H.pylori是胃癌的重要致病因子,一些前瞻性研究显示,人群中根除H.pylori有使胃癌发生率下降的趋势[3]。
2 胃癌病因的基础研究
胃癌的发生是多因素参与、多步骤的复杂病理过程,是环境因素、H.pylori感染和宿主基因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却环境因素,目前病因的基础研究集中在基因因素及H.pylori致病性和毒力因子等方面。另外,胃癌干细胞成为近期的研究热点,为胃癌的发病机制研究及诊疗开辟了新的途径。
2.1 基因因素 基因因素包括调控异常及基因多态性,近年的研究报道了多个被认为在胃癌发病中起关键作用的基因,这些基因参与H.pylori感染后的炎症反应、黏膜保护和对氧化损伤的DNA保护,在胃癌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基因表达异常由基因突变、异常甲基化等原因引起,例如基因CDH1突变引起的E-钙黏蛋白表达下调,影响H.pylori黏附及感染后的信号传导通路,与胃癌发生有关[3];三叶肽因子2(TFF2)影响黏膜修复机制,被认为是抑癌因子,胃癌患者中存在TFF2基因启动子异常甲基化,使TFF2表达下降[4]。另外,抑癌基因p16、p53等表达异常也受到关注。
一系列研究均证实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基因的突变和过表达,以及其下游信号转导通路的异常激活与胃癌的发生、转移显著相关,已经成为胃癌分子靶向治疗的靶点。Runx3是近年发现的一个抑癌基因,对细胞的分化、周期调控、凋亡和恶性转化起作用,在胃癌患者中存在Runx3启动子甲基化现象[5]。
基因多态性是另一参与胃癌发生的重要因素,主要集中于白介素及炎症因子TNF、COX-2等。白介素是炎症反应的重要因子,在肿瘤的发生中起到一定作用,近年白介素基因多态性在胃癌的病因研究中受到关注。白介素-1-β(IL-1b)的基因多态性最先被报道。其余白介素如IL-6、IL-10及IL-16等的基因多态性与胃癌的关系也得到广泛研究[5]。
2.2 H.pylori致病性及毒力因子 H.pylori相关的致病因子包括细胞毒素相关蛋白(CagA)、空泡毒素(VacA)和外膜蛋白(OMP)。CagA蛋白由cag-PAI编码,通过Ⅳ型转运进入细胞质,引起细胞分裂和增殖。CagA阳性菌株感染的患者,胃癌发病率较高。VacA蛋白由vac基因编码,使胃上皮细胞空泡形成,诱发细胞凋亡,vac基因信号区有s1和s2两种等位基因,中间区有m1和m2,s1/m1基因型被认为与胃癌最相关。东亚地区的H.pylori菌株均为s1,日本和韩国m1型多见,m2型在亚洲南部较为常见,而此地区胃癌发病率较低。目前至少32种OMP被识别,与幽门螺杆菌的黏附作用有关。目前发现与胃癌显著相关的OMP包括:OipA、BabA、SabA 和 AlpAB[6]。
2.3 胃癌干细胞 随着肿瘤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大量证据表明肿瘤本质是一种干细胞疾病,Takaishi等[7]首先将于无血清培养基中体外培养人胃癌细胞系产生的球状克隆种植入裸鼠皮下,这批小鼠在几个月后形成胃癌移植瘤,表明胃癌细胞系中确实存在肿瘤干细胞。
目前鉴定肿瘤干细胞的主要方法包括体外球形克隆形成实验和体内成瘤实验两种;体外实验,即应用无血清培养的方法从候选细胞中分离出具有球形集落形成能力的细胞;体内实验,将候选细胞植入裸鼠皮下或器官特异位点,观察其致瘤性,为鉴定的金标准。在胃癌干细胞的识别方面,经流式细胞技术发现CD44、CD24可能是胃癌干细胞的标记物,但并不特异,由于尚缺乏特异性表面标记物,对胃癌干细胞的起源、分离、鉴定及靶向治疗的研究造成困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胃癌干细胞必将为胃癌的发病机制及诊疗开辟新的途径。
3 胃癌筛查及诊断
3.1 胃癌筛查 日本作为胃癌高发国家,长期采用钡剂双重对比造影进行人群普查,每年600万人接受X-线造影普查,早期胃癌病例占胃癌病例的70%以上[8]。我国受到经济及医疗等多方面制约,早期胃癌诊断率仍不足10%。近年,血清胃蛋白酶原检测作为无创、简单、经济的筛查方法受到关注,日本从90年代起开始应用于人群普查,筛查癌前病变及胃癌。胃蛋白酶原(PG)是胃蛋白酶的前体,人体内表达两种同工酶:PGⅠ和PGⅡ,PGⅠ主要由胃主细胞和颈黏液细胞产生,PGⅡ不仅由这些细胞产生,在贲门、幽门和十二指肠布氏腺中也有生成。文献推荐以PGⅠ≤70 ng/mL和PGⅠ/PGⅡ≤3定义为阳性,预测萎缩性胃炎的敏感性 93%,特异性 88%,检测胃癌的敏感性84.6%,特异性67.2%[9]。日本学者推荐血清PG与H.pylori抗体联合检测作为胃癌筛查的初筛方法[10],确定高危人群,然后对高危患者进一步行内镜检查,结果显示早期胃癌诊断率高达78%。在一项对日本17 647人进行筛查的研究中,以PG检测联合造影作为筛查手段,胃癌发现率0.28%,高于单纯应用造影筛查的0.1%,其中88%为早期胃癌[11]。
3.2 胃癌诊断及分期 胃镜及活检病理仍然是诊断胃癌的最主要途径。近年内镜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除传统内镜外,新的内镜技术,如放大窄带成像(M-NBI)、荧光成像、色素内镜、共聚焦显微内镜,均提高了内镜下发现病变及活检的准确率,对于形态学上进一步认识病变,指导活检起到重要作用。
自2010年起,美国癌症联合会(AJCC)及国际抗癌联盟(UICC)的第7版TNM分期标准颁布实施,与第6版TNM分期相比,新版分期系统对肿瘤浸润、淋巴结转移等判定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如:(1)肿瘤侵及浆膜下层定义为T3(原为T2b);(2)肿瘤侵透浆膜定义为T4a(原为T3)。N分期淋巴结的枚数也进行了修改:(1)N0无局部或区域淋巴结转移;(2)N1:1~2枚淋巴结转移;(3)N2:3~6枚淋巴结转移(原为N1);(4)N3a:7~15枚淋巴结转移(原为N2);(5)N3b:大于或等于16枚淋巴结转移(原为N3)。同样TNM分期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新版TNM分期可能对评估预后更具有指导意义。
4 早期胃癌的内镜下治疗
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和内镜下黏膜下剥离术(ESD)作为早期胃癌治疗的主要手段,已经受到广泛认可,内镜下病变整体切除率达到95%以上,日本学者对1 370余例术后患者进行随访,随访32个月复发率为1%[12]。内镜下切除不伴淋巴结转移的早期胃癌得到新版NCCN胃癌指南的推荐。随着近年ESD术的广泛开展,日本胃癌学会将内镜下治疗传统(分化良好、<2 cm的非溃疡型早期胃癌)扩展为:(1)分化良好的黏膜内癌,没有淋巴管或血管浸润,病变≤3 cm,不管是否合并溃疡;(2)分化良好的黏膜内癌,没有溃疡,没有淋巴、血管浸润,无论病变大小;(3)黏膜下SM1(黏膜下层的上1/3)癌,分化良好,没有淋巴、血管浸润,病变≤3 cm[13]。
5 胃癌的药物治疗
在辅助化疗药物方面,亚洲国家学者主张进展期胃癌行根治性胃癌切除术后应行S-1单药化疗。S-1是由日本研发的新型口服氟尿嘧啶类抗肿瘤药物,含有细胞毒性药物替加氟及另外两种酶抑制剂CDHP和OXO,S-1在胃癌化疗的单药有效率是所有化疗药物中最高的,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2007年,日本的ACTS-GC实验[14]证实S-1单药辅助化疗可以提高胃癌术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此后多项临床实验均印证了此结论,因此日本新版胃癌处理规约推荐Ⅱa-Ⅲb期患者术后采取S-1辅助化疗,我国临床应用S-1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胃癌分子靶向治疗是近年研究的热点,很多靶向治疗的药物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曲妥珠单抗为首个被推荐应用于临床的靶向治疗药物。ToGAⅢ期临床试验[15]的结果于2009年公布,这是一项包括24个国家130所医院参加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入组3 807例不能手术的局部晚期/转移性胃癌和胃食管接合部癌,治疗组采取曲妥珠单抗联合5-Fu或卡培他滨+CDDP治疗,对照组单纯应用化疗,结果显示治疗组可使患者平均生存期延长2.7个月,死亡风险下降26%,组织HER-2高表达的患者可更进一步获益。此研究成为胃癌分子靶向治疗领域的重大突破。基于此项研究,2011 NCCN[16]及英国的新版指南均推荐对于不能手术切除的进展期胃癌检测HER-2,表达阳性的患者进行靶向治疗。更多的进一步评估其疗效和安全性的临床试验尚在进行当中。
其他尚处于Ⅱ-Ⅲ期临床试验中,具有临床应用前景的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包括: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单克隆抗体西妥昔单抗(Cetuximab);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吉非替尼(Gefitinib)和埃罗替尼(Erlotinib);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抗贝伐单抗(Bevacizumab)以及VEGF酪氨酸激酶受体拮抗剂舒尼替尼(Sunitinib)等[17]。虽然目前大部分药物还处于实验室研究或Ⅱ-Ⅲ期临床试验阶段,且目前仅局限于应用在进展期不能手术的患者中,但生物靶向治疗无疑是肿瘤治疗领域的重大突破,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及发展。
[1]Ferlay J,Shin H,Bray F,et al.Estimates of worldwide burden of cancer in 2008:GLOBOCAN 2008 [J].Int J Cancer,2010,127(12):2893-2917.
[2]Yang L.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gastric ncer in China[J].World J Gastroenterol,2006,12(1):17-20.
[3]Bornschein J,Rokkas T,Selgrad M,et al.Gastric cancer:clinical aspects,epidemiology and molecular background [J].Helicobacter,2011,16 Suppl 1:45-52.
[4]Kim H,Eun JW,Lee H,et al.Gene expression changes in patientmatched gastric normal mucosa,adenomas,and carcinomas[J].Exp Mol Pathol,2011,90(2):201-209.
[5]Correia M,Machado JC,Ristimäki A.Basic aspects of gastric cancer[J].Helicobacter,2009,14 Suppl 1:36-40.
[6]Herrera V,Parsonnet J.Helicobacter pylori and gastric adenocarcinoma[J].Clin Microbiol Infect,2009,15(11):971-976.
[7]Takaishi S,Okumura T,Tu S,et al.Identification of gastric cancer stem cells using the cell surface marker CD44[J].Stem Cells,2009,27(5):1006-1020.
[8]Wanshanyayi.Diagnostic experience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in Japan[M].In:Xia YT,Wu YL,Fang DC,et al.Progress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gastric disease.Shanghai: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press,2005:123-124.丸山雅一.日本早期胃癌的诊断经验[M].见:夏玉亭,吴云林,房殿春,等主编.胃病诊治进展.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123-124.
[8]Miki K.Gastric cancer screening using the serum pepsinogen test method [J].Gastric Cancer,2006,9(4):245.
[9]Miki K.Gastric cancer screening by combined assay for serum anti-Helicobacter pylori IgG antibody and serum pepsinogen levels-“ABC method”[J].Proc Jpn Acad Ser B Phys Biol Sci,2011,87(7):405-414.
[10]Kim N,Jung HC.The role of serum pepsinogen in the detection of gastric cancer[J].Gut Liver,2010,4(3):307-319.
[11]Ahn JY,Jung HY,Choi KD.Endoscopic and oncologic outcomes after endoscopic resection for early gastric cancer:1370 cases of absolute and extended indications[J].Gastrointest Endosc,2011,74(3):485-493.
[12]Haruta H,Hosoya Y,Sakuma K,et al.Clinicopathological study of lymph-node metastasis in 1,389 patients with early gastric cancer:assessment of indications for endoscopic resection [J].J Dig Dis,2008,9(4):213-218.
[13]Sakuramoto S,Sasako M,Yamaguchi T.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gastric cancer with S-1,an oral fluoropyrimidine[J].N Engl J Med,2007,357(18):1810-1820.
[14]Van Cutsem E,Kang Y,Chung H,et al.Efficacy results from the ToGA trial:a phaseⅢstudy of trastuzumab added to standard chemotherapy(CT)in first-line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positive advanced gastric cancer(GC)[J].J Clin Oncol,2009,27(18 Suppl):LBA4509.
[15]Allum WH,Blazeby JM,Griffin SM,et al.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oesophageal and gastric cancer[J].Gut,2011,60(11):1449-1472.
[16]NCCN.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gastric cancer[M].Version 1.2011,NCCN.org.
[17]Zagouri F,Papadimitriou CA,Dimopoulos MA,et al.Molecularly targeted therapies in unresectable-metastatic gastric cancer:a systematic review[J].Cancer Treat Rev,2011,37(8):599-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