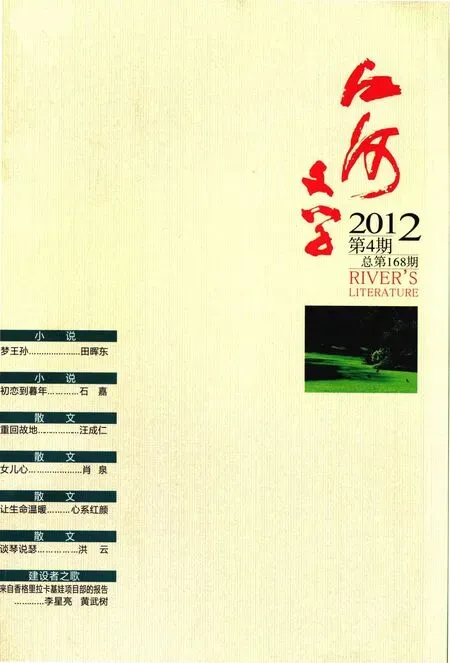初恋到暮年
■石嘉
我现在靠一份退休金生活,在南方的大城市有固定居所,原籍已无亲人。每年清明的时候,我都要回苏北老家曹集一趟,除了祭奠祖坟,我这辈子难已割舍的还有儿时的老师。她是我的启蒙老师,在当时的知识女性中有些标新立异,她是抽纸烟的,中指和食指的二分之一处夹着香烟,坐在书案前备课,聪慧的目光从眼镜片后透出来,巡睃着做作业的同学们。缕缕的烟雾沁入教室,袅袅的散开,混合着粉笔沫儿的气息。老师的年龄比我们学生大三五岁,名叫阮敏君。我的家乡曹集镇仅此一所小学,坐落在运河边儿上,整天都可闻到潮润略带腥味儿的河风。
镇小学是破败的河神庙改建的,因教舍短缺,学生便分上下午两部分上课。下午,我这个班级里顶顽皮的学生,便会被阮老师领到她家里去做作业,这名义上是管束以防贪玩误学,实际上是她给我的学业开了“小灶”。功课完成以后,阮老师便绘声绘色的给我讲“西游记”,东周列国故事和古代寓言。她很优雅的抽着香烟,清丽的脸上有一种悠远神奇的魅力,紧紧地吸引着我。
阮老师孤身一人,爹娘死的早,她十五岁便开始以教书为生了。据说老师的爷爷中过前清秀才,所以她家在镇里颇为显赫,老宅院虽然破旧,大门口还蹲着两座石狮子,老屋雕花窗棂残漆班驳,老式红木书橱里满架子的书,墙上挂着发黄的镜框,椭圆形的相片是位清代装扮的老者,还有一幅水墨画“雪江寒钓图”。我思忖着图上的渔翁将头缩进蓑衣里,明明一幅畏冷状,并不像老师讲的那般悠闲快乐。书案上卧着一尊镇纸铜兽,眼窝里嵌着红珠儿,可神灵了。总之这古色古香的老屋里,似乎浮荡着许多难以捕捉的奇妙趣味。童稚的好奇好动,我总免不了碰翻了花瓶,或者扯乱了床上的帏帐。阮老师丝毫不嫌烦,她恬静的坐在太师椅上,吸完了一支香烟,便来了兴致,用斗笔悬腕泼墨,在宣纸上写了两个字“学童”,竟有脸盆大,惊得我目瞪口呆。她说:“学童和老师,一根绳拴着的两只蚂蚱,跑不了我,也蹦不了你。”说着刮了一下我的鼻子。整个下午,老屋里时而书声朗朗,时而欢笑盈盈,直到晚霞染红了归巢的雀儿,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六月间,过了麦季,便会有乡间的农妇,在学校门旁卖蚕。娘给我五分钱,让我买一个葱油烧饼作早点,我舍不得花,却用这钱买了一条白胖透着光泽的蚕儿,当作玩物带到阮老师家。蚕光秃秃的躺在纸盒里,没有桑叶,它昂着头左顾右盼,拼命找吃的东西。我用草棒拨弄着蚕儿,玩得津津有味。一脚踏进门里,我便愣住了,只见一个秃顶络腮胡子的男人,将阮老师摁在床上,用手在她胸脯上胡乱搓揉,还把老师的裙子给拽下来了。我的两腿僵了似的不能动弹,大张着嘴巴却叫不出声,“叭嗒”把盛蚕的纸盒扔在地上。阮老师披散着头发,小声央求道:“快走吧,你吓着孩子了。”那男人油光光的脸膛,敞开的衣襟露出胸毛,“嘿嘿”笑着,摸摸我的脑袋,走了。阮老师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说:“看见只当没看见,回去别朝人讲呀。”她匆匆整理弄乱的衣裙,看到掉在地上纸盒里的蚕,心疼的“哎呀”叫一声,捧起纸盒,说:“这是条性命,它饿的慌,蚕宝宝怎能给你织一枚美丽的茧呢?”她焦急的责备,使我从刚才的惊怖中猛醒。我知错的站在老师面前,问:“怎么办?忘记向卖蚕的讨几片桑叶了。”她沉吟了一阵,忽然大叫:“蚕儿有救了,有救了。”便飞快地跑到一堵颓败的土墙下,定了定神便攀爬起来。我仰起脸,看到野草戳红了老师白嫩的腿。墙头上有株小桑树,她终于手里抓了一簇鲜嫩的桑叶,不料裙子被挂住,竟失足从墙头跌落下来,我害怕地哭了。她拍拍自己身上的泥土,却乐呵呵的笑出声:“待我吸几口烟,腿自然就不疼了。”说罢牵着我的手去喂蚕,如同亲热的大姐姐。其他班级的同学经常挨教鞭的体罚,而我却不必有这种惧怕,倒时常和老师嬉闹一团,其乐融融。
那天回家后,我忍不住将看到秃顶络腮胡子男人的事儿,讲给娘听了。娘叹口气说:“那是阮老师爹活着时候许下的娃娃媒,治病欠了人家大笔钱,男人是县城鲁记肉铺的掌柜。”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鸡叫三遍了,迷迷糊糊做个梦,阮老师到县城成了亲,让那个姓鲁的杀猪匠给害了。我抽抽泣泣哭醒过来,娘正给我揩眼泪,说:“这孩子发呓怔了,醒醒。”我翻身爬起来,便朝阮老师家跑,心想,跟老师厮守在一块儿,看护着她,那鲁掌柜便抢她不去。其实,我对秃顶络腮胡子惧怕得要命呢。此后,我上了瘾似的,每天下午必须到阮老师家里做功课,喝她书桌上紫砂壶里的香茶,在她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扒土翻泥的逮虫儿玩。阮老师会撺掇我在她书架上翻弄书,我小时长得胖墩墩的,她便喊我:“小胖孩,去拿书,我要讲故事啦。”我爬上凳子,在书架上拣有好看画儿的书,琢磨着里面的事物。十岁出头的孩子毕竟是识不了几个字的,可在老师鼓励的目光里,我却对书有了天然的亲近感觉。阮老师穿着白洋布衫儿,黑绸裙子,腰身很好看,她笑容可掬的神态令我蓦然腼腆起来。这个年纪的男孩,大概是性别意识觉醒的时候,除了娘,老师便是我依恋的女性,我喜欢上了她,也更喜欢在斑斓如梦的老师家里玩儿。在老师娓娓道来的故事熏陶下,我愈发规矩懂事了,我帮老师洗手绢儿,还唱“拉魂腔”给她听。“拉魂腔”是家乡土戏,拖长调要拐几个弯儿,挺好听的。阮老师也唱了起来,唱着唱着便落了泪,静静地想起了心事,腮上挂着晶莹的泪珠儿。她把我揽在怀里,沉默不语,好久好久,忽然笑着柔柔地说:“小胖孩,将来你准能娶上称心如意的好媳妇,过甜甜蜜蜜的小日子。”我贴身偎着阮老师,闻到她衣裳上有一股幽幽的香肥皂味儿,我想摸她的脸,又不敢,心里惶惶的。
阮老师是正月初六出嫁的,曹集镇一团过年的喜庆,店铺都张灯结彩。鲁家接亲的队伍摆了老长老长,喜幡华盖,吹吹打打,花轿颠得翻江倒海,却不闻阮老师的声音,连哭声也没有。街坊邻居说阮老师是鲁家的人捆绑堵嘴弄进花轿里的,什么娶亲呀?活土匪,抢亲哪。我跟着花轿跑了好几里地,腿跑软了,一下子趴在铺着积雪的青苗地里。运河结着薄冰,水在冰下呜咽,花轿的笙弦喇叭“叽叽哇哇”,鲁家迎亲的喧嚣渐渐隐进苍凉的冬野里。
阮老师嫁进城里以后,我便厌学,逃学,被爹打了好几场,实在没有办法,家里便把我送到曹集镇的布店当学徒,给老板看孩子,生炉子做饭干杂活。我每逢走过阮老师家,便要在那停一会儿。阮老师的老屋已变卖改作镇上的粮行仓库了,我老是在门前遛来遛去,看门的便怀疑我是小偷,高声斥骂撵我走。我走了几步,不忍心依旧回转来,朝门里窥视,仿佛听见阮老师笑吟吟地招呼我:“小胖孩去拿书,讲故事啦。”
这一年,过了清明天气转暖的时候,夜里我真的听到后窗有人在叫我小胖孩,啊,是阮老师,我跳下床,光着脚丫儿跑到门外,一看,阮老师在月光下浑身像裹了一层纱,苍白的脸儿清秀憔悴,她没戴眼镜,还掉了一只鞋,两手空空,贴在我脸上耳语道:“给我拿包烟,好几天没抽烟,我馋死了。”我飞快地回屋将爹的一包香烟拿给阮老师。她接过烟,匆忙说:“千万别吱声,回去睡觉,我死在曹集镇也不走了。”我躺回到床上,想着阮老师月光美人的模样儿,怎么也弄不清楚是做梦呢还是阮老师真回来了呢?
清晨,我被一阵嘈杂惊醒,爹娘和邻居们都向运河边跑去。我赶到河边,阮老师湿淋淋的尸体,已被鲁家的人抬到马车上,盖着草席。鲁掌柜向众乡邻抱拳道:“家门不幸,俺媳妇寻了短见,她生是鲁家的人,死是鲁家的鬼。”说罢催动马车回县城了。我死死憋了一整天,没有哭出声,傍晚,我偷偷拿了过年攒的压岁钱,买了一条上好的香烟,跑到阮老师投河的地方,将烟烧了。烟雾中,我哭得昏天黑地,眼泪鼻涕湿了衣襟,哭累了,我便趴在河堰边儿上睡着了。乡邻们打着灯笼,举着火把满世界寻我,将我抱回家时。我的胳膊和腿都冻僵了,嘴里还喃喃的叫阮老师。娘心疼的抚慰我道:“阮老师那闺女走了倒干净,她到天堂享福去了。别伤心啦,将来一定给你娶个像阮老师那样的好媳妇。”娘已故去近半个世纪了,她的话语犹在耳畔,我却年过花甲,夕阳垂暮,生活几经变故至今仍形孤影单。家乡的运河水变浑变瘦,浅不及胸,倘若阮老师复生再投水,运河也是淹不死她的。清明时节,我照例到老师投水处祭奠,往年我总要痛哭一场,今岁欲哭却无论如何哭不出来,无奈便微笑着唱了一段“拉魂腔,”直唱得残阳如血,运河水红金闪烁,就像我儿时的初恋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