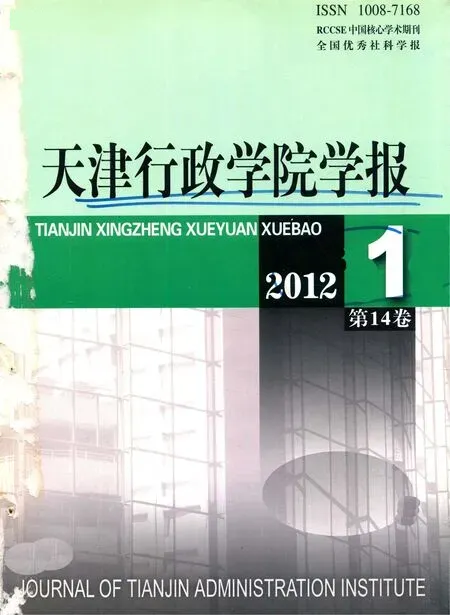民主政治条件下社会稳定的内在机理探析
黄毅峰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03)
民主政治条件下社会稳定的内在机理探析
黄毅峰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03)
社会稳定是政治生活的价值追求和现实需要。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政治实践所采取过的全部政体中,只有民主政治较好地实现了社会稳定。究其原因,民主政治所内含的信任、妥协、宽容和法治理念以及在此理念基础上建构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机制、权力更替机制、冲突调控机制、协商谈判机制和社会资本增量等民主机制为其实现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提供了价值基石与根本保障。
民主政治;社会稳定;内在机理
政治稳定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系统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达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是政治的终极价值,要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必须具备两方面要素:一是该政治体制中内含秩序稳定的价值理念,它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是要有一整套建立在此价值理念基础之上的制度架构,它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保障和动力。唯有如此,方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迄今为止,民主政治在实现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了较好作用,是最为有效的政体之一。其原因在于民主政治内含的价值理念以及在此理念基础之上所架构的机制制度,为实现和维持社会的动态稳定与平衡提供了可能和保障,正如有人所言:“民主立国是政治稳定的大前提。”[1](p.429)
一、思想理念是支撑民主政治条件下社会稳定的价值基石
戴维·赫尔德说:“民主的思想是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体现了自由、平等和公正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而且它是可以联系和协调相互竞争的既有问题的一种价值。”[2](p.377)民主政治所内含的信任、妥协、宽容、法治等思想理念,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精神”,为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奠定了最坚固的价值基石,成为民主政治条件下实现社会持久稳定的动力源泉。
(一)信任为民主国家的大众支持提供了内在源动力
信任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没有信任这样的东西,人类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就此而言,信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人类关系就将为猜疑所支配。每个人都将把任何其他人作为一个潜在的敌人,一旦有机会,这种潜在的敌人就会使他栽跟斗”[3](pp.44-46)。显而易见,信任是人们走向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信任可以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增强社会整合、公民参与的动力,它是社会政治系统实现良性运行的润滑剂。罗伯特·达尔在谈到多头政体的时候就曾经指出,“相互信任有助于多头政治和公开争论,而极端怀疑有助于霸权政治。首先,多头政治需要双向的或相互的交流,而在彼此不信任的人们中间,双向交流受到阻碍。其次,人们要自由的聚集起来以便实现他们的目标,就需要有一定的相互信任。以命令为基础的组织,权威向下,也许适合于相互信任;在一个怀疑气氛里很难建立和维持以相互影响力为基础的组织。最后,冲突对彼此怀疑的人们是更大的威胁。公开争论要求人们对他们的对手有充分的信任:他们可能是对手,但不是死敌”[4](p.166)。而信任缺失则是社会冲突和政治灾难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不稳定源于“阿拉伯人的互不信任感,在他们还处于孩提时期,就开始浸蚀到其价值体系中去了。……更主要的是,他们对统治者普遍缺少信任感和信心”;厄瓜多尔“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和长久的互不信任互为因果,致使我们不能不给民族的灵魂留下创伤;这种政治浪费了我们的精力,使我们变得虚弱不堪”;埃塞俄比亚“由于对人的团结和协同一致的能力不很重视,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充满了一种互不信任不合作的气氛”[5](p.10)。显而易见,民主政治首先是信任政治,离开信任,民主将不可能存在。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曾经谈到,“信任民主的程序(选举、代表制、多数人选举等)是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中达到最合理的妥协的最好途径。或者信任适当的法律程序是达到公正公平的判决的最好方法”[6](p.59)。信任的政治理念可以提供一种信任氛围和大众支持的持久基础而使民主得以稳定。无论是社会冲突的预防和调控,还是公众与政府间的合作、协商、妥协、谈判等,都离不开社会政治主体双方以相互的信任作为前提。政治系统内部纵向上下级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横向的部门之间关系的调整与沟通,同样以信任作为前提。而政治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互动,更是离不开信任。可见,离开了信任,整个政治系统将摇摇欲坠,根本无法达成社会稳定。
(二)妥协是民主国家用于解决矛盾分歧的重要原则
妥协是指相互冲突的社会主体为了某种程度上的共同利益,基于避免直接对抗造成相害后果的共同认识或默契,通过协商谈判做出让步以求得缓和矛盾或解决争端的行为过程及结果。妥协是人类理性逐渐成长和走向成熟的必然结果,它的根本价值是以和平、和谐的方式促成合作,解决矛盾冲突。有了妥协,矛盾的解决无需依靠暴力,不同利益诉求也可以在妥协原则下和平共处。当冲突发生时,矛盾双方能通过思想的宽容和理性的说服来获取最大社会利益。与此相反,两败俱伤、玉石俱焚是一种非理性的冲突解决方式。妥协通过达成各社会主体相对满意的结果而重新整合,这样,妥协润滑了政治系统和协调了政治过程,避免了高强度冲突的形成从而威胁社会稳定。同时,妥协还是一种理性共识和合作精神的体现,没有妥协也就没有政治合作。英国历史学者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7](p.165),事实上,可以更进一步说,妥协是民主的灵魂。妥协精神被视为民主所有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民主国家的公民须乐于以妥协的办法解决他们的分歧。民主的所有条件之中,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而有关各方如不愿妥协,即无达成妥协的可能”,“妥协是民主程序的核心”,“妥 协的过程对 民 主 是特殊的支 持”[8](pp.182-186)。妥协精 神 是 民主政治制度内生的、必然的政治现象,也是民主政治能够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奥秘。如果没有妥协的精神气质,民主政治必然不能扎根,至多只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和瞬间即逝的过客。因此,妥协也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美德。民主依赖妥协,而且民主理论本身也充满妥协——若干冲突的、互不相容的原则之间的妥协。达尔曾分析指出,民主政体显然要比专制政体更容易有冲突,从而民主政体中必然存在着大量的政治冲突;然而,另一方面,虽然民主政体冲突频繁,但冲突的激烈程度与专制政体却相对较低[9](pp.110-112)。究其原因,就在于民主国家特别是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公民在长期的民主实践过程中已培养起一种妥协精神,能够并希望在既有制度规范内通过协商谈判与互谅互让来解决矛盾与冲突。否则,大量涌现的无处不在的政治冲突与拒绝妥协的极端斗争精神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民主政体。而在所有的策略中,妥协也是民主国家用以调控政治冲突最经常使用也最行之有效的策略之一。与之相反,专制政治往往倾向于政治强力而排斥政治妥协,即使有政治妥协,至多也只是在政治强力不及的地方作为其补充偶尔使用。所以,有人提出,在如何对待政治冲突问题上,强制与妥协已经成为区分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宽容是民主国家由多元化趋于和谐一致的驱动力
宽容是民主和自由的前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和自由的象征。宽容可以理解为政治权力主体在宪法范围内,通过尊重和保障政治权利对象的政治自由与权利,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并使它们得以和平共存,以实现有利于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和谐政治秩序的一种政治手段。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如何,就会有何种程度的宽容意识。安托万·加拉蓬曾指出:“一个民主的社会往往被认为比其他社会更宽容,不是因为它更有道德,而是因为它并不满足于容忍各种差别,反而鼓励或甚至造成这些差别。”[10]宽容是民主的支柱,宽容意味着政治主体与客体将以民主协商、平等对话以及和平竞争作为主要的活动方式和伦理取向,它是现代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政治民主化以及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宽容会使政府与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包容,从而缓解社会矛盾,降低政治的风险系数。达尔研究发现,“宽容的国家绝大多数是稳定的和非暴力的”[9](p.111)。当然,宽容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寻求和谐与秩序的解决办法和手段;而这种办法可以维系和实现社会政治稳定。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从压制到宽容、从强权到说服、从垄断到竞争、从无序到有序的逻辑趋向,而政治是否宽容已经成为区分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原则界线。“极端往往是动乱的根源。这是资产阶级稳定自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的经验总结。它是反对神学专制主义、反对经院哲学长期斗争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稳定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11]总之,宽容是民主政治理性成长的产物,“是一种有利于大家共同发现真理、维护真理,有利于在多元化、多样化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与和谐的一条现实的必要的原则”[12],是人类实现和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理性使然。
(四)法治使民主国家的社会稳定获得了广泛而现实的制度基础
民主与法治也许不能达到最好,但一定能防止最坏,特别是防止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法治是人类为争取自由平等长期奋斗的结果,反映着人类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从等级特权走向主体平等、从权力专制独裁走向权力制约、从诉诸武力解决冲突走向和平解决冲突的艰难历程。实践证明,法治是协调价值和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是治理社会和管理国家的可行之道。只有实现法治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洛克就曾经说过:法律的终点是暴政的起点。而完善和健全的法制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前提与基础。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最大的法制——宪政的框架下,建构起完善的法制体系,使整个社会笼罩在巨大的法网中。政治运行的法治化实际上就是政治制度化、有序化的过程。通过政治运行法治化,在政治系统的框架内,各种政治关系被制度化、契约化,变成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通过政治运行法治化,政治权力更替的每一环节都具有合理的程序、专门的机构和有效的保障措施,能够防止权力交接过程的中断和极端行为的产生,防止企图根本改变政治体系和政治演进等现象的发生;通过政治运行的法治化,权力的使用有了约束力量,可以防止权力滥用和政治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也就预防了由于政治腐败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因为只有在法治得到尊重时,强制性权力才会受到限制;政治运行法治化所要求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更是转型社会维持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事实上,民主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秘诀之一就在于政治过程和法律过程的截然分离。所以说,从一定意义来讲,宪政意识和法治意识的不断强化,才会使社会政治稳定具有广泛而现实的制度基础。
二、机制制度是实现民主政治条件下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
民主政治内涵的精神为国家的社会稳定提供了理念支撑,但是,理念只有借助于有效的机制制度,才能实现它的价值与功能,民主政治成功地实现了理念与制度的完美结合,在理念的基础上建构起制度大厦,实现和维持着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动态稳定。
(一)制度化的调控机制为社会冲突的调节与化解提供了长效武器
冲突与合作是政治生活固有的内在特性,但冲突并不必然导致不稳定,冲突是否导致不稳定取决于政治系统是否具有调控冲突的能力机制。政治的本质也就是处理、利用以及缓解冲突的过程。作为权力安排的一种手段——民主政治,它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公开的竞争性,也即允许政治竞争与政治冲突。甚至有人说,“发展一种允许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立、抗衡或者竞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不断地对公民的选择做出响应,公民在政治上被一视同仁”[5](p.11)。冲突、竞争、领导以及组织是民主政治的本质所在。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为大量的民众在其中发挥作用创造特殊条件[13](p.124)。但是,关键在于,民主政治在允许冲突与竞争的同时,也为冲突和竞争提供了制度框架,建构了制度性的冲突运行和调适机制。被誉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三大支柱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其制度建构思想与灵感无一不是来自于制度性冲突调控的理念基础。所以说,“稳定的民主政权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能调节这种冲突,从而所动员起来的是选票而不是武器”[14](p.149)。这也就不难理解S·N·艾森斯塔德谈到的,政治稳定与否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社会能否产生容纳持续变迁的制度框架,能否孕育出一些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机制[15](pp.24-25)。与此相反,专制政体更多的是借助于国家机器,以暴力来对抗暴力,采用压制冲突的办法来实现社会稳定。然而,压制只能是暂时的缓解而不能根除不稳定力量对政治系统的稳定构成强大威胁,因为“不管压制冲突的这种努力怎样被证明是合理的,冲突和对抗是不能排除的。它们植根于权威关系的结构之中。简单地压制或否认冲突,只能使冲突没入表层之下,在那里,它酝酿着、积累着,长期不被人们觉察。然而不管怎样,被浸没的冲突总要周期性地爆发出来。当它爆发出来的时候,往往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由于现在的结构缺乏处理冲突的途径与方法,暴力革命的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极权主义的模式中,压制冲突的努力被暴力反抗的爆发而同期性地加强了”[16](p.608)。社会依靠行政权力采取压制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办法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强制性权力已经越来越难于发挥冲突调控的功能。现代社会冲突的调控只能求助于行之有效的外部机制和冲突的自身免疫机制。民主政治实现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成功奥秘之一就在于为社会冲突提供了制度化的调控机制。
(二)制度化的参与机制架起了民众与政府之间良性沟通的桥梁
“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5](p.79),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较好地实现和维持着社会稳定,还在于它为公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提供了制度性渠道,它架起了公民的利益诉求、意见呼声与决策者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没有制度规范的大众参与无异于乱政,缺乏游戏规则的政治竞争必然导向流血。因为,拥有资源的集团可以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左右利益和权力的分配,视平等原则如敝屣,不掌握资源或资源短缺的集团只有通过游行示威、骚乱、暴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置秩序法制于不顾。这样,社会稳定的基础就被倾覆了。政治参与被达尔认为是民主政治的两要素之一。民主的本质就是公众能够通过制度性渠道最大限度地参与政治,表达其利益要求。然而,政治参与本身对于社会稳定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定范围的政治参与既可能是社会稳定的缓冲器,但也可能是政治动乱的催化剂。而决定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之间关系的关键在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孕育政治稳定,而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则往往通向动乱或战争。民主政治通过政治系统的输入功能,引导公众需求进入政治系统,这样可以使政治系统及时洞悉和满足公众需求,缓和公众不满情绪,增强公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感。如果政治系统不能向公众提供畅通的、及时的、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公众就会转向制度外借助非正式、非理性的手段与方式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从而威胁政治稳定。因此,要实现社会稳定,就要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而民主政治运行机制当中的选举制度、舆论反馈制度、决策制度等恰好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来表达利益需要与释放不满情绪,为持异议的公众表示不满并继续追求其目标畅通了渠道,提供了可以积极地、公开地、体面地进行反对现行政治人员及其公共政策的制度性渠道,他们对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具有申诉的机会,因此避免了暴力。不论公众如何不满,他们无需忍气吞声,噤若寒蝉,更无需诉诸革命以图补救。正如科恩所言:“如果我有真正参与政府的机会,有发言权而且是算数的发言权,不论我对结果如何感到不快,绝不会企图用武力去改变它。”[8](pp.228-229)
(三)制度化的协商谈判机制避免了由于极端行为引起的社会不稳定
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如果各种政治力量逐渐习惯于合法渠道的共同协商,就会更少地依靠武装的暴力革命来实现政治目的。实践证明,对于特定公众的利益诉求,只要相关各方切实对话,只要有公正合理的协商机制,矛盾就可以缓和,冲突就能够化解。罗伯特·达尔说:“当冲突发生——因为冲突不可避免时,使用政治资源有助于个人和团体防止靠压力和强制来解决冲突,而是坚持通过某种程度的——直率的和含蓄的、合法的、非法的和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谈判协商来解决。”[4](p.88)在协商谈判机制中,政府充当斡旋者或调解者角色,帮助它们寻求一种能让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帮助它们去除冲突的非理性的和进攻性的泛音。约翰逊认为“控制冲突需要形成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和建立处理争端的公共机构。利益群体的组织既引导着又控制着对抗的表现,同时进行协商的机构在冲突着的双方之间提供了一种结合物”[16](p.608)。民主国家通常能够避免严重的社会冲突,因为在这些国家即使存在重大分歧,多数时候它们大体都能让冲突通过协商方式加以解决。而一个有效的“协商体制需要具备的条件:调解的才能;对妥协异常的宽容;值得信赖的领导人,他们能够通过谈判,以支持者同意的方式解决冲突;在基本目标和价值上的一致,但为了能够达成协议,这又应当是非常宽泛的一致;一种民族认同感,它遏制了彻底分离的要求;承担遵守民主程序的义务,排除暴力或革命手段的使用,等等”[8](p.162)。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协商体制既不能产生,即使产生出来也不能运行。卡特赖特等人也指出,政治沟通对于防止和消除政治冲突的功能在于:其一,政治沟通可以发现政治冲突的缘由;其二,政治沟通可以消除政治共同体内的紧张和对峙;其三,政治沟通可以改变政治冲突的指向;其四,政治沟通可以温和的方式阻止政治冲突的发展或解决冲突[17]。总之,通过协商,能够使政治主体通过表达和相互交流取得谅解,缓解冲突强度;并通过协商、谈判和交易,经过各方的妥协和让步,形成和解,从而弥合分歧,化解冲突,实现冲突的整合。因此,政治协商机制不仅是和平地进行冲突的机制,更重要地,它也是和平地解决冲突,在冲突基础上达成一致的政治机制。而民主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在政治体系中建构起了完善和有效的协商机制,从而使得大量的分歧与冲突能够在协商谈判中得到弥合和化解,实现和维护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四)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增量机制提高了民主社会的信任水平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8](p.195)。民主政治是信任的政治,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壮大有赖于信任,反过来,社会资本的壮大又会促进信任的增长。社会资本的壮大是民主政治的发展的重要结果之一,也是“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18](p.216)。政治学家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南方和北方的历史考察发现,民主是一种有利于社会资本成长的制度,而社会资本的增量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因为建立在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上的发达的社会资本,将提高政治主体之间的信任水平,减少或缓解政治冲突,使社会趋于稳定与和谐。首先,社会资本的发达,意味着公民政治参与扩大,政治参与渠道畅通,公民通过参与各种社会团体和俱乐部组织,使其意志得以表达;同时,在团体的大量活动中,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群体与群体成员之间通过不断的互动,加深相互认识与了解,为互相信任提供了认识基础。其次,社会资本促进了自发的合作,形成一种合作本身会带来信任。社会资本的稳步发展,正是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地区的良性循环的关键部分[18](p.200)。第三,社会资本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器。“从革命的观点来看,一种民主的秩序之所以不可能被推翻,其原因正是在于它承认冲突是合法和必要的,并使它的公民有机会参加和支持为各种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斗争的组织。”[19](p.6)现有的证据也表明,当群体与个人有许多横向的、与政治上相关的密切联系时,扩大稳定的民主范围的机会就会增加。如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人口中比例很大一部分被牵扯到各种冲突力量中时,其成员愈关心降低政治冲突的强度[20](pp.58-63)。通过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量来实现和维持政治稳定,已经引起了政治学界和世界各国政治领导者的高度关注。而民主政治中的信任精神理念为社会资本的增量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和源泉。
(五)制度化的权力更替机制为政权的平稳过渡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个国家政治稳定不稳定,其基本标志之一就是看这个国家有无能力按宪法所规定的民主程序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也就是说,要看这个国家有无能力建立起有领导的、有秩序的、合法的制度化民主选举制度。”[21](p.162)权力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政治发展的需要与必然,但实现权力平稳过渡则是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力更替代际转换是与政党制度、普选制、代议制等一整套现代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一般都是通过法律的、正常的、和平的形式,以程序性民主选举和政治竞争,实现政治权力更替的制度化、公开化、理性化和程序化,从而防止了由于权力更替的非常态化、非制度化等对社会稳定造成的重大影响。因此,民主国家虽然政治权力的执行者频繁更替,但由于拥有制度化的运行机制,从而能平稳过渡,成功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
三、结 论
稳定与秩序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标志,寻求稳定有序的政治生活与完美和谐的政治共同体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家与政治学家为之苦苦奋斗的目标,也是人民大众冀图拥有的理想生活。塞缪尔·亨廷顿曾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很显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又自由。”[5](p.8)任何社会都不希望冲突频繁发生而陷入政治混乱与社会动荡,然而矛盾与冲突又是政治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因此,如何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找秩序和稳定,就成为政治的最高目标。但是,和谐稳定的社会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而是内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冲突预防和调控机制,能够实现从冲突动荡到秩序稳定转化的社会。秩序与冲突并不矛盾,压倒一切的秩序并不是真正的秩序,而是奴役的秩序;秩序是冲突中的秩序,稳定是动态中的稳定,这就是政治发展的逻辑。从冲突到
秩序的转化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秩序并不会自动形成,“政治秩序是需要用心建设的公共物品”,“成功的社会必然要求某种保证政治秩序的途径”[22](pp.18-19),即内生或建构起行之有效的社会稳定的调控机制。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能善待冲突。毫无疑问,社会冲突并不是好事,但也并不全然是坏事。一个具有活力的社会往往充满矛盾与冲突。因为矛盾与冲突的存在能让我们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并加以弥补与修复,这显然是社会自我完善的过程。冲突犹如一面镜子,一把尺子,能够随时映照或者检测社会的健康程度。所以,重要的不是存在冲突,而是我们如何善待冲突。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善于纾解冲突,而不是杜绝冲突。对待冲突应该像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越是冲突凸显时期,就越是需要政治智慧。简单打压虽然简便迅捷,然而问题非但不能得到缓解,反而会使冲突能量累积酿成大祸。这就犹如河流被堵塞后形成的堰塞湖一般,当不断增高的水位越过警戒线,垮塌是必然的。而要防止突然崩溃带来的危害,就需要我们在围堰上挖通导流槽,让河水一点点地流出来,以减轻围堰所承受的压力。稳定固然重要,但不能“压倒一切”,“压倒一切”的稳定不是真正的稳定。当一切都被压倒的时候,社会稳定也就不复存在,只有乱象。E·E·谢茨施耐德说:“既然政治源于冲突,那么政治策略就是处理、利用以及抑制冲突的过程”,“如何控制冲突是政治的关键。无法应对冲突的政治体制将难以为继。所有的政治、所有的领导过程以及所有的组织均涉及对冲突的控制问题。所有的冲突都对政治空间进行分割。冲突的结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未建立冲突系统的情况下,一个政治体制的存继便难以想象。”[13](pp.59-63)借用哈耶克之言作为本文的结尾:如果上帝能够降临凡世,一切按无所不晓、又慈悲为怀的上帝的指令行事,我们可以避免一切冲突,达到和谐与完美。可惜上帝即使存在,也不会降临人间,所以人类社会必定要在冲突中寻求秩序。
[1]陶德麟.社会稳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2][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4][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6][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英]阿克顿.自由史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8][美]科恩.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9][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0][法]安托万·加拉蓬.法律和宽容的新语言[J].第欧根尼,1998,(2).
[11]杜镇远.关于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宽容原则的历史考察[J].晋阳学刊,1996,(5).
[12]李德顺.宽容的价值[J].开放时代,1996,(1).
[13][美]E·E·谢茨施耐德.半主权的人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14][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5][以]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6][美]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
[17]王浦劬.西方当代政治冲突理论述评[J].学术界,1991,(6).
[18][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9][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0][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1]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2][美]道格拉斯·C·诺斯,等.秩序、无序和经济变化:拉美对北美[C]∥[美]布鲁克·布恩诺·德·梅斯奎塔,希尔顿·L·鲁特.繁荣的治理之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D082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7168(2012)01-0027-06
10.3969/j.issn.1008-7168.2012.01.005
2010-09-1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群体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及调控机制研究”(10CSH041)。
黄毅峰(1977-),男,江西南康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