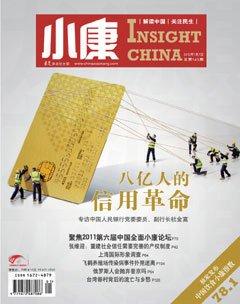台湾眷村背后的流亡与乡愁
于靖园



台湾眷村是离乱历史的产物。居住在眷村中的台湾老兵,背井离乡40年,怀揣着乡愁渐渐凋零。然而战争背后的人伦悲剧,又绝非“乡愁”二字可一笔带过
“这是一个不说就很可能会随即消逝的故事。”
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宣传册子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2011年11月25日,北京,《宝岛一村》剧组第三次来大陆巡回演出。
舞台上,简单的布景,几张桌椅,衣服古旧的男女,灯光打在那些小人物身上,把他们的故事,融汇进历史里。
《宝岛一村》是虚构的名字,位于嘉义某地的空军眷村,经过制作才子王伟忠回忆中的众多人、事、物和导演赖声川的创作,化成舞台上的三家人所经历的近60年生活。记录这个族群曾经在大时代中经历的故事。
再也回不去的家
“眷村”,顾名思义是“眷属居住的村落”,尤其是指军人的眷属。1949年,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包括60万军队在内的国民政府党团官员、公务员和军眷等合计约为120万人,那是中国近代史上仅见的一次民族大迁徙,在人类历史中也算一次巨大的迁徙。当时为解决新移民的居住问题,当地兴建不少临时性的眷舍予以安置。这批当时被视为战败外来者的新住民,带着“反攻大陆”的期望,在这些眷村中居住下来。
由于当时国民党宣传的是台湾只是暂时的避难场所,所以绝大多数普通士兵的家庭分到的都是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住,就是四十年。”现居北京的第三代眷村人张嫱说,从小,她就耳濡目染祖辈的这种心酸的感慨。
四十年间,浓浓的乡愁浸入每一个生活的角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愁与吃食永远有着脱不开的联系,于是,在《宝岛一村》的开头一场戏,过年,就出现了“一尾鱼”、“湖南腊肉”和缺少了“北平醋”的饺子。
而这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场“钱奶奶”教“朱太太”包包子的戏,手提一根擀面杖的钱奶奶是天津籍,1949年跟女儿、女婿从北平落脚到台湾嘉义的眷村。住在他们隔壁的是朱太太是“本省人”,一句“国语”听不懂。钱奶奶用天津话向朱太太传授天津包子的诀窍:肥肉跟瘦肉的比例要根据季节变化来调整,夏天肥瘦比例三比七,冬天肥瘦四比六。钱奶奶念叨着:“天津,我家,我老家……”她连比带划,高声大喊,终了,黯然垂泪。
《宝岛一村》中不少细节都值得人久久回味:厕所墙上一首夹杂错字的《静夜思》,寄托着眷村人思乡的情绪。还有老赵、老朱、周伯三人经常在大树下讨论“戴笠到底有没有死”,很戏谑地传达出他们对于回家的深切渴望。诸如《松花江上》这首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歌曲,也时常穿梭在舞台剧的场景里。
赖声川记得,《宝岛一村》在台北首演的时候,“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声音甫一响起,台下一位老奶奶突然站起来跟着一起唱。“照理说,在剧场里面是会被旁边的观众制止的,因为这是扰乱秩序的,可是没有人阻止,老人就一直跟着唱,唱完了大声说,‘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歌,然后坐下,所有人都为她鼓掌。”
这种回乡的渴望无疑已经在那一辈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当年相信回家之期指日可待,许多人家里连家具都只买最廉价的藤制品。
“有一个眷村第二代,他的妈妈从大陆带过去很好的皮箱,每年都把皮箱打蜡,把皮保养好,而且那个箱子是空的,不放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有一天要回去。”为了编撰《宝岛眷村》一书,张嫱搜集了许多眷村人记忆中的故事,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关于皮箱的故事。
“你一旦要回去,拎着箱子就可以走了。等到那个人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回家发现他母亲在哭,然后开始往箱子里放东西,就是把冬天的衣服,不穿的衣服往里面放,收起来的时候,他不讲话,他妈妈也不讲话,但是他们心里都知道,家,他们回不去了。”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无数眷村人嚎啕大哭,他们多年翘首企盼的回家路成了一场梦。
梦想没有成真,承诺没有兑现。
有人跻身上流,有人成黑帮老大
眷村中这群永远的过客只能把记忆里的家乡描述灌输给下一代。“我们是他们的祖孙,在我们长大的环境,他们都不断地在叙述他们家乡的故事,其实这种叙述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疗愈乡愁的方式。”张嫱回忆说。
从会说话开始,大陆老家的地址就成为眷村子弟必背的功课,当时谁也不知道,背这些地址到底有没有用,亲自踏上父母亲故乡的那一天到底会不会来。但逢年过节时,遥祭大陆列祖列宗的固定仪式绝不能免。
在以前台湾旧身份证上有籍贯一栏,填各种表时也要填,从小张嫱就在上面写“辽北省昌图县”——那个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家乡的名字。每年除夕夜全家在左营眷村爷爷家团聚吃东北酸菜火锅时,爷爷总是说起张家的历史,过年的习俗,还有那些留在东北的面目模糊的亲戚们。
背井离乡的老人不仅把家乡的一点一滴通过血脉传承到子女身上,他们还把“冲出”眷村的期望寄托到子女身上。
在《宝岛一村》里,赵家的大女儿大毛跟隔壁朱家的大牛青梅竹马,却遭到母亲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嫁给自己村子里的人是没有出路的”。
王伟忠专门对“眷村上一代人感情很好,相濡以沫,但是偏偏对‘你家小孩和我家小孩谈恋爱有着莫名其妙的反对”的普遍现象作出了解释:“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会觉得没出息——老一辈总是希望小孩离开眷村,嫁得远一点也许有比较好的发展。”
在那时,眷村长辈常灌输给下一代的观念就是:“读书是唯一翻身的机会,家里没能帮什么,只有靠你自己了!”
“本省人的家里有田地,无论怎么样,你还可以回家里种田。可是外省人不行,他们两手空空,到了一个异乡,什么都没有,只能跟孩子说好好读书,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没有什么机会了。”张嫱说,由于不知道在大陆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眷村下一代变成老一辈唯一的命脉。“就只剩下这一支了,要尽其所能把好这一脉,对祖宗有个交代。”
张嫱不会忘记当自己在北京拿到博士学位时,爷爷眼里的骄傲与宽慰。“就像家里出了一个举人那般。”那一天,张嫱的爷爷特别慎重,一定要张嫱穿上博士服跟他拍一张照。
这些外省子弟,读书读得好的,很多进入了新闻界、影视界、文化界甚至政界,对近30年的台湾社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至于读得不好的,有些则组成了台湾最早的外省帮派,在地下社会同样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去世不久的“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就是赫赫有名的眷村子弟。
他说出去玩玩,这一玩就是四十年
《宝岛一村》里,太多故事令人唏嘘,但是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最真实的一面。话剧的高潮部分,出现在三家眷村人回大陆探亲时。
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眷村长辈少小离家老大回,虽然乡音无改,两鬓却已斑白。
1988年,蒋经国去世,台湾地区红十字会开始受理转递大陆信件,台湾客轮开始驶往基隆—那霸—上海航线。两岸关系逐渐缓和。
在《宝岛一村》里,眷村的后人回到北京寻亲时有一句台词:北平的马路很陌生很陌生,我却觉得很熟悉很熟悉。
父亲老赵已经不在人世,儿子小毛回到北京,他给祖母看他们全家人在台湾的合影,却猝不及防地挨了祖母一巴掌。祖母说:“这一巴掌是你替你父亲挨的,他说他出去玩玩,这一玩就是四十年,到现在也回不了家。”
舞台上在这时有了一个静默的留白,而舞台下则开始抽泣声一片。在被情节感动的同时,却很少有观众知道,这个家庭的故事正是取自王伟忠父母的真实经历。
王伟忠的母亲孙绍琴是很多眷村女人的缩影,她们一辈子都在念叨“我是被你骗到台湾来的”。
王伟忠的父亲生在北京胡同,长在北京胡同,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也有一身随机应变的胡同智慧,他本是国民党空军的地勤人员,却自称是开飞机的飞行官,把王伟忠的母亲孙绍琴追到手。1949年的离乱中,一句“我带你们家绍琴玩玩”把她“骗”出家门,一路“骗”到台湾。那时,王伟忠的父亲19岁,他的母亲16岁。
——以《台北人》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