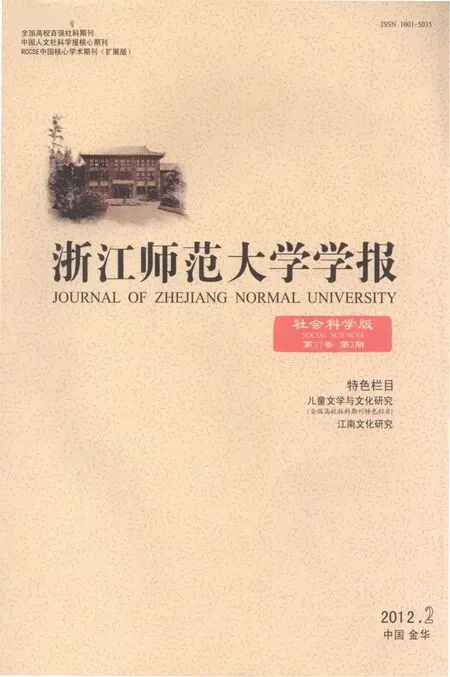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的近代意识
韩洪举, 魏文艳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先生,也称旧史氏、曲园叟、曲园老人、曲园居士等,浙江德清人,是晚清嘉道年间著名的文学大师。他一生专于治学著述,《清史稿》称其“生平专意著述,先后著书,卷帙繁富”,[1]有作品集《春在堂全书》,多达五百卷之巨。俞樾在考据学方面成就最为突出,被张之洞誉为“守朴学于经籍将息之秋”,“列儒林真无愧色”。[2]
虽然俞樾本人并不看重他的小说,但其成就却非常突出。正如陈节先生所说:“清末的文言小说作家中,俞樾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3]占骁勇也认为:“俞樾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与其在经学上的地位相当,是古小说的终结者。”[4]其文言小说《右台仙馆笔记》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代表了俞樾文言小说作品的最高成就。
一、俞樾与《右台仙馆笔记》
俞樾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意识萌动发展的时期,同时,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也在渐渐发生。鸦片战争使中国由闭关锁国变为开放海禁,出现了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作为意识形态,文学的反应更为强烈,从内容到形式都在求“变”求“新”,都在向近代化迈进。而小说是最能够灵敏地再现社会现实的文学形式,小说家感受时代脉搏也最为敏锐,体现在小说和小说家身上的“新”与“变”,首先就是近代意识的迅速萌发。所谓近代意识,即是思想的近代化,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这是由封闭的思维体系向开放的思维体系转化的必经过程,由传统观念到面向世界、社会人生转化,在文学上主要表现为批判社会的堕落、呼唤人性的复归。中国近代意识中求新、求变、求用的精神激励着晚清文人积极思考、勇于创作。这种意识突破了封建士大夫原有世界观的局限,体现了他们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流露出其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作为文学大师,俞樾不能不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加上他的家乡浙江又处于沿海开放地区,民主主义思想充斥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下,他成为了一位具有近代意识的进步人士。
俞樾的笔记小说集《右台仙馆笔记》共十六卷,前四卷在小说《耳邮》的基础上增删而成。俞樾创作此书的初衷是为了排解爱妻去世后的苦闷,事先并没有进行有意识的材料积累工作。《右台仙馆笔记·序》曰:“余自己卯(1879)夏姚夫人卒,精神意兴日就阑衰,著述之事殆将辍笔矣。其年冬,葬夫人于钱塘之右台山,余亦自营生圹于其左。旋于其旁买得隙地一区,筑屋三间,竹篱环之,杂莳花木,颜之曰‘右台仙馆’。余至湖上,或居俞楼,或居斯馆,谢绝冠盖,昵就松楸,人外之游其在斯乎?余吴下有曲园,即有《曲园杂纂》五十卷;湖上有俞楼,即有《俞楼杂纂》五十卷,右台仙馆安得无书?而精力衰颓,不能复有撰述,乃以所记《笔记》归之。”由此可知,此书创作始于光绪五年(1879)冬。又因《右台仙馆笔记》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最晚在“光绪辛巳岁立夏之日”(卷十四),即1881年5月上旬,光绪七年(1881)的《春在堂全书》已收有《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因此可以推定,《右台仙馆笔记》于光绪七年(1881)下半年完稿。此书创作的时间,正是中国历史处于近代时期,是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期,因此,《右台仙馆笔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明显的近代意识。
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序》中写道:“《笔记》者,杂记平时所见所闻,盖《搜神》、《述异》之类,不足,则又征之于人,嗟乎!”将创作缘由和素材的来源作了大致的交代。素材主要来自作者的家人、门下弟子和友朋亲眷等,另外还有不少人热情地为俞樾提供原料,如陈广文。俞樾的创作还吸引了日本来华者,《右台仙馆笔记》卷十二记载了多则有关日本国的轶事:“以上日本诸事,皆本其国人吉堂所录。吉堂姓东海氏,名复,在海外曾读余所著书。及至中国,知余有《右台仙馆笔记》之作,录此十数事,托余门下士王梦薇转达于余,因粗加润色而存之。余诗所云‘旧闻都向毫端写,异事兼从海外求’,洵不虚矣。”纵观全书,俞樾的小说以表现近代故事为主,虽然还有很多故事没有指明来源,但均有一定的真实性,反映了当时的风俗人情与社会状况。
众所周知,小说的思想往往是一定时期社会实况的真实反映,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承载着传统的文化精神。小说的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侧面,它紧密联系着社会的动荡与变迁。俞樾身处晚清,曾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乱,亲眼目睹了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剧,对当时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俞樾以教书为业,经常奔走于苏杭之间,对社会的真实状况有着亲身的感受。他曾经为官,且名重一时,晚清的许多达官贵人都与他有交往,因此,他对社会发展态势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感受。所以,《右台仙馆笔记》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反映了晚清的社会风貌,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开通进步的思想。下面我们就从危机意识、重视小说的实用功能和较为进步的妇女价值观三个方面,来阐释《右台仙馆笔记》所体现出来的近代意识。
二、危机意识
19世纪初,清王朝经历了18世纪的“盛世”之后已日薄西山。19世纪中后期爆发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把侵略的炮口对准已经腐朽的东方古国,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继此之后西方列强一步步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腐朽的清王朝在强敌面前一筹莫展,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危机时刻,一批较早觉悟的有识之士,一方面提倡改革弊政,一方面对乾嘉以来的文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魏源等少数先觉者就对衰朽的满清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萌发了朦胧的近代意识,开始对某些传统文学的创作原则产生质疑,要求转换文学的发展方向。到19世纪中后期,由于清王朝政治的黑暗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形势急剧恶化,先觉者的忧患意识逐渐演变成为群体的危机意识,俞樾就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
一个小说家的社会意识进步与否,主要体现在他以什么眼光去观察社会的动向,如何从社会生活中选择素材,又如何以文学形式反映到广大读者面前。即使作为一个埋首学问的经学大师,俞樾也不能不对当时衰颓的社会坐视不问,他把自己对社会的批判和思虑融入到了小说的创作中。《右台仙馆笔记》中的许多篇章都真实地展现了世风日下的社会面貌和作者对社会的强烈批评。
首先,小说对封建意识形态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对残害百姓的豪绅恶棍表示出强烈的愤慨之情。比如卷四的“民间呼县衙曰四衙”一则,通过生动地描摹一个小县衙的形象,对清廷官僚统治机构展开了全面的暴露与抨击,揭示了封建统治分崩离析、病入膏肓的末日图景。在这则故事中,一个小小的衙役竟然在民间横行霸道,他上面的官员是怎样地鱼肉百姓便可想而知了。老百姓没有办法抗衡这些骄横的恶势力,俞樾也感到无能为力,只能在书中借冥报来表达对他们的憎恨之情。卷八记载了“居心险恶”的沈岳良,混入太平军中仗势欺人,“每掠得妇女,必裸而淫之。禅国山东南有石洞,极深邃,妇女避乱者数百人入焉。沈积薪焚其洞,皆毙之”。[5]186这个作恶多端的人后来被怨鬼溺死厕中,“遍身青黑,七窍流血,臭秽不可向迩”。真是恶有恶报,令人拍手叫快。
其次,晚清战乱不断,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骗子,其骗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对此,俞樾也发出了批判之语。社会上偶有诈骗行为在所难免,但行骗成风就不正常了,说明当时世风日下,道德堕落现象日益严重,应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卷三的一则故事中,俞樾将四个小故事集中在一起,讲述了妇女为贼、童子为贼、士子为贼、官吏为贼这种极端不正常的现象。作者在文末意味深长地感叹道:“嗟乎!外户不闭之风,固难望于中古以下矣。”文中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
面对腐败的社会现实,俞樾感到深深的无奈,只能把对社会现实的不争与愤恨写在纸上,试图唤醒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让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和社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为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社会付出实际行动。俞樾从特定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封建统治下人们的生活实质,预示满清王朝社会危机重重,前途一片黑暗。
最后,俞樾对当时流行的愚昧迷信活动持反感态度,作品中流露出明显的反封建、讲科学的进步思想,体现了作者的近代意识。虽然各个朝代都有封建迷信,但是到了晚清动荡不安的时期,迷信更是肆无忌惮,不仅普通百姓沉迷于淫祠和邪教,一些士大夫也迷惑于神仙之术,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污浊的瘴气。卷一的“汉阳朱勋臣”一则,记载了箕仙降于朱家之事。作者在文中不禁议论道:“余雅不信箕仙,窃谓当今之世,而欲绝地天通,宜首禁此术也。”[5]10对迷信活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希望彻底禁止此类活动。又如卷七记载了江西张真人府派使者到慈溪城隍庙投书审冥案一事,作者在文中明确表态:“余书虽志怪,然于此等事固不信之也。”虽然是文学大师,但俞樾却有着模糊的科学意识,他对这些雕虫小技有着本能的反感,批判中充满不屑与不满,表现出他在思想认识上的进步性与独立性。
俞樾通过对迷信活动的否定告诫世人,千疮百孔的封建统治已经不可救药,强烈地反映出他悲世的伤痛。
之所以选择这些记录事实的材料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是因为俞樾敏锐地体验到了末代王朝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从理性的高度进行关照,并给予生动的表现,显示出进步的近代意识,这是前代小说家都缺乏的,即使在同时代作家中也极为少见。
小说是现实的真实写照,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些“社会史料”向世人提供了末代王朝即将土崩瓦解的信息。借此,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极度黑暗和百姓生活的无比惨苦。
三、重视小说的实用功能
由于近代社会发生了时代性剧变,社会危机不断加剧,学术界自然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士林风气由此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仅诗风、文风发生新变,而且诗论、文论也出现了以经世文学观为核心的变革思潮,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文学社会功能论的强化,向民众传授了西方近代思想,使中国民众革新了观念,树立了近代意识。文学中最浅显易懂且趣味性又强的当属小说,所以,提高小说的地位成为了文学变革的重点。
小说自产生以来就被人们认为是小道、残丛小语,是“治身理家”的短书,而不是为政化民的“大道”。《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后世对小说的阐述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一范围。直至清代,正统观念仍旧对小说不屑一顾,《四库全书》就将许多小说视为“猥鄙荒诞”[6]之书。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受到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梁启超等为教化国民、开启民智,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并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同时,人们也认识到,要提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必须遵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加强小说的社会实用功能。这样一来,原本处于附庸地位的文体——小说,终于跻身于文学的殿堂,这意味着文学内部结构关系的重组,也意味着文学已发生了由古代向近代根本性的转变。尽管梁启超等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最终未能力挽狂澜,但小说的地位确实较之以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作为著名的经学家兼小说家,俞樾注意到了文学和时代的密切关系,并始终遵循“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来进行创作。
《右台仙馆笔记》取材偏重于具有教化意义的故事,体现了俞樾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的观念和重视人情的较为开明的思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光绪中,德清俞樾作《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止述异闻,不涉因果;又有羊朱翁(即俞樾)作《耳邮》四卷,自署‘戏编’,序谓‘用意措辞,亦似有善恶报应之说,实则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劝惩’。”[7]鲁迅此说,颇有颠倒之嫌,说明此小说确有教化劝惩之意。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序目》在谈到清代笔记时也说:“有谈说神鬼狐怪者,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是也;有称述因果报应者,如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之类是也;有录奇闻轶事者,如焦循《忆书》之类是也。”[8]俞樾在小说中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百行孝为先”,这是俞樾评判一个人的重要道德准则。他在小说中大力提倡孝行,写了很多孝子孝女的故事,开篇即是“冯孝子传”,作者的劝善惩恶之心不言而喻。另外,俞樾为了劝人行善,在小说中还写了许多行善者皆得善报、作恶者自然遭恶报的故事。如卷八第40则记载朱新甫因一念之善和不记旧恶保全了自己和妻子的性命;卷二第23则中的张少渠也因平时行善而避免了沉船之灾。
俞樾非常关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所表现出来的侠肝义胆,乡土气息十分浓厚。他在小说中将目光投向了普通人,对那些有着高尚行为的平民百姓大加赞赏。如卷一中“何明达”一则,主人公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却能在困境中帮助别人,与前面所举士人为贼的故事形成鲜明对比,确是“虽士大夫或不及矣”!另外,书中还记载了许多女子的侠义行为,如卷三的红兰。作者不但对勇于改正错误的人宽容待之,对具有“义行”的动物也不惜笔墨,加以表彰,如卷五说的即是鹦鹉在战乱中勇救主人的故事。晚清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人人自身难保,面对动物的种种义行,只怕连人类都自叹不如。俞樾对动物侠义的赞誉,目的是为了唤起民族灵魂的核心——道德和人性的回归。作者把战乱中平民身上的珍贵美德看作是挽救晚清的良药。如卷三记载了安徽柳翁苦心照管故人的儿子,想尽办法令其改邪归正。文末写道:“稗官小说家,固不必拘泥于事之真伪,但取其足以风世而已矣。”[5]71充分表达了俞樾希望利用小说来达到潜移默化、感化人心的愿望。
四、较为进步的妇女价值观
受西方进步价值观的影响,俞樾的视野冲破了固有的局限,显得更加广阔。但由于中国几千年正统文学的熏陶,他对妇女价值的认识难免带有传统的色彩。一方面,俞樾在妇女观上仍然遵循正统观念,强调妇女“敦礼”,为丈夫守贞节,从一而终。如卷十五记载了翠姑因父母想要悔婚而自杀的故事;另外,小说还记载了大量烈女节妇的故事,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另一方面,俞樾又是开明的。他并不是一味地讲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将贞节看得重于一切,而是能结合“情”来说“理”,客观地写出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精神的桎梏。如卷一“阿胜”篇,女主人公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自追寻心仪之人,这在当时无疑是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行为;俞樾不但没有责备她,反而是欣赏其魄力,赞之为“奇女子”,表明作者面对情与礼的冲突,理智上要维护礼,情感上却难以拒绝人性的要求。又如邢阿金结了四次婚,丈夫死后,她也殉节而死。俞樾在文末评到:“此女四易所天,不为贞,卒殉其夫,不得不谓之烈。使其初适即得良奥,必为善妇。乃所如不合,遂历四姓,卒成大节,是谓质美而未学。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盖可也。”[5]3不怪其不贞,反惜其不遇,还为她辩护,在名节与情感中更倾向于“情”。
从整体上看,俞樾对封建礼教制度没有作出实质性的否定,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在小说中对真情的肯定,的确有着很大的开放性和进步性。
俞樾认为,文学作品中必须充满真情,这是其进步文学观的具体反映。文学之真情是从《诗经》以来我国古代文学的一种优良传统。但是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这种传统虽然整体上是不断传承的,而单就某一个时期来说,却又往往被人们所抛弃,晚清时期即是如此。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禁锢人民群众的思想,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从理论上否认“人”在物质生活中的需求和精神生活中的渴望。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激发了深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意识。嘉道之际,与“经世致用”相适应,文学领域要求因时兴感、主张直抒胸臆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经学大师,俞樾在“注经”的同时,实质是凭借“经文”而阐发自己的见解,即性情。与当时的忧时感世相联系,其真情是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的。俞樾虽处于腐朽的末世,却并不放弃对于美好人生的追求。俞樾的性情之说是有历史渊源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李贽的“童心说”与公安三袁的“性灵说”。“童心”即真心,真实的思想情感。在李贽看来,文学作品只有真假之别,而不以时代之先后论其优劣。“性灵”即出自胸臆的自然感情,强调个性的自然流露。这些见解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具有叛逆性。明末清初,那些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为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争取自由,曾主张文学创作应表现人的真实情感。俞樾继承了前人的表情说,在作品中用真情作为评论事情的标准,相对前人来说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五、《右台仙馆笔记》的地位
近代意识作为中国文学转型期的产物,是清末小说家从事创作的动力。要研究清末小说的积极意义和小说家们进步的思想,就应该探究他们内心深处的近代意识。近代意识中极力追求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思想,表明传统的封建意识正在被动摇;但近代意识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这就决定了当时新观念的表现力尚不够充沛,呈现出朦胧的性质。
《右台仙馆笔记》是俞樾在文言笔记小说领域的封山之作,包含了他先进的的学术思想和近代意识,如危机意识和重视小说实用功能的意识等,影响深远。根据陈翔华《中国古代小说东传韩国及其影响(上)》一文记载,清刻本《右台仙馆笔记》藏于韩国的奎章阁和成均馆。[9]缪荃孙在《俞先生行状》中云:“先生《右台仙馆笔记》以晋人之清谈,写宋人之名理,劝善惩恶,使人观感于不自知。前之者《阅微草堂五种》,后之者《寄龛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华者所可比也。”①俞樾小说虽有浓厚的学术化倾向和因果报应的劝惩性,但并不是直接说教,而是充分发挥小说的社会实用性功能,善于通过故事本身让读者领悟其中的道理,以达到劝惩的本意。周作人对《右台仙馆笔记》评价最高,认为它“虽亦有志于劝戒,只是态度朴实,但直录所闻,尽多离奇荒陋,却并非成见,或故作寓言,自是高人一等,非碌碌余子所可企及也”。②俞樾比纪昀更高明一些。《阅微草堂笔记》注重议论,而俞樾只对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发表议论,在很多篇章里甚至不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小说的故事来传达信息。总之,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虽时有议论,但故事情节性强,所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流传很广,“在晚清志怪小说中占有重要一席”。[10]
应该看到,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性,《右台仙馆笔记》还存在着很多陈旧落后的思想观点,如对一些鬼神报应之事的相信和宣扬。小说中很多篇章写到鬼神,但对鬼神形象的描写却相对单薄。小说用大量篇幅来阐发鬼神观点,目的是神道设教,欲借鬼神的故事来传名教。诚如作者自己所言:“风俗浇漓,人心凉薄,则鬼神之事,固有足以辅政教之所不及者矣。”[5]306当然,俞樾的小说也不完全是鬼物假托。俞樾相信鬼神的存在,反对无鬼论,“讲学家必执无鬼之说,魄降魂升归之大虚无物,由是而背死忘生者众矣”。[5]179认为鬼有贤愚的分别,其精气不能长久存在。善良的人其气轻而上扬,恶毒的人其气浊而下沉;因此,若死而有怨气的人,心有所系,故不能上升。可以说,俞樾的鬼神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教化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的。诚如宁稼雨先生所言:“虽然作者的思想没有跳出旧礼教的圈子,但他已感到了圈子的狭小和对人的桎梏作用,这已足弥珍重。”[11]
虽然俞樾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想的局限性,但从他作品中所散发出的进步的近代意识,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觉醒中的晚清知识分子为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断前行的轨迹。
注释:
①详见缪荃孙《俞先生行状》(《艺风堂文续集》八卷,外集一卷),清宣统二年刻,民国二年印本。
②此观点参考周作人著、钟叔河编《知堂书话》中“右台仙馆笔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29页。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298.
[2]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289卷“书札八”[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0346.
[3]陈节.俞樾评传[J].明清小说研究,1999(4):17-21.
[4]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228.
[5]俞樾.右台仙馆笔记[M].梁脩,点校.济南:齐鲁书社,1986.
[6]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82.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4.
[8]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序目[J].文史哲,1979(4):45-48.
[9]陈翔华.中国古代小说东传韩国及其影响(上)[J].文献,1998(3):132-154.
[10]张立旦.俞樾与通俗文艺[J].文史杂志,1989(2):8-10.
[11]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