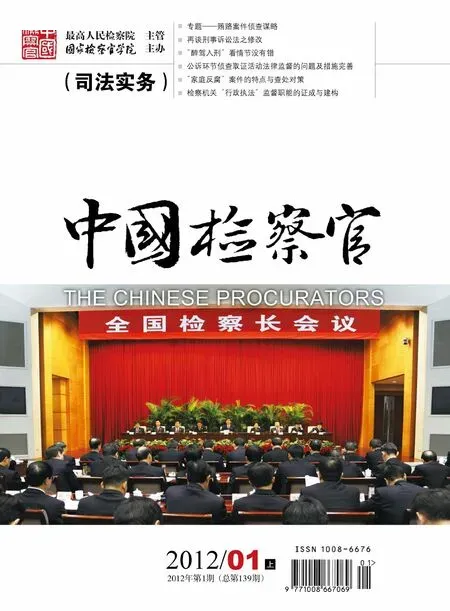“醉驾入刑”看情节没有错
文◎刘仁文
“醉驾入刑”看情节没有错
文◎刘仁文*
今年2月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增加“危险驾驶罪”作为《刑法》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关于醉驾并不一律入刑、而要结合《刑法》总则第13条的但书来对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作除罪化处理的说法引起极大争议。本文作者认为,张军副院长的基本观点并没有错,但此举引来公众对有权有钱者逃避制裁的担心值得我们深思。
一、关于《刑法》总则第13条和第37条的适用范围
其实,社会上把针对醉驾把可否适用第13条但书的讨论称为要否一律入刑,并不准确,如果要准确地用法言法语来表述,应当涉及《刑法》总则第13条和第37条两个条款:第13条的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涉及的是要否一律入罪的问题;第37条 “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涉及的是要否一律入刑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长期以来在刑法学界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一般认为,刑法总则应当适用于刑法分则,但在具体如何适用方面,存在争议。有的认为,第13条和第37条可以直接适用于分则的每一个条文,[1]另有的认为,这两个条款不能直接适用于分则的每一个条文,除非分则的具体条文体现了这两个条款的内容。[2]
上述第一种观点是目前的通说,本文作者也持这种观点。具体到醉酒驾驶,我认为在法庭审判这类案件时,对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根据第13条但书,依法作适当的除罪化处理;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根据第37条,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二、“看情节”不违背罪刑法定
在刑法理论上,犯罪定义有两种,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形式定义就是只从犯罪的法律特征上来界定,如直接规定依照刑法应受处罚的行为就是犯罪;实质定义则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界定,我国《刑法》第13条采取的是实质定义,即突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特征。[3]从此出发,《刑法》第 13条规定了一个著名的“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个但书有两个功能:一是照应功能,我国刑法分则中大约有2/3的罪名都有数量或情节限制,如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等,都要求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构成犯罪,又如假冒专利、消防责任事故等,要求“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才构成犯罪;二是出罪功能,对于另外1/3的不含定量因素的罪名,第13条但书可以将那些轻微不法行为直接做除罪化处理,如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38条规定只要有非法拘禁的行为就构成非法拘禁罪,但实践中对非法拘禁时间很短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一般不作犯罪处理。抢劫罪也是如此,《刑法》第263条规定任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都构成抢劫罪,但实践中如果抢劫一块几毛钱的手绢,恐怕也不会去追究行为人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吧。对这种除罪化的处理,如果要从法律上找到根据,那就应当是第13条的但书。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国家和地区对犯罪采形式定义,那么他们在犯罪定义中就没有这个但书,但即便没有,也会有各种各样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做除罪化处理的做法。比如在我国台湾地区,他们对盗窃罪并没有规定数量限制,从法条上看,一切盗窃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犯罪,但同一个宿舍的人,一个不在,另一个急着上厕所,于是拿了他的手纸,这也构成盗窃罪吗?实践中肯定没有将此作为犯罪来处理的。于是他们形成了一个理论,叫“推测同意”,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即便当事人在场也会同意。又如在德国,他们则规定对于盗窃数额较小的,由被害人决定要不要自告,也就是说,被害人如果不告的,则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也是一种除罪化的方式。
有人认为,直接适用第13条的但书和第37条的免予刑事处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我不这么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罪刑擅断、保障人权而提出来的,它主要是反对类推、法律溯及既往、立法模糊等不利于被告人的做法。演变至今,中外刑法学界一般都认为,对符合常理常情、有利于被告人的做法,可以允许适当的超法规,如刑法中的被迫行为、自救行为等,虽然法律并没有一一明示,但理论解释一般承认这些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可以作为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理由。又如,我们现在提倡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即法不强人所难,如果在特定条件下换成第三人也不能期待他作出合法行为,则应当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这在学说上也不成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13条的但书和第37条的免予刑事处罚是有利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它与罪刑法定原则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当然,即便有利被告人的做法,也不是无边际的,它应当受到相关法治原则、理论学说和常理常情的支持与制约,这一点后文还将论及。
三、“看情节”可化解立法尴尬
现在重点谈谈在醉驾没有规定情节的情况下,能否直接适用第13条?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如前所述,我的学术观点是,即便分则中没有规定情节,也可以适用第13条。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象前面对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等的分析,就是例证。
但是另一方面,危险驾驶罪这个条文比较特殊,它一句话里规定了两种情形: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前者明文要求“情节恶劣”,后者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这时候能不能适用第13条但书呢?刑法理论似乎并没有给出唯一的答案。公众也有理由质疑:如果笼统的给醉酒驾驶套用第13条但书,那么前面对情节恶劣的规定不就是多余的了吗?反过来,前面规定了情节恶劣而后面没有规定,就容易给人一种醉驾一律要入罪的印象。
这就涉及法律解释。众所周知,法律解释有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之分,主观解释强调遵循立法者原意,客观解释强调不拘束于立法者原意,要从社会现实出发。现在看来,立法者的原意很可能是不分情节,就是要醉驾一律入罪,以表明其严厉态度。但我愿意作客观解释,具体思路是:追逐竞驶使用了“情节恶劣”,并不能说明醉酒驾驶就是要不分情节一律入罪,因为情节恶劣下面还有情节一般,再下面才是“情节显著轻微”,也就是说,前者之所以不必用第13条但书,是因为它已经规定要情节恶劣才构成犯罪,连情节一般都不构成犯罪,更不用说“情节显著轻微”了;后者就不一样,不需要达到情节恶劣才构成犯罪,情节一般就可以构成犯罪了,至于情节显著轻微,仍然要受第13条但书的约束,不宜以犯罪论处。
一般而言,客观解释相比主观解释,往往是扩大字面含义和打击面,因而不利于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但本文这个话题相反,采客观解释反而缩小打击面,有利于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何况从现实中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如果不加区别地一律入罪,不仅在某些案件中显得过于严苛,而且也将使公安司法机关不堪重负,把过多的精力用到这一类案件上,从成本收益的观点来看,也是值得深思的,毕竟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精力还是应当用于打击那些严重的暴力犯罪。
执法出现这个困局,其实根子还是来源于立法。我曾经在立法征求意见时针对该罪的条文设计提出过几点建议:一是要考虑情节,二是要将处罚后果中“拘役并处罚金”改为“罚金或者拘役”。台湾醉驾也入刑,但初犯一般罚金,或者罚做公益劳动,再犯才处剥夺自由刑。我们一上来就并处,刑罚偏重,没有退路,于是只好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去找出口。另外,我还提过,对于服用毒品等危险驾驶、情节严重的行为,也应当与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一并规定进去,因为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已经突显出来了。[4]
总之,这个条文的立法是有教训的,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冲动、受民意的影响过大了点,对刑法与行政法的对接、刑法如此规定给执法机关带来的压力以及执法的成本与收益等都缺乏深入的论证。
四、“看情节”不是无限度开口子
其实,像第13条但书这件事本来就没有必要由最高法院站出来说话,办案法官自己应当有这个担当,通过判决书的充分说理,并且引用刑法学界的通说来支持自己,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来处理;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则可以依据第37条作出免予刑事处罚。此外,还可以通过适用缓刑来实现某些情形下的刑罚轻缓。但我们长期以来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一遇疑难问题就向上请示汇报,在得到上级法院的指示之前,该作轻缓化处理的也不敢,这种状况遏杀了第一线法官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致使我们的刑事司法走入了一个“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法官本来就不应该过度依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其他指示,法官自己就是法律的最好解释者。一个良性的司法运作机制应当主要由一线法官来承担解释任务,因为只有处在办案一线的法官才能结合案情和行为人的具体情况,凭借司法说理和对法律的善意解释,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寻得最佳正义。
鉴于立法已成定局,短期内不可能修改,我倒想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及时跟踪醉驾的司法实践,将那些真正需要明确的问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5]例如,关于醉驾的标准,现在采用的是行政处罚的醉酒检测标准,即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的,就属醉驾。但从有关资料来看,这一标准较之美国、日本等国,确实偏低。从学理上讲,刑法上的醉驾标准和行政处罚的醉驾标准也是可以有所区别的。因此,如果经过论证,觉得这一标准可以作适当提高的话,就可以考虑通过立法解释来确立一个刑法上的醉驾标准。另外,我还是觉得应把一般的醉酒标准和行为人的个人身体状况结合起来,如美国抓到醉酒驾驶者后,还要让他走一定的线路,若清醒得很,走得一点都不差,就不作为醉驾来对待。总之,像这样的涉及到醉驾标准的认定问题,可以考虑由立法解释来作出更科学的调整。
顺便要说的是,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在醉驾要否一律入罪、一律入刑这个问题上,公安、检察、法院三家的表态相互不一致,对此,我觉得也要辨证地看,一方面,在公安阶段,就是不应当作除罪化处理,应当把所有涉嫌醉驾的案件在侦查完毕后移送检察机关,因为如果允许在公安阶段就开口子,确实不能避免对执法公正的担心。但另一方面,我又主张,面对新生事物,我们的办案机关还是要有适当的克制,而不要一味从严,比方说在强制措施方面,对醉驾这类危险驾驶者审前尽量不要羁押,采取取保候审即可,因为他毕竟不是杀人犯、恐怖分子等重大恶性犯罪,不羁押对社会也不会有多大的危险。[6]
从有关报道看,应当承认,目前我们对醉驾的量刑还是比较重的,像高晓松一案,初犯就判了顶格6个月,再犯怎么判?另外,几乎见不到判缓刑的案例。我觉得,还是要宽严相济,根据不同的情形运用好缓刑和第37条的免予刑事处罚。
最后想说的是,无论是第13条但书的出罪,还是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的免刑,都不是无限度地开口子,前者只限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后者则限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从这个意义上看,那种认为官员和有钱人将有机可乘的担心可能是放大了。但另一方面,从民意这种放大了的担心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前整个社会对司法不公的敏感,折射出司法公信力不强的现实,对此,我们不可不加以深思。
注释:
[1]参见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2]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485页。
[3]关于我国犯罪定义中的“社会危害性”特征,现在有的学者提出批评,主张要把“社会危害性”这一概念逐出我国刑法,我认为这值得商榷,具体理由另行文阐述。
[4]参见吴应海:《整治‘毒驾’,应上升为国家行动》,载《法制日报》2011年9月8日。
[5]立法解释相比起最高人民法院自己作的司法解释,要更权威,也可以避嫌。
[6]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的条件之一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最高刑为6个月拘役,因此包括醉驾在内的危险驾驶行为不能适用逮捕。由此也可以反推出对于此类犯罪嫌疑人,应当尽量少用审前羁押强制措施。即便目前普遍使用的拘留,深究起来也是可以质疑的:刑事诉讼法使用的是“先行拘留”,这暗含着拘留是以可逮捕为前提的,而法律规定醉驾不能适用逮捕,即这类案件拘留后法定不能转捕。参见戴玉忠:《醉酒驾车犯罪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检察日报》2011年6月20日。
[7]参见邢世伟:《醉驾入刑将近满月 已判案例无一缓刑》,载《新京报》2011年5月26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博士生导师[1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