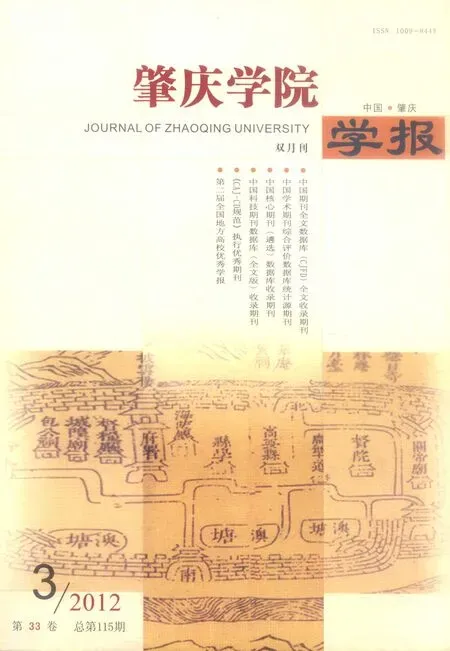1910—1911年《香港华字日报》中革命党形象探析
——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心趋避
周军
(肇庆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1910—1911年《香港华字日报》中革命党形象探析
——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心趋避
周军
(肇庆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从庚戌新军起义到黄花岗起义,再到武昌起义,革命党的形象在《香港华字日报》中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最后革命党人赢得报纸称赞,这一变化多因革命党人的表现及革命军军纪良好。报纸通过革命党与盗匪的比较,革命军与清军的比较,凸显了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崭新的形象。这些报道也反映出社会剧变中民心趋避和社会舆论的走向。
《香港华字日报》;辛亥革命;革命党形象
武昌起义前,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广东发起一系列革命活动:庚戌新军起义,刺杀孚琦,黄花岗起义,刺杀李准、凤山。在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中,以黄花岗起义影响最大,孙中山称此役“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1]50。 《香港华字日报》①行文中如不特别提出,均用“该报”指称《香港华字日报》。对这一系列事件均有相关报道,该报本为英商所办中文报纸[2],至少从1910年庚戌新年起,在省城设有代理处[3]。1910年初,该报“每日印刷数千张之多”[4],意味着报纸在香港、广州有一定销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该报的政治态度较为“稳健保守”,不从属于某个党派或某个政权[5]。中立派报纸对革命党的态度,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在清廷与革命党对立的过程中,该报的报道体现了中间派报纸对革命党认识的变化,这一变化也成为革命党人在广东逐渐为民间所认识的见证,反映出“革命”“革党”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接纳程度和影响力,显然,这要比其他政党报纸的宣传或者诋毁更具说服力。本文通过该报对庚戌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中有关革命党的报道,探讨革命党在报纸中的形象变化,借此反映社会剧变中民心趋避和社会舆论的走向。
一、“张大其词”的革命党
1910年庚戌新军起义,原为同盟会南方支部所策动,当时新军士兵与巡警发生斗殴,形成“军警冲突”,党人乘机鼓动,发动起义[6]22-23,35。此事发生于1910年2月10—13日(庚戌新年正月初一到初四),当时该报正值春节放假,2月16日(庚戌正月初七日)开馆后即报道新军起义一事,在广东新闻栏里记述该事件时,新闻中已点明“此次兵变之由系革命党首领杨凤岐、赵珊林、江建有此三人鼓动”,不过在报道中,新军起义并不具备革命意味,相反,报纸将之称为“初三日兵变”,在文内又将革命军称为“叛军”。文中记述革命党人形象时描述道:“擒获之首领王占魁,身衣黑缎军装,体格高大,目光灼灼,神首不清,常直视,年约二十五六岁。”[7]除了对革命党外貌、年龄的描述较为中性之外,所谓“神首不清,常直视”之语,可以看出这种用语并非对革命党的赞誉之词。
2月17日的时事评论中,论及新年中有新意者为三事:新年、新军和新政。“贺新年则岁岁如是,讵物换星移,而自春徂冬,则年之新者忽焉成故矣。练新军则日日如是,讵甫见成立,而随机激变,则军之新者,忽焉又蹶矣。行新政则处处如是,讵但事敷衍,而殊少认真,则政之新者,忽焉中隳矣。”[8]文中对“新”失望只是对清廷的不满,类于“处士横议”,而对新军起义之态度,则立场模糊。
不过,广东新军新年生变,从各方而言,都是值得注意的大事。2月19日的报纸将之称为“羊城新年十变局”之一:“新军之练,所以巩卫朝廷,防范革命也。乃巩卫朝廷,防范革命者,忽变而震惊朝廷,倡言革命,是为羊城军界之变局。”并认为新军肇变是“藉口革命,张大其词”[9]。对于新军肇变的原因,报纸进一步认为“此次肇变之原因,其不尽关革党之运动也”,真正原因乃是“当轴者张皇过甚,小题大做,遂至激成水火”[10]。从而将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两广总督袁树勋。由于该报对袁树勋的攻击,1910年3月,袁树勋以港报“议论狂悖”“纪载虚诬”“颠倒黑白”“肆口鼓簧”“希图煽惑”等罪名,曾禁止港报入口[11]。直到1911年初,两广总督张鸣岐开禁,才允许该报重新入省[12]。
到了1911年初,广东匪患日益严重,1月时,东安陈作岭乡全乡被劫[13],新任东安知县,认为东安盗匪猖獗,准备微服私访查询地方利弊,“以通民隐而资整顿”[14]。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则遵奉上司命令,不断拿获革命党,如于2月24日在新军中拿获革命党邓明德等人后[15],不久又在巡警教练所秘密拿获革命党罗升、张国樑二人[16]。3月8日,该报批评李准剿匪不力,却严拿革命党。“若以妨害治安论,则革党之煽乱,与劫贼之肆虐,同在不赦之条。而但以吾粤人之所为革党,与一般无意识之劫贼相比较,则劫贼之为害于地方,实远过于革党万万。盖吾粤之所谓革党,都是影响之谈,煽惑之伎耳。其真能鼓励大风潮,如外国之所称为革命军,足可与政府相抵抗者,吾敢断定吾粤人目下决无此能力。而李准偏鳃鳃然独以革党之贻害于国家为虑,毋亦以革党之迹近疑似,而易于掩捕耶。抑或姑张大其词,冀以邀功而并以卸过耶。不然,而何以对于劫贼,则常主宽容,而对于革党,则独主严缉也耶。”[17]所谓“革命党”当为清廷的掘墓人,从清廷重视自身统治之稳固而言,轻剿匪而重拿获革命党,本为应有之义。该报此时抨击李准,反映出该报力图为民间立言的倾向。但是报纸对革命党虽有所同情,因革命党势力尚未强大,该报对革命党不免有轻视之语。
二、“秋毫莫犯”的革命党
1911年4月27日 (阴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等革命党人持炸弹进攻两广总督府,震动广东社会及全国视听,是为黄花岗起义。孙中山曾说此役中“吾党菁华,付之一炬”[1]50,反映出革命党失败相当惨烈。此事之经过及真相自然为社会所关注。
事发两天后即4月29日(阴历四月初一日),报纸对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进行专电报道[18]。5月1日,又用大量篇幅报道详情。在这次报道中,报纸侧重于报道张鸣岐“定乱之才”,如临事镇定、雍容,并详细介绍张鸣岐的应对措施,如“闭城门颁军律”“限制轮渡”“限制电报”“限制电话”“限制火车”“高悬赏示”“遍告内国”“安慰外人”等,又在消息中称革命党为“乱党”[19]。
5月2日,报纸针对张鸣岐的措施,称赞张鸣岐处变有方。在革命党纵火和逃避中,张鸣岐选择“捕匪”,“才哉张督,明知其纵火,特任其延烧,惟是预令卫兵,一心捕匪,革党不能奏有成之功者,实张督先立于不败之地也”。随后,张鸣岐又“关闭城门,以断其交通;限制电话电报,以截其消息;搜查轮渡,停止火车,以绝其接济。一面将得手情形,时电外人,一面将防剿事实,通告国内,使内外不至为乱党谣言所惑。乃徐为布置,密事编查,比户不惊,余孽就逮。吾观于此,非特叹张督之处变有才,且不能不赞张之才足济变也。”[20]
需要注意的是,在5月2日的消息中,报纸除了继续报道张鸣岐的处变有方之外,也增加了对革命党的报道,如“革党粮台供词”“革党授首之查报”“革命军乔扮尼装”“党人隶籍”“乱党所用之器械”“革党起事之续闻”“革党渠魁黄兴殆真死矣”等[21]。这些报道有的虽未经核实(比如报道黄兴已死),但大多介绍革命党的情况,没有将革命党妖魔化,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对革命党人的了解,只是很难看到报纸对革命党的支持。
相反,报纸从边沁的幸福学说出发对革命党起事进行批评。报纸认为,按照边沁学说,“牺牲少数人之利益,以谋大多数人之利益,然后社会之安定秩序,乃可得而维持”,既然如此,“将谓粤垣之变起,某党果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欤?则不起于北方,而仅起于粤垣,其何能济?粤离中原与北方甚远,非起事之要区者也。既起于粤垣矣,不发难于旗满界中,乃发难于督署。揆诸某党排满之宗旨,又为混淆不清,实属侵扰社会之安宁秩序,然则亦师出无名而已矣。”而且张鸣岐来粤后禁赌,是有利于广东地方的“新政”,革命党此时起事,“非可乘之时者也”。“起于非可乘之时,抑又非可乘以起事之地,贪天之功,欲求有济,窃未见其可也。而孟浪之党人,宁不自悟其非哉。”[22]值得注意的是,当报纸批评广州起义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的“孟浪”行为时,报纸中的革命党人形象却发生了变化。当广州发生起义时,顺德乐从曾起事响应,报纸报道说:“乱党在乐从起事时,秋毫无犯,对于巡警亦无嫉视,所有酒米店皆派人看守,不准居奇,已属举动奇异。迨初三日十二点钟,在佛山败后,复回乐从墟,将前日早晚膳二百七十余席酒菜银,壹概向原店清结。又将起事时所夺该墟巡警枪支,一一点还清楚,乃各散去。吁!亦异矣。”[23]革命党仍被称为“乱党”,但革命党对于民间的“秋毫无犯”,已经开始让报纸连连称异了。
同时,革命党的正面形象也出现在报端,报纸报道了革命党人受审时的情形:“该乱党系闽籍人,剪辫西装之美少年。据供,年廿四岁。”在讯问中,革命党开始操福建语,因清廷官员听不懂而“改操英语”,问答之际,“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各国时事了然胸中”,挥笔写字时,“写尽两连白纸,不假思索,顺笔而挥,搁笔三次。写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槌其胸,欲不忍写”。写完之后,“某官命人给茶烟,起身行立正礼。迨将就刑,尚如此从容。写完供词,在堂上演说,说至时局,悲观槌胸顿足。力劝各官长将来治下如此如此,切不可如此如此,吾死犹生,虽千刀万斩,亦所甘心。”[24]据统计,广州起义死难的86名烈士中,广东籍51名,福建籍19名,21~30岁的40人,学生12人(其中留日学生8人),工农30人[6]63-65。死难烈士应不止86人,而且上述统计数据也未能说明未被难者的情况,但因起义中有“工农”参加,意味着报道中“美少年”的知识水平在起义人员属于少数比较高的。报纸对该革命党的报道,突出了革命党人有知识、有理想、文明程度高等特点,实际上通过一名革命党人的表现,塑造了整个革命党的形象。
与革命党人形象对比的是兵勇军纪的败坏。报纸报道,4月30日,有良民“被兵勇剥衣搜去财物”的,还有“营勇多名闯进涎香茶居抢掠饼食,并到左邻右舍抢食烟仔”,报道指出“惟巡警兵及督练公所勇,往查各户,秋毫无犯,同是办公,其纪律之优劣,判若天渊。”[25]5月9日的论说中指出,“此次羊城乱事,革党无一不失败,官军无一不胜利”,但是革党却获得了好名誉,而清军获得了坏名誉。“何谓好名誉,则以革党对于政界,虽属凶悍,今为问对于民间,果有骚扰乎?何谓坏名誉,则以官军对于革党,虽属奋勇,今为问对于百姓,果无侵害乎?……洵如所传革党借帽给价,败旋还枪,及卒偿酒席,不肯纵火,诸凡举动,其是否出于谲计,收买人心,姑勿具论,而即此观以,不皆似绝无损害闾阎之意欤?至于官吏,则除新军警兵卫队之外,其有所谓巡防营者,竞传每藉搜索军火为名,抢夺银物为事。省报初载其抢及饼食,抢及烟仔,行同盗贼。”[26]此论本意在于指出起义中清军抢劫让人不满意,从而提醒两广总督张鸣岐严办,但无形之中,却树立了革命党不骚扰民间,远胜清军的形象,客观上宣传了革命党。经过这样的报道,可以说革命党在围攻督署时“完败”,在社会影响上却是“完胜”。
三、“敦崇道义”的革命党
张鸣岐在武昌起义后曾说:“今日大局不在兵力之不足,防备之不周,而在已去之人心无从挽救。”[27]张鸣岐并不是在为防范不力卸责,他的话反倒是当时社会心理的真实反映。《申报》对谣言有过以下评论:“谣言无补于事实者也。谣言足以表见人民之心理者也……若夫谣言之于心理,则大有可证者。同一谣言也,闻某处失守,某人某人被刺被杀,则欣欣然有喜色。官军大胜,官军克复,则惨然以忧色,然以怒或且愤而无所发泄,而群诘其谣言之所由来,是则心理上之蕴蓄,断非谣言所能改变者。”[28]民心倾向于何方,是显而易见的。
武昌起义后,广东深受震动,该报即以大量篇幅在 “省新闻”内报道湖北革命史及九江、南昌、湖南等地革命情况。随着北来消息增多,湖北等地情况越来越明确。报纸于11月8日刊载言论,就民国军与清军在对待商业、临阵对敌、对待外人、战俘的态度等情况进行比较,道出“中华民国军之敦崇道义,与夫满洲军之野蛮自恣”、“一以暴,一以仁”的形象差异,并进一步指出“盖北兵犹□专制之余毒,肆为残暴,民军实能力守文明轨度,而诚信弥纶,此即专制为天所弃,与共和为众所归之天然一确证也。”[29]11月8日为阴历九月十八日,即广东光复前一天。到第二天,香港报界公社召开会议讨论“粤省独立事”,认为江孔殷有赞成张鸣岐独裁倾向,“大背共和宗旨”,决定“本公社不识江孔殷为何人”[6]133-134。 该报将这种对比上升到“专制”与“共和”的高度,显示报纸日益抛弃清廷、倾向于革命党,而且高扬革命党的奋斗目标。
到1911年底,该报公开为同盟会辩护,认为社会应该破除党见,因为同盟会为公而非为一党之私。而且,“革命”非必革命党人——同盟会所尊奉,而是人人“皆有革命之心理,革命之精神,以鼓励进行于不懈,方之同盟会,又何以异。”[30]“革命”未必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接受,但报纸的言论折射出广东社会对“革命”和“革党”认识的转移。《申报》在武昌起义后论全国形势时,指出最重要之地为北京和湖北,其次为湖南和河南,再其次为江苏和广东。而“广东为南洋门户,一得则海外之革命党人可以并为一气”,全国革命“血气已活,虽欲不成,而不可得矣”[31]。广东光复后的民心向背对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对辛亥革命大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论
从1910—1911年的消息和言论来看,《香港华字日报》并不倾向革命党,对革命党组织的历次起事,也颇多微词。从庚戌新军起义到黄花岗起义,再到武昌首义,报纸对革命党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最后革命党人赢得报纸称赞。这并不只是因为革命党人的宗旨,更多的是因为革命党人的表现及革命军军纪良好。报纸通过革命党与盗匪的比较,革命军与清军的比较,凸显了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崭新的形象。中国地域广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且报纸众多,背景各异,该报的认识并不能代表全国的看法。不过,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大背景,与其同调的报纸应当也有。比如《申报》是上海地区最大的商办报纸,这份报纸对庚戌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的报道虽与该报略有不同,但也大致展示了同样的过程,可见这种对革命党认识的变化并非广东一地所独有。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 宁树藩.十九世纪香港报业概述[J].新闻大学,1997,秋.
[3] 佚名.本报广告[N].香港华字日报,1910-02-17(4).
[4] 佚名.改换新字广告[N].香港华字日报,1910-04-01(4).
[5] 邱捷.香港华字日报对研究辛亥革命的史料价值[J].广东史志,2002,(2).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辛亥革命史料[G].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7] 佚名.省垣军变续闻[N].香港华字日报,1910-02-16(4).
[8] 毅父.论新[N].香港华字日报,1910-02-17(4).
[9] 博郎.羊城新年之十变局[N].香港华字日报,1910-02-19(4).
[10] 佚名.追论军变始祸之由[N].香港华字日报,1910-02-20(4).
[11] 毅父.揭袁督禁港报入口之谬[N].香港华字日报, 1910-04-01(4).
[12] 佚名.准弛禁港报[N].香港华字日报,1911-02-17(4).
[13] 佚名.东安盗风猖獗[N].香港华字日报,1911-01-19(4).
[14] 佚名.新任知县之先作侦探[N].香港华字日报,1911-02-15(4).
[15] 佚名.城内拿获革党紧要详情[N].香港华字日报,1911-02-25(4).
[16] 佚名.拿获革党案续闻[N].香港华字日报,1911-03-02(4).
[17] 毅父.李准能严缉革党而何以独宽容劫贼[N].香港华字日报,1911-03-08(4).
[18] 佚名.革党毁督署第一次特电[N].香港华字日报, 1911-04-29(4).
[19] 佚名.羊城廿九晚乱事详情汇志[N].香港华字日报, 1911-05-01(4).
[20] 客星.论张督处变之才[N].香港华字日报,1911-05-02(4).
[21] 佚名.广东新闻[N].香港华字日报,1911-05-2(3/4).
[22] 佩弦.粤垣变起之疑问[N].香港华字日报,1911-05-03(4).
[23] 佚名.乐从乱党之手段[N].香港华字日报,1911-05-04(4).
[24] 佚名.革党第六侃侃而谈[N].香港华字日报,1911-05-04(4).
[25] 佚名.兵勇行抢之抵杀[N].香港华字日报,1911-05-04(4).
[26] 客星.论张督宜严办抢物之防勇以满人意[N].香港华字日报,1911-05-09(4).
[27] 佚名.张督电陈粤省之大局[N].香港华字日报,1911-10-26(4).
[28] 佚名.谣言说[N].申报,1911-10-31(3).
[29] 佚名.民国军与满洲兵之比较[N].香港华字日报, 1911-11-08(4).
[30] 敬父.论同盟会[N].香港华字日报,1911-12-27(4).
[31] 佚名.革命大势说[N].申报,1911-10-28(2/3).
The Media Image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in Chinese Mail(1910—1911)——Discuss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1911 Revolution
ZHOU Jun
(School of Tourism and Historical Culture,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526061,China)
From the uprising of Gengxu New Army to the Huanghuagang uprising,and then to the Wuchang uprising,the revolutionary party’s image in Chinese Mail has undergone a changing process.Finally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won the praise of the newspaper because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good performance and the revolutionary army’s discipline.The newspaper highlighted the new image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911 Revolution,by comparisons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with the bandits,and with the army of Qing Dynasty.These reports revea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pular aversion and public opinion towards social upheaval.
Chinese Mail;1911 Revolution;the revolutionary party’s image
K257.4
A
1009-8445(2012)03-0040-05
(责任编辑:杨怀玫)
2011-10-13
周 军(1971-),男,湖北松滋人,肇庆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