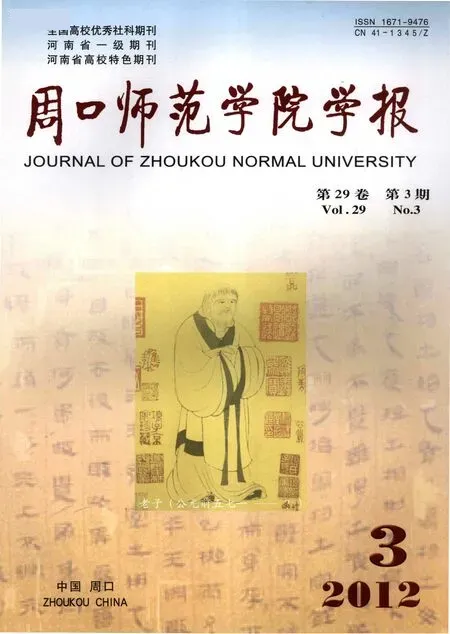试析《大教学论》在教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
岳定权
(周口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河南周口466001)
1632年,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撰写了《大教学论》一书。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大教学论》在教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众说纷纭。归结起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是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雏形。如唐莹认为,在教育学发展史中,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于17世纪上半叶掀起了第一道狂澜,他的《大教学论》被认为是相对独立的、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的滥觞[1]。第二种观点认为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标志着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肖昊认为,1632年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的问世,标志着教育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
厘清《大教学论》在教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可以明晰教育学发展的过程和逻辑,对教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而要厘清其地位,关键在于评价标准。以前的大多学者是站在理论教育学的角度制定标准,再以这一标准审视《大教学论》,从而得出其在教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这一做法具有“理论”倾向,而且似乎有一定的偏颇。笔者尝试将教育学分为“理论教育学”与“实践教育学”,在探讨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判断《大教学论》在教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以期客观评价《大教学论》的学科地位。
一、理论教育学、实践教育学及其关系
在此之前,首先应区分教育学与教育科学。在《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对教育科学的分类框架中,没有出现“教育学”,著者认为“对'教育学'的理解还有着分歧,姑暂'悬置',有待共析”[3]。从分类学或逻辑学上来讲确实有理,但在教育史上,教育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只是在科学化、专业化过程中,教育学成为了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在研究《大教学论》在教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上,教育学应为教育科学的代名词,两者所指为同一对象。
作为一门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综合学科,教育学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果笼统地评说《大教学论》在教育学发展史中是什么地位,不但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在现代教育学中,其基本取向有两个,即理论取向和实践取向,从而形成理论教育学和实践教育学,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科学的教育学,旨在描述教育事实,考察各种教育现象发生的原因与条件,从而揭示其中规律性的联系。简单地说,它着重回答教育'是什么'(含'教育目的'是什么、'学校制度'是什么、'课程'是什么等);实践教育学则主要回答教育'应当是什么'(教育价值观念)、教育'应当做什么-怎样做'(教育规范),即确立教育价值-规范,以指导实践。”[4]172可见,理论教育学与实践教育学在目的、对象与结构等方面有较大区别。从目的上看,理论教育学是为揭示本质、发现规律进行理论创新,而实践教育学则是制定规范、指导实践,两者在取向上是分向而行的;从对象上看,理论教育学本着科学精神,以“普遍存在的教育事实”为其研究对象,实践教育学则“研究受教育者怎样有效地理解和掌握教育'应当',从而形成教育实践能力”[5]10;从结构上看,理论教育学需要从普遍的教育事实中归纳出教育规律,因此是一种归纳体系(如陈桂生的《教育原理》体系),而实践教育学“一般采用从目的到手段、从内容到方法逐步演绎的体系(如熊川武的《实践教育学》体系)”[4]173。理论教育学与实践教育学的划分及其区别为思考《大教学论》的学科性质提供了借鉴。
学科的形成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研究科学发展,不仅要把科学作为整体来考察其历史演进的规律以及横断逻辑结构,也要把科学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研究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科学特点。”[6]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共同构成的对教育的需求是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在人们讨论教育学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以理论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以理论的标准来衡量著作,恰恰忽视了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往往是来自“实践”的土壤。众所周知,人类产生之日,便有教育。人类总是在自己对教育的需求过程中来改造教育和推动教育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求达成自己理想人格状态的方法与手段,制定规范,形成观点和理论,最后冠以“教育学”之名。可以说,没有实践的需求和目的,没有为实践的目的而形成的方法、手段与规范,就难有思想和理论,更难有理论教育学之存在,“人们对教育问题认识的教育经验阶段和教育思想阶段是前教育学阶段”[7]。但后人在反观教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将太多的赞歌送给了“理论教育学”,而忽视了理论教育学之源的实践教育学。就算有学者在努力“另眼相看”实践教育学时,也大多认为是“将理论教育学的理论具体化的过程中,发现理论教育学的不足,从而为理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材料”[5]2。这确有本末倒置之嫌。
二、《大教学论》是理论教育学还是实践教育学
如上所述,理论教育学与实践教育学在目的、对象与结构方面存在明显区别,现在我们就从目的、对象、结构三个方面来审视《大教学论》的学科性质。
1.从目的上讲,《大教学论》的目的十分明确。在著作的前言就写到,“我们这本《大教学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8]著作自始至终也在努力寻求这样一种“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显而易见,《大教学论》是在“建立规范,指导实践”,而非通过教育事实去探寻教育规律。
2.从对象上讲,由于《大教学论》是要形成“教”与“学”的全部艺术这样一种实践的能力,因此,其研究的对象正是如何有效形成这样一种能力。综观全书,其核心是教学原则。前面部分主要论证应当教,而后面则论述怎样运用教学原则。这种指向“如何形成能力”的研究对象符合实践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特征。
3.从结构上讲,《大教学论》一共33章,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第1~12章),包括论人和论学校,为后面论述奠定逻辑基础;第二部分是论旨(第13~19章),主要论述教学的普遍原则;第三部分是应用(第20~31章),主要论述教学的原则在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教与学中的运用;第四部分(第32~33章)是总结[9]19。从这样一个内容体系可以看出,《大教学论》正是以“怎样教”这一实际教育问题来演绎形成体系的,遵循着“应当做什么-怎样做”的应用逻辑。而且,《大教学论》在论述过程中,首先是建立观念,再将观念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最后形成一定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遵循着“观念-对应问题-形成能力”这一从知识向能力转化的程序。如在论述教学原则时,总是先说自然是怎样的,然后模仿自然,发现偏差,最后纠正,形成了“自然-模仿-偏差-纠正”的逻辑,并提供案例,以形成实际的操作能力。这样以形成实际能力为最终目的逻辑体系,符合实践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基本特征。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目的、对象还是结构,《大教学论》都具有实践教育学特征。这正如陈桂生所理解的那样,按照后来教育学家的观点,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教育学”(指“科学”的教育学),为“教育的科学原理的汇集”,而“实践教育学”则是“教育活动规则的汇集”,《大教学论》恰恰具备“实践教育学”的特征[9]20。因此,与其说《大教学论》是教育学著作,不如说《大教学论》是一本实践教育学著作显得更为准确。
三、《大教学论》在实践教育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教育的实践形态由来已久,从人类产生到现在,教育的实践形态就一直按照某种逻辑不断演变着。《大教学论》具有实践教育学的基本特征,但它究竟在实践教育学发展过程中居于何种地位呢?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独立”意味着不受其他支配,有着自身的特质。如果从理论教育学视角来看,《大教学论》算不得独立的教育学。因为,“教育学的'独立'的学科地位问题,主要是同它的学术声誉相关的两个问题,即以'学科'标准与'科学'标准衡量教育学问题……”[4]50无论是从严格的“学科”标准(自身的概念体系,并用这些概念进行逻辑推理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还是“科学”标准(实证的方法,严密的逻辑),都能发现《大教学论》与理论教育学相差甚远。但实践教育学应有其自身的学科标准,只有参照实践教育学的学科标准,才能真正理解《大教学论》在实践教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顾名思义,实践教育学应有“实践”的特性与“教育学”的规范。实践的本义是“做”与“行”,相对于“思”与“想”,是一种有形的活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把实践规定为“人的感性活动”。不同于传统的“追求本质”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使人们从关系中去寻求理解,并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育学,从广义上说,“它是关于教育的学问,即人们对于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的知识、学说或理论”[10]。但在教育学前冠以“实践”之修饰,表明了其价值取向,即舍弃了对教育内在规律的追问,而侧重于在关系中对“怎样做”的探索。因此,实践教育学的“独立”应该重在研究对象的“实践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教育学研究范围的确定。
以这样的标准反观《大教学论》,首先,《大教学论》研究的是教育中最基本的“教学”问题,且并没有从“理论”视野来研究,而是从“解决问题”角度来研究怎样增强“教学”的有效性问题,希望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能够“迅速地、愉快地、彻底地”进行。因此,其对对象的研究取向是指向实践的。其次,“教学”问题不但是著作研究的主要问题,著作还以“教学”为基本的逻辑起点构建成了教育学的研究范围。在著作中,无论开篇所表露的著书目的——阐明“教”的全部艺术,还是著作结构,无不显示出“教学”在著作中逻辑起点的作用。正是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构成了第一部分的引论——说明“教学之因”,第二部分的论旨——详解“教学之实”,第三部分的应用——展示“教学之果”,三个有机部分第一次确立了教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
在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产生之前,欧洲已经有众多的教育家对教育进行了思考和实践,产生了一系列的教育著作,如古罗马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培养》、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的《巨人传》等。这些论著大多也在思考教育的实践问题,但由于其并未建立起一个基于实践逻辑的教育学体系,故而不能说形成了独立的实践教育学。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夸美纽斯以“如何教”作为其学说的逻辑起点,建立起了“为谁教”、“教什么”和“如何教”的内容逻辑,从而初步确立了教育学的研究范围。
四、确立《大教学论》学科地位的意义
《大教学论》从解决问题的初衷入手,围绕教育中处于核心的“教学”问题,首次确立了教育学的研究范围。美国教育史学家卡伯莱指出:在夸美纽斯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几乎所有18、19世纪教育理论的萌芽[11]。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认为,《大教学论》的问世,标志着独立实践教育学的开端。而这一结论,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1.明晰了教育学学科发展过程的逻辑线索。教育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实践的探索与丰富,人们在对教育实践进行反思、追问与科学化解释的过程中,教育理论得以逐步形成。同时,教育理论一旦形成,便具有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有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逻辑和方式,并以特定的方式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二者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同等的价值,忽视任何一方都不是应有的态度和做法。
在承认《大教学论》作为独立教育学形成的标志后,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教育学发展的轮廓:混沌时期——零散的实际的教育问题的解决;突显时期——实际教育问题的分类,组成框架,形成规范;系统时期——教育学开始按一定的逻辑形成一定的系统,并对系统的合理性进行解释;理论化时期——对教育学的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构建;成熟时期——教育学具有科学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大教学论》是系统时期的产物,它对以前实际的教育问题进行规范和解释,为以后理论教育学的产生奠定基础。
2.为我们思考教育研究的理论取向与实践取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借鉴。目前,教育学正处于成熟建设时期。但人们往往热衷于对其理论化的建设,使得教育学研究深深地“藏”于“象牙塔”之内,与实践相脱离。理论如果脱离实践,那么其研究除了丰富理论,起到“庸人自娱”的作用外,还能做什么呢?反之,实践的规范如果不进行概念构建,又怎能与他人“分享”?《大教学论》作为教育学发展史中独立实践教育学的开端,至少向我们展示了教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取向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即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的源泉,教育理论是对教育实践的反思、总结和升华,二者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有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才能彰显二者的有机融合。这正如邱学华总结的那样,“以上简略回顾尝试教学理论从萌芽、初试、成型到发展的轨迹,每一步都有着教育实践的基础,充分证明教育理论源于教育实践的真理,离开了教育实践不可能有尝试教学法的产生,尝试教学法也不可能提升到尝试教学理论”;“正由于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反过来再指导教育实践,促使尝试教学法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应用”[12]。
[1]唐莹.元教育学:西方教育学认识论剪影[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44.
[2]肖昊.教育学从“艺术”到“实用价值”再到“科学发展”的追求[J].湖南社会科学,2011(1):170-175.
[3]瞿葆奎,唐莹.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1.
[4]陈桂生.教育学的建构[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5]熊川武.实践教育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6]李光,任定成.交叉学科导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130.
[7]瞿葆奎.教育学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347.
[8]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
[9]陈桂生.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0]胡德海.教育学原理[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 4.
[11]程翔章,曹海东.世界著名教育家科学家的命运[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49.
[12]邱学华.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的源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6):4-6.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