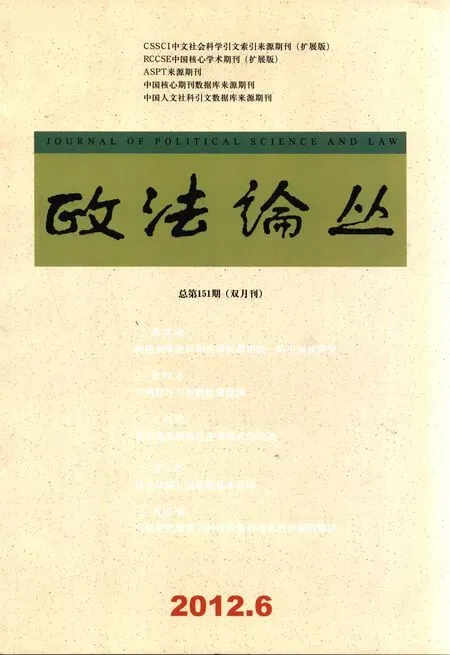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之保护
——由 “校长拒绝警察询问学生”切入
王 婧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 上海 201620)
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之保护
——由 “校长拒绝警察询问学生”切入
王 婧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 上海 201620)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中,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负有作证义务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针对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机制存在疏漏。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亲属间的作证特免权,完善了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考虑到证人人权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社会和谐,今后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借鉴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完善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
未成年人 作证特免权 合适成年人参与
2012年5月,上海一位12岁孩子的母亲涉嫌诈骗外逃,警察到学校,提出要询问这个孩子。校长“拒绝”了警察的要求,提出“学校可以让班主任接受询问,提供所有掌握的信息,但警察不可以在校园内直接询问学生”。校长的理由是,孩子是未成年人,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没有形成,学校不鼓励孩子揭发自己的父母、撕裂亲情,这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做法。父母犯错是大人的事情,和孩子没有关系。学校有义务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①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校长的行为获得了公众的赞誉:“重视人性考量”,着力保护未成年人;“立足教育本旨”,拒绝冷酷无情的执法,是“理性之举”②。相形之下,法律的地位则略显尴尬:从立法层面而言,有评论指出现行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存在不周延之处③;在执法层面,近年来频频出现公权力强硬甚至暴力执法的案例凸显了校长的“拒绝”立场,也让这一行为更容易获得舆论的关注和肯定。
面对打击犯罪的需要,是“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古今中外不同的立法例诉诸不同的选择,当需要作证的亲属是未成年人时,其中所涉及的法律与道德的纠葛更加复杂。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于立法上首次确立了亲属间的作证特免权,同时也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专章列出。作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最为重要的法律之一,《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内容和技术层面上传递了强化保护社会基本伦理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价值取向。本文意欲探讨的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的作证问题——兼具未成年人以及亲属身份属性的证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证问题——涵摄了上述两种价值取向的选择。本文将从梳理现行法律规定入手,分析保护社会基本伦理与保护未成年人两种价值取向在刑事诉讼立法中的体现(或者背离),指出相关规定衔接的不周延之处,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一、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的立法现状
有关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的立法主要体现于《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同时涉及《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下文的梳理将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为基准,兼顾新近修订之规定。
(一)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有作证的义务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60条继承了上述条款。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具有作证的资格,也有作证的义务。
根据上述规定,亲属身份并不能免除公民作证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条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免除了亲属的作证义务。同样,未成年人也负有作证的义务,但是未成年人作证义务的履行要受到其作证能力的限制。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未成年人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年幼”的人作证要具备“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能力。如何判定未成年人是否具备上述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57条规定,对于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者鉴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4条同样规定了对于证人的作证能力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审查和鉴定。
除上述情形外,负有作证义务的公民如果不履行义务,则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98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第3款规定,“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时,应当依法处理”。我国《刑法》第305条对于证人故意做虚假证明规定了伪证罪,第310条将明知是犯罪的人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虚假证明的行为认定为窝藏、包庇罪。而针对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了强制出庭制度,对于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法庭可予以训诫或者拘留。
(二)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机制
1.作证方式
个人包括未成年人可以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人证言要成为定案的根据,则要经过法庭的质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人需要出庭。考虑到未成年人身心的特点,有关司法解释以未成年人不出庭作证为原则,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9条规定,“公诉人一般不提请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2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人是未成年人的,除法律规定外,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不出庭”。
2.作证程序
未成年人作证程序的特殊保护主要体现于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目的在于保障未成年人作证时的心理稳定,弥补未成年人对于相关问题以及后果认知能力的不足,以获得更好的作证效果;防止公权力滥用而导致的程序不公正,防止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情况发生。《刑事诉讼法》第98条规定,询问不满18周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人、被害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61条规定,询问不满18周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对证人证言应着重审查以下内容:……询问未成年证人,是否通知了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等。”
二、 相关立法之评析
根据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在保护亲属关系方面,现行法律的规定背离了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突破;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法律注意到了未成年人身心的特点而做出了特殊规定,但依然有提升和完善的空间。具体分析如下:
(一)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义务的不合理之处
1.造成法律与道德的背离
法律将指证亲属的犯罪行为规定为义务,违背了人最基本的道德情感,长久而言,也不利于法律秩序的实现和法律权威的树立。当证人是未成年人时,对其身心的伤害会更加严重。维护血缘亲情是人类最基本和朴素的道德情感,也是维系家庭的重要基础。公元前66年,西汉宣帝在历史上首次确立容隐制度的诏书中已经言明:“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1]P251将指证有犯罪嫌疑的亲属规定为义务,使得人们陷入了情与法的两难抉择:如果人们惧于法律的惩罚而选择大义灭亲,那么即使亲属罪有应得,“亲情撕裂”的痛苦也无可避免,甚至加剧因为亲属犯罪已经为他们带来的社会某种负面评价,危及家庭的稳固。而一个被亲人告发的人很容易不再相信亲情甚至成为一个精神上无所寄托与牵挂的“孤家寡人”,这样的人对于社会的危险性自不待言。一项本意在维护秩序的法律规定,却可能因为破坏社会制度的基础而导致更大的混乱。如果人们选择维护亲情,虽然违反了法律却换得“心安”,法律的权威依然受到了损害。
不可否认,新近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使得学界倡导已久的亲属作证特免权首次落实于立法层面。所谓证人作证特免权,或称证人特权、证人免证特权,是指在法定情形下,特定公民享有的拒绝作证或制止他人作证的权利。[2]P216这一修订在保护人权、维护社会基本道德伦理关系方面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新法所确认的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有限:从对象角度而言,仅限于配偶、父母和子女;从诉讼阶段的角度而言,仅限于庭审阶段不受强制到庭,在其他诉讼阶段,即使是上述亲属,也依然有作证之义务。
2.影响未成年人的作证能力
理论上,证人的作证能力包括三个方面:感知能力,即一个证人在其将要作证的事情发生的关键时刻必须具备有感知的能力,无论他运用一个或者多个器官;记忆能力,即证人的记忆必须完好无损;表达能力,即证人必须有能力并愿意真实而清楚的表达,以便调查人员不会误解。[3]P417-418总体而言,未成年人的心智发育尚未成熟,对作证所需的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乏。社会心理发展方面,未成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较成人弱,表现出一定的心理脆弱性特征:(1)冲动性。情绪起伏大,容易波动,缺乏时间感,缺乏对于供述长期后果的认知;(2)对于风险的态度不成熟;(3)容易受到权威人物和同伴决策的影响。[4]P89法律将指证亲属的犯罪嫌疑规定为义务,使得很多未成年人第一次介入高度对抗性的刑事诉讼程序,当面临着要么揭发自己亲人要么承担不利后果的抉择,未成年人很容易出现情绪波动,也增加其被诱导的可能性,这些都将对未成年人有限的作证能力造成负面影响。在我国现行立法对于未成年人作证能力审查程序尚未有详细规定的情况下,这样的法律规定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
(二)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的不完善之处
1.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对于通知是“可以”抑或“应当”规定不一致
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中,《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可以”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虽然规定为“应当”通知家长、监护人或者教师到场,但同时规定“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使得通知与否诉诸于侦查机关的自由裁量,为不通知预留了空间。
2.到场人员范围的界定不一致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法定代理人”,其第83条规定,法定代理人的范围包括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是监护人。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定的到场人是家长、监护人或者教师。其中最为重要的不足在于《刑事诉讼法》的法定代理人范围与《民法通则》监护人的范围衔接失衡。学理上,法定代理的基础是一定的身份关系,如亲权、监护等。我国民法没有明确规定亲权制度,因此监护人身份就成为了法定代理产生的事实,故而法定代理人与监护人的范围应该一致[5]。《民法通则》第16、17条对于无民事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刑事诉讼法》却将民法上的监护人与其范围内的父母、养父母概念并列,同时将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代表纳入法定代理人的范畴之内,使得刑事诉讼中法定代理人的概念外延扩展,造成了到场人范围规定上的冲突。
正是这种扩展使得校长“拒绝”警察的依据出现了争议。在笔者看来,学校不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因而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作为未成年学生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学校代表的到场是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中关于学校保护未成年学生身心健康与人格尊严责任的规定④。原因如下:首先,监护是一种法定关系,《民法通则》第16条关于可以成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机构规定中并未提及学校。其次,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显然,监护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与责任。如果让学校承担诸如“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财产”、“代理诉讼”等责任,学校将不堪重负,而且未成年人的父母等监护人也未必愿意学校如此干涉未成人的生活[6]。再次,根据《民法通则》第133条的规定,我国对于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监护人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让学校作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承担被监护人的侵权损害的损失,对于学校过于严苛。
3.法律对于法定代理人到场后可以行使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以及不到场的后果都没有明确规定
由于相关权利义务不明,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定代理人相互推诿都不到场,有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之后不知如何履行职责,还有到场法定代理人站在司法机关一边去训诫未成年人反而加重未成年人心理负担,这不仅使得这一制度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效果上大打折扣,也可能对司法机关正常行使权力的行为造成干扰等等。本文开篇所提及的案例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与其说校长“拒绝”了警察,不如说校长于法律不明确之处对于警察的询问方式提出了建议:不直接在校园内询问孩子,而是改由班主任接待,配合警方提供了家访的地址,复印了家长在学校登记的信息等等。从效果而言,学校既履行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也实现了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的目的,即在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前提下查明案件事实。
三、 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保护的完善
总结上述不完善之处,笔者认为,在现有条件下,要加强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之保护,在立法上扩大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范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完善未成年人作证特殊保护机制是当务之急。
(一)扩大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范围
为了保护孩子,校长用心良苦,但是即使如此,保护依然难以周全。毕竟离开校园,警察依然有权询问孩子,孩子还是需要面对情与法的纠结,其根源在于指证有犯罪嫌疑的亲属是法律义务而不是权利。考虑到证人的基本人权、未成年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必要在立法中进一步扩大一定范围的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而传统“亲亲相隐”的伦理意涵与现实立法的趋势已经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1.必要性
首先,亲属作证特免权维护了证人的基本人权。刑事诉讼法被誉为“小宪法”,它所体现的人权保护水平是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司法文明的程度及人权保障状况的重要标志。《世界人权宣言》第16条(三)规定,“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3条重申了上述规定,并且在第7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此次修订《刑事诉讼法》亦被列入基本原则中。确立亲属作证特免权有利于纠正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将证人作为发现案件真实的工具而漠视了其基本人权的状况。亲属作证特免权是一种权利,它否定了“必须告”的义务,但也绝不是“禁止告”,而是赋予证人维护亲情和人伦的选择权利与可能性,这是尊重证人主体地位的体现,也是给予证人人道待遇以及取证方式文明化的体现。
其次,亲属作证特免权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1999年4月2日对我国生效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儿童、未成年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和谐稳定的家庭,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确立有利于亲情的维系和家庭关系的和谐,这一点在需要作证的人是未成年人时尤为重要。
再次,亲属作证特免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本性,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信息”。[3]P356确立亲属作证特免权是价值权衡的结果,它可能会阻碍个案中案件真实的发现,但是它维系了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家庭,更为重要的是它维系了对于社会秩序稳定更为重要的忠诚、信任以及信赖关系,长远而言,这对于社会和谐意义重大,也有助于从根本上减少犯罪。
2.可能性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原则之一,其维护血缘亲情的伦理意涵可以成为时下确立亲属作证特免权所赖以为凭的“本土资源”。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段话一直被视为儒家“亲亲相隐”思想的经典表述。自西汉宣帝时期正式入法以来,“亲亲相隐”在制度层面日臻完善,至唐律,“同居相为隐”原则已经位列相当于刑法总则的《名例律》并为后世所继承直至清末。从晚清修律到民国的诉讼立法,“亲亲相隐”去除了传统法律制度中“禁止告”的义务性特征而转化成为拒绝作证的权利[7],但是其维护血缘亲情的伦理意涵依然保留,成为移植自西方的作证特免权得以在中国生根的重要原因,相关规定更是成为今天台湾地区亲属作证特免权的滥觞[8]。当下,我们欲重构亲属作证特免权,“亲亲相隐”原则中的伦理意涵无疑可以成为我们利用的“本土资源”。此外,确立亲属作证特免权,并非完全否定了从亲属处获知案件情况的可能性,因为亲属可以自愿放弃作证特免权,指证犯罪。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⑤而免除上述亲属出庭作证的义务,可以认为表明了今后立法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趋势。
亲属作证特免权并非绝对,需要以法律明确界定适用范围与例外。在现有条件下,可以考虑以民事立法中所界定的近亲属作为权利主体范围,对于伦常犯罪、严重危害国家与公共安全的犯罪不适用作证特免权等。此外,立法需要规定相应的程序,如司法机关应当告知权利主体享有权利,权利的申请、批准和救济性程序,以及不利推定之禁止等。
(二)借鉴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考虑到上述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中法定代理人含义的局限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未来立法中可以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引入对未成年证人的询问中。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目前许多国家刑事司法中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基本含义是,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适当的成年人(如监护人或专设的适当成年人)到场,其作用在于通过他或她的讯问时在场,阻止警察的压迫行为并确保未成年人所作的陈述是自愿的。[9]P167未成年证人是刑事诉讼的参与人,他(她)们的介入是帮助国家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其本身是无辜的,理应获得不低于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保护。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弥补了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的一些不足:首先,明确了询问证人时“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次,明确了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补救措施,即可以通知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再次,明确了到场法定代理人的一些权利、义务,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进行补充陈述”。
但是上述规定依然没有解决法定代理人衔接范围失衡的问题,因此,未来立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可以继续作如下完善:首先,统一将到场人称之为“合适成年人”,以立法明确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其次,统一将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规定为“应当”;其次,明确司法机关不通知的后果。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规定,将没有特定人士在场情况下取得的青少年的证言或者口供视为以欺压手段获得的证据而排除。[10]再次,完善合适成年人在场时的权利、义务。如合适成年人需要按照要求到达现场,可以帮助未成年人与司法机关沟通但是不得诱导未成年人,需要保守案件秘密以及未成年人隐私等。
结语
社会转型之时,价值多元与价值冲突凸显,需要法律在整合不同价值方面做出更为细致与妥帖的安排,将宏大与抽象的价值取向化为可行的制度设计与具体的操作规范。同样重要的是,一个畅达而理性的法律执行机制将“书本中的法律”化为“行动中的法律”。在恪守亚里士多德“服从已经成立的法律”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参与法律实施的各方能够诉诸于内心道德律令,守护作为法律之源的社会风纪,正如校长之“拒绝”与警察的克制和理解,才能达到更好的法律实施效果,并且推动法律不断完善,促进社会达致善治的良性循环。
注释:
① 杨玉红:《母亲涉诈外逃,警察欲询问稚子,最牛校长婉拒:请保护未成年人》,载《新闻晚报》,2012年5月10日。
② 傅达林:《校长拒绝警方要求是理性之举》,载《京华时报》,2012年5月12日。
③ 殷国安:《校长和警方都应赞扬,但更需完善法律》,载《广州日报》,2012年5月12日。
④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9条、第21条以及《教育法》第44条。
⑤ 王兆国:《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03/08/content_24838939.htm,2012年6月23日访问。
[1] [东汉]班固.汉书·宣帝纪第八[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3] [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4] 许永勤.未成年人供述行为的心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5] 孟红,崔小峰.未成年刑事案件中法定代理人制度研究[J].少年司法,2005,5.
[6] 王成.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义务及责任承担[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3.
[7] 张建飞.亲属免证权制度及其法律效益价值探微[J].政治与法律,2008,7.
[8] 吴丹红.特免权制度的中国命运——基于历史文本的考察[J].证据学论坛,2005,2.
[9] 赵国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 姚建龙.英国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及其中国的引入[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4.
TheProtectionofMinorRelativesofCriminalSuspectstoGiveTestimon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admaster’s Stopping the Police from Questioning the Students”
WangJing
(The Science Institute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minor relatives of criminal suspects are compulsory to give testify, which violates social’s basic ethics. The procedural safeguard of minor’s giving testimony is also unperfect. The newly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recognizes the privilege of witness of the relatives to some extent, and improves the system of legal representatives present to the scen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f the witnesses, the healthy growth of minors and social harmony,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privilege of witness of the relatives further, and to draw on appropriate adults participa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minors; the privilege of witness;appropriate adult participation
1002—6274(2012)06—121—06
DF713
A
王婧(1981-),女,山东威海人,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
(责任编辑:黄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