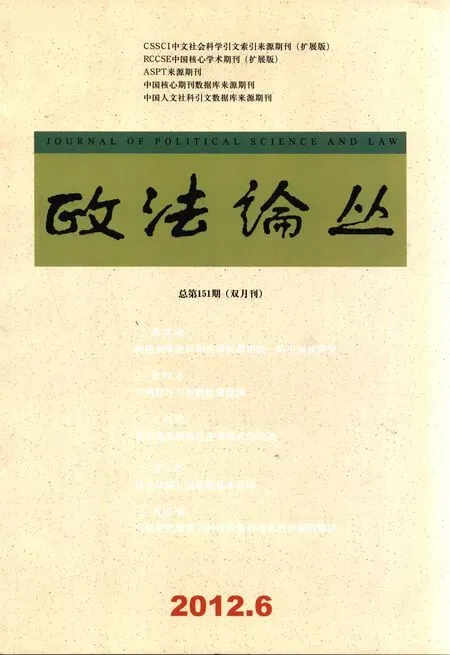论语用学视域中的法律推理*
齐建英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论语用学视域中的法律推理*
齐建英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语用学是从微观、语言的层面分析和把握法律推理的新视角。在语用学规范性视域中,法律推理是一种融合话语行为、命题行为和语用行为的交互言语行为。其中,“说者”与“听者”都是法律推理主体;达成合理共识是法律推理的目的和原动力;遵守合作原则是法律推理语言有效性的保证。语境通过语言选择的“装扮”来影响法律推理,是影响话语权分配、共识达成及合作原则遵守与否的关键因素。改善语境是发展法律推理的必由之路。
语用学;言语行为;法律推理;语境
如今,在法律推理研究的宏观层面上,逻辑、对话和修辞三种进路的理论日趋成熟,三者的沟通与融合已成定势,然而,在对法律推理实践的指导上仍有“隔靴搔痒”之嫌。如何从微观的细节层面分析和把握法律推理,弥合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缝隙是一个新课题。法学的语言转向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法律推理是通过语言进行的,离开了语言,法律推理的逻辑失去了依托,对话失去了桥梁,修辞失去了载体。法律推理中的语言是使用中的鲜活语言,它不仅涉及语言本身的意谓和使用规范,而且涉及语言的使用者、使用目的和使用环境,这就进入了语用学的范畴。
一、语用学是研究法律推理的新视角
(一)语用学是一个综合的视角
美国哲学家莫里斯首先提出了“语用学”的概念,他指出,“从指号过程的三维关系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成分(即符号载体、所指事物、解释者)来看,很多其他二维关系可以抽象出来加以研究。……研究主题也可以是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叫指号过程的语用维度[……],对这一维度的研究就叫语用学。”[1]当时的莫里斯正在尝试着提出一个统一的符号学理论,该理论将“囊括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心理病理学家、美学家或社会学家对符号所做的一切有趣的讨论”[2]P255,语用学的提出是该理论尝试中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语用学从一开始就体现的多学科性,几十年来,来自各个方面的对语用学的定义不胜枚举,它的学科本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语用学是一种观察语言的视角。“可以说,语言学的语用学,……表现了一种新方法的特征:观察语言现象,而不是明确划分与其他学科的界限。”[2]P270维索尔伦指出,“语用学并不构成某一语言理论的一个新增部分,而是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总而言之,我们能够进一步将语用学阐释为一个,融认知、社会和文化于一体的综合视角,它作用于与行为方式应用有关的语言现象。”[2]
这一综合视角虽然很难定义,但是对于它的视野框架,即研究范围,在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即语用学主要研究指示语、含义、语境、预设、言语行为等。George Yule指出,语用学研究说话人意义、语境意义、言外之意、表达的相对距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3]P3Horn & Ward认为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含义、预设、言语行为、参照、指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4]P1-151索振羽认为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语境、指示词语、会话含义、预设、言语行为、会话结构六个方面。[5]P16从语用学的视角研究或观察某一领域的语言现象,总会从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着手。
(二)法律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语用学逐渐从“废纸篓”、“垃圾袋”的地位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许多研究方法和分支学科不断出现。法律语用学也应运而生。由于法律语用学首先在语言学界发起,它研究的路径是从语言到法律,即通过在法律语言中寻找语用特质来建立二者的连接点。法律语用学讨论了法律语言中的语用思想和概念。首先,预设在法律语言中鲜明地体现为律师在法庭上刻意使用yes/no问题,利用预设来诱导证人。其次,在法律语言中的指示词(人称代词)反映了法庭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第三,在法庭中,确切含义还需要通过法庭调查、证人证言和法庭话语的其他形式来推断。第四,言语行为最经常发生在法律语言中了,那是因为,“言语行为理论和法律是由同样的材料组成。语用学的概念,如权威、可证明性和义务都是双方的基础。”[6]P254法律语言是旨在实现法律目的的语言活动。法律与语言之间的连接非常复杂,它不能被降低为一些发生在法律话语中的语用概念的简单结合,它需要一个多维的更加广泛的视角。它至少还应涉及社会语用学、话语分析和跨文化交流分析。如,法庭话语的参与者们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社会语用学的解释。Luchjenbroers曾指出,“首先法庭过程是单方面的,其中,律师在整个过程中单方面地控制着话题”[7]P513。这种控制是权力的表征,是语用学讨论的议题。
(三)法律推理研究需要语用学的新视角
到目前为止,在对法律推理的规范性评价上存在着逻辑、修辞和对话三种研究进路,三者分别从形式向度、实质向度和程序向度提出各自的规范要求。它们共同作用于法律推理的评价理论中,缺一不可,因此三者的融合与互补已成为理论界共识。如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一次法律论辩中,要适用三种形式的合理性条件,即作为结果的论证的逻辑条件,作为程序的论证的对话条件以及作为过程的论证的修辞条件。[8]P197在法律推理的具体方法上,分析(形式)推理和辩证(实质)推理二分法已经达成共识。只不过,英美法系侧重于以判例法为基础的类推,而大陆法系侧重于以制定法为基础的演绎。魏德士虽然只对演绎推理进行了论述,但他同时指出,“在法律规范的适用中,语法、逻辑和目的论三者可能陷入紧张关系。”[9]P301-302法律推理的理论不断完善,而在中国的法律推理实践中,被倒置和被省略的法律推理[10]随处可见,此时的法律推理不仅不能实现自身的法治价值,而且成为非正义的嫁衣。法律推理研究亟待找到一条与法律实践更加贴近的,更微观的思路和视角。
法律推理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法律方法。它被赋予法治价值的理由之一是“法律推理是防止外界干预法官独立审判活动的一道屏障”[11]P163。这一屏障论的预设是:法律推理的一面是法律,另一面是法外因素。那么法律推理本身又怎能脱离开法外因素呢?凭借它的逻辑、程序和说理?外界因素可以将法律推理的逻辑倒置,剥夺一方的话语权,省略说理或者强词夺理。法律推理主体面对着法律与法外干预,该如何应对呢?他是否有抗干扰的素质和能力?社会是否能为那些为了法律正义而抵制外界因素的主体以应有的保护?麦考密克曾敏锐地指出“正如我所竭力强调的那样,基于规则的推理活动只能带领我们走这么远了,而且推理是仅仅属于法律活动内部的一个特征,因为规则在适用过程中经常不能够实现自身的实际功效,对于给定的一个具体情境也起不到确定无疑的规约作用。”[12]前言P5法律推理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方法和手段,它自身的各种具体操作方法能否实现,“通向正义之路”的光荣使命能否完成,还依赖于观念和制度的支持力度。这就进入了社会语用学的范畴。
二、语用学视域中法律推理的主要面向
(一)法律推理是一种交互言语行为
法律推理,不仅要借助语言来进行,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法律言语行为。“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作为‘法律语句’的语句形式表达出来,可以说,语言之外不存在法。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达、记载、解释和发展法。……如果没有语言,法和法律工作者就只能失语。”[9]P71法律规范是一种用语言来表述的“符号集”,法律事实也要通过语言来建构,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之间目光流转形成的法律理由需要表达,法律推理的结论需要公开,这一切都离不开语言。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而且建构着表达本身。有什么样的语言就能表达什么样的内容。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意义的载体,主体对客体的表达,而且是说者行为意图的表达。法律推理是在命题内容的基础上,加上语用力量,并通过语用行为来建立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影响人们的行为。
法律推理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要在交互的言说中完成。法律推理的交互性是其本身的推理特质决定的。伯顿认为,“法律推理的首要特征是,它被用于预知或解决高级社会中大量纠纷的过程”[13]P8。既然法律推理的任务在于要通过语言解决纠纷,那就必然涉及到纠纷解决双方和裁判人。法律推理的语言就要在这三方之间展开,呈现出一种交际性和动态性。借助孙培福教授提出的“变焦推理”理论①,从个体而言,法律推理要在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之间进行“变焦”,从主体间而言,法律推理还要在主体之间进行“变焦”。法律推理并不是在控辩双方各自独立的语言表达之后得出结论的过程,而是在双方的互动、交流、辩驳之中形成结论。控辩双方并不仅仅是被动接受法官的目光在他们之间进行“往返流转”,而且要在主动表达和反驳中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法律推理言语行为的交互性,不仅体现在书面语言形式的起诉书和答辩状上,而且体现在庭审现场的口头语言上;不仅体现在控辩双方之间的对抗式论辩中,而且体现在律师和自己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同向交流中,体现在法官与控辩双方的中立对话中,体现在社会各界对法律推理的评论中。
(二)“说者”与“听者”都是法律推理的主体
近代法治以“职业自治”为基本特征,法律推理也被认为是法官的专属权利。德沃金认为只有法律帝国的王侯——法官才具有解释法律,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德沃金创造了一个听诉判决活动的完美典型,却没有注意到受理上诉的法官席的那个可能最普遍引人注目的制度特征:它的多数性。”[14]P275只有建构多主体视角,才能实现推理的交互性。实际上,“法本身是一种关系,一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具有相互主体性或曰主体间性,适用法的过程不啻是一个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过程,对法的理解即是不同主体自身经验的重述。”[15]P317法律的真正书写者,既不是立法者也不是法官,而是整个社会行动者。法律推理的主体间性,并不否定法官的权威,而是对传统的绝对化了的以独白自语为特征的单一决定模式的扬弃和反省。
法律推理的主体间性体现在“说者”与“听者”的区分性与交互性上。法律推理作为一种交互言语行为,有说必有听,同时,“说者”与“听者”的角色不是静态的、僵化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流动的、可以互换的。如在庭审过程中,言语行为的“听者”与“说者”一直处于一种动态的流转过程。法律推理不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过程,而是一个恰当性的衡量过程。法律推理的每个参与者都是理由和结论的建构者。法官的推理活动不仅要与当事人进行充分的沟通,而且要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和推敲。“现实中,法官的结论并不是在真空中作出的,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充满着预期的环境中。从长远来看,除非能够满足一些底线预期,没有人能够成功地扮演任何社会角色。法官应当回应的预期不仅来自政治和公众,而且还来自其他法律职业群体,即实务届和学术界。没有满足这些预期的法官将失去他的合法性。”[16]P43因此说,法官及所有参与言说的人都是法律推理的主体。
(三)达成共识是法律推理的言说目的
法律推理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和平而公正地解决纠纷。只有通过主体间的言说活动,得出共识性结论才能化解矛盾、定纷止争。然而,法律推理能否达成共识是理论界争论颇多的一个话题。共识论的支持者以哈贝马斯、佩雷尔曼和阿列克西为代表。他们认为法律推理能够达成共识,只有共识性结论才是可接受的,只不过在言谈情境、论证起点、论证步骤和论证规则上做出一定的限制。共识论的反对者们则认为共识论者的限制性条件是形而上学的虚构,是一种乌托邦,法律推理无法达成共识。共识的达成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理想性目标和努力的方向而已,法律论证的效能主要在于排除法官专断,而非达成共识。考夫曼批判道:“‘合意性’几乎成了一个神秘的魔笛,人们以为用这支魔笛便可以把握真理和正义的答案。然而,‘合意性’真是这种答案吗?毫无疑问,它是命题即规范的真实性和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它是……道德和法律判决的最终依据吗?这自然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如此一来,真理发现就会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成了一种强迫人们把合意的恶意也作为合法的东西予以承认的自我行为。”[17]P27-28
然而,反对者只是提出了一些缺点和问题,并不能解构共识论的理论路径。在法律推理中,达成共识的目的,不仅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理想和愿望,而且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如今,在纠纷类型中,不仅民事争议尤其是涉及到合同内容的纠纷非常注重当事人双方的合意与自治,而且在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也体现着双方的共识。在纠纷的解决方式中,调解结案的纠纷越来越多,即使在以判决结案的诉讼中,国家公权力只是提供了一种制度和程序的架构,当事人之间的交涉及由此产生的共识已成为诉讼的核心。棚濑孝雄认为“法官在作出判决过程中应该不断地通过解释在结论的衡平性与法律适用的严肃性之间进行反馈,尽可能地获得符合实际并对双方当事者都有说服力的解决已成为一般认识。”[18]P131与此同时,只有强调控辩双方之间达成谅解和共识,才能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减少法官专断的空间。鉴于种种社会现实条件的限制,我们可以把共识的标准降低,范围扩大,将以往仅限于积极认可与支持的共识,扩大到消极的认同和接受。
(四)合作原则是法律推理的言说规则
为了达成基本共识而进行的法律推理言说,不仅要有理有据,而且要求依特定的方式和规则“说”出来。“会话合作原则”是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为解决形式逻辑(形式主义)和自然语言逻辑(非形式主义)之间的争论问题而提出来的。[19]P279合作原则认为,会话参与者只有彼此合作,遵守合作原则,向彼此可接受的方向前进,交际才能进行下去。合作原则包括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法律推理是话语主体为了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而进行的言说,有明确的目的性,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合作是题中之义。法律推理的话题明确而集中,比起日常话语话题的多变性,有理想性的一面。法律推理在法定的程序内进行,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对法律推理的具体言说内容和方式有着严格的限制。因此,会话的合作原则能够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法律推理也需要合作原则的支持。法律推理话语与日常会话不同,它既可以是直接言词,也可以是书面材料,并且有着明确的利益指向性和制度化特征。
首先,量的准则。法律推理的每一个言说者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既要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又不能重复冗赘。其次,质的准则:说服力准则。法律推理言说中的“质”不能用真假值来衡量,而要看话语对言说目的的支持力度,因此说,质的准则应该被修改为说服力准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言说中,更能支持结论的言说有更强的说服力。再次,关联准则。在法律推理中,关联准则指语言要与两方面相关,一是推理的话题,即法律推理所针对的具体案件纠纷;二是言说者的观点和主张。最后,方式准则。在法律推理中,运用语言要明确具体,避免晦涩模糊;要条理清楚,避免模棱两可和逻辑错误。正如大法官霍尔默斯所说“如果要向世人发一个警告,这个警告要用世人能懂的语言来表达才是公正的。”[20]P102
三、改善语境是发展法律推理的必由之路
(一)语境通过语言选择影响法律推理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法律方法,它是由主体在特定的主客观环境中运用的。法律推理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它要实现什么目的,以什么方式呈现,最终还取决于主体及其主客观环境。语境正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在主体的认知系统中综合并内化的产物。它是依据主客观的环境,被主观地建构起来的动态认知系统。正是因为主观建构性,语境在法律推理中呈现为一种逻辑变项,与此同时,“语境做为一种具有本体论特征的实在,为一切意向、态度和行为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成为知识结构和理解模式的一个不可还原的基础。”[21]法律推理的主体间性能否实现,合理共识能否达成,言说规则能否被遵守都与语境密切相关。
例1,在某庭审的质证过程中,辩护人一次插话后:
审判长:辩护人说话请举手。
辩:公诉人刚才发言也没有举手示意。请法官一碗水端平。
审判长:请辩护人注意你的言辞。
在同一审判过程的后一次开庭中:
审判长:继续开庭。……辩护方有什么意见?
辩:形式上来说,……
从2016年6月——2017年6月在我院急诊科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抽取8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平均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42人,对照组43人。其中,对照组的患者年龄在25岁-37岁,平均年龄为(29.34±3.74)岁,平均不孕不育时间为(64.31±6.34)月,实验组的患者年龄从23岁38岁不等,平均年龄为(30.64±3.64),平均不孕不育时间为(66.31±6.94)月。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方面均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公诉人:在此打断辩护人。
辩:你没有举手。审判长,……
审判长:公诉人发言。
公诉人:之所以有必要打断,原因在于该份举报材料不能成为案件的证据。
辩:我反对。我刚刚阐述理由还没说完。请法庭一碗水端平。
在上述的法庭对话中,审判长面对同一个打断问题,对辩护人说“说话请举手”,而对公诉人则说“公诉人发言”。这表面上只是一个言辞问题,实际上则透露了法官在庭审中并没有以中间人自居的法律问题,其背后是深层次的司法制度。
正是因为特定的语境存在,法律推理的主体间性、共识性和言语规则才形同虚设,法律推理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出现了裂缝。可喜的是“语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概念。”[23]P40语境“不再是一个被适应的对象,它时时处在交际主体的不断选取中,它完全可以被创造。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并非一味适应语境,更多的时候是打破固有语境的束缚,创造语境,创造有利于交际效果的语境。”[24]为了发展法律推理,发挥其在法律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实现“通向正义之路”的美好愿景,改善语境势在必行。
(二)改善语境的主要着力点
一般来讲,语境建构的基础分为客观环境和主观认知。前者涉及到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后者主要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认知素质。
在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社会政策和伦理道德等已经不能直接作用于具体的法律推理,但它们可以通过为法律理由提供正当化基础而发挥作用。伯顿认为“法律含有目的:它们贯彻良好的原则和政策,同时又被这些原则和政策证明是正当的。”;“原则和政策没有建立法律的类别,确定法律的后果。但它们为规则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把案件归于规则所定的法律类别中的法律理由提供了正当理由”。[13]P116-117原则和政策等渗透到主体的认知语境中,影响到法律推理语言的选择。“如果说法律话语的机构化是个统一体的话,那么这个统一体不是基于独立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基础的专业实践的典型统一体。”[25]P172棚濑孝雄认为,审判只是解决具体个别的纠纷,政治则制定一般规范。法院的判决就是一个个具体的“政治性决定”。法律推理中,公权力虽然不能明目张胆地使用暴力,但却可以通过垄断话语权,将权力倾注在对话语的控制中。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司法与行政不分,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不分,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长同时也是该地的审判治狱首长。这种思维方式和制度安排以惯性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政党和行政力量对法律推理的直接干预时有发生,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仍然在发挥作用,这严重制约了法律推理的发展,是改善语境的重点所在。
客观环境通过主体的认知建构才能成为认知语境的一部分,法律推理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例1的庭审话语中,司法制度对法律推理的影响,体现为法官对控辩双方的不同态度,以至于辩护人两次请求“一碗水端平”。法官是推理过程的推动者,是推理的权威主体。“在现实中,中间人(即法官)并不是一个毫无独立意识的传话人,他通过‘重新表述’他所传递的信息来施加影响。他能够在不经意间提供许多代表自己意见的建议。而且通过对一方描述另一方当时的灵活性与不灵活性,他能够加强或者减弱一方或者另一方当时人谈判地位。”[26]P5法官的主观认知能力和语境建构能力在推理主体中具有典型性。法官对法律渊源的掌握程度,运用法律方法的熟练程度,以及法官的性格、气质、信仰、价值追求等都会影响他对客观环境的理解,对法律理由的建构。法律推理不是一台“自动售货机”,需要进行多维的价值考量和利益权衡。在外在压力、内在素质和法律正义之间把握平衡,维护法律推理的发展空间;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往返流转,协调各方利益,得出兼具合法性与合法律性的结论,是法律推理能力的体现。目前,中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业务水平偏低,影响了法律推理能力的提升。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够完善,错案追究中的“错案”边界不清,影响了法官的独立性和积极性。这些都制约着法律推理的发展,是改善语境的重点之一。
注释:
① 孙教授的“变焦推理”理论认为,在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往返流转这种独特的思维形式,犹如照相机的聚焦器不断地远近推拉。法律推理的结论(C)存在于法律规范(A)和案件事实(B)之间,在A与B的互动中才能获得C。参见孙培福、黄春燕:《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齐鲁学刊》2012年第一期。
[1] Morris,C.(1938).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Foundations of the unity of science: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I, 2.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6.
[2] Jef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何自然导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 Yule,G. (1996).Pragma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Horn,L.R.&G.Ward. (2004).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Boston: Blackwell.
[5] 索振羽编著.语用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 Hencher M (1980). Speech acts and the law. In Shuy R & Shnukal A (eds.) Language use and the uses of language. Georgetow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7] Mey, J. (2009).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ragmatics. Elsevier.
[8] [荷]伊芙琳·T·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 [德]魏德士.法理学[M].丁春晓,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0] 王涌.被倒置的和被省略的法律推理[N].法制日报.2000-02-27(03).
[11] 吴玉章.法治的层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2] [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M].姜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3] [美]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M].张志铭,解兴权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0.
[14] 转引自[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5] 郑永流.自然法,一个绝代佳人[A].法哲学与社会学论丛(第二卷)[C].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6] George.C.Christie. (2000).The Notion of an Ideal Audience in Legal Argument.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7] [德]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M].米健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8] [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9] 廖美珍.问答:法庭话语互动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2.
[20] 廖美珍.语用学和法学——合作原则在立法交际中的应用[A].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5辑) [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1] 殷杰.语境主义世界观的特征[J].哲学研究.2006,5.
[22] 周礼全主编.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3] Mey,J.L.2001.Pragmatics:An Introduction[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Second edition.
[24] 胡霞.认知语境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25] [美]古德里奇.法律话语[M].赵洪芳,毛凤凡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6] [美]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M].张生,李彤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TheLegalReasoninginPragmaticsHorizon
QiJian-ying
(Law Schoo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Hubei 430074)
Pragmatics is a new perspective from microcosmic and language level to analyze and grasp legal reasoning. In the field of pragmatics, legal reasoning is a mutual discourse behavior. Among it, the Speaker and the Listener are all subjects,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ve role guarantee the interoperability; Reasonable consensus is the purpose, which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speech act; Cooperation principle is the language rule, which decides the validity of the language itself. Context through language choose to influence legal reasoning. To improve the context is the important way of legal reasoning development.
pragmatics; speech act; legal reasoning; context
1002—6274(2012)06—064—06
DF0-051
A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律推理研究———语用学与语用逻辑的视角》(07BZX046)的阶段性成果。
齐建英(1980-),女,河南叶县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法学方法论、法律逻辑。
(责任编辑:唐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