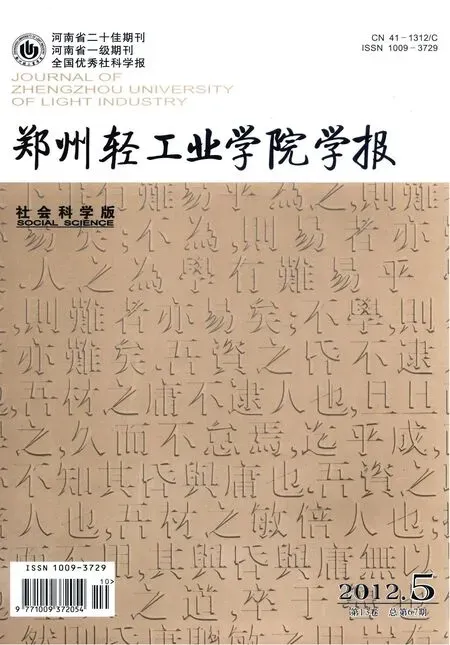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新范式——从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到巴迪乌
吕清平
(杭州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基础部,浙江 杭州 310036)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系列理论争论的焦点,传统学界关于自然与历史二元分立的辩证唯物主义、青年卢卡奇贬低自然而抬高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施密特关于自然与历史相互中介的辩证唯物主义、萨特贬低结构而抬高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贬低历史而抬高结构的辩证唯物主义等,这些论争使马克思主义在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一团迷雾之中。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1937—)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此论题上的新视野。当然,在法国思想史上,对唯物主义概念的变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巴迪乌之前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此亦各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比较突出的人物是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本文将以考察其历史演变为基础,通过逻辑视角的转换来比较巴迪乌与萨特存在主义、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的差异,以揭示出巴迪乌在唯物主义概念上的开创性贡献。
一、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在自然与历史关系范式上的方法论之争
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之“历史与辩证法”一节中展开的与萨特的精神斗争,意味着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方法论的思想较量。此较量以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大获全胜告终,表现在文本上就是: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在出版第一卷之后,第二卷胎死腹中,而《野性的思维》在当时盛极一时。此较量的重要意义是:在揭示萨特存在主义之先验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局限性的同时,将法国结构人类学的方法论特质概括为“野性的思维”。
在方法论上,列维-斯特劳斯确实击中了萨特人学辩证法的要害,但在解决方案上仍然陷于失败。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在方法论上的功绩在于,他在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之先,尝试性地将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结合起来,以便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的理论诉求。在具体操作上,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的融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门学科掺入自己”,而此掺入“应该包括在具体领域的古典决定论背后与整体之间的辩证联系,或者在我们论述的过程中,它的辩证性质早已被承认的情况下,揭示出部分的辩证性质是更深层的总体运动的表象”[1](P150)。此方法论特质表明,既要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又不能使之堕落为科学上的经验主义,只有将“辩证法确立为人类学的普遍方法和普遍法则”[1](P150)。就是说,在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只有将先验一元论的辩证法置于科学经验主义的优先地位,才能防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滑向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的批判。应当说,列斐伏尔是最具人本学总体性理论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但即使这样,他的总体原则也受到萨特的批判。批判的原因是,列斐伏尔“拒绝始终如一地采取总体观的态度”[1](P149)。萨特想说的是,作为先验方法的辩证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对它优先地位的挑战都会歪曲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是,在坚持先验一元论的总体辩证法的同时,是否真的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呢?
列维-斯特劳斯持否定态度。在肯定萨特将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融合的基础上,他指出萨特在此问题上存在自相矛盾性:“萨特在他所持的两种犹豫不定的假设中,赋予辩证理性一种独特的实在性,它独立于有时作为其对立面、有时又作为其补充者的分析理性而存在。”[2](P280)导致此矛盾出现的关键是:辩证理性作为统一原则或整体原则,当它被赋予一种实在性时就具有超验性意味。如果将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看做是相互对立的,那么会导致现实具体化要求的不可能性,并导致科学知识怀疑论;如果将两者看做是相互补充的,那么萨特赋予辩证理性的优势地位就没有任何根据——只要两者在通向真理的路上具有同样的效果,则两者就没有优劣之分。所以,实在化辩证理性的理论后果,一方面是“让纯粹的系列性逃逸了”,另一方面是“排除了可使这类系统臻于完善的图式化的可能性”。[2](P279)辩证理性未能成功地实现与分析理性的融合,萨特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愿望破产了。列维-斯特劳斯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出路,在他看来,只有自己成功实现了分析理性视域内“纯粹的系列性”与辩证理性之统一原则或整体原则融合,从而真正实现了使科学具体化的诉求。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颠覆辩证理性的优势地位,以便始终将其看做“构成性的”,即辩证理性“是一座由分析理性假设于深堑之上的、永远在延伸和改良之中的桥梁;它不可能瞥见对岸,但确悉岸在哪里,即使岸边会不断地远退”[2](P280)。可见,与萨特将分析理性看成是静态性不同,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理性变成一种能超越自身的动态之物,而辩证理性就是分析理性不断超越自身的努力过程。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分析理性就是辩证理性。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并未真正完成使科学具体化的任务,因为他对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的融合并不成功:一方面将辩证理性看做分析理性之内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将它视为附加于分析理性的东西。“附加”说明的是两者之间的外在关系,怎么又能说它内在于分析理性呢?列维-斯特劳斯的描述显然模棱两可。总体而言,列维-斯特劳斯已经取消了辩证理性,或者至少已经使分析理性处于优势地位。
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方法上的异质性导致两个方面的差异。首先,萨特使先验一元论的辩证理性处于优势地位,导致他在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承袭康德、胡塞尔以来将哲学作为其他科学的女王的做法,这使哲学失去了具体化的可能性。从基调上看,萨特的哲学是诗化哲学,注重哲学方案的政治力量。问题是,当哲学能够替代政治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就意味着政治化的哲学要承担一切由政治带来的后果。海德格尔在法国思想界的沉浮正说明了这一点。相反,列维-斯特劳斯取消了辩证理性或至少使分析理性取得了相对于辩证理性的优势地位,致使他在实现科学的具体化诉求时,走上了反哲学的道路。所以,列维-斯特劳斯的思考方法并未捍卫哲学存在的价值,相反,取消了哲学的价值。其理论后果是:诗在哲学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因此成为大陆哲学唯一的表达方式。当这种思考方式走到终点时,它就像分析哲学一样以一种先辈的身份融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洪流。其次,由于取消辩证理性,列维-斯特劳斯以唯美主义的方式“把人类的事物分解为非人类的事物”,因而“把人当做蚂蚁来研究”。[2](P281)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结构主义者已经将人由社会归于自然,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分。实际上,这是卢梭和科耶夫理论以一种结构主义的方式在当代的复活。相反,由于使辩证理性处于优势地位,萨特以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将非人类事物当成人类的事物来研究,即“把蚂蚁当成人来研究”。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主义上的对立,在思路上以一种逆向的方式重蹈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与人本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其对立的现实版本正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
二、历史唯物主义与结构唯物主义: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历史概念之争
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在方法论上的异质性导致他们持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列维-斯特劳斯的无主体历史观(或说自然观)和萨特的个人主体历史观(或说历史观)。在历史观问题上,《辩证理性批判》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结构主义之先使自然与历史统一,从而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实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结合,以阻止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法问题上滑向唯心主义。萨特认为,“我们必须追踪从物质产生生命、从生命的原始形态式中产生人类、从最初的人类群体中产生社会历史的运动”。这先验地表明,“辩证法是自然的根本规律”。[1](P160)从青年卢卡奇一直到《辩证理性批判》之前的萨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辩证法问题上始终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因而总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特别令人尴尬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政治领域发挥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号召功能,而它却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理论。实际上,作为前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后来在现实实践中蜕变为唯意志主义,与萨特存在主义的套路不谋而合。以此理论框架为基础,萨特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中公开为斯大林主义辩护。但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主义在共产主义者心中的神圣形象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当斯大林唯意志主义在法国不再具有有效性的时候,萨特认为,挽救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就是,以作为自然的惰性物质对人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作用进行物质性制约,以便实现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化。但是,列维-斯特劳斯对萨特的历史谴责表明,萨特挽救历史唯物主义的计划是失败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萨特失败的关键是他赋予了历史优于一切的价值。当在共时性和历时性关系问题上赋予后者可理解性的特殊权威时,萨特式的自然辩证法,“实际上指的是物质事实的整体性——过去、现在、未来——或者用另一种表述,它所指的是时间性的整体化”[1](P161-162)。列维 - 斯特劳斯想说的是,作为所有有限者人类个体汇聚而成的历史虽然与每个有限个体的内在性关联,但要赋予个体理解总体化历史的特权,则显然是将历史变成了一个神话。在这种情形下,个人的发展俨然变成历史的连续性,而关于历史的认识俨然变成对个体内在感觉存在的证实。所以,萨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最终还是唯心主义。在政治上,萨特唯我论的人类解放理念,无非是西方种族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存在主义版本。列维-斯特劳斯提供了另一种出路。在他看来,既然萨特走向唯心主义的原因在于他将历史事实认定为首先由个人构成和选择的东西,那么走出困境的途径只有一个,即将历史事实认定为“诸历史领域组成的非连续体的集合,其中每一领域都是由一种特殊频率和由一在前与在后的特殊的编码来确定的”[2](P297)。问题是,虽然列维-斯特劳斯消除了萨特历史概念所具有的神话性,但是他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了。
实际上,萨特时间性维度具有的合理性是其作为历史事实的统一原则的身份;萨特错误的地方在于,他将此统一原则优先地赋予个体内在性的时间。当列维-斯特劳斯彻底驱逐这种优先地位时,他也彻底清除了历史事实的统一原则,从而使历史成为“非连续体的集合”。当然,这已经不是历史,而是自然了。所以,当列维-斯特劳斯声称自己已经对历时性和共时性平等看待时,他口惠而实不至,因为他实际上已经赋予共时性以优先地位。列维-斯特劳斯没有意识到的是,“共时性”机能恰恰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它幻想性地使资本自我运动的圆圈封闭起来。因此,如果说萨特的自然是人化或哲学化的自然,而其历史是内在时间性的历史,那么列维-斯特劳斯的自然就是科学化的自然,而其历史就是自然化的历史。我们认为,无论是萨特还是列维-斯特劳斯,他们都将自然和历史看做对称的东西,即仍然处于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同构性的圈套中。与此不同,巴迪乌将自然和历史看做并非对称的东西,认为两者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通过批判萨特的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者已经走出了被分解者与分解者高低层次的区分。就是说,尽管作为生命的“人类的事物”可分解为作为惰性物质的“非人类的事物”,但它们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结构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已经为后斯大林政治提供了出路,即政治上以反官僚主义的平等原则为核心。当然,如果站在巴迪乌哲学的视域,那么这种平等原则显然缺乏激进性。正因为如此,巴迪乌的《元政治学》一书在肯定阿尔都塞为走出斯大林主义政治做出的理论探索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失败之处。[3]实际上,如果平等原则没有激进政治做保证,那么平等原则的实现只能以消极等待的方式进行。所以,结构主义者适时地提出了平等原则,但牺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激进性内涵。在巴迪乌心中,德勒兹是在平等政治理念上取得成就最大的哲学家,但是,他在政治上也略显保守。在《存在与事件》一书中,巴迪乌力图在政治上实现平等原则与激进内涵的结合。结构主义者在政治上取得成就的同时,却在哲学上付出了代价,即在走出萨特的历史主义的同时,彻底否定了作为合理性的统一原则。当然,结构主义者借助于语言学结构来阐释此原则,但此结构相对于分解者而言完全是超验性的,不仅如此,此结构也是封闭性的。德勒兹为了摆脱结构主义的这一困境,将此结构充当的统一原则替换为虚拟性的统一原则。此替换的功绩在于,它使德勒兹能够返回形而上学,并且走出了结构主义者结构概念的封闭性。问题是,从表面上看,虚拟性统一原则已经内化为分解者的组成部分,但在巴迪乌看来,它仍然是超验的。其理论结果是,德勒兹最终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区分出高低等级。
三、巴迪乌自然与历史关系新范式:呈现与再现视域中的唯物主义
要摆脱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上述理论困境,统一原则必须满足下述要求:“内在的相互联系的元素所构成的统一体,是全然具有同一性的;所不同的是联系类型。而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的,意味着整体就是各个不同部分的连贯。整体不是什么‘进一步’的类型,可以添加在不同类型的元素所组成的开放系列之上。相反,其开放性(或者说系列)明显具有的不可中断特质,并不排除统一性或整体性。”[4](P8)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乌的“自然倍数的本体论规划”满足上述要求。简单说来,此规划就是以公理性集合理论形式化常态性观念,即“过渡性集合”。因此,实现上述的规定任务,必须将统一原则纳入作为自然情境定义的过渡性集合思考,以便实现呈现与再现之间的最大平衡——使术语同术语的术语都是常态性的。
在呈现与再现的关系[5]中,再现对呈现的过剩表明,统一原则不可能排斥空集,即不可能排斥事件;而在过渡性集合视域中,呈现可转化为再现表明,在集合之元素不可能排斥统一原则的同时,统一原则离不开元素,用罗森的话说就是“内在的相互联系的元素所构成的统一体,是全然具有同一性的”[4](P8)。在巴迪乌看来,过渡性集合就是属于某一集合的元素,同时也是此集合的子集(或部分),就是说,被两次计数为一的此元素“一次作为元素,另一次作为子集;一次通过呈现,另一次通过状态”[6](P131)。从术语承袭视角看,过渡性集合中“属于”与“包含”之间的关系是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之间关系的集合论转化形式。当然,此转化并非简单地对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阐述的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复制,因为经过巴迪乌集合论式的转化,后者中隐含的困境获得了解决。无论是萨特将优先地位赋予作为统一原则的辩证理性,从而出现列维-斯特劳斯揭示出的困境,还是列维-斯特劳斯将优先地位赋予分析理性,从而出现“反哲学”倾向和唯美主义倾向的困境,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只在元素与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之间作简单区分。当萨特赋予后者优先地位时,由于元素与统一原则之间没有很好地融合起来,以至于最终使统一原则变成没有内容(或没有内在结构)的东西,这实际上使统一原则变得与绝对虚无等同;而当列维-斯特劳斯赋予分析理性优先地位时,元素与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也不能很好地融合,以至于最终使元素本身变成比较零散的东西,使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变成了元素在数量上的总和,而不是形式的统一。当巴迪乌在“属于”与“包含”之间作出区分时,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虽然与元素区分开来,但并不会出现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将优势地位赋予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或元素中的任何一方,从而不可能出现将统一原则认同为没有任何内容的形式统一或认同为元素的总和的情况。因为巴迪乌的区分实际上使统一原则成为具有元素内容的形式统一,这既使得统一原则与绝对虚无区分开来,从而既避免了萨特哲学的虚无主义倾向,又避免了科学经验主义倾向。这就彻底解决了萨特存在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出现的困境。换句话说,巴迪乌的统一原则是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统一原则的恰当融合。当然,由于在过渡性集合中,所有属于整体的元素都能作为整体的部分(或再现,或子集),所以,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并不是简单地附加在各种不同类型元素上的东西,而是各种不同元素所属类型(或部分)的统一。巴迪乌以此方式既保留了统一原则,又没有贬低数的地位。两者的不可分离性说明“‘自然’和‘数’是可互相替换的”[6](P140)。这是他的自然概念区分于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关键点。
方法论的彻底变革表明,巴迪乌以常态性观念为基础的自然概念完全异质于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自然概念。无论是萨特使自然历史化的自然历史概念,还是列维-斯特劳斯使历史自然化的自然历史概念,它们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历史与自然的对称性主张导致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的同构性。从表面上看,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都实现了自然与历史的平等,但这种平等以一方吞噬另一方为代价。所以,在哲学上,无论是萨特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列维-斯特劳斯自称的“先验唯物主义”,最终都是一种唯心主义。在政治上,与结构主义同源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为当一切被化归为自然时,人最终变成了动物;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总是与悲观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历史与自然永远在相互转化,因而人永远受困于自然。巴迪乌认为,要走出这种理论困境,就必须实现历史与自然平等,其最佳途径是使它们成为非对称的东西,以便真正实现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化。“如果一个人在此承认,成为历史事件场所是必然的,那么就能作出如下观察:历史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历史化。此处有一个明显的禁止(在纯粹倍数的本体论之思框架外)自然和历史之间任何统一的不对称性。”[6](P176)与萨特自然能被历史化和历史能被自然化不同,巴迪乌通过主张“历史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历史化”化解了萨特存在主义中内含的悲观主义倾向。
问题是,承认“历史能被自然化,但自然不能被历史化”是否表明巴迪乌陷入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困境,是否在此主张历史终结论呢?通过仔细考察我们发现,完全不是如此。在《黑格尔导读》一书中,科耶夫对历史终结论有两种解释:第1版注释将历史终结解释为与“战争和流血革命的消失”和“哲学的消失”的理论后果关联;第2版注释将历史终结解释为与“人回到动物的状态”的理论后果关联。[7]但在巴迪乌看来,历史被自然化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历史终结论。巴迪乌从两个方面入手破解历史终结论之迷:一方面是使自然概念视域内的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纳入无限开放性,以便消解结构主义者结构系统的有限封闭性;另一方面使以事件、真理和主体为构架的历史视域不可能消失。由于“包含”对“属于”的过剩,所以,空集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因而处于空集边缘的事件、真理和主体也就不可能被消除。当然,之所以能引入以事件、真理和主体为构架的历史框架,其原因是:作为整体的统一原则不能排斥无限开放性,否则事件是不可能出现的。与萨特认识论化的主体相比,巴迪乌虽然引入了主体,但没有走向唯心论,因为处于空集边缘的事件、主体首先是本体论的,而不是认识论性质的。所以,巴迪乌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也正因为如此,巴迪乌消解了萨特将优先地位赋予历时性的做法。与列维-斯特劳斯系统结构的有限封闭导致“预设”自身(其典型例子是资本自我封闭地循环)从而最终走向唯心主义相比,巴迪乌在空集处对主体的引入已经消解了结构主义者将共时性优先于历时性的做法。既然如此,历史被自然化就不会成为历史终结论的翻版,因为历史被自然化后并不会使哲学终结,也不会使人与动物等同。恰恰相反,巴迪乌的历史是作为整体统一原则外部的历史前提假设,它排除统一原则封闭的可能性。在此点上,齐泽克认为,通过在“辩证的说明”和“历史描述”引入空集,马克思在逻辑与历史问题上已经将两者非对称化,这只不过是巴迪乌化的马克思。[8]
当然,在巴迪乌那里,自然与历史关系被替换为序数与基数的关系。自然与数的可互换性使巴迪乌可能将自然倍数的本体论规划转变为序数集。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理解作为统一原则的属于关系对序数之间前后相继所起的统一功能。前面的论述表明,此功能既彻底驱逐了结构主义将统一原则等同为总和的可能性,也彻底驱逐了存在主义者将统一原则等同为内在历史性时间的可能性。通过“属于”关系对序数的链接,序数集就变成“从空集的名称出发,继续下去,直到不包含自己”的“属于”链条。[6](P139)这意味着,在“属于”秩序内,序数集不仅不能包括空集本身而只能包括空集的名称,而且不能包括自己本身而只能包括它的能指名称。所以“序数集是名称所是东西的数”[6](P139)。由此,序数与序数的关系不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仅仅是非连续性的点与点之间的关系,而是连续性的,即能够用“属于”关系统一起来的东西。我们在此要注意的是,巴迪乌以“属于”关系所起的统一作用完全不同于德勒兹以生命之力所起的统一作用,因为前者是数学性的,而后者是历史主义的。问题是,能否通过“属于”关系将所有序数总括在一个序数集中呢?从巴迪乌对序数集的界定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序数集的原初存在之点不是空集本身,而是空集的名称,而它自己不能属于自己的属性也表明,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自然呈现本体论规划的同质性在名称—数链的无限开放性中实现,以至于每个都由所有在其之前的数组合而成”[6](P141)。从表面看,巴迪乌的序数集似乎遇到了芝诺悖论,即序数集似乎是潜无限集合。芝诺悖论中龟兔赛跑悖论表明,如果将兔子到达的目标无限地分割下去,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此悖论实际上是潜无限概念遇到的悖论。以亚里士多德的整数集合概念为例,他认为,所有整数的集合“不能作为固定的整体存在”,而只能是“潜在无限的”。[9]以此潜无限为基础,芝诺悖论是不可能解决的。但在巴迪乌看来,序数集不是潜无限集合,恰恰相反,它是实无限集合。从术语对应上看,德勒兹的生命之一对应于潜无限集合,而巴迪乌的自然概念对应于实无限集合概念。所以,巴迪乌所讲的开放性不是德勒兹式的潜无限开放性,而是康托尔式的实无限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要通过本体论决断引发,它是历史前提引入的地方。在数学集合中,它是基数领域的问题。
总之,从萨特的历史唯物主义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先验唯物主义,最终到巴迪乌的新辩证唯物主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时代的理论诉求,力求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精神。萨特式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尽管反映了斯大林主义之后约束主体意志的诉求,但它在人的解放诉求上始终与流血暴力关联在一起。这种马克思主义激进有余,而建设不足。列维-斯特劳斯的先验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反映了斯大林主义之后在人的解放问题上追求平等原则的愿望。这种马克思主义缺少激进性。继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之后,凭借《存在与事件》的影响力,巴迪乌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挽救哲学和左翼政治而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在政治上,在承袭结构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结构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事件、主体使之激进化,并以同一性为基础的平等替换以差异为基础的平等,以便重新激活革命政治和解放政治;在哲学上,通过重新引入统一原则,在破解后现代迷宫的基础上,又不单纯复古古典理性哲学,以便在数学公理化集合论视域内返回理性哲学。在这两个贡献中,政治是落脚点,哲学是实现此落脚点的途径。与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相比,巴迪乌的马克思主义将激进性、平等原则和建设性融为一体。巴迪乌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贡献,是因为他继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后在自然与历史关系问题上实现了范式转换,即以集合理论中的序数与基数之间的关系替换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了他的新辩证唯物主义。
[1][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2][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Badiou Alain.Metapolitics[M].New York:Verso,2005:59.
[4][美]斯坦利·罗森.诗与哲学之争[M].张辉试,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5]Badiou Alain.Theoretical Writings[M].New York:Continuum,2004:76.
[6]Badiou Alain.Being and Event[M].New York:Continuum,2007.
[7][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17-518.
[8][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M].郭英剑,高稳,冯元元,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58.
[9][美]莫里斯·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4册)[M].张理京,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