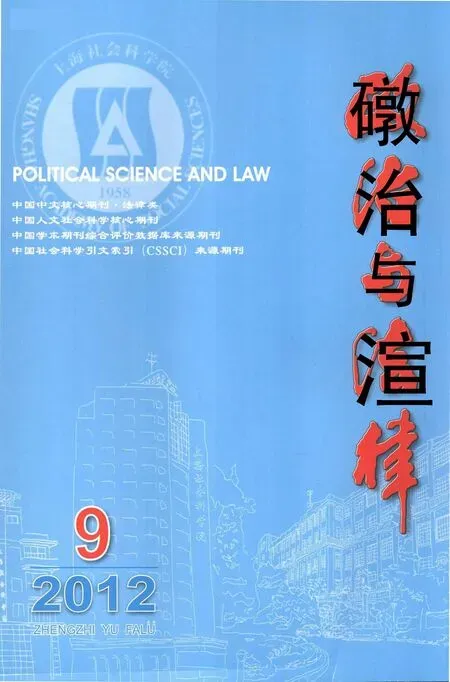港澳基本法中有关授权的概念辨析
王 禹
一、港澳基本法有关授权的规定
香港基本法正文共160条,有13个条文出现了中央“授权”或“授予权力”的表述,澳门基本法正文共145条,有12个条文出现了类似的表述。1这些条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在其第1条规定香港和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继而在其第2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的“授权”。其第13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
第二,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在其条文中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政府和法院处理有关事务或行使权力。如以澳门基本法为例,第50条第13项规定行政长官处理中央“授权”的对外事务和其它事务,第64条第3项规定澳门政府办理本法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授权”的对外事务,第94条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协助和“授权”下,澳门可与外国就司法互助关系作出适当安排,第116条规定澳门经中央人民政府“授权”可进行船舶登记,第117条规定澳门政府经中央人民政府“具体授权”可自行制定民用航空的各项管理制度,第139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政府依照法律给持有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中国公民签发中国澳门特区护照,给其它合法居留者签发其它旅行证件,第143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别行政区的法院有权解释基本法自治范围内条款。2
第三,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有些条文虽然没有出现“授权”的提法,如香港和澳门应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可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名义参与国际社会,签署国际协议,法院可以解释基本法除自治范围外的条款,等等,3然而,这些规定都是以中央的授权为前提,建立在授权与被授权的法律基础上,属于默示授权。
第四,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规定中央还可以“授予”香港和澳门以其它权力。如澳门基本法第20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它权力。”
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反复强调了授权。如果对比我国内地的法律体系,我国宪法并没有出现“中央授予地方权力”或者“中央授权地方”的明确提法,我国的《地方组织法》4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很少出现这样明确的表述。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却多次出现了“授权”的字眼和表述。这是因为我国通过和平谈判,采用“一国两制”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在香港和澳门建立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时,首先就要回答高度自治权的来源问题。两部基本法规定的“授权”就是这个问题的简明答案。
然而,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里多处出现的授权是否具有同一个内涵?其采取的形式又有什么不同?这些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理解的。这里尤其有三个最核心的问题,迫切需要予以回答:第一,中央将“高度自治”的权力授予香港和澳门以后,能不能重新收回,不再实行“高度自治”?第二,中央将权力授予香港和澳门后,自己能不能行使已经授出的权力?第三,中央对于其已经授出的权力,能不能行使监督的权力?
二、授权的词源
“授”是指“给予”和“给付”的意思,《国语》曰:“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无逆命矣。”5“权”在我国当代汉语中,既可指权力(power),也可指权利(right),因此,授权在我国当代法律体系里,既可指权力的授予,也可指权利的授予。后一种意义上的授权,主要是指民法意义上的委托授权。这种授权是指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的两个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本文并不研究此种授权,除非特别指出,本文所指的授权,都是指权力的授予。
香港基本法英文本主要使用了authorize、givetheauthorityto、authorization等词来翻译“授权”,唯有在翻译第20条特别行政区还可以享有中央“授予的其它权力”时,使用了grant。Authorize主要是权力和权威(authority)的词源变化所致,是指给予权力,使其成为权力当局或权力主体的意思。Grant在英文中主要是指赋予某些与土地有关的权益,同时也适用于国王创设的权利。6从香港基本法中文本的有关条款来看,第20条里所指的授予其它职权,没有明确指出与土地有关权益的意思,与其它地方的授权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这里应当将其理解为主要是翻译问题,“授予”翻译为GRANT,“授权”翻译为AUTHORISED。
澳门基本法葡文本将授权主要译为autorização,然而,葡萄牙法律体系里的授权,在民法范围内,表述为“Procuração”,其行政法上的授权则为Delegaçãodepoderes,其中行政法上的授权Delegaçãodepoderes,是指决定权由多个机关之间或由该等机关与行政人员分享,或由机关与其直接下级、助理或代任人分享。这种授权被认为是行政分治的一种手段。7这与澳门基本法第2条里所指的授权是不同的。
我国法律体系里所使用的“授权”本身就包含着多种含义,不仅是不同法律部门所使用的授权内涵本身并不一致,而且,即使是同一法律部门所使用的授权,其概念也是多义的。譬如,我国行政法学领域所使用的“授权”,至少存在着两种含义:一种就是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概念,这里的“授权”是指法律与法规对行政权力的设定,另一种是其它有关法律和法规所使用的“授权”,是指行政机关将自己的行政权力“授权”其它机关行使。8这两个授权的内涵是不同的。第一个授权是指法律与法规直接赋予有关组织拥有和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力,第二个授权是指已经由法律与法规赋予权力的行政机关再次通过自己的行为把权力授予其它机关来行使。一个是“第一次授权”,另一个是“第二次授权”,而且授权主体与被授权主体都是不同的。
另一个与授权经常一起使用的概念是“委托”。我国在民法领域里经常将这两个概念合并使用,如“授权委托书”和“委托授权”。这是指民法上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作出了授权的意思表示,双方就成为委托人(被代理人)和受托人(代理人),授权的法律效果随之产生。这里授予的是一种权利,而非本文所讨论的权力。而在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却刻意区分了“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行政委托是指行政机关委托行政机关系统以外的社会组织行使某种行政职能,办理某种行政事务,与上面所指的授权在行政诉讼法上具有不同后果:“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9然而,行政委托其本身也是一种权力的授出与接受,这种含混使用“授权“概念的情况增加了行政法研究的难度。10
这些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授权”概念,不可避免地也反映在这两部基本法里。
三、不同意义上使用的授权概念
授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并非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所独有。我们不仅在私法意义上广泛使用授权的概念,而且还在政治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领域广泛使用“授权”:既有建立在人民主权宪法原则基础上的人民对政府的授权,也有自魏玛宪法以来被当代宪法学广泛运用的授权立法和委托立法,还有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授权,等等;既有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也有国家机构内部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既有上下级之间的授权,也有行政机关与其它社会组织的授权。
授权的概念广泛存在于法律体系中:只要将自己的权力委托给其它机构行使,都是授权。这里仅对具有公法意义而且又在不同语境下使用的授权概念作一个简单梳理。
(一)君权神授与人民主权理论
如果我们追问统治我们普罗大众的国家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其权力运行的最终依据在哪里,就必须回答国家的权力来源问题。对此,历史上首先出现的是君权神授理论。这种授权理论认为君主的权力是由上天授权而形成的,是在上天授权的基础上行使的。譬如,中国古代的君主们自称“天子”,秦始皇的玉玺上就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皇帝圣旨前面冠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是指他们认定自己的权力起源于天,是由上天授权他们统治天下的。11
这是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授权,其目的是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解决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问题。近代宪法产生以后,这种授权理论就被人民主权理论取代了。12人民主权理论的核心是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所以,政府不得行使人民未明确授予的权力,人民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政府的统治必须经过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的同意。这个理论是近代宪法产生以来的最重要的宪法原则,这就使得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天上转移到人间,构成了整个国家运作的基础。13我国宪法第2条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3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就体现出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授予的宪法原则。
(二)单一制下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授予
这种授权的概念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授予。单一制国家的核心是国家本身是统一的整体,国家为了方便管理,才把全国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并据此建立地方政权。国家的主权由中央统一行使,地方没有主权,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不具有独立的外交权,也没有退出该国的权力。国家的所有权力都是中央行使的,中央可以对该国领土内所有的事务与所有的居民行使权力,地方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其权力是来自中央授权的。
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通常被分为中央集权型和非中央集权型。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是指地方的权力较少,地方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法律、政策和指令,地方的权力受到中央严密控制。非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是指地方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地方在解决地方事务时,既要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指令,又享有一定自主权,地方还往往拥有对地方一般性事务进行立法的权力。14这种分类法说明,地方权力的大小以及是否具有自治权力,都取决于中央的授权程度。
(三)宗主国对殖民地总督的授权
在理解单一制下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授予时,有必要区分另外一种授权,即宗主国对殖民地总督的授权。近代殖民主义兴起以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管治,是通过派遣作为宗主国的代表——总督完成的。总督大权独揽,对宗主国负责,这就是所谓的总督制。总督的权力来源于宗主国,由宗主国授权,如香港总督获英国皇室授权,澳门总督获葡萄牙总统的授权。英国发布的《英皇制诰》明确规定在香港设立总督,总督由英皇委任,皇室授权并指令总督兼总司令行使在他职权范围内之一切权力。15葡萄牙发布的《澳门组织章程》明确指出总督是葡萄牙共和国的主权机关(除法院外)的代表,总督由共和国总统任免,并授予职权。16
这种授权与单一制下中央对地方的授权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其不同的实质在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占领和管治,是以异族入侵的面目出现的,其权力行使的理论基础不可能建立在本殖民地居民的授予和同意上,只能是由来自异族的宗主国自上而下的授予。在单一制下,地方的权力来自于中央的授予,而中央的权力却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上,是由各个地方组成的全国范围上的人民授予的。而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权力授予缺乏这个最根本的原则,这种授予更多地带有个人化和人格化的特点。在这种授权的形式下,权力是授予总督个人的,由他代表宗主国进行管治。正因为所有的权力是授予总督个人,总督再将权力授权给其它机构进行管治,所以,殖民地往往不存在着严格法律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如在回归前的香港和澳门,其宪制文件往往不再规定政府的权限,甚至连政府这个词也鲜有提及。17我们通常所说的回归前的香港政府和澳门政府,应当是指包括所有政权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18
(四)授权立法、行政授权与其它有关某种具体权力的授权
通常所说的授权,实际上是指某种具体权力的授予。自从洛克和孟德斯鸠提出权力的分立与制约的思想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概念就成为分析和划分国家权力的主流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某种具体权力的授权,可以是立法权力的授权、行政权力的授权和司法权力的授权。这些授权既包括横向意义上的授权,也包括纵向意义上的授权,其中比较常见的授权主要有授权立法和行政授权。
授权立法,也称委托立法,是指立法机关将自己的立法权授权行政机关去行使。这就打破了立法权力只能由立法机关行使的传统宪法观念。19立法授权的普遍运用,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以来的一个重要宪法现象。20在我国,这种意义上的授权立法是指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立法权授予国务院行使。这种向国务院授权的做法有三次。第一次在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部分规定进行修改和补充。21第二次是在1984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22第三次授权是在1985年4月10日,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必要时可以根据宪法,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的规定或条例。23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在2003年制定的《立法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规定与完善,规定了授权立法的位阶和界限,明确指出了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目的与授权范围,被授权机关不得进行转授权,并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权力。24
在我国,授权立法的概念还包括着以下两种。一种是全国人大将自己的立法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这种情况1959年有一次,1982年宪法制定后有三次。25另一种授权立法是指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地方人大授权。这种授权是在我国建设经济特区的过程中出现的有五次,主要是让经济特区能够更加灵活自主地制定单行经济法规。26另外,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行使全国人大授予的其它职权。这里的“授予的其它职权”的表述,不仅说明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全部权力是来源于全国人大,而且包括既可以授予其立法权力,也可以授予立法权以外的其它权力。如果从形式上看,全国人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其它权力,属于立法机关之间的授权,也可以归结为立法授权的范围。
行政授权,主要是指上级行政机关将自己权力授权给下级行政机关去行使。在这里使用的“行政授权”,不是指法律与法规对有关行政机关与组织的“第一次授权”,而是指有关行政机关与组织在取得法律法规对其行政权的设定后,再将自己的行政权力授予其它机关行使。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国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原香港和澳门政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应由中央人民政府自己负责接受和审核,考虑到高度自治和平稳过渡,国务院才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接受与审核。27这里,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接收原港澳政府的资产和债务,是宪法对其规定的职权与职责,而国务院将此权力授权给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行使,是在第一次授权基础上的第二次授权。
这种意义上的授权,在行政法领域比较普遍,主要用于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授权,而且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只有法律与法规明确规定其可以授权的,行政机关才可以将其行政权力授出,否则视为授权不能成立。同时,必须制作授权文件,其内容包括授权主体与被授权主体、授权的事项与范围、授权的期限,等等。28
除了常见的授权立法和行政授权外,在我国,还有一种授权也比较常见,可以称为“司法授权”。这是指上级司法机关将某种司法权力授予下级司法机关行使。如我国法律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复核权,但同时也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29两部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和澳门法院可以解释基本法,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具体司法权力的授予。
四、授权的一般原则
有一种意见认为,所谓授权,是指某种国家权力在授权主体与被授权主体之间依照一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的转移。因此,授权关系一旦形成,就会发生特定的后果:授权者原来拥有和行使的某种权力就会被被授权主体拥有和行使,而被授权主体则会拥有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某种权力,行使该权力并为行使该权力的后果承担责任。30
这里涉及到授权的核心内涵,然而,授权是否就是指权力本身的转移?这种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我们应当将授权理解为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这里的重点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的“所有”转移。譬如在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对主权的“授权”,是指人民拥有主权,而政府只是主权的行使者,而非所有者。单一制下中央对地方的授权,在法律意义上是指中央将权力的行使转移给地方,如果认为是权力本身的转移,就会推论出这么一个结论:当中央收回某种权力时,就必须征得地方的同意,如果地方不同意收回权力,中央就不能收回权力。这个结论与单一制国家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经验恰恰相反。
授权这个本质性的特点还可以在行政法上找到相应的例子。譬如在葡萄牙的行政法理论里,关于授权的性质,理论上有三种学说,一是转移和转让说,二是许可说,三是实施转移说。转移和转让说认为,授权人根据授权法将本属于自己的权力转移或转让给被授权人,被授权人获得授权后,该权力就属于被授权人的权力范围。许可说认为,授权人和被授权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权限范围,授权人授予权力,只不过赋予被授权人行使自己权限的条件和限制,在授权人未授权前,被授权人不得行使自己的权限。实施转移说认为,授权人根据授权法将本属于自己的权力行使转移给被授权人,权力仍然属于授权人,授权只不过是转移权力的行使。31第三种学说是主流的学说,这种学说与其它类型的授权理论是一致的。
在理解国家结构形式时,授权主体在授出权力以后,能否再度收回权力,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如果当授权的这一方将自己的权力授出以后,就不能再行使此种权力了,这就不是“授权”,而是“权力让渡”。权力让渡主要发生在联邦制国家。在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属邦通常先于联邦制国家组成存在,已经是单独的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在组成联邦制国家时,联邦制成员国把各自的部分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这里说的“让渡”是指联邦制成员国将这些权力本身转移到联邦政府,而自己不能再行使。这样就形成了联邦制下双重主权的宪法理论,即联邦拥有主权,而属邦亦拥有主权。所以,授权与权力的让渡不同,让渡是权力本身的转移,而不是此处所说的权力行使的转移。
授权主体授出的权力应当是可以授给被授权主体行使的权力。如果是自己必须行使的权力,就不能授出。通常所理解的授权立法,是指立法机关将自己的部分立法权力授权给行政机关来行使。立法机关不得将自己所有的立法权力授权给行政机关行使,我国《立法法》就明确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得将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授权国务院进行立法。32民法意义上的授权中,授权主权亦不可将自己所有权利尤其是一些人身权利授予他人行使。
授权主体在授权过程中不能将自己所有权力都授予被授权主体。将自己所有的权力授予他人,就等于取消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因此,我国政府在提出“一国两制”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指出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非“一个中国”,高度自治不能没有限度,其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33这是说,“完全自治”和“两个中国”本身挑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没有限度的高度自治即完全自治,本身就会损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授权主体的地位。
授权还必须遵守法定明示原则,民法上的授权必须签署授权委托书,以授权委托书所载的授权内容为界限。在某种具体权力的授权关系上,如宪法学上的授权立法和行政法上的行政授权,亦是如此,要求授权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34在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对政府的授权,通常认为授权的范围是以宪法为准,政府不能行使人民未授予的权力,主要表现在政府不得行使宪法未许可的权力。只有在古代的君权神授理论下,天神对君主权力的授予是不明确和不具体的,而且可以被君主随意解释,用于统治人民。当然,这种授权理论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上,已经被近代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取代了。
授权者既然有权将权力授出,而且保留权力的所有权,就必须在必要时将被授权主体的权力收回。这就说明授权者还有监督被授权者的权力和责任,有对被授权者发出指令的权力。35当授权者发现自己的意志无法贯彻,自己的指令无法下达给被授权者的时候,就可能导致授权的取消和变更。譬如在人民主权意义上的授权,人民将自己的权力授予政府,但是如果发现政府不能达致人民的愿望并实现人民的福祉时,可以推翻政府。美国《独立宣言》就确认了这一点:“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这就指出了有授权,就有取消授权与变更授权的原则。
行政法上的授权更加强调这个原则。授权主体,往往也就是上级行政机关,不仅对被授权主体有取消与变更授权的权力,而且还可以直接废除被授权主体所作出的法律行为。36而中央与地方的授权上,亦有这种例子。单一制国家有权对全国范围内行政区域进行重新划分,就是对地方授权的变更、取消和重新配置。所以,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对特别行政区授权高度自治的政治基础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信任,如果缺乏信任,其结果就是可能导致撤回全部或部分授权。英国曾经四次撤回对北爱尔兰自治政府的授权,就是缺乏信任的结果。37
综上所述,授权的基本原则包括:(1)授权是指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2)授权者不可能授出自己所有的权力,而必须保留自己必要的权力;(3)授权必须法定明示;(4)授权者负有监督的责任,有发出指令的权力;(5)授权者有取消授权与变更授权的权力,当然也有在授权期限届满后重新予以授权的权力。
这些原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和解决“一国两制”架构下的授权所衍生的各种法律问题:我国对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是指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将中央所固有的权力分割给特别行政区,从而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固有权力;中央必须保留保障行使主权的必不可少的权力;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必须以基本法的规定为限,不存在联邦制下的剩余权力;38中央有权对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进行监督;等等。
五、基本法里的两种授权概念及两种授权形式
我们所说的授权至少在以下两种涵义上被使用。
一种授权是指宪法与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对某个主体的权力赋予,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置,基本法授权行政长官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等等。这里的授权是指对权力的直接设定,宪法与基本法并不是授权的主体,而仅是授权的形式和载体。
另一种授权是指已经拥有某种权力的机构再将法律赋予自己行使的权力授权给其它机构来行使,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行使立法权,行政长官授权司长行使某种具体的行政权力,等等。这里的授权是指宪法与基本法本来将国家立法权与行政管理权等某种权力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行政长官行使,而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及行政长官将宪法及基本法赋予自己行使的权力授权给国务院及司长行使,这是第一次授权基础上的第二次授权。
两部基本法所使用的“授权”至少具有以上两种不同的涵义。如两部基本法第2条都规定全国人大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里的授权是指法律对特别行政区权力的设定,所以,我们通常也说基本法授权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是因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和通过的,全国人大是授权的主体,基本法是授权的载体与形式。
这种授权属于前文所指出的单一制下中央对地方的授权。这种授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所设置的特别行政区权力的直接设置,体现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而且,必须看到,这种授权与港澳回归前宗主国对港督和澳督授权有本质上的不同。我国中央对地方的授权,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因此,基本法还规定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选举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39而回归前的香港和澳门根本不存这个根本性的宪法原则。
至于基本法其余条文出现的授权,往往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人民政府将某种本应自己行使的权力授权给特别行政区行使。如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法律,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能解释法律,当然能解释基本法。40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考虑到“一国两制”的种种特殊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将此种权力授权给特别行政区法院行使。又如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国务院负责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当然也包括负责处理回归后与香港和澳门有关的外交与对外事务。41但是,基本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将有关的对外事务授权给特别行政区行使。这里的授权已经是在中国宪法“第一次授权”基础上的“第二次授权”,属于中央对地方某种具体权力的授予。基本法为这些授权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不仅基本法里有关授权的概念存在不同的涵义,而且我国向特别行政区授权的形式亦有两种。
第一种形式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第2条都明确指出,全国人大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里的“依照本法的规定”,指明了全国人大向特别行政区授权的形式主要是由基本法完成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不仅在第2条对高度自治作出授权,而且在其它条文中对有关需要授权的事项作出具体安排。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是授权的法律文件,是中央向特别行政区授权的主要载体与形式。
第二种形式是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制定的其它法律文件。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第20条明确指出,香港和澳门可享有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授予的其它的权力,这就明确了授权的第二种形式。这里的其它法律文件主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作出的决定。这种授权形式是次要的,仅对基本法的授权起补充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第二种形式的授权是指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制定的决定,不包括法律。42笔者认为不能作这样绝对的理解,不能排除将来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他法律里将某种权力授予特别行政区。
以上第二种形式的授权,从“一国两制”的具体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1)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指定其入境事务处处理有关国籍申请事宜(1996年5月15日);43(2)国务院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1997年7月1日起接收和负责审核原香港政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并自主进行管理(1996年5月15日);44(3)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指定其有关机构处理国籍申请事宜(1998年12月29日);45(4)国务院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1999年12月20日接收原澳门政府资产(1999年12月18日);46(5)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深圳湾口岸内设立的港方口岸区(2006年10月31日);47(6)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2009年6月27日)。48
另外,中央人民政府在“钱七条”里宣布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时,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台湾地区之间以各种名义进行的官方接触往来、商谈、签署协议和设立机构,“须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经中央人民政府具体授权,由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批准”。49这里所指的“授权”也应当属于第二种形式的授权。
有必要探讨的是此处所说的高度自治授权的第一种形式与第二种形式的关系。第一种授权形式已经被两部基本法的有关条文所明确规定,第二种授权形式则表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等中央机构通过的个别决议和决定,是对基本法有关条文的进一步补充。当然,授权的第二种形式已经被两部基本法第20条所明确指出,其直接法律依据是该第20条,而两部基本法第2条已经明确指出全国人大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依照本法的规定”其中已经包括了第20条的授权在内,因此,这里所说的第二种形式的授权本身就包括在基本法内,就包括在授权的第一种形式内。
这两种授权形式是统一的。不管是这里所说的授权的第一种形式,还是授权的第二种形式,其最高依据都是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不能认为如果没有两部基本法的第20条,中央就不可以再授予特别行政区的其他权力,而特别行政区也不可以再接受这样的授权。50在我国单一制下,中央向地方的授权,这种行使授权的权力本身是主权的表现,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在法律上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即使两部基本法没有其第20条的规定,也不能排除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等中央机构在基本法以外的其他决议和决定甚至法律中,将有关权力再授予特别行政区行使。两部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授权关系,而且更加明确指出了第一种形式的授权和第二种形式的授权的关系。
注:
1这里的授权不包括特别行政区内部的授权关系,如香港基本法第111条和澳门基本法第108条规定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授权制定银行发行或继续发行港币和澳门元等。
2参见香港基本法第48条第9项、第62条第3项、第96条、第125条、第133条和134条、第153条、第154条、第155条等。
3参见香港基本法第23条和澳门基本法第23条,澳门基本法第136条和第137条等。
4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年通过,经多次修改,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04年10月27日)。
5《国语·鲁语上》。
6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第483页,及Black’sLawDictionary(seventhEdition).BryanA.GarnerEditorinchief,ST.PAUL,MINN.,1999,p129、707。
7陈华强:《管治权让渡后的一国两制与授权》,《澳门法制研究会》会刊第1期。
8可参考有关条文,如《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25条规定:“中国政府在国外受理外国人入境、过境申请的机关,是中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和外交部授权的其他驻外机关。”《测绘法》第13条规定:“承担测绘任务的单位,施测前应当按照规定向测绘项目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进行测绘任务登记。需要进行登记的测绘任务的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规定。列入全国基础测绘规划、专业测绘规划的测绘任务,施测前由编制测绘规划的部门将任务安排通知测绘项目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不再另行登记。”
9《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
10胡建淼:《有关中国行政法理上的行政授权问题》,载刘莘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新理念》,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11古代世界的其它地方也普遍信奉这种君权神授理论。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9B% E6%AC%8A%E7%A5%9E%E6%8E%88%E8%AA%AA,2011年3月28日访问。
12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如巴基斯坦宪法规定主权属于真主,“鉴于全宇宙的主权仅属于全能的真主”,而巴基斯坦人民在真主规定的限度下行使的权力是神圣的委托。
13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宣布:“政府的正当权力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3条明确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1791年法国宪法指出,“一切权力只能来自国民,国民只得通过代表行使其权力。”菲律宾宪法规定:“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个原则也纷纷被写进了各国宪法里,而且,除了明确规定人民主权外,还有些国家通过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形式来保障人民主权,以及通过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来体现人民主权。参见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192页。
14见唐晓、王为、王春英:《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孙关宏:《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9页。
15参见《英皇制诰》第1条和第2条。第2条还规定总督权力来源依据本制诰及经御笔签署及盖上御玺而颁发予他之委任状,经御笔签署及盖上御玺而颁发予他之皇室训令,枢密院敕令,皇室通过一名重要国务大臣传达之指令以及本殖民地现行及日后制订之有效法律。
16《澳门组织章程》第3条第2款规定:“与外国发生关系及缔结国际协议或国际协约时,代表澳门之权限属共和国总统,而涉及专属本地区利益的事宜,共和国总统得将代表澳门之权限授予总督”。其第5条第1款规定:“总督由共和国总统任免,并授予职权。”
17参见《澳门组织章程》和《英王制诰》、《皇室训令》有关条款。如《澳门组织章程》规定澳门的管理机关(órgãos degoverno)为总督和立法会,这里的órgãosdegoverno也可译为政府机关。参见吴志良:《澳门政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80-81页。如果对比《澳门组织章程》1990年修改前的文本,governo这个表述曾被广泛使用,其内涵亦不尽相同,有时表示总督,有时表示总督和立法会,有时表示由总督、各政务司及保安司令等组成的整体。1990年葡萄牙重新修改《澳门组织章程》,除órgãosdegoverno用来表示澳门本身两个管治机关外,其余地方不再出现,或者用总督或地区的表述予以替代。参见VitalinoCanas(简能思):《政治学研究初阶》,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1997年版,第312-318页。因此,即使将《澳门组织章程》里órgãos degoverno译为“政府机关“,这里的政府也是广义的。
18参见蓝天主编:《一国两制法律问题研究》(总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6-417页;李沛泽主编:《香港法律概述》,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法律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第7-13页。
19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92年的菲尔德诉克拉克案(Fieldv.Clark)就指出:“国会不能将立法权授出,这是一项广泛接受的原则,这对保证宪法导控的政府系统的纯洁与运作至关重要。”在罗斯福新政初期,美国法院在“热油”案和“病鸡”案中,以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授权标准,授权过于宽泛为由,分别判决相应授权无效。
20如联邦德国宪法第80条规定:“联邦政府、联邦阁员或邦政府,得根据法律(Rechtsverordnungen)。此项授权之内容、目的及范围,应以法律规定之。所发命令,应引证法律根据。如法律规定授权得再移转,授权之移转需要以命令为之。”法国宪法第38条规定:“政府为执行其施政纲领,可以要求议会授权自己在一定期限内以法令的形式采取通常属于法律范围内的措施。”
21其全文如下:“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对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部分规定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22其全文如下:“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2009年6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明确废止了该授权文件。
23其全文如下:“为了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工作的顺利进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必要时可以根据宪法,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经过实践检验,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
24兹引用有关条文如下。《立法法》第9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第10条规定:“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它机关。”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251954年宪法制定时,第22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立法权。然而,随着国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家工作的进一步要求,仅靠一年只开一次,一次只有半个月会期的全国人大完成国家的立法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1959年全国人大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现行法律适时予以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种立法权在1982年宪法里予以进一步确认。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有三次授权。一次是在1981年12月13日,全国人大原则批准民事诉讼法草案后,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根据代表和其它方面所提出的意见,在修改后公布试行。一次是在1987年4月11日,全国人大原则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后,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审议修改后颁布试行。还有一次是在1989年4月4日,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市依法选举产生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后,再授权深圳市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
26第一次授权是1981年11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广东和福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各该省经济特区的单行经济法规。第二次授权是1988年4月13日,全国人大授权海南省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在海南经济特区实施。第三次授权是1992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授权深圳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授权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在经济特区实施。第四次授权是1994年3月22日,全国人大授权厦门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授权厦门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在经济特区实施。第五次授权是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授权汕头市和珠海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在经济特区实施。
27参见国务院1997年6月28日发布的《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接收原香港政府资产的决定》,其文如下:“国务院决定: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1997年7月1日起接收和负责审核原香港政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自主地进行管理。”1999年12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接收原澳门政府资产的决定》,其文字表述大致与前一决定相同。
28澳门《行政程序法典》其中第二部分第一章第四讲专门规定了“授权及代任”问题,对行政授权的概念、转授权、授权行为要件、获授权者或获转授权者资格、授权者或转授权者的权力、授权或转授权之消灭等问题作出了系统规定,其条文见第37条、第38条、第39条、第40条、第41条和第42条。
29198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将除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包括受贿案件、走私案件、投机倒把案件、贩毒案件、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件)外的其它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199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将毒品犯罪的死刑核准权授权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93年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毒品犯罪的死刑核准权分别授予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和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刑法的修改再次明确规定了死刑复核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最高人民法院仍然以通知的形式维持了原来对死刑复核权的下放。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
30李元起:《澳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性质和特点初探》,载《纪念澳门基本法实施1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31José EduardoFigueiredoDias:《澳门行政法培训课程》,关冠雄译,澳门法律及司法培训中心2008年版,第73页。
32参见《立法法》第9条。
33参见邓小平:《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载《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
34如澳门《行政程序法典》规定了授权行为之要件,指出“在授权行为或转授权行为中,授权机关或转授权机关应详细指明其所授予或转授予之权力,又或获授权者或获转授权者可作出之行为;授权行为或转授权行为须公布于《澳门政府公报》;如属市政机关,尚应将之张贴于常贴告示处”。我国亦明确规定了有关授权立法的具体条件,可参见《立法法》第10条。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35年美国“谢克特生蓄公司诉联邦案”(A.L.A.SchechterPoultryCorp.v.UnitedStates),美国国会无法授予总统制定“公平竞争法”的权力。法院认为美国国会的授权范围太过广泛,“鉴于那个宽泛的宣言的范围以及施加的少数限制的性质,总统批准或制定法规,从而制定法律来管理全国商业和工业的任意决定权几乎是不受限制的。我们认为这样授予总统的制定法律的权力是违宪授予立法权”。[美]斯坦利·L·库特勒编:《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朱曾汶、林铮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41页。
35如澳门《行政程序法典》第41条规定:“授权机关或转授权机关,得发出指令或对获授权者或获转授权者有约束力之指示,说明其应如何行使获授予或获转授予之权力。”
36如澳门《行政程序法典》第41条规定:“授权机关或转授权机关有收回权,且有权依据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废止获授权者或获转授权者所作之行为。”
37转引自程洁:《中央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以基本法规定的授权关系为框架》,载《2007年香港基本法的回归与前瞻研讨会论文集》。
38有关联邦制下剩余权力理论能否适用在特别行政区的讨论,可参见肖蔚云:《论香港基本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5页、第199页及第273页;王叔文:《王叔文文选》,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288页;李元起、黄若谷:《论特别行政区制度下的“剩余权力”问题》,《北方法学》2008年第2期;王振民:《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辨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175页、第204页;王禹:《“一国两制”宪法精神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张定淮、孟东:《是“剩余权力”,还是“保留性的本源权力”?——评中央与港、澳特区权力关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提法》,《“一国两制”研究》2010年第3期。
39参见香港基本法21条和澳门基本法第21条。
40参见中国宪法第67条第4项。
41参见中国宪法第89条第9项。
42骆伟建:《论“一国两制”下的授权》,载杨允中主编:《“一国两制”与宪政发展——庆祝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09年版。
43参见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其第5条指出:“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指定其入境事务处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受理国籍申请的机关,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和以上规定对所有国籍申请事宜作出处理。”
44参见国务院1997年6月28日发布的《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接收原香港政府资产的决定》,其文如下:“国务院决定: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1997年7月1日起接收和负责审核原香港政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自主地进行管理。”
45参见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国籍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其中指出:“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指定其有关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和以上规定对所有国籍申请事宜作出处理。”
46参见1999年12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接收原澳门政府资产的决定》,其文如下:“国务院决定: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1999年12月20日起接收和负责核对原澳门政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并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自主地进行管理。”
4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10月31日通过《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其中规定:“一、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深圳湾口岸启用之日起,对该口岸所设港方口岸区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实行禁区式管理。二、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的范围,由国务院规定。三、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土地使用期限,由国务院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48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其中规定:“一、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启用之日起,在本决定第三条规定的期限内对该校区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与横琴岛的其他区域隔开管理,具体方式由国务院规定。二、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横琴口岸南侧,横琴岛环岛东路和十字门水道西岸之间,用地面积为1.0926平方千米。具体界址由国务院确定。在本决定第三条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变更该校区土地的用途。三、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的土地使用权,租赁期限自该校区启用之日起至2049年12月19日止。租赁期限届满,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续期。”
49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处理“九七”后香港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和《中央人民政府处理“九九”后澳门涉台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
50王振民:《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