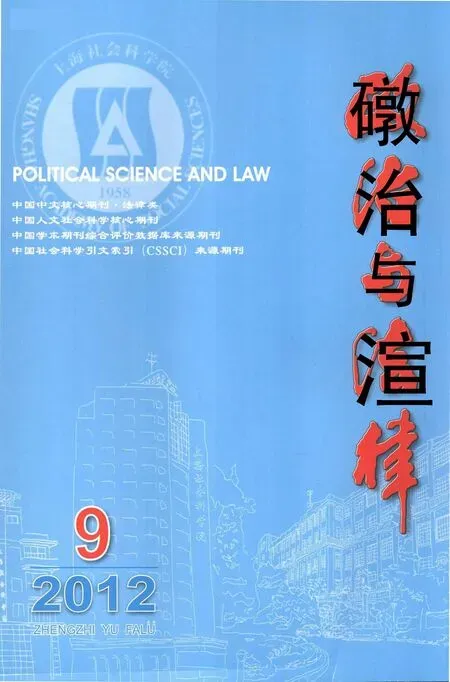论数罪并罚死刑案件量刑中基准刑的确定和自首的适用
王 刚
一、问题的提出
数罪并罚,“是指人民法院对一人所犯的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按照刑法规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罚”。1数罪并罚死刑案件,是指审判时一人犯有数罪,其中至少有一罪应被判处死刑的案件。数罪增加了量刑的复杂性,死刑又关涉被告人的生与死,且表明罪行极其严重,故数罪并罚死刑案件的量刑既是刑事审判的重点,又是考验法官智慧和良知的难题。倘若此类案件量刑不当——主要表现为判处死缓,则很容易引起民意与司法之间的严重对立,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李昌奎案即是典型代表,东莞敖翔案同样争议颇大。特别是在职务犯罪中,对被告人判处死缓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如贵州樊中黔案、湖北刘志祥案、浙江王华元案等。虽然不能武断地否定这些判决的合理性,但对国家工作人员所犯严重数罪大范围地适用死缓,不符合我国重典治吏的法制传统,易引起人们对刑法公正性的怀疑。网络上的“死罪贪官判死缓,已经成为潜规则”2、“巨贪死缓:‘中国特色’”3等声音,反映了人们对当前死缓判决公正性的严重质疑。而“中国巨贪被判死缓等于度假,过几年就可到国外安度晚年”4的说法亦会对人们的刑法信仰造成剧烈冲击。如果法官在一些重大案件的判决上总是与民意存在严重分歧,一定程度上就表明这些判决脱离了群众基础,偏离了民众的通常观念。因此,如果死缓适用不当,成了罪犯规避死刑的“免死金牌”,则刑法的威严将荡然无存,人们对刑法的信仰自然无从谈起。诚如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我们对死缓的异化应保持高度警惕。
如果可以理性的审视即可发现,除了李昌奎案这类明显量刑不当的案件外,大部分数罪并罚死刑案件的死缓判决是否妥当,确实存在见仁见智的理念分歧。理念分歧关乎价值立场,“而价值立场层面的讨论,又总是具有难以争辩、不易说服的非逻辑性的特点”。5因此,有必要“通过技术渠道消解理念之争”。技术渠道即是量刑方法,科学的量刑方法的运用和展示不仅有助于消除民众的质疑和由此产生的理念之争,而且有利于在实体上促进量刑公正。在量刑过程中,基准刑是裁量刑罚的基础,自首等量刑情节是裁量刑罚的依据,因此基准刑的确定和自首的适用是数罪并罚死刑案件量刑方法中的核心问题,下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论述。
二、数罪并罚死刑案件量刑中基准刑的确定
我国《刑法》第69条确立了数罪并罚的三项原则:吸收原则、限制加重原则和并科原则。“但对于判决宣告中有数个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最重刑为死刑、无期徒刑的应当按照什么原则实行并罚并未作明文规定。但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吸收原则。”6司法实践中也是这么操作的。“吸收原则,是指对于数罪分别宣告刑罚,然后选择其中最重的宣告刑,作为数罪的最终处罚或者应当执行的刑罚,其余较轻的宣告刑被最重的宣告刑所吸收,而不予执行。”7不过,“数罪之处罚原则应当从两个层次上加以理解:其一为数罪并罚的处理理念,其二为数罪并罚的具体实现方法”。8作为处理数罪并罚死刑案件基本理念的吸收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实现,我国刑法未予规定。《刑法》第69条至第71条以犯罪发生或被发现的时间为标准设置了三种并罚方法,但这对数罪并罚死刑案件的具体量刑都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司法实践中的通常做法是,数罪中若有一罪被判处死刑的,不论其他犯罪被判处何种主刑,只执行死刑而不再执行其他主刑。这种裁量思路虽然正确,但由于许多法官在理解上存在偏差,导致常常采取错误的方式进行量刑,即直接适用吸收原则来确定基准刑(基准刑是指具体案件在不考虑各种量刑情节时应当判处的刑罚),这最终会影响到量刑结果的公正性和均衡性。笔者认为,吸收原则虽然是数罪并罚死刑案件量刑的基本理念,但其只能适用于数罪的宣告刑确定以后,对数个宣告刑进行并合处理的量刑最后阶段。在刑罚的裁量过程中则应适用并科主义来确定基准刑,即以量刑情节指向的数罪的基准刑之和作为数罪的整体基准刑。下文从两个方面对此作必要分析。
第一,在数罪并罚死刑案件的量刑中,为何死刑可以吸收其他罪行的刑罚,而其他罪行的刑事责任不能实现?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死刑是以剥夺受刑人的生命为内容的刑罚,生命即不存在,其他以剥夺或限制自由为内容的较轻的主刑就失去了继续执行的可能”。9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死刑只能执行一次,故无论被告人的罪行多么严重,最终只能被判处和执行一个死刑。但我们应当认识到,以死刑吸收其他罪行的刑罚实际上是与数罪的罪责程度不相称的,因为死刑只体现了本罪的刑事责任,它无法满足报应全部罪行之整体罪责的需要。事实上,其他罪行的刑事责任并未消亡,但其刑罚效果却被死刑吸收,从而在判决中无从体现。换言之,行为人只承担了死刑罪行的刑事责任,其他罪行的刑事责任因被死刑吸收而未能实现。在此意义上来说,对数罪并罚死刑案件判处死刑通常是罚不当罪的。但鉴于死刑不能累加计算和重复执行,这实属无奈之举,因而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况且,即便罚不当罪,但如果行为人最终被执行了死刑,人们在法感情上也是能够接受的。但问题是,倘若数罪极其严重,在量刑过程中以死刑吸收其他罪行的刑罚,最后又因从轻情节而判处死缓,则该判决的公正性就会大打折扣,近年来一些争议较大的数罪并罚死刑案件几乎皆因这样的量刑问题而引起。因此,数罪并罚死刑案件量刑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吸收原则。
第二,在数罪并罚死刑案件的量刑中,死刑如何吸收其他罪行的刑罚,基准刑应如何确定?司法实践中死刑吸收其他罪行的刑罚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刑罚裁量过程中吸收,即先用死刑吸收其他罪行的基准刑,再用量刑情节对死刑进行调适;二是在刑罚裁量之后吸收,即先适用量刑情节对其指向的所有罪行进行量刑,得出数罪的宣告刑之后,再以死刑吸收其他罪行的刑罚而决定判处死刑。量刑是以量刑情节为根据对基准刑进行调适的司法活动,死刑在不同阶段吸收其他罪行的刑罚会产生不同的基准刑,进而会影响到最终的量刑结果。在前一种情况下,量刑情节调适的基准刑仅仅是死刑;在后一种情况下,量刑情节调适的基准刑是死刑与其他罪行的刑罚之和。对此,应当如何取舍呢?笔者赞成后一种做法,认为吸收原则只能在量刑的终局意义上被采用——通过对全部犯罪构成事实和非犯罪构成事实的综合评估,得出各个罪行的宣告刑之后,再以死刑吸收其他罪行的宣告刑而决定判处死刑才是恰当的。上文中学者对吸收原则所下的定义使用的是“宣告刑”,也说明以死刑吸收其他罪行的刑罚之前提是数刑作为宣告刑已经确定下来了。日本学者也认为,“并科原则,是指对各个罪分别量刑,然而将各个刑合并执行的原则”。10这表明数罪的量刑应先于并合处理,而不应先并合处理再继续量刑。如果死刑还处于需要适用量刑情节进行调适的基准刑阶段时,就不应用其来吸收其他罪行的刑罚。这是因为:其一,死刑不可量化,其不能体现同样达到死刑适用标准但危害程度不同的一罪和数罪之间的实质差异;其二,其他罪行的刑罚已被死刑吸收,故死刑无法评价数罪并罚死刑案件的全部罪责;其三,以死刑为基准刑实际上降低了数罪的整体基准刑,其他罪行的基准刑在刑罚裁量过程中无从发挥作用,在从轻量刑情节的调适下容易产生非死刑判决的结果。所以,在刑罚裁量过程中应采取并科主义确定基准刑,即以量刑情节指向的全部罪行的基准刑之和作为数罪的整体基准刑,此时若适用吸收原则就很容易导致量刑失衡。例如,甲实施了一起应判死刑的犯罪,乙实施了分别应判死刑和15年有期徒刑的两起犯罪,二人均具有自首情节。倘若都以死刑为基准刑从轻处罚,很可能会对二人都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其原因是量刑方法错误:在对乙进行量刑的时候,先用死刑吸收15年有期徒刑,再适用自首对死刑进行从轻处罚,这实际上是将15年有期徒刑排除于自首的调节范围之外,使其未能在刑罚裁量过程中发挥作用。将其他罪行的刑罚排除于基准刑范围之外的做法,恰恰是我国数罪并罚死刑案件量刑中的一个常见误区,这是机械地理解和适用吸收原则的结果。例如,原国家民委办公厅副主任杜茂基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杜茂基如实供述指控的犯罪事实,主动退赃,且赃款赃物大部分已追缴和退还,决定判处死缓。原贵州市市长助理樊中黔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樊中黔主动交代尚未被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具有一定的悔罪、认罪表现,其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及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已被依法查获,可酌情从轻处罚,决定判处死缓。应当说,这些死缓判决的公正性是值得怀疑的。
“如何在数罪中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是数罪并罚(日本称之为合并罪,而德国称之为实质竞合)制度的目的诉求。”11为了纠正上述错误做法,保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笔者主张在数罪并罚死刑案件的量刑中应当采用并科主义确定基准刑,即以量刑情节所指向的全部罪行的基准刑之和作为数罪的整体基准刑。以量刑情节指向的犯罪数量为根据,数罪并罚死刑案件量刑的基本方法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其一,如果量刑情节是指向某一罪行的,适用量刑情节对该罪的基准刑进行调适即可,然后再对其他罪行进行量刑,最后对数罪的宣告刑进行并合处理;其二,如果量刑情节是指向部分罪行的,应适用量刑情节对这些罪行的基准刑之和进行调适,再将此量刑结果与其他罪行的宣告刑进行并合处理;其三,如果量刑情节是指向全部罪行的,应以全部罪行的基准刑之和作为量刑情节的调适对象,然后确定最终的宣告刑。在数罪并罚死刑案件的量刑中,凡是需要适用量刑情节的场合,其基准刑必须是该量刑情节所指向的全部罪行的基准刑之和。因为,“我们必须重视数罪中其他罪名对死刑罪名之责任判断的增量效应……这类犯罪之责任轻重进行自我判断之后,必然会以某种方式潜在性地累加到死刑罪名的判断之中,并成为死刑罪名能否适用死缓的判断依据。换句话说,这部分责任的轻重是不能被死刑罪名吸收的,而是需要和死刑罪名的责任轻重叠加在一起,作为能否选择死缓的标准之一。两者的责任轻重合二为一,才是完整的行为人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等的综合体现,而这种综合体现才是法官决定被告人最终宣告刑的依据”。12
三、数罪并罚死刑案件量刑中自首的规范适用
除了基准刑的确定之外,如何规范适用自首情节也是数罪并罚死刑案件量刑中的一道难题,因为“数罪整体上的违法性与有责性远远超过单一的同种一罪的违法性与有责性”,13而自首会产生从轻处罚的效果,所以数罪和自首对量刑结果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对数罪并罚死刑案件判处死缓的依据主要是从轻或减轻量刑情节,因减轻情节而判处死缓争议不大,争议的焦点是根据从轻情节判处死缓,故本文以自首为例探讨这类案件中从轻情节的适用问题,其他从轻情节的适用可以参照自首的适用进行,本文不再分别论述。)关于自首情节的规范适用,笔者提出三条路径:(1)定量分析法——将相关刑罚对应的罪量进行量化分析;(2)相互抵消法——以其他罪行的刑罚抵消自首的从宽效果;(3)综合评估法——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检验量刑结果是否公正。
(一)定量分析法:将相关刑罚对应的罪量进行量化分析
自首的从轻效应,在不同的刑种中表现各异。自由刑可作定量分析,其从轻前后的刑罚差异一般不会很大,故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由于死刑不能进行定量分析,其从轻效果与自由刑大相径庭:若判处死刑,则自首的从宽功能无从体现;若不判处死刑,又会出现“生死两重天”的巨大差异。死刑的适用标准模糊不清,使得准确把握自首的从轻效果变得十分困难,这必然会增加法官在决定是否适用死刑时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但死刑不仅关涉被告人的生与死,而且死刑案件素来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所以死刑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否符合刑法规定、是否符合国情民意是刑事审判中的核心问题。为此,笔者提出量化分析的方法为数罪并罚死刑案件中自首的规范适用提供思路。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罪量与刑量之间保持均衡关系,实现这种均衡关系的最佳途径是在罪量和刑量之间构建一种转换机制,这种转换机制的构建依赖于对罪量的量化处理。因为刑量是确定的,但罪量却千差万别,而且不同形态的犯罪之罪量可能相等,故笔者设想通过对主要刑罚所对应的罪量进行赋值,以构建罪刑之间的转化机制。假设可以将15年有期徒刑对应的罪量赋值为85-90,将无期徒刑对应的罪量赋值为90-95,将死缓对应的罪量赋值为95-100,将死刑对应的罪量赋值为100。赋值以后,将数罪的罪量进行累加,罪量之和对应的刑罚即为基准刑。然后,再根据自首的从轻比例对数罪的罪量之和进行调节:调节结果在100以上的,一般应判处死刑;调节结果在100以下的,不应判处死刑。现举例说明:假设被告人分别实施了罪量为110的故意杀人罪和罪量为60的强奸罪,同时案件中存在从轻比例为20%的自首情节,则本案从轻处罚后的罪量为:(110+60)×(1-20%)=136,故应当判处死刑。
这种量化分析的方法要比以抽象的死刑和自由刑作为基准刑进行量刑科学得多,同时又解决了死刑与其他主刑如何并科处理的问题。因为死刑既不能定量判断也不能累加计算,若不对罪量进行量化处理,死刑很容易抹杀不同罪行之间罪量上的实质差异。例如,致一人死亡和致二人死亡的两起故意杀人罪,其罪量显然不同,若都判处死刑就无法体现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而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如果两案都因自首而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显然有失公正。因此,只有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才能更好地甄别不同的死刑罪行之间的实质差异,防止死缓适用不当,保障量刑结果公正。但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数罪并罚死刑案件量刑中的基准刑应采用并科主义确定,基准刑对应的罪量为相关罪行的罪量之和;其二,如果案件不存在死刑罪行,不能以加总后的罪量大于100为理由适用死刑。此外还应当承认的是,量化分析法在操作中还存在不少困难,数据设置的科学性还有待考证,因而该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尚待未来继续研究。
(二)相互抵消法:以其他罪行的刑罚抵消自首的从宽效果
定量分析法为处理数罪并罚死刑案件的量刑提供了新的思路,但鉴于其操作上存在困难,并且尚未获得学界的支持和法律的认可,因而还难以直接适用于司法实践。在此情况下,笔者提出相互抵消法,进一步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被告人自首的数罪并罚死刑案件中,有三种因素会对死刑适用产生重要影响:死刑罪行、自首情节和其他罪行。死刑罪行是适用死刑的基础,舍此就谈不上适用死刑;自首是从轻量刑情节,会产生削弱适用死刑的效果;其他罪行增加了被告人的罪责程度,是增强适用死刑的根据。法官在量刑时应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考察,不仅要考虑自首情节,还必须兼顾其他罪行,通过对这些事实进行综合评估后作出判决。否则,认识上的片面性必然难保量刑公正。诚如姜涛博士所言:“如果我们不把其他罪名作为死刑罪名之宣告刑选择的参数之一,则会出现这样的司法怪圈:犯罪危害严重者反而被判处死缓,危害轻者却被判处死刑。因为数罪并罚需要对各个犯罪进行单独评价并得出量刑结果,然后再以吸收原则湮没其他犯罪的量刑结果,而单独犯罪则可能因情节特别严重或后果特别严重而直接被判处死刑。这是不正义的。”14从作用方式上来看,其他罪行的刑罚对自首的从宽效果会产生抵消作用,抵消的结果是:如果其他罪行的刑罚大于自首减少的刑罚的,通常应判处死刑;如果其他罪行的刑罚小于自首减少的刑罚的,可以不判处死刑。相互抵消后应如何判决,法官需要结合其他罪行的严重程度和自首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其他罪行属于犯罪构成事实,直接反映了犯罪的罪责程度,而自首是非犯罪构成事实,间接反映了犯罪人的人格状况,故前者对刑罚的影响力一般大于后者;其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根据各个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确定全部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据此,如果案件中存在从重量刑情节的,其对自首的从轻效果也具有抵消作用。
(三)综合评估法: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量刑结果作最后检验
作为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检验数罪并罚死刑案件的量刑结果是否公正、死缓判决是否恰当的最后标准。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刑罚应与犯罪的严重程度保持均衡关系,一般应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一罪一罚、数罪数罚、罚当其罪、罪刑相当。因存在自首情节而对应判死刑的一罪案件判处死缓,一般不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但当数罪并罚死刑案件中存在自首情节时,法官必须慎重考虑是否判处死刑,因为数罪的罪责程度一般高于一罪的罪责程度,这种罪责差异经自首调节之后仍然存在,所以即使存在自首情节,数罪案件最终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一般也是大于一罪案件的。在这类案件的量刑过程中,如果定量分析法和相互抵消法都不能为裁判结果提供明晰的指导,只能诉诸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一最后的检验标准了。法官必须仔细斟酌拟判决的结果是否与被告人的罪责程度相适应,是否符合特殊预防的需要。而且,“依据责任程度科处的刑罚,不能出于一般预防或特殊预防理由而被超越”,15所以自首情节虽有削弱死刑适用的功能,但其从轻效果是有限度的,法官因自首而作出的从轻判决不能过分偏离罪责程度所确定的刑罚,而让社会一般人感到“不可理喻”或“大吃一惊”。应当切记的是,“我们的法律是人民的法律,绝不应该对其做出根本背离老百姓所共同认可的常识、常理、常情的解释”和适用。16尽管司法具有专业性、独立性特征,但司法赖以存在的土壤是社会,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大众,司法判决“绝不能显失公平、绝不能违背常理、绝不能不顾人情”。17因此,法官应当综合考虑全部案情,合理解释刑法规定,认真考量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作出合法合理的判决。如果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抛开而机械地适用自首情节,量刑结果极有可能会偏离公正的轨道,超越公众的心理承受范围,引发人们对刑事司法乃至整个刑法制度的信任危机。
四、余 论
“如果要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搜索‘中国特色’的制度化因子的话,相信每一个刑法学人都会不假思索地俯首去捡拾‘管制’和‘死缓’”。18诚然,死缓制度为我国所独创,但这一点对死缓制度的合理性解释毫无助益,亦无力掩盖死缓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因此,在我国刑法保留死缓制度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死缓被不当适用而沦为该当死罪者规避死刑的“免死金牌”,避免死缓向“巨贪死缓:‘中国特色’”异变,是刑法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们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在一罪案件中,死缓异化的主要原因是从轻情节适用不当;在数罪案件中,死缓异化的原因还包括基准刑确定错误。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采用并科原则确定基准刑和使用定量分析法、相互抵消法、综合评估法适用自首等从轻情节的司法对策,期望对数罪并罚死刑案件量刑的规范化和死缓适用的正当化有所助益。
注:
1、9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0页,第471页。
2参见秀才江湖:《死刑贪官判死缓,荒唐理由大盘点》,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5149824,2011年12月12日访问。
3参见《巨贪死缓成“中国特色”,死缓不应等同免死》,http://news.sohu.com/20110512/n307394270.shtml,2011年12月12日访问。
4尹鸿伟:《中国巨贪被判死缓等于度假,过几年就可到国外安度晚年》,http://finance.ifeng.com/news/
20100914/2620434.shtml,2011年12月12日访问。
5车浩:《从李昌奎案看“邻里纠纷”与“手段残忍”的涵义》,《法学》2011年第8期。
6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下卷)(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页。
7张小虎:《刑罚论的比较与建构》(上卷),群众出版社2010年版,第529页。
8张淼、翟一平:《数罪并罚原则及方法辨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0[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2页。
11、12、13、14姜涛:《从李昌奎案检讨数罪并罚时死缓的适用》,《法学》2011年第8期。
15[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16、17陈忠林:《“常识、常理、常情”:一种法治观与法学教育观》,《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6期。
18高铭暄、徐宏:《中国死缓制度的三维考察》,《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