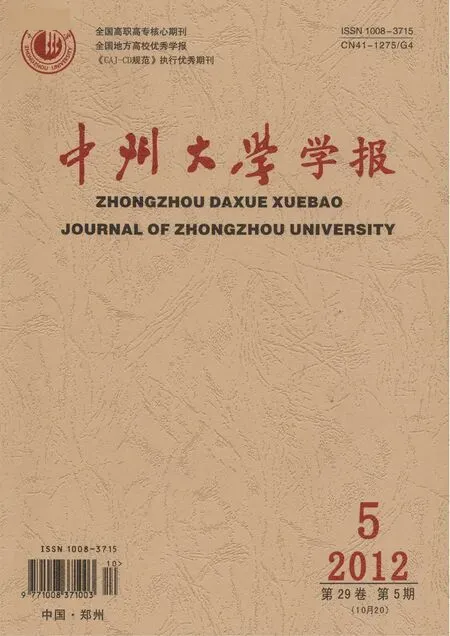墨白小说叙事里的并置结构
——对《失踪》文本世界的解析
苏常青
(郑州大学中文系,郑州450001)
抗日战争作为历史,已成为昨天,但作为文学表现的永恒主题,它却成为作家多角度观照的对象。墨白的《失踪》正是打着那一时代烙印的短篇小说。当我们的内心贴近它时,无时不发现作者的情感闪光,感受到作品的内在韵律和飘逸的情绪,体会到那个时代的苦涩、苦难和悲伤。勿庸置疑,作品深远悠长的意味还不仅限于此。
作为历史性的悲剧,随着人类文明、文化的进步,它的历史越漫长,它的悲怆意味也就越浓厚,并以时间的距离和积淀使读者对侵略和掠夺进行再次的审视与批判,在内心产生让邪恶与侵略永远埋葬于沼泽,让这段历史永远成为过去的心理情结,从而构建人类优美、和谐的生存方式。
结构范式:传统小说是以情书为结构中心的范式,“文似看山喜不平”,可看作是这一结构范式的审美注脚。这里,笔者无意拿20世纪的小说观来观照中国古代小说范式,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以情节结构小说,由于采用连贯叙述的方式,讲究有头有尾,首尾相照,使得读者在审美过程中无以介入作品,读者与作品人物不能融契,而仅以局外人的身份去消极欣赏,这无疑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养成审美的惰性。当然,以情节结构小说也有其优势,故事的险奇曲折可以对读者的欣赏心理造成现时性的共鸣。《失踪》的结构范式避开了这一传统的形式,代之以潜在的、内涵的情绪结构,以情绪统辖故事,而情节则成了文本中情绪的载体。
若按正常的情节结构来叙述,《失踪》至少可以设置几处惊心动魄的场面,从而形成情节发展中的“闪光点”,制造出令人发聩的情节效果,如三藏法师、许木匠之父及许木匠的死。但叙述者在十分节制的节奏中叙述了这些人的壮举,血的残酷仅以两片“红光”与“一道紫色的血”表露出来,看似简约平淡,但却在我们的心理场上唤起绵绵不尽的感喟与浩叹,引发出情绪的波动。在叙述中,叙述者设置了故事的双向选择方式:外在的方向,以山川丘对中国的施虐与对经书的掠夺作为外在情节线,意在暴露侵略者的贪婪与残酷;内在的方向是通过外在情节的催化,引发出觉生和尚的情绪流动,使他在外在情节的发展中逐渐感受并外化,最后以自己肉体的毁灭完成了作为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人的独立人格实现。
若对墨白20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小说作宏观透视,就会发现情绪统辖情节的结构,成了他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如《黑房间》、《红房间》、《同胞》等,无不属于这一范畴。这些作品虽也有情可寻,但更能让读者获得审美体验的仍是情绪,是以情绪作为内在结构的小说。
在这一结构范式的营造中,《失踪》的意象结构组合也从属于情绪结构,我们可称之为“情绪意象体系”,如红光、紫色、沼泽、藏经楼、灰色砖塔、墓穴等无不带有死亡的情绪信码。这些无情之物,在叙述主体觉生和尚的情绪流动中,经过情感的浸润,产生心理移情,注入情绪。通过这中间渠道,这些意象符号与叙述主体沟通起来,因而整个作品显得结构规整、浑然一体。
视角选择的对称性与自觉性:由于文本中结构范式的特点,使得叙述者的叙述视角与主体人物的内视角等同。一般来说,情绪浓厚的小说其视角选择多倾向于内视角。内视角运用得比较成熟的作家多具有主观抒情的特性,他们所选择的题材生活容量和涵盖面不大,人物不多,线索单一,情绪较浓,具体到情绪结构的小说,其表现形式与内视角的选择具有对称性与自觉性。
就《失踪》的叙述视角而言,叙述者选择了主要人物的固定性内视角,即以作品中的主人公觉生和尚作为视点的叙述。觉生和尚既是故事围绕的中心,又是叙述的焦点;他既能观照别人在故事中的种种行为,同时又能叙述自己幽暗的内心世界,自己的情绪,甚至自己的无意识和梦境。他的视点既是流动的,又是不变的。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谈到小说的视点时认为:一丝不苟地运用我们称之为内聚焦的情况十分罕见。墨白是个注重技巧的小说家,他对视角的统一要求很严格,尤其是文中的内心独白和追忆,更是运用了纯熟的内视角,在面临一些难以处理的场景时,他采取了一些保持视角统一的技巧。
小说家的托词:当叙述者对某些视域外(包括次要人物的心理感受)的聚焦对象比较模糊或不甚明了时,叙述者就以假设的形式,运用表态性词组,如“好像”、“仿佛”等模态语码表述,可称之为“小说家的托词”。如“觉生好像看到一群带了面具的村人在火光里舞蹈,好像看到了许木匠那驼着的背。”这是带有主观性的内视角,既可视为幻象,又可视之为实际行为。墨白正是运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视角,来掩盖内视角使用时的一些不足,并以这隐蔽扭曲的模糊视角来发挥内视角所具有的功用。
信息预叙:在《失踪》中,小说家为了提供较多的信息量,并给予作品以暗示,有时采用预叙的手法,这种叙述手法提供的由于是隐含的暗示的信息,因而仍应称之为不严格意义的内视角。三藏法师画给山川丘的去龙泉寺的地图,已为后来的觉生和尚领日寇进入沼泽作了预告。而觉生和尚的梦,这一潜意识的心理活动,也预示了主人公的结局将要在血的溅喷中消灭侵略者。但叙述者是极狡黠的,他为了内视角的统一,也为了预叙的更加隐秘,又故意伪装成这超自然的梦,梦并不能准确地预示人的未来,所以梦中觉生和尚插入山川丘背后的刀,异化为现实中山川丘将刀插入主人公的背上。这预叙信息的错位,使读者意识到所谓超自然能力的梦,实质上是受觉生和尚的认知能力限制的,它同样无法超越现实。这种预叙,拉开了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使我们看到叙述者是超过主人公的认知能力的;但另一方面,又让我们感到这种叙述信息还是人物后来的行动,所以他们还应该是在不严格的意义上统一的。
情绪语言:《失踪》在墨白悒郁负重的视野里,染上了历史的悲怆色彩。开篇“日落时分”的叙述就给作品定下了悲怆、苍凉的基调,这种基调是与作品的结构相伴生的,也是叙述者语言选择的情绪化特征之呈现。
我们以往对文学语言的评论,总是把它放在文学的从属地位。我们在给文学下定义时,讲的是“语言的艺术”,如果有人胆敢说“文学是艺术化的语言”,那简直是背逆常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形式,是具有独立个性的文化产物,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得到印证与传播。语言与文学成了互相占有的协同关系,语言是文学生存的载体,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文学。这样就得出一个结论:作家的情感体验,先诉诸的是语言而非文学,文学语言在形成文本之前,就已具有了独特的个性。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文体,情绪结构小说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基质。
文本是具有潜在意义的语言实体,读者对于文本的接受,首先意味着对于文本语码的破译。因此,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存在着语言距离,而这种距离又取决于各种语言表现方式之间的差异。小说语言作为转述语言,在形成文本的过程中,具有内在的律动性与一定的必然性。
《失踪》中所采用的转述语式,多为描述式转述语、直接引语式转述语、间接自由式转述语。
描述式转述语:因其包含的信息量相对丰富和语言信息传递的相对复杂,而更容易接近读者,又因《失踪》中描述性词汇选择多色彩性与情感性,所以这种描述也就成了情绪描述,如:
他们(就)看到(有灰红色的)光从(漆黑的)岸上的村子里发出来,那光(越来越亮)冒出一股(滚滚的黑)烟,许木匠手中的浆停住了,他(呆了半刻不由得惊)叫了一句,“爹——”(就)跳下水朝岸上游去。
作一粗疏的比较,若划去括号内的文字,就成了陈述语言形态。这种语句只能让读者获得一个事件过程的客观印象,而难以就这一事件过程进行价值判断,更难以透出情绪,发生感情交流,因为这里读者得到的信息量很少,而且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任何情感的叙述者。若补足括号内富有情绪色彩的词汇,读者得到的信息就有了不同,就可以进入叙述者在作品基调中设置的氛围。当然,仅是这种比较,文本选择的语言方式仍无法显示,但通过这一手段,却能让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出情绪语言与不带情绪的陈述语言之不同。
直接引语式转述语:主要体现在对话中,它是带引号的直接引语,直接记录人物语言(说话人在这种语式中自称“我”),具有直观、明晰的特点。它一方面是人物语言的直录,是独立于叙述者之外的;另一方面,它是被转述的对象,服从于叙述结构的总要求,因此在叙述者控制的范围之内,它有利于说话人性格的显现,并通过言词、语调、语境传达出人物的情绪。
觉生的牙齿磕打了一下:“没有钥匙……”不情愿而又无奈,既畏怯又不愿屈从,后面的省略号,是被山川丘武断地打断了的表述。
间接自由式转述语:主要运用于追忆、幻想与梦境中。由于表述这些现象时主要采用间接内心独白手法,所以句式选择上也以间接自由式转述语为主。在叙述中,叙述者又将这种句式与正常的叙述语流融合在一起。由于不必加引号,所以叙述语流很顺畅地滑入正常叙述,而不给人以叙述中断的感觉,这种间接自由式的转述语因其是凭借叙述者调控的,所以它仍被赋予了叙述者的情绪,并应和着叙述基调。它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切合人物的心理状态,符合特定的叙述基调与人物的情绪,便可插上想像的翅膀。因此,它不像直接内心独白那样模糊和晦涩,而是具有情绪流动的逻辑性。这种情绪语言还带有随机性和非线性的特点,如觉生和尚在看到竹叶时,就联想到淡淡的清香,并以此为契机进入到回忆中,使心理时空发生转换与调节,并产生怀恋法师的情绪。
综上所述,《失踪》的情绪语言是一种充满情感、包容着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的语言。
众所周知,撇开语言环境,孤立地分析语言特征是比竹篮打水容易不了多少的事。正如“杭育杭育”的喊叫声,孤立地看它仅是一个摹声词,无任何情感附丽,但若将其放在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中,则寄予了一种亢奋的情绪。这就是语境的作用。具体说来,它包括两方面:人物语言与产生人物语言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失踪》很注重语境的营造,每当人物的对话出现时,总配合以特定的语境态势,使人物的情绪流露出来。
“我出生在奉天,一直在那儿长到九岁,而后跟着家父到国清寺一住就是三年。你是佛门弟子,特别是法师的门徒,应该知道国清寺不但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而且是天皇帝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庭,所以,在我一走进这座寺院的时候,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山川丘说完又拍了一下觉生的肩,而后一边走一边舞动着手说,“这大雄宝殿,这藏经楼,太相似了。”
乍看起来,这段话似乎是山川丘与觉生和尚在探究两国佛教文化的渊源,而且山川丘对中国佛学文化颇有造诣,并具有一种崇尚之心。但时代环境是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中国的领土,还进行着文化的掠夺,山川丘则是这掠夺者中的代表符号。而觉生和尚则是作为一个被奴役、被掠夺、被侵略的对象出现在这一语境中的。这就使我们不难看出山川丘作为一个侵略者的阴险、狡猾、贪婪的本性。
《失踪》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91年第9期,尽管它属于墨白的前期创作,但现在读来,小说里各种叙事手法的并置仍然让我们感到新鲜。《失踪》里各种叙事手法的并置,对墨白后来的小说创作在文本上有着导向作用,这篇小说对墨白小说叙事风格的形成是一次最重要的实践。
[1]王彪.新历史小说选[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
[2]墨白.事实真相[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
[3]墨白.霍乱[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
[4][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C].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 《印象:我所认识的墨白》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