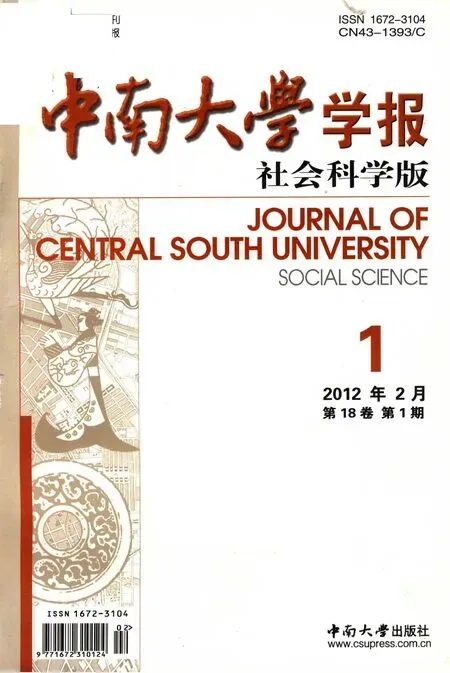基于“抗战”“文学”视点的“抗战文学”论析
刘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广西柳州,545007)
一
以“抗战”眼光来看,学术界此前对于“抗战文学”的认识并不明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抗战文学”至今尚未具有特指的意义。有的人以时间为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1](1−204),这当然包括非抗战内容的文学作品在内,实际上并非专门研究抗战文学;有的人则从作品的内容出发,把五四之后至抗日战争结束期间与抗战相关的作品统称为“现代救亡文学”[2](337−387),时限上并不与“抗战”相吻合;有的人又把目光对准“七·七”之后至新中国建国之前,称之为“抗战的民主的文学运动”,[3](129−200)这不但把许多非抗战内容的作品,还把许多非抗战时期产生的作品归纳其中;有的人却又把“七·七”之前的作品,归为“抗日救亡”作品,而把“七·七”事变之后的作品,称为“为民族解放而歌的抗战文艺”,和“在‘为工农兵服务’方向下的解放区作品”,以及“皖南事变以后的国统区文艺”,[4](437−649)这表现出并未确立真正的“抗战文学”的概念。此外,网上又有人把建国后冯德英的《苦菜花》等,甚而当今以抗战为题材的电影和小说,统归为“抗战文学”,这显然是把具有特定写作时限的“抗战文学”,同历史文学混淆起来;当然,还有人以八年抗战为时限,收集此间抗战题材的作品,称之为“战时文学”。[5]这最后一种似乎准确些,只是,这又忽略了“八年”之前的相关作品,把它们排斥在抗战文学之外,又造成了对此间文学“抗战”意义的轻视与忽视。
这些事实表明,在此前的研究中,学术界并未从“抗战”的角度来审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作品。同时也表现出,学界对于“抗战文学”还缺乏明晰的认识。
当代美国批评家科林·马加比 1999年在埃克塞特大学所作的题为《为批评辩护——为纪念加拉斯·罗伯茨及托尼·坦纳而作》的讲演中说过:“建立一种研究,一般说来首先是要在对特殊的用词的构成的分析之中,找到它最基本的合理性。”[6]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科学的。因此,抗战文学应当具有以下“质”的规定性才能体现出“最基本的合理性”:一是“抗战”的内容;二是“抗战”的时限;三是写作和发表的时间。从内容上看,“抗战”的内容应该包括前方、后方,部队、民间,正面和侧面对日寇的斗争,不论以何种方式,只要指向抗日就可归属。从时限上看,作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是从“七·七”开始的,但民间的反抗却是在“九·一八”前后就出现了。萧红于 1935年出版的小说《生死场》叙述的就是“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沦陷后“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沦于奴隶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辗轧,……的人民,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刻……在生与死两条界限上辗转着,挣扎着,……或者悄然地死去,或者是浴血斗争着……的现实和故事”[7]。从写作、发表时间看,应该是从“九·一八”到1945年抗战结束期间所创作、发表的作品。如为之后所写,那就只能算作历史题材的作品了。所以,以“抗战”眼光看来,所谓“抗战文学”,就应该是指称上世纪“九·一八”前后至 1945年抗战结束期间创作的,直接反映各界民众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所作的斗争,或者描写与抗战相关的生活,以抗日为思想指向的一切文学作品。“抗战文学”有特定的写作背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和肆意欺凌),有特定的创作思维(文艺服务于抗日救亡),有特定的作品题材(包括各种方式和各个侧面的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斗争),有特定的思想情感(对侵略者和汉奸的仇恨,对有碍于抗战的一切行为的愤慨和反对,以及对积极抗战者的赞颂)。正因这样的作品具有特定的含义,所以它在文学史上具有特定的意义,占有特殊的地位。
二
以“抗战文学”的眼光来看,“与抗战无关”和“服务于抗战”,都是对“抗战”和“文学”的割裂,实际上两者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在抗战文学的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武汉失陷后开展的文学“与抗战无关”还是“为抗战服务”的论争。梁实秋首先在重庆自己主编的《中央日报》“平民”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批评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他们的作品是“空洞的‘抗战八股’”[8](9)。此后的1931年1月,沈从文又连续发表文章,称文学只有“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那些战争的浪漫情绪”,“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8](9)。而侍桁则在1940年的《文艺月刊》上,称作家们“对于他们的过度的抗战服务的热情有加以深刻检讨的必要”[8](10)。他们的说法立刻遭到了罗荪、陈白尘、宋之的、张天翼等人的反驳。而后来的文学史家也都一致谴责和批判梁实秋、沈从文们。当然,这一谴责自有其道理,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高喊“与抗战无关”完全是错误的,是文人们丧失社会责任感和爱国心的表现。但是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观察点上回眸这一历史事件时,便又会发现,这次论争其实质并非不同政治立场的搏击,而是不同眼光对文学的不同要求的交锋。罗荪等人是站在政治的即抗战的立场说话,而梁实秋们则是站在文学的立场要求文学。前者强调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强调宣传教育功能;而后者则主要着眼于文学的艺术质量,着眼于文学的主体性,他们“与抗战无关”的主张,主要是面对当时为抗战服务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状况而发的。现在看来,两者都有片面性:强调要服务于抗战的人,忽视了文学的主体性,这一主张发展到40年代,形成了文学的“工具论”和“武器论”;强调“与抗战无关”的人,则忽视了或者说不承认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性,抛弃了文学应有的思想正义的灵魂,也无视政治所具有的文化性。实际上,无论是“服务论”者还是“无关论”者,都是把“抗战”(政治)和“文学”割裂开来。
而我们完全可以把两者统一在一起。这是因为:一方面,“抗战”的思想内容和“文学”的主体性,都是“抗战文学”所应该具备的品质,两者的结合才是它的应有之义。而所谓“抗战的思想内容”是广泛的,应该包括前方与后方、军队与民间的正面与侧面的斗争。其感情,也应该包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对汉奸的忿愤,对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和行为的谴责,对积极抗战者的赞颂,对一些软弱、忍耐的民众的怨艾和嗟叹……等等。这样,就能给“文学”以许多选择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以致不与文学的主体性、多样性发生矛盾。而所谓“文学的主体性”,也就应该体现在作家对于上述不同内容的选择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以及语言、体式和作家个人风格等方面的选择上。这样,就不但能解决怎样为抗战服务的问题,而且也能实现文学的多样化。事实证明,这种要求是能够做到的。另一方面,“抗战”也并非一般的阶级、民族之间的斗争,而是人道与反人道、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抗战的“政治”本身就蕴涵着文化的内涵。反映抗战,完全可以由政治走向文化,从而体现出丰厚的文化意蕴。西方许多描写战争的作品,例如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不就是既是政治的同时也是文化的文学吗?
三
以“文学”的眼光看: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的作品表现的多为悲愤之情,而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作品多问世于《讲话》之后?为什么许多作品总是把抗日和揭露国民党的丑恶结合起来?为什么典型形象都是反面人物?
我国的抗战文学是丰富多彩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前,正面描写抗日斗争的作品并不多,而且,表达的多为悲愤之情。
先看“九·一八”至“七·七”之前的作品。小说方面,萧红的《生死场》“以纤细而又带有几分粗犷的笔触,在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乡间生活的沉滞和闭塞”的同时,“又写出了这些‘愚夫愚妇’们的民族和阶级意识的最初觉醒”[2](364),鲁迅称其写出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9],作品的感情是悲愤的。与此同时,舒群的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中篇《老兵》,黑丁的短篇《回家》,端木蕻良的短篇集《憎恨》,罗烽的中篇《归来》、短篇集《呼兰河边》,白朗的短篇《轮下》,“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东北人民的苦痛和抗争,也渗透了作者自己的悲愤的感情”[1](368)。此外还有夏衍写于1936年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真实地反映了上海日本纱厂女工的非人遭遇,愤怒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共同压榨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戏剧方面,1931年由陈鲤庭执笔、集体创作的独幕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叙述了“九·一八”之后,一对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父女,从东北沦陷区逃亡来到内地,演出时因饥饿难忍,女儿晕倒在地,后来父女叙说了东北沦陷后他们的悲惨境遇,激起观众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慨。此外,还有田汉的短剧《战友》和《回春之曲》,它们写的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停战、反动政府签订卖国条约后爱国青年们的悲愤心情和抗战要求”[1](383)。此外,还有夏衍创作于1936年冬的多幕历史剧《秋瑾传》,在赞扬民主革命者秋瑾的同时,无情地鞭挞了媚外残内的汉奸走狗。诗歌方面,田间写于“七·七”之前的诗集《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表现的是“侵略战争给祖国农村、尤其是东北大地带来了苦难”[8](43)。这些作品都呈现出民间生活的情状,内中既有我国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也有他们的挣扎和反抗,所以都突出地表达了悲愤的情怀。总的说来,上述作品所写的都是情绪上、心理上的“抗战”,也可以说是作品从侧面表现了抗战的主题。
期间,正面描写抗日斗争而且较为引人注意的只有一部作品,即萧军的《八月的乡村》(1934),记叙的是一支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和日伪激烈的斗争中,经受了各种困难和挫折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10],其情调,依然是悲愤交加的。
再看看“七·七”之后的作品。就戏剧而论,夏衍写于1940年的四幕剧《心防》,表现的是上海沦陷后,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为坚守这个城市‘五百万’中国人心里的防线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其情感是深沉而悲愤的。其写于1942年的五幕剧《法西斯细菌》,“主要通过细菌学家俞实夫由不问政治到‘再出发’的曲折的觉醒过程,严正批评了超阶级、超政治的科学至上主义,揭露了法西斯主义与人类一切进步事物为敌的反动本质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8](84−85),其感情同样是愤慨而又悲酸的。丁西林写于 1939年的四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写的是留学回来的梁治和高中学生梁玉断然与做汉奸的父亲决裂,而年事已高的母亲,也知道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气节”,于是毅然和子女一起离开上海前往内地,其感情当然也是愤慨而悲壮的。沈浮的三幕剧《重庆二十四小时》,描写的是一个从东北流浪到重庆的女青年,识破了邪恶势力的圈套,毅然投入抗日的戏剧工作,作品在对邪恶势力表达憎恨的同时,依然流露出悲伤的情怀。此外,郭沫若自1941年起,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写出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六部历史剧,“反对侵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主张坚持节操,是这些剧本从不同角度所表现的共同主题”[8](96)。欧阳予倩自1937年始,先后改编成多个剧种的《桃花扇》,阿英也先后写出了南明史剧《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等,这些作品都大力宣传民族气节,而内中又都流露出悲愤的情调。
小说方面,丘东平在抗战初年所写的短篇《暴风雨的一天》,“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塑造了狂风暴雨中坚守岗位的少年游击队员形象”,反映出“战争初期人民奋起抗战、慷慨悲歌的感人情景”[8](110−111)。吴组缃的长篇小说《鸭嘴崂》(《山洪》),表现的是抗战初期皖南农民坚持中国人要“争口气”的想法,投入民族解放斗争的历程。丁玲1940年底写成1941年6月发表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叙述的是抗日根据地农村姑娘被日寇侮辱后坚持送情报的故事。还有姚雪垠的短篇《差半车麦秸》,讲的是一个绰号叫“差半车麦秸”的农民的故事:他抱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思想参加了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却仍然挣扎着说要“留下来”,不愿退下火线。这些作品尽管内容不同,人物的精神各异,但作品的情调或多或少带有“悲”的成分。
相反,1942年《讲话》之后的作品情况却大不相同。邵子南的小说《地雷阵》,叙述晋察冀民兵开展地雷战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的故事。杨朔的短篇小说《月黑夜》,叙述一位革命老人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接送八路军小分队执行任务,途中被敌人抓住杀害的故事。华山的《鸡毛信》,叙述儿童团长海娃,在一次反‘扫荡’中,为了送一封鸡毛信(表示十万火急),一路上和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克服困难和险阻,把情报送到八路军手里的故事。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叙述一次日寇的突袭中,一个活泼的小孩独自一人机智地掩护区交通员,在敌人的诱骗和威逼下逃走的故事。这些作品虽然写了牺牲,写了艰难困苦,但是因为革命的亢奋情怀压倒了悲伤,所以作品表达的不再是悲愤,而代之以激愤之情。还有孙犁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等,“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抗日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的抗日战争。”[8](333)它们更是洋溢着乐观的情调,散发出浪漫主义的气息。
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为什么《讲话》之前抗战文学表达的是悲愤,而之后表现的却是激愤、奋发和乐观呢?
在笔者看来,其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在“七·七”全民抗战之前,抗战的形势严峻,作家们往往对侵略者的行径虽然愤慨但却无力;二是“七·七”后的抗战初期,作家们对抗日的前途信心不足,因而悲愤难免;三是到了《讲话》发表之时,抗日战争已经从防守阶段到了相持阶段,抗战的形势比以前推进了一步,这给我国人民包括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抗战胜利的信心。而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11](53)。怎么变化,怎么改造呢?毛泽东提出: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11](79)。与此同时,他还一再特别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站在党的立场上”[11](49),而作品的感情、情绪就是立场的重要表现。在这种情势下,作品表达激奋、向上的情怀是很自然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讲话》无疑对我国的抗战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讲话》是抗战文学思想情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当然,这转变主要表现在抗日根据地的创作上,因为表达激愤、乐观情怀的作品,主要就是产生于抗日根据地的作品。
以上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这些反映抗日斗争的作品,许多都是把描写抗日斗争和揭露国民党官僚、土豪劣绅的丑恶行径结合起来,甚至是以抗战为背景,主要写国民党的反革命活动。其中最有名的是张天翼写于1938年的《华威先生》和沙汀发表于1940年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前者揭露国民党官僚对抗日战争包而不办、表面积极实际压制的消极态度;后者则展现抗战时期,国民党乡绅借抓壮丁之名徇私舞弊、敲诈勒索的恶行。此外,艾芜的长篇小说《故乡》写抗战初期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余峻廷回到家乡,本想大干一番抗日的宣传事业,可是当他接触了当地的许多官绅之后,便感到无可奈何,感叹“我们的家乡,真是黑暗,黑暗,第三个黑暗”。沙汀的长篇小说《淘金记》,写地主劣绅们因为争发国难财而起了内讧。宋之的写于1940年的五幕剧《雾重庆》,同样是“揭露和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的[8](88)。陈白尘写于1939年的多幕剧《乱世男女》,也“描写了抗战乍起由南京逃到‘大后方’的一群都市‘沉渣’的形形色色丑态”[8](90),这“沉渣”就是指国民党的官僚和党棍。而茅盾写于1941年孟夏的长篇小说《腐蚀》,以皖南事变前后‘陪都’重庆为背景,暴露了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的罪恶和他们反共反人民、投降卖国的本质,被称为“抗战期间以现实为题材暴露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2](381)。即使是写于“七·七”之前,正面描写抗日斗争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是一方面写出“东北人民反抗日寇侵略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而另一方面,也同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3](216)。
为什么会如此?
一是出于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突出的恶劣表现,即使是在“七·七”之后,蒋介石、国民党虽然和共产党签订了抗战协议,却又从1939年起,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这使许许多多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本性,认清了这些人对于抗战事业的严重危害,从而决心揭露他们。沙汀说过:“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将一切“新的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8](133)。二是出于共产党的号召,毛泽东在《讲话》之前的1941年5月就说:国民党“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12]正是这一号召,鼓动着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注意观察和表现国民党官僚的真面目。三是国统区的作家对于国民党的内幕有足够的了解,比如茅盾,就有论者指出,他“所选的题材(指《腐蚀》——笔者)……是十分熟悉的”。[13](177)这又表明,他们具有揭露国民党官绅丑行的条件。
当我们检视抗战文学时,还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在这些为数众多的抗战作品中,所刻画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丰满的人物形象不多,真正能够站立在文学史上的人物形象,大概只有华威先生(张天翼《华威先生》)和邢么吵吵(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凑巧,两者都是国民党身份的人物形象,学术界评论前者是“抗战初期一个文化官僚的典型形象”[2](425)。笔者认为,后者是一个不顾国难、借公行私,横行霸道,痞气十足的国民党土豪的典型。前者具有官场的文化气息,后者则具有乡间的污浊味。这两个人物形象,不同于文学史上包括《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古典文学中所有的官绅形象,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他们是具有抗战时代特点的、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类型性人物。
为什么典型形象都是反面形象?一是因为作家们囿于生活。不说《讲话》之前,就是《讲话》之后的作家,到抗战前线的人也不多,所以对于正面的抗日人物还不够熟悉,很难写出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形象,特别是英雄形象。二是因为他们对于国民党包括上下层人物都特别地注意审察,对于这些人的行为、心理,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为他们塑造反面典型提供了可能,张天翼和沙汀都是如此。如沙汀说: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悲剧”。[2](427)因而,遵从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也就自然地把他们描绘出来。三是因为他们厌恶这些人物,应该说,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并不都是持有无产阶级立场的,但是进步作家都具有爱国之心,他们是有意把国民党官绅塑造成反面形象,借以鞭笞国民党的。正如有的学者评论《在其香居茶馆里》时所说:“作品的锋芒”是“指向兵役问题上弊政产生的根源——国民党政府。”[8](135)
四
再以“文学”的眼光来看我国“抗战文学”的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发生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我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遗憾的是,由于资料所限,我们难得读到国外战时所写的反映这次大战的作品。我们容易看到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前苏联作品如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等,其他都是战后多年创作的,应视为历史文学的小说和电影,如前苏联的《莫斯科保卫战》《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南斯拉夫的《桥》,以及美国的两部曲小说《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等。但是可以肯定,我们有值得骄傲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抗日战争,既是全民的军事抗战,也是全民的文化(文学)抗战。据统计,1939年以前,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所创作和演出的比较成功的戏剧,就有 30种以上,包括独幕剧、活报剧、小歌剧等多种形式[8](22),同时,“抗战初期,人们纷纷以写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服务于抗日斗争,其中大量的是青年作者,也有长期未写诗或从未写过诗的作家”。[8](23−24)更有民间的快板、民歌、说唱和短剧,可谓形式多样,色彩纷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就战时创作而言,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再认真体味一下,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突出的文化性。从文学史收录的作品看,都是一方面极力展示侵略者非人道的残暴行为,展示我国人民所受的沉重灾难;另一方面极力展示我国人民反抗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从“寻求正义”的角度,把抗日战争表现为正义对邪恶的斗争,做到了政治性与文化性的统一,也就是从政治走向了文化,是政治与文学的结合。同时,许多作品,如沙汀、孙犁、萧红、田间、老舍、张天翼等人的小说和诗,都渗入了浓烈的地域意识和历史内涵。从中,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沙汀作品的“天府味”,孙犁作品的“荷花淀味”,田间作品的“燕赵味”,萧红作品的“黑土味”,老舍作品的“北京味”,张天翼作品中国式的“官僚味”……。这些,既表现出我国抗战文学的艺术品位,更表现出它的文化精神。学者杨义先生说:“抗战文学的文化精神史的价值高于它的文化艺术史的价值”,[14]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其次是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作品都遵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表现生活,无论是侵略者的嚣张和凶残,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还是我国民众的反抗行为,特别是作品所表现的我国人民先是悲愤后是激昂的情感,都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特色。而理想化的色彩,只有在《讲话》发表之后创作的某些工农兵文学作品中才有所体现,如《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雄传》)以及孙犁的《荷花淀》等。当然,即使它们也只是在生活的基础上,表现得更理想一些,或者注重意境的营造,散发出某些浪漫的气息而已。因此所有这些作品都给人以真实感和亲切感。在这些作品中,现实主义既是一种创作方法,又是一种创作精神。
最后是色泽分明的人物描写。我国的文学传统是,在人物描写方面表现为所采用的主要是以《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所代表的色调模糊的手法,比如李逵、林冲、宋江,曹操、刘备、诸葛亮,还有林黛玉、贾宝玉等人物,都不是单纯的“好”或“坏”的角色,而是优缺相杂的复合型人物。然而自清末《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出现之后,创作界便慢慢风行另一种人物描写的色彩分明的手法,即对人物思想品行的描写,进行好、坏的鲜明对比。这种手法,在五四新文学之后、抗战文学之前,革命文学就广泛采用了。抗战文学继承了这一手法。这些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如《雨来没有死》中的雨来,《鸡毛信》中的海娃,还有《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中那同汉奸父亲决裂的两位青年,甚至《差半车麦秸》中那位绰号叫“差半车麦秸”的农民……,都只是写出了他们的正面的思想品质(只有《四世同堂》例外),即使是那些愚昧的人们,当他们觉醒之后,他们的表现也都完全是正面的。相反,那些国民党官僚、党棍和乡绅、土豪,无论是华威先生,还是邢么吵吵,还有那联保主任方治国,或者是艾芜《故乡》中的“反动腐朽的社会势力”《等太太回家的时候》中的汉奸,都完完全全是坏人。正因如此,抗战文学的人物显现出色泽分明的面貌。
站在今天的观察点上,看看几十年前我国的抗战文学,我们感到自豪,就其总体而言而不是就某些作品而言,它多了这之前文学中少有的浓烈的民族正气,少了这之后工农兵文学强烈的工具性,给人以更多的亲切感和文学味(大概只有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文学气息少些,《吕梁英雄传》等政治功利性强些)。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有才华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和风格,诸如田间的激越情怀,艾青的深沉情调,萧红的散漫浑浊之风,张天翼的尖酸刻薄之气,孙犁的浪漫主义气息,艾芜的凝重风韵,沙汀的辛辣格调,老舍的古朴京味……
抗战文学是我国重要的文学类别。即使不从政治角度看,而单从“文学”着眼,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重要的。就它的波及面和影响力来说,远远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种反映“抗战”的文学(如南宋和清末的抗战作品)。如果说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反侵略战争,那么抗战文学就是我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反侵略文学。笔者认为孟繁华教授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一种能够称得上经典的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13]这话不够准确。这是因为他把侧面反映抗日战争的《华威先生》和《在其香居茶馆里》排除在“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之外,其立论的根据只是战后创作的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和《平原枪声》等作品,与本文所主张的“抗战文学”的含义不符。其实这两篇小说完全称得上是抗战文学的经典作品。
[1]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下)[M].北京: 作家出版社,1956.
[2]冯光廉, 刘增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3]冯光廉, 等.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M].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4]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5]张燕.山西抗战文学优秀作品首次结集出版[EB/OL].山西新闻网, 2010-09-27.
[6][美]科林·马加比.为批评辩护——为纪念加拉斯·罗伯茨及托尼.坦纳而作[C]// 王逢振.2002年度西方文论选.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3: 156.
[7]肖军.〈生死场〉重版前记[C]// 萧红.生死场.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1.
[8]唐弢, 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三)[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9]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C]// 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22
[10]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C]// 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9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7:740
[13]孙中田.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14]作者不详.抗战文学作品: 对人性的挖掘还欠深度[N].中国读书报, 2005-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