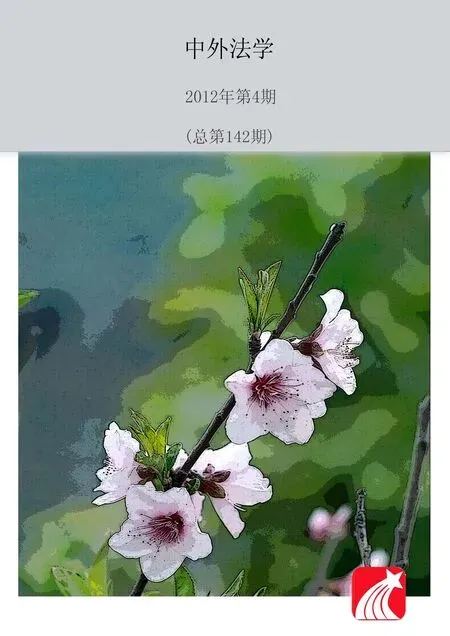论过失犯的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
陈 璇
一、 问题的由来
对于过失犯不法的成立来说,除了要求①行为违反注意义务以及②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事实因果关系之外,还要求③行为的注意义务违反性与结果之间必须存在规范上的关联。其中,第③个要件是现代过失理论发展出的归责要素,它源自于过失犯中被容许之危险的存在。在现代社会中,刑法在保护法益不受侵害的同时还必须防止因刑罚制裁过于严苛而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因此,立法者在创设某一注意义务规范之初就注定不可能以避免相关领域内的所有法益侵害结果为其目标;相反,他必然会在对法益保护和社会发展进行权衡的基础上将注意义务的规范效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由此容许部分法益侵害危险的存在。所以,即使确定行为违反了注意义务,同时行为与现实发生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也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如果该结果并不处于注意义务效力的作用范围,而是处在被容许的危险之中,那么由于它本来就不属于注意义务所意图和能够防止的对象,义务违反也并非引起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故无法从客观上将之归责于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例如,如果立法者想彻底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他本可以对一切高速驾车的行为均加以禁止。但这样一来势必阻碍交通运输的正常进行,故立法者在权衡利弊之后允许机动车司机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高速行驶。于是,凡是关于最高限速的注意义务无法避免的法益侵害都在注意义务规范的效力范围之外,从而属于立法者有意加以容许的危险。因此,若虽然某个司机违反最高限速驾车并引起了交通事故,但事后证明法定的车速实际上对于阻止该结果的发生也无能为力,那就说明该结果超出了立法者为注意义务规范所预设的能力范围,结果的发生与注意义务的违反并无内在关联,故对于违反义务的行为也没有处罚的必要。可见,正是注意义务在规范效力上的有限性决定了由违反注意义务之行为所引起的结果未必能在规范上归责于行为,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或者说注意义务的结果避免可能性)是过失犯不法构成中需要专门加以研究的一个独立要件。正因为如此,我国刑法第16条明确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据此,当注意义务违反(即过失)并非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时,不成立过失犯。[注]我认为,注意义务的违反与结果之间欠缺规范关联的情形应当属于刑法第16条所规定的不可抗力,而非意外事件。因为,虽然在绝大多数的相关案件中,行为人确实对导致过失犯罪无法成立的事实因素(如后述案例中路面已濒临垮塌、被害人处于醉酒状态等)没有预见可能性;但在这种情形下之所以不成立过失犯,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行为人对该因素无法预见,而是在于该因素的出现导致注意义务规范避免和防止结果发生的能力不复存在。故刑法第16条所规定的不可抗力实际上包含两种情形:①虽然某一举动引起了法益侵害结果,但外部因素的介入使该举动脱离了行为人意志支配和控制的范围,故不能将之视为刑法意义上的行为。我国刑法学通说历来只把这一情形解释为不可抗力。(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页71、126;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56-157、368-369;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138。)②虽然行为人主观上有过失,但由于外部因素的介入导致注意义务规范对于抵御损害结果的发生已无能为力、合义务的行为已无法抗拒和避免法益侵害的出现,故不能从客观上将结果归责于该过失行为。此外,我国刑法关于过失犯的诸多条文都使用了“违反……法规∕规章制度∕规定,或严重不负责任,因而∕致使发生……事故或者造成……后果”的用语(例如刑法第131—137、139、335、338、408、409、419条等),从而表明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是相关犯罪的必备构成要件要素。
现在,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来说,最为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结果与注意义务违反之间是否具有必要的关联,怎样判断结果是否处于规范的效力范围之内呢?这是在战后德国的客观归责理论发展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但它长期以来并未受到我国刑法学的重视,[注]例如,我国学者在论述交通肇事罪等具体过失犯罪的客观方面时,往往只要求①必须有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以及②该行为必须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并未提及行为的义务违反性应当与结果具有关联。(参见高铭暄、马克昌,见前注〔1〕,页399、403、405。)虽然张明楷教授在此之外还强调了“结果必须由违反规范保护目的的行为所引起”(张明楷,见前注〔1〕,页541。),但他所说的规范保护目的与注意义务的结果避免可能性并不是一回事。有的学者尽管初步论及了注意义务的结果避免可能性问题,但却将“义务违反与结果的规范关联”和“违法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混为一谈。(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页180。)直到近年才逐渐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注]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305-307;周光权:“结果假定发生与过失犯——履行注意义务损害结果仍可能发生时的归责”,《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车浩:“假定因果关系、结果避免可能性与客观归责”,《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鉴于该问题对于我国过失犯理论的深入化和精细化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尚有诸多难点亟须深化、不少疑点有待澄清,本文打算依次对该问题的首要前提、基本思路、判断标准以及体系定位展开系统的分析。现特将这方面的典型案例选取如下,以供下文研讨:
1.货车超载案:某一货车司机超载超速行驶,路过某一地段时,路面突然垮塌,货车翻入路旁的农田之中,将正在田间劳动的一名农民当场压死。事后查明,该路段当时已到必然垮塌之时,即使货车司机既不超载也不超速行驶,当他驶过该路段时,路面也会发生垮塌。[注]参见刘志伟、左坚卫主编:《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363。
2.载重卡车案:某一驾驶载重卡车的司机在对某个骑自行车的人实施超车时只与之保持了75厘米的车距,但道路交通规则却要求至少应保持1.5米的距离。受卡车司机超车的刺激,当时正处于高度醉酒状态的自行车驾驶者猛然向左转向,结果跌入从后方驶来的汽车的后轮而死亡。事后查明,鉴于被害人当时的醉酒状态,即便卡车司机在超车时保持合法的距离,事故也很有可能仍然会发生。[注]Vgl. BGH St. 11, 1-7.
3.山羊毛案:某一画笔制造厂的厂主购进一批中国的山羊毛,并且在未按照要求对山羊毛进行事先消毒的情况下将之交给工人加工。结果四名女工因感染山羊毛中的炭疽菌而死亡。事后查明,由于当时允许使用的消毒剂并不足以完全杀灭羊毛中的病菌,故即使厂主事先对羊毛实施消毒,被害人也还是可能染病身亡。[注]Vgl. RGSt. 63, 211-215.
4.奴夫卡因案:某一医生在对病人实施麻醉时,未按规定使用奴夫卡因,而是为其注射了可卡因,由此导致病人死亡。但事后的专家鉴定表明,鉴于该病人的特殊体质,即便遵守规定使用了奴夫卡因,病人可能仍然难逃一死。[注]Vgl. Günter Spendel, Die Kausalitätsformel der Bedingungstheorie für die Handlungsdelikte, 1948, S.65ff.
5.药剂师案:某一药剂师已开始根据医生的处方向病人出售了某种含磷的药物。但此后,应病童母亲的恳求,药剂师在未按要求向医生咨询的情况下又多次出售了该药。结果病童服药后因磷中毒而死亡。但是即便药剂师此后向医生提出咨询,医生也会同意他继续出售该药物。[注]Vgl. RGSt. 15, 151-155.
在以上案件中,虽然行为均违反了注意义务,而且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都不容否认;但由于事后的调查表明,就算行为人实施符合注意义务要求的行为,该结果也仍然可能发生,所以能否肯定义务违反与结果发生具有规范上的联系就成为疑问。
二、 前提:作为犯还是不作为犯?
在对这类案件进行分析时,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将行为人的行为界定为作为还是不作为?因为这些行为均同时包含了积极作为和消极不作为的要素。货车司机驾驶车辆、卡车司机超车、工厂主向工人交付山羊毛、医生注射可卡因以及药剂师出售含磷药物的行为无疑都属于作为;但与此同时,货车司机未遵守关于运载量和限速的规定、卡车司机未保持法定的超车距离、工厂主未事先对羊毛进行消毒、医生不注射奴夫卡因以及药剂师未咨询医生的举动又都是典型的不作为。由于不作为犯的归责要求与作为犯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不作为犯的行为人必须具备法律上的保证人地位,不作为必须与作为之间具有等置性以及只有当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确定可以阻止结果发生时才能肯定不作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注]Vgl.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T, Bd. Ⅱ, 2003, § 31 Rn. 69; Wolfgang Wohlers, NK-StGB, 3. Aufl., 2010, § 13 Rn. 4.所以对行为的性质加以确定是我们展开进一步讨论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标准问题,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学说:①社会意义或法律非难重点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和部分学者认为,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分所涉及的并非事实问题,而是价值评判问题,故对于同时包含作为和不作为要素的行为来说,应当以社会意义或法律非难的指向重点为标准决定其性质。[注]Vgl. Thomas Fischer, StGB, 57. Aufl., 2010, vor § 13 Rn. 17; Schönke / Schröder / Stree / Botsch,StGB, 28. Aufl., 2010, vor § 13 Rn. 158.②作为的因果关系标准说。目前多数学者主张,只要行为人积极投入力量的行为要素与结果具有合乎法则的因果联系,就应当将行为认定为作为;只有当积极的举动缺乏与结果的因果关系或因其他缘故不成立犯罪时,才可以补充性地考虑不作为犯的问题。[注]Vgl. Claus Roxin, Pflichtwidrigkeit und Erfolg bei fahrlässigen Delikten, ZStW 74 (1962), S.415; Georg Freund, MK-StGB, 2003, § 13 Rn. 8ff; Thomas Weigend, LK-StGB, 12.Aufl., 2007, § 13 Rn. 6f; Wohlers (Fn. 〔9〕), § 13 Rn. 7.
我认为,作为的因果关系标准说是值得赞同的。理由如下:第一,所谓“社会意义或法律非难重点”的区分标准过于模糊,由此得出的结论也难免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该说的首倡者Mezger认为,前述山羊毛案和药剂师案涉及的是不作为,因为法律对被告人予以非难的原因不在于他将羊毛交给工人加工以及出售药物,而是在于他未对羊毛进行消毒以及未事先向医生咨询。[注]Vgl. Edmund Mezger, Strafrecht, 3. Aufl., 1949, S. XIX.若将该观点贯彻到底,那就应当认为,在载重卡车案中,由于法律非难的重点不在于超车而在于未保持合法距离,故应将司机的行为认定为不作为。然而,Mezger却提出:在该案中,尽管非难的对象是行为人未保持合法距离的行为,但他毕竟是以积极超车的方式导致了自行车驾驶者的死亡,这才是案件事实的关键所在,因此还是应将其行为认定为作为。[注]Vgl. Edmund Mezger, Anmerkung zu BGH, Beschluβ v. 25.9.1957, JZ 1958, S. 282.但是,为什么法律非难的重点在前两个案件中是行为人不遵守注意义务的事实,而在此案中又变成了积极引起结果的举动呢?由此可见,“法律非难重点”的标准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只不过是一种全凭感觉的非理性判断。”[注]Roxin (Fn. 〔11〕), S. 418.第二,法律非难重点说颠倒了犯罪判断的阶层顺序。区分作为和不作为是我们在进入构成要件的实质性判断之前就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但法律能否对行为予以非难,其非难的重点何在,这是只有在不法和责任判断全部结束之后才能确定的问题。因此,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可非难性这样一个责任论中的重要规范概念竟然可以成为用于解释客观构成要件以及决定事实问题的标准呢?”[注]Günter Spendel, Zur Unterscheidung von Tun und Unterlassen, in: Festschrift für Eberhard Schmidt, 1961, S. 191.第三,按照法律非难重点的标准,由于一切过失犯均以行为人不遵守某一注意义务为其要件,而法律评价和关注的重点又必然在于注意义务的违反,所以就会得出一切过失犯均是不作为犯、只有在行为人具有保证人地位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过失犯的结论。但实际上并无任何学者赞同这一结论。第四,在刑法的规范评价中,作为与不作为相比具有相对优先的地位。事实上,“以实现刑法上有重要意义之结果为指向的因果流程基本上都包含了一系列的作为与不作为。”[注]Weigend (Fn. 〔11〕), § 13 Rn. 7.由于在某一时刻往往存在多种行为的可能,所以当我们实施某个积极作为(例如举枪向他人射击)时,其背后也必然蕴含着大量的不作为(例如,没有放下枪支、没有向被害人发出警告、没有离开现场等)。但是,因为积极作为的举动毕竟对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起着最为直接、明显和有力的推动作用,故刑法的关注重点首先应当选择放在作为之上,不作为只具有从属和补充的地位。这一点从不真正不作为只有在与作为犯相等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犯罪的原则中也可以看出。第五,在上述案件中,不作为的要素必须依附于作为的要素才能对结果的出现产生影响。例如,未遵守关于运载量和限速规定的事实只有置于积极的驾驶行为中才可能对路面塌陷发挥原因力;未与被害人保持1.5米距离的事实只有放在超车行为中才具有引起碰撞事故发生的危险;工厂主单纯不给羊毛消毒的行为并不会对工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只有当他将未经消毒的羊毛交付给工人加工时才能对法益侵害的结果产生现实的作用;医生未使用奴夫卡因实施麻醉和药剂师未向医生咨询的事实只有与行为人实际注射了可卡因以及出售了含磷药物的行为相结合才足以说明病人死亡的因果过程。因此,不作为的事实在这里只不过是包含于积极作为之中、用于表现作为之具体实施形态的要素。
综上所述,在过失犯领域中,当行为同时兼具作为与不作为的要素时,只要积极作为的方式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就应当首先以作为犯的标准对行为进行考察;只有当作为与结果欠缺因果关系,或者虽有因果关系但不符合过失犯的归责要件而不成立犯罪时,才可以考虑不作为犯的问题(如下图所示)。据此,在上述案件中,由于驾驶、超车、交付羊毛、注射可卡因以及出售药物等积极作为都是直接导致法益侵害发生的事实,是引起结果出现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应当从作为犯的角度出发对其加以审视。[注]在载重卡车案判决出台以前,由于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的关联尚未成为过失犯的独立要件,故德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都是通过尽量将这类案件解释为不作为犯的方式来解决义务违反和结果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如前所述,这种方法一方面容易得出所有过失犯皆为不作为犯的结论,另一方面在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问题上会采取社会意义或法律非难重点等极为模糊和随意的标准。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在关于载重卡车案的判决中指出,过失犯的成立除了要求行为违反注意义务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之外,还要求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具有因果关联。这就意味着,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本来就是过失犯的一个固有成立要件,没有必要非得先将过失犯解释成不作为犯之后才能对义务违反与结果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故该判决被学者誉为“在归责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Ingeborg Puppe, Brauchen wir eine Risikoerhöhungstheorie?, in: Festschrift für Claus Roxin, 2001, S. 287.)

三、 核心:危险升高还是确定能够避免?
以下将探讨的问题是,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规范关联的成立究竟是仅以违法行为升高了危险为要件,还是要求合义务行为必须确定地能避免结果发生。但不论采取哪一种判断标准,都首先需要对基本的思维方法问题加以厘清。
(一)基本思路:对假定因果流程的限制性运用
在引起现实结果发生的整个因果流程中,往往混杂着各种不同性质的事实,有的是结果发生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有的对于结果来说则是可有可无的因素,还有的甚至是对因果进程起阻碍作用的事实。但是,仅依靠对现实因果过程的直接观察往往很难将这些不同的事实因素区分开来。这时,就需要采取类似科学实验的做法,将待检验的事实从因果链条中暂时剥离出去,看因果过程会发生何种变化,由此来间接确定该事实在整个因果关系中的功能和地位。若当某一事实被抽取出去后,因果进程会发生逆转而无法导致结果发生,那就说明该事实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若某一事实被去除后对因果流程的发展毫无影响,则说明该事实对于结果的发生不起作用。同理,当我们想要检验某一行为违反注意义务的属性与法益侵害结果究竟是否具有必要的关联时,也必须暂时将前者从因果流程中抽取出去。但我们又不能将整个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都排除出考察范围,因为这是在客观归责之前判断事实因果关系时所采用的方法。于是,由于一方面必须采取排除性的思考方式,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因果流程中保留行为人的行为,以此单独对行为的注意义务违反性本身进行检验,而所谓“没有违反注意义务”就是“遵守了注意义务”,故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将违反注意义务的性质替换成符合注意义务的性质。换言之,应当用符合注意义务的行为取代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由此观察在行为人行为合法的条件下结果是否仍然会发生。但如此一来就不免使人产生疑虑:这会不会使本已广受批判和反对的假定因果关系又在过失犯的客观归责中死灰复燃呢?
所谓假定的因果关系(hypothetische Kausalverläufe)是指,假设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不存在,结果也会由其他因素(既可以是他人的违法行为,也可以是他人的合法行为,还可以是自然事件)引起时的因果过程。由于刑法规范不能因某一法益身陷多个危险因素的威胁而放弃对它的保护,任何在事实上引起了他人死亡结果的人也均不能以“就算我不干,其他人横竖也会杀死被害人”为由推卸自己的罪责,所以刑法理论目前一致认为假定的因果关系既不影响因果关系的认定,也原则上不影响客观归责的判断。[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168-169;车浩,见前注〔3〕,页146-148。Vgl. Erich Samson, Hypothetische Kausalverläufe im Strafrecht, 1972, S. 129ff;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T, Bd. Ⅰ, 4. Aufl., 2006, § 11 Rn. 23, 58ff; Tonio Walter, LK-StGB, 12.Aufl., 2007, vor § 13 Rn. 76; Urs Kindhäuser, Strafrecht AT, 5. Aufl., 2011, § 10 Rn. 18ff, § 11 Rn.12.但如前所述,我们在检验行为的注意义务违反性对结果的发生是否有实质推动作用时,也需要首先假设行为符合注意义务。既然在这两种假定性的思考方式中,前者受到禁止,而后者却获得允许,那么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①两种假定性的思考方式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②若证明二者确有实质区别,则问题迎刃而解;但若二者实际上并无根本差异,则需要进一步追问:在考察义务违反与结果的规范关联时运用假定因果关系思考方式的正当化根据究竟何在?
我认为,在检验注意义务的结果避免可能性时运用的方法其实归根结底并未、也不可能跳出假定因果关系的思维模式,只不过它根据规范目的的要求对这种假定因果关系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正是这种限制使假定因果流程具有了成为归责判断思路的合法资格。具体分析如下:
1.迄今为止,试图将过失犯中的结果避免可能性与假定因果关系截然分开的努力并不成功。在我看来,一些学者所列举的“区别”实际上无法将两者清晰地划分开来。以行为人违章驾车引发车祸致被害人死亡,但即便无此事故被害人也会在同一时点被其仇人射杀的案件(假定的因果关系)与山羊毛案(结果不可避免)为例,具体分析如下:①“假定因果关系往往是‘替代行为人(或事件)’,结果不可避免则是‘合义务的替代行为’。假定的因果关系是指即使没有行为人,其他人或者事件也会引起抽象意义上的相同结果;结果不可避免是说即使行为人遵守了注意义务,这种被替代的合义务行为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结果。”[注]车浩,见前注〔3〕,页149。但是,无论在假定因果关系还是在结果不可避免中,替代者都是行为人的假定合法行为(即司机合法驾驶和工厂主对羊毛消毒),被替代者都是行为人的现实违法行为(即司机违章驾车和工厂主未对羊毛消毒)。可见,两者都是通过用合法行为替换违法行为的方式来观察因果流程的变化情况。因此,假定因果关系并不是直接以某个他人的行为(或自然事件)来取代行为人的行为,而是同样必须首先用一个合义务的举动去置换违法行为,这一点和结果不可避免中的“合义务替代行为”是共通的。至于说在经过此番替换后,是否有其他外在因素“替补”行为人的违法行为而导致结果发生,这是实验结果的问题,不能将它与实验方法相混淆。②“假定的因果关系涉及两个原因力,而结果不可避免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力。”“假定因果关系不影响归责,是指不能根据一个假定的因果关系来否定之前已经清楚无疑的因果关系;结果避免可能性所使用的‘合义务的替代行为’的思考方法,则是要去检验一个义务关联尚不明朗的因果关系。”[注]车浩,见前注〔3〕,页149、150。但是,这种说法仍然是将不同的判断结论看成了思考方法本身的区别。在结果避免可能性中,究竟是否只存在感染炭疽病菌这一个致人死亡的原因力,对此必须等到整个判断都结束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如果证明病菌可以被杀灭,那么事实上就存在两个致死原因力:义务违反和病菌感染。但这丝毫不影响合义务替代行为思考方法本身的合理性。而且,既然论者也承认结果避免可能性是“要去检验一个义务关联尚不明朗的因果关系”,那又怎么能断言它就“只有一个原因力”呢?同样,在假定因果关系中,由于没有前行为结果同样也会发生,所以在理论上也并非不存在否定前一行为与结果之间关联的可能。总之,相同的思考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思考方法也可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试图证明“结果避免可能性与假定因果关系本来是两个问题”、[注]车浩,见前注〔3〕,页149。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那就应当从二者的结构本身、而不是从其结论出发寻找区别点。③“假定因果关系的‘假定’仅仅是针对行为人引导的因果关系而言,但是其中的原因力却是真实存在的……;相反,结果避免可能性中的‘合义务替代行为’,则是彻头彻尾的‘假定’,完全是基于检验规范有效性的目的而人为设计的一个假想的比较。”[注]车浩, 见前注〔3〕,页150。hnlich Vgl. Roxin (Fn. 〔18〕), § 11 Rn. 99.然而,无论是假定因果关系还是结果避免可能性,都需要在假定行为人的行为合法的前提下去观察其他客观事实因素对于因果流程的影响。即便在结果避免可能性中,被假定者也仅仅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注意义务(即工厂主对羊毛进行了消毒),但在这个假定条件之下发挥作用的也仍然是案件发生时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因素(即炭疽病菌的存在)。这与假定因果关系在假设行为人行为合法(即司机正常行驶未造成事故)的条件下对真实存在的另一原因力(即另一行为人射杀被害人)进行观测的思路并无根本差异。
正是因为无法从思考方法上将结果避免可能性截然隔离于假定因果关系之外,故越来越多的德国学者不得不承认:用于检验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合义务替代行为就是假定因果关系的体现;[注]Vgl. Joachim Vogel, LK-StGB, 12.Aufl., 2007, § 15 Rn. 192; Kristian Kühl, Strafrecht AT, 6. Aufl., 2008, § 17 Rn. 62.由于合义务替代行为能够决定过失犯的成立与否,所以它属于“假定因果关系不影响归责”这一原则的例外。[注]Vgl. Schönke / Schröder / Lenckner / Eisele / Sternberg-Lieben, StGB, 28. Aufl., 2010, vor § 13 Rn. 99a, § 15 Rn. 174.
2.其实,客观归责并不是一概地排斥假定因果关系;相反,假定因果关系是归责判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思维方法。这是由客观归责的核心要素——“行为必须升高了法所不容许的危险”所决定的。具体来说:
第一,在所有引起结果发生的行为中,只有明显升高了法益侵害危险者才能进入客观构成要件的归责范围。若行为只是降低了法益所面临的已有危险,则由于它不仅没有使法益处于更糟的境地,而且还令其状态得到了改善,故并不符合构成要件。以常举的A将飞向B脑门的石块打偏、使其击中B肩膀的案件为例,由于B已处于危险状态之中,仅从现实发生的因果流程(即A使飞行中的石块击中B的肩膀)出发尚无法断定行为在实质上到底是升高还是降低了已有的危险,所以必须首先在假定没有行为人行为的条件下对因果关系的发展进行观察,然后将之与现实的因果关系加以比较。因为A的行为与假定的情形(即A不实施行为,石块击中B的头部)相比明显减弱了生命健康法益遭受的危险,故应排除归责。[注]当然,这个由Roxin提出的“危险降低(Risikoverringerung)排除归责”的原理(Vgl. Claus Roxin, Gedanke zur Problematik der Zurechnung im Strafrecht, in: Festschrift für Richard M. Honig, 1970, S. 136; ders. (Fn. 〔18〕), § 11 Rn. 53ff.)看似清楚明了,但实际上仍存在不少争议问题,例如被害人对行为人救助行为的同意、危险降低与违法阻却事由的关系等。(Vgl. Urs Kindhäuser, Risikoerhöhung und Risikoverringerung, ZStW 120(2008), S. 490ff.)由于假定的因果关系在此具有否定归责的功能,故危险降低也被某些学者视为“假定因果关系不影响归责”原则的又一个“例外”。[注]Vgl. Roxin (Fn. 〔18〕), § 11 Rn. 61, 63; Kindhäuser (Fn. 〔18〕), § 11 Rn.14.可是,一方面,危险降低作为客观归责中关于危险创设的一个基本判断原理很难说只针对某些极个别的情况;另一方面,既然在合义务替代行为和危险降低中均出现了对“假定因果关系不影响归责”原则的突破,那我们恐怕就不能再简单地求助于所谓“例外”,而是必须对该原则本身的权威性进行反思。
第二,在过失犯中,如前所述,注意义务规范在阻止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同时也必然容许某些法益侵害危险的存在;当危险处于注意义务规范既不想、又不能加以避免的法益侵害范围内时,就无法将由此导致的结果归责于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因此,判断是否存在被容许之危险的事实往往就成为检验结果是否处于注意义务规范的效力范围之内的关键。假设所有关于被容许之危险的案件类型和事实情况均已事先为人们尽数网罗、了如指掌,那我们当然只需将现实发生的因果流程与预先知晓的事实类型加以比照就可以直接判断是否存在被容许之危险的情形。然而事实上,由于被容许之危险的情形因具体案件的复杂多样而千变万化,所以试图预先将被容许之危险的全部表现形式一网打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注]Vgl. Wolfgang Frisch, Tatbestandsmäβiges Verhalten und Zurechnung des Erfolgs, 1988, S. 530(Anm. 89).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结合个案的具体事实,通过用假定的合义务行为暂时代替现实的反义务行为的方式来检验注意义务在该特定情形下能否发挥规范所预设的功能和效力,并由此确定现实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发生在规范力所不及的被容许之危险还是规范意图防止的可避免之危险的领域。故假定因果关系的思考方法之所以对于归责判断必不可少,就是因为在具体案件中对被容许之危险的范围和界限加以明确是回答归责问题的前提,而这只能通过合义务行为的假定因果流程才能实现。
由此可见,“假定的事实流程只是在经验的因果关系判断中才不具有重要性;但是从规范的角度来说,它却构成了客观归责的基础。”[注]Urs Kindhäuser, Zum Begriff der Beihilfe, in: Festschrift für Harro Otto, 2007, S. 367 (Anm. 52).
事实上,尽管德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在判断注意义务违反性与结果的关联时也都存在刻意与假定因果关系划清界限的某些倾向,但它们要么最终并未真正摆脱这一思路,要么根本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①Roxin在推介其危险升高理论(对此下文将有详细评述)时曾反复强调,只有当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与被容许的危险相比升高了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时才能将结果归责于该行为,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假定因果流程的发展情况如何,而是在于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本身是否升高了危险。[注]Vgl. Roxin (Fn. 〔11〕), S. 433, 434, 435.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要确定违反义务的行为是否升高了危险,归根结底还是必须要看合义务替代行为能否降低危险。以山羊毛案为例,按照危险升高理论,应当将被容许之危险的事实情况(即羊毛中的病菌无法被消毒剂杀灭)与现实行为所处的事实情况进行比较。若现实中的病菌有被消毒剂杀灭的可能,则说明行为升高了危险;反之,若现实中的病菌也无法被杀灭,则说明行为并未超越被容许的危险。但是,对于“病菌能否被杀灭”这一关键问题,只有在假定行为人履行了消毒义务的条件下,通过观察病菌的存活状态才能得到回答。故危险升高理论实际上仍然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假定因果关系的思考方法。[注]Vgl. Puppe (Fn. 〔17〕), S. 289.②Jakobs也明确反对假定因果关系的思考逻辑,他认为在判断能否将结果归责于义务违反性时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行为违反义务的属性对于说明结果发生的因果过程来说是否必要?以载重卡车案为例,如果是卡车司机过窄的超车距离引起了被害人的惊恐,那么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对于说明结果的出现来说就是必要的;反之,若过窄的超车距离对于惊恐的发生毫无作用,例如,深度醉酒的被害人只是因为听见了卡车的马达声而陷于惊恐,则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对于说明结果的出现就不是必要的。[注]Vgl. Günter Jakobs, Strafrecht AT, 2. Aufl., 1993, 7/78, 7/98.但是,这一结论明显将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即便是被害人只因听见卡车的马达声而感到惊恐,但若合法的车距有助于降低马达声的音量,从而减弱惊恐的程度并避免被害人死亡的话,也应认为违规驾驶是结果发生的必要原因;相反,即便是过窄的车距引起了被害人的惊恐,但若合法的距离一样会使被害人产生同等程度的恐惧从而无法避免事故,那也应当认为义务违反并非导致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离开了假定因果关系的思考方法根本无法得出切合实际的合理结论。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虽然一方面声称,在判断结果与义务违法之间的关联时,关键是要考察现实已经发生的事实过程,而非假定的因果流程;[注]Vgl. BGH St 10, 369 (370); BGH St 24, 31 (34); BGH VRS 13, 278 (279).但另一方面又经常以假定的合义务替代行为为根据限定归责的成立范围。[注]Vgl. BGH VRS 21, 341 (343); BGH St 11, 1 (7).故学者们指出,最高法院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已经表明,它和学界一样均无法排除假定因果关系思维的影响。[注]Vgl. Vogel (Fn. 〔23〕), § 15 Rn. 197; Ingeborg Puppe, NK-StGB, 3. Aufl., 2010, vor § 13 Rn. 210.
3.在认定注意义务违反性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时,必须对假定因果关系中可资考虑的事实以及用于替代违法行为的合义务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定。
首先,应当将假定因果关系的考察范围仅仅限定在处于行为人行为的控制领域之内、可能影响规范效力发挥的事实因素。既然如前所述,关于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假定的因果关系,那么怎样才能将被允许和被禁止的假定因果关系区分开来呢?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对被禁止的假定因果关系受到排斥的内在原因进行分析。仍以C违章驾车将D撞死,但即便无C的违法行为D也会被E在同一时刻射杀的案件为例,人们之所以一致认为该假定因果关系不能否定对C行为的归责,其根本原因在于:E持枪以待的事实并不处于C行为的覆盖范围之内,关于合理驾驶的注意义务规范所具有的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能力也不会因为E的存在而有任何减损,所以它对C所违反之规范的效力发挥毫无作用,自然也无法影响C行为本身的性质。因此,假定因果关系受到允许的前提条件是它所考虑的事实必须能够影响注意义务之规范效力的实现,即它必须有助于回答“规范按照其预定的计划能否(以及是否希望)避免该因果流程出现”[注]Frisch (Fn. 〔27〕), S. 532.的问题。只要我们在假定行为合法的同时只将那些处于行为领域之内、与规范效力的发挥具有关联的事实因素纳入因果流程,就可以使假定因果关系的运用严格限定于检验规范的有效性和考察行为自身危险性的合理范围之内。具体的做法是:首先,结合行为人所违反的注意义务的规范目的,考虑哪些方面或种类的事实因素可能影响被容许之危险的成立;其次,看现实案件中的某个具体事实是否属于这类因素。以前述诸案件为例:①在假设货车司机驾驶时遵守法定运载量和限速的因果流程中,可以对公路路面濒临垮塌的事实加以考虑。因为:其一,路面状况是机动车驾驶行为必然涉及的因素。其二,道路交通规则之所以对货车运载量和速度设置了一定的限制,其目的在于避免公路因受到过度的损害而发生塌陷事故。一旦公路本身已失去正常的承受和支撑能力,那么该规范就不再具有避免事故发生的能力了。所以公路的路面状况是否正常就成为影响被容许之危险是否成立的关键因素。但是,诸如事发当时恰好有另一辆汽车即将撞向货车并使其翻入农田的事实则不属于应予考虑的因素,因为它不仅脱离了行为人行为的作用范围,而且毫不影响关于限量限速行驶的注意义务规范本身的结果避免能力。②在假定卡车司机于超车时保持了合法车距的条件下,可以将自行车驾驶者处于醉酒状态的事实纳入考察范围。理由在于:一方面,被害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处于超车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内。另一方面,交通规范之所以要求司机在超车时必须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因为这种距离能够为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其他驾驶者提供必要和充足的反应空间和时间。所以,自行车驾驶者当时的身心状况对于该规范能否正常发挥作用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某个被害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极度异常,以至于法定的超车距离也无法保证他能够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那么这就属于规范有意加以容许的危险。相反,对于诸如被害人在卡车司机超车之前就已决心自杀,并随时准备一头撞向从侧面驶过的车辆,以及另一行为人早已埋伏一旁准备射杀被害人的事实则不能加以考虑。因为一方面,这类事实根本不在超车行为的控制和影响领域之内;另一方面,被害人是否准备自杀、某个第三人是否可能致被害人于死地,这与超车应保持一定距离的规范毫无关联,也不可能对该规范的效力发挥产生任何阻碍作用。③在假设工厂主事先已对山羊毛进行了消毒的条件下,可以考虑羊毛中的炭疽病菌可能无法被消毒剂杀灭的事实。因为:第一,病菌本来就是消毒行为的指向对象。第二,“必须事先对羊毛进行消毒”这一注意义务的规范目的在于清除羊毛中的危险病菌从而保障工人们的健康和安全。所以,病菌能否被杀灭直接影响到注意规范的效力,而存在个别无法被消毒剂杀灭的病菌也正是该规范事前已经预想到并予以容忍的危险。但是,像在羊毛加工过程中某一患病工人引起了瘟疫传染、某人向羊毛中投放了致命的化学药剂等事实则不能进入假定的因果流程,因为它们既不处于行为人行为的覆盖领域,也影响不了关于事先消毒的注意义务规范本身的效力。④在假设医生按规定注射了奴夫卡因的条件下,之所以可以考虑病人的特殊体质,是因为该注意规范的目的在于,在保证麻醉效果的同时尽量避免药物对病人的健康和安全产生不良影响,而对于拥有正常体质的人来说奴夫卡因的危险性明显低于可卡因。但是,如果出现了连奴夫卡因也无法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个别特殊体质,那么该规范只得归于无效。可见,被害人的体质如何直接影响注意义务效力的发挥,也直接影响行为人行为的实质危险性。⑤在假定药剂师按规定事先向医生进行过咨询的因果流程中,由于医生是否会批准用药既是咨询行为的直接结果,也是咨询义务能否避免结果发生的关键因素,故也可以成为假定因果事实的考察对象。
总而言之,要判断某一事实能否被纳入到假定因果流程的思考之中,关键是要看它是否处于行为人行为的覆盖范围以内,是否属于能够影响规范效力实现的事实。只要某一因素可以影响规范目的所预想的被容许之危险的成立,那么无论它是被害人自身所具有的因素还是属于外界的自然原因,均可以成为假定因果关系考察的事实。[注]有学者认为,在用于判断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假定因果关系中,原则上应将被害人、第三人的行为以及不可控制的自然力排除在外;但是“对于那些在案件发生时事实上存在的被害人、第三人的行为或者自然力的作用则应予以考虑”,例如载重卡车案中自行车驾驶者醉酒的事实。(Vgl. Vogel (Fn. 〔23〕), § 15 Rn. 200.)但某一事实能否进入假定因果关系,既不取决于它属于被害人、第三人还是自然力方面的因素;也不取决于它是否在案发当时现实存在,因为禁止进入假定因果关系的事实,例如被害人打算自杀、第三人埋伏一旁准备射杀被害人,也同样是案发时客观存在的因素。所以,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该事实究竟是否与规范效力具有关联、能否影响被容许之危险的成立。[注]值得注意的是,Puppe在行为人与被害人均违反了注意义务的案件中对合义务替代行为的思考方法提出了质疑。她认为:如果我们在假定因果关系中将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排除出去,并代之以合义务的替代行为,那么这实际上就不是在考察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而是在考察被害人一方违反注意义务所产生的危险,故这种思维方法是错误的。以载重卡车案为例,由于卡车司机与自行车驾驶者双方均违反了一定的注意义务,而且由这两种违法行为产生的因果关系交汇到了一起,所以想要单独考察其中一方的义务违反的危险,就必须将之从多重的因果关系中分离出来。按照传统的合义务替代行为的思考方法,在将卡车司机的违规超车行为替代成合法行为的条件下,若自行车驾驶者的醉酒状态自身已具有100%引起事故的危险,则可以否定卡车司机的义务违反与结果具有关联。但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不是立足于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本身来进行判断,而是以被害人行为的危险性去否定行为人行为的危险性、以被害人的责任来推卸行为人的责任,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因此,应在保持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不变的情况下,假定被害人一方的行为符合注意义务(即自行车驾驶者处于清醒状态),并以此检验前者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只要由此可以认定卡车司机违法行为的危险已达到了足以单独引起事故发生的程度,那么不论自行车驾驶者的违法行为具有多高的危险,也不能否定行为人的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关联。(Vgl. Puppe (Fn. 〔17〕), S. 291-294; dies., Strafrecht AT, Bd. 1, 2002, § 3 Rn. 47ff.)但我认为这一观点还值得商榷。假定因果关系思维的任务在于检验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处于规范无法发挥效力的被容许危险之中,而被容许的危险必然以独立于行为人行为之外的某种特殊因素的存在为其成立条件。正如在山羊毛案中,虽然病菌可能无法被消毒剂杀灭的事实属于外界的自然因素,但由于病菌能否被杀死直接决定在本案中注意义务的效力能否实现、被容许的危险是否成立,所以我们还是必须将其保留于假定的因果关系之中,而不能在假设病菌可以被杀灭的条件下去抽象地判断行为的危险性。同理,正是由于被害人醉酒的事实是决定载重卡车案中被容许之危险能否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离开了它我们无法确定个案中的某一行为是否创设了法所禁止的危险,故不应将其排除出假定的因果关系。可见,将被害人醉酒的事实纳入考虑范围并非是为了以被害人的责任否定行为人的责任,而是因为在注意义务规范容许一定危险存在的情况下,该事实本身就是决定行为人行为性质的关键要素。Puppe提出其反对意见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出现用被害人违法行为危险性的存否或大小去决定行为人违法行为危险性的现象,但她明显混淆了与规范效力相关联的被害人因素,和与规范效力无关的被害人因素。
其次,应当对合义务的替代行为本身进行限定。在许多情况下,用于代替行为人违法举动的合义务行为往往有多个选择可能。例如,在载重卡车案中,行为人能够实施的合法行为既可以是在超车时保持法定1.5米的距离,也可以是在超车时保持3米的距离,还可以是完全放弃超车,而且选择不同的替代行为会直接影响假定因果关系的判断结论。因为即便保持1.5米的超车距离也同样会引起事故,但保持3米的车距就可能明显提高结果的避免可能性,而放弃超车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事故的发生。又如,L违章将其货车停靠在高速公路旁,结果喝醉了酒的F驾车从后方驶来撞上了该货车,导致F身受重伤。[注]Vgl. BGH VRS 24, 124 (125).用于代替L违章停车的合法行为既可以是将货车停靠在被允许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是继续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还可以是在高速公路上缓慢行驶。前两种行为均可以确定防止事故的发生,但后一种行为则很可能无法避免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假定因果关系的判断不致流于随意和主观,必须对合义务替代行为进行明确的限定。筛选的标准主要有二:①合义务的替代行为必须与现实的违法行为同属一个行为类型。换言之,只有当某一合法行为所追求的目标或利益与行为人事实上实施的违法行为所追求者完全一致时,该合法举动才能成为替代行为。[注]Vgl. Ellen Schlüchter, Zusammenhang zwischen Pflichtwidrigkeit und Erfolg bei Fahrlässigkeitstatbeständen, JA 1984, S. 678; Frisch (Fn. 〔27〕), S. 536; Gunnar Duttge, MK- StGB, 2003, § 15 Rn. 170; Schönke / Schröder / Sternberg-Lieben, StGB, 28. Aufl., 2010, § 15 Rn. 176.例如,当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是违反法定距离超车时,合义务替代行为就只能是符合法定距离的超车,而不能是放弃超车,因为放弃超车与行为人当时的目的完全相反,它与现实违法行为不属于同一类型;同理,当行为人的行为是在高速公路上违章停车时,合义务的替代行为就只能是在被允许处停车,而不能是继续行驶。②若有多个与违法行为同属一种行为类型的合法举动可供选择,则应将其中最低限度的合义务行为作为替代行为。因为被容许之危险的成立仅以行为最低限度地符合注意义务为要件,法秩序没有理由在此之外向公民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在载重卡车案中,能够成为替代行为的应当是保持1.5米距离,而非保持3米距离的超车。
(二)判断标准:对法益侵害危险的优势性升高
在确定了判断的基本思路之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合义务替代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究竟要达到多高的程度才能使注意义务违反性与法益侵害结果建立起必要的关联呢?
对此,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立场:①确定能够避免说(Vermeidbarkeitstheorie)。该说认为,只有当合义务替代行为确定地能防止结果发生,即在行为符合注意义务的条件下绝对不可能再出现该法益侵害结果时,才能成立客观归责。因此,只要无法排除“合法行为也同样会引起结果”的可能,不论该可能性有多小,也应一律根据罪疑唯轻的原则否定归责。这一观点是目前德国学界和判例的多数意见,[注]Vgl. Schlüchter (Fn. 〔39〕), S. 676; Frisch (Fn. 〔27〕), S. 537ff; Baumann / Weber / Mitsch, Strafrecht AT, 11. Aufl., 2003, § 14 Rn. 86f; Walter Gropp, Strafrecht AT, 3.Aufl., 2005, § 12 Rn. 54; Vogel (Fn. 〔23〕), § 15 Rn. 182ff; Schönke / Schröder / Sternberg-Lieben (Fn. 〔39〕), § 15 Rn. 177ff; Fischer (Fn. 〔10〕), vor § 13 Rn. 26.同时也得到了我国部分学者的赞同。[注]车浩,见前注〔3〕,页154。②危险升高理论(Risikoerhöhungstheorie)。该说提出,只要能够认定行为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与被容许的危险相比升高了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就足以肯定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换言之,只要根据事后查明的所有客观事实能够认定合义务替代行为具有防止结果发生的可能,不论该可能性有多低,即可成立归责;只有当合法行为确定地完全无法避免结果时,才能否定归责。其理由在于:注意义务规范的制定者往往会根据实际的需要容许一定危险的存在。若虽然某一行为违反了注意义务,但实际上合法行为也不能避免结果发生,那就说明该违法行为只不过实现了一个被容许的危险而已,故不应予以处罚,否则就违背了相同情况同等对待的原则;反之,一旦违法行为与被容许的危险相比升高了结果发生的概率(即合义务的行为能够降低结果发生的可能),那么它就超越了立法者所能容忍的范围,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必须使法律的天平朝有利于法益保护的一边倾斜,故应将结果归责于违法行为。[注]Vgl. Roxin (Fn. 〔11〕), S. 431-433; ders. (Fn. 〔18〕), § 11 Rn. 89.由此可见,通说和危险升高理论实际上均以合义务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作为归责判断的核心标准,只不过前者要求这种可能性必须达到100%的程度,而后者(根据Roxin的观点)则认为只要这种可能性存在即可,不论它是1%还是100%均足以实现归责。在合义务行为能还是不能避免结果均存在一定机率、但又并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通说认为应排除归责,而危险升高理论则主张肯定归责。所以,后者与前者相比明显扩大了过失犯的处罚范围。危险升高理论虽然也不乏支持者,[注]Vgl. Jescheck / Weigend,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T, 5. Aufl., 1996, S. 585; Michael Köhler, Strafrecht AT, 1997, S. 197ff; Hans-Joachim Rudolphi, SK-StGB, 6. Aufl., 1997, vor § 1 Rn. 65ff; Bernd Schünemann, Über die objektive Zurechnung, GA 1999, S. 226ff; Puppe (Fn. 〔34〕), vor § 13 Rn. 224ff; Stratenwerth / Kuhlen, Strafrecht AT Ⅰ, 6. Aufl., 2011, § 8 Rn. 36f.但却受到了来自通说的猛烈抨击。人们对它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危险升高理论违背了罪疑唯轻原则。因为如果合义务的替代行为能否避免结果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那就说明过失犯所要求的义务违反和结果之间的关联无法得到证明,故应做出有利于行为人的判断,从而排除归责。第二,危险升高理论把刑法明确规定的结果犯转化成立危险犯。因为作为一种结果犯,过失犯的构成要件不仅要求义务违反性与法益侵害结果分别存在,而且还要求两者必须具有内在关联。但该说仅仅强调义务违反与危险升高之间的关系,而并未说明危险升高与侵害结果本身的关联,所以它实际上是将结果犯的归责要求降格为了危险犯。[注]Vgl. Schlüchter (Fn. 〔39〕), S. 676; Duttge (Fn. 〔39〕), § 15 Rn. 178.
在进入实质性讨论之前有两点必须首先加以澄清:①只有合义务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才能在结果与义务违反之间建立起为实现归责所必要的联系,对于这一点其实理论上并无分歧;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建立这种联系所必需的结果避免可能性至少应达到何种程度?实际上,危险升高理论并未如其反对者所说的那样直接将结果犯转变为危险犯,或曰“切断了这种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注]车浩,见前注〔3〕,页155。相反,在结果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危险升高理论也同样承认在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是成立归责的必要条件,只不过它认为只要反义务行为升高了危险,或曰只要合义务行为有避免结果的可能即可满足这一要求。因此,有说服力的批判应进一步揭示:为何危险升高的标准尚不足以使义务违反与结果建立起为归责所必要的关联?为什么只有当合义务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达到100%时才能肯定该关联的存在?同样,危险升高理论若想捍卫自己的立场,也不能仅停留在“行为只要升高了被容许的危险就必然超出了规范容忍范围”之类的辩解上,因为从“行为无法为规范所容忍”还不能顺理成章地直接推导出“结果可归责于行为”的结论。故危险升高理论必须回答:以单纯的危险升高为根据肯定义务违反和结果之间关联的实质理由何在?②应将实体法问题与程序法问题截然分开。换言之,不能将合义务替代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的程度,与针对该种可能性的证明标准相混淆。[注]在德国,最先提出应将两者区分开来的是Arthur Kaufmann。Vgl. Arthur Kaufmann, Kritisches zur Risikoerhöhungstheorie, in: Festschrift für Hans-Heinrich Jescheck, 1985, S. 277ff.确定合义务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要达到多高才能成立归责,这是一个实体法上关于构成要件的价值判断问题,它并不涉及关于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故与罪疑唯轻原则毫无关联。例如,假设某一学说将归责所需要的结果避免可能性确定在30%,只要它坚持对该构成要件事实,即30%的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证明仍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那么尽管人们可以说把避免可能性定在30%是不合理的,但不能认为该说违反了罪疑唯轻原则。否则,如果说一旦在构成要件中出现低于100%可能性的事实就认为违反了罪疑唯轻原则,那么刑法典中所有的危险犯岂不都违反了该原则?因此,如果通说认为危险升高理论在结果避免可能性低于100%的情况下仍肯定归责的观点不正确,那就应当从实体法的角度(即上述①中提出的问题)出发论证为何只有100%的结果避免可能性才符合过失犯归责的要求。只有当危险升高理论在是否存在危险升高的事实,即合义务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结果避免可能性尚存在疑问的情况下仍坚持肯定归责时,方能认为它违反了罪疑唯轻原则。[注]Vgl. Arthur Kaufmann (Fn. 〔46〕), S. 282; Jescheck / Weigend (Fn. 〔43〕), S. 585; Schönke / Schröder / Sternberg-Lieben (Fn. 〔39〕), § 15 Rn. 179/179a.
我认为,从实体法来看,在假定行为符合注意义务的条件下,若合义务替代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达到了占据优势,即超过50%的程度,即可认定注意义务违反性与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关联。具体论述如下:
首先,由事实的复杂性和变量的多样性所决定,在假设行为合法的情况下因果流程将会如何发展,对此人们只能以概率的形式推测其基本趋势,而无法给出绝对百分之百的确定回答。以载重卡车案为例,在将保持75厘米的距离超车的行为替换为保持1.5米的距离超车的行为之后,处于醉酒状态下的被害人究竟会如何反应,这取决于他在当时那一瞬间的体力、心情、感官灵敏度和承受惊吓的能力等各种因素。且不说因为被害人已经死亡,故无法进行真实的模拟试验;就算他得以幸存,由于人的上述因素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其中任何一个参数的微小变动都会影响最终的结局,故即便我们能将客观环境和条件一五一十地复原至案发当时的情况,但特定时刻和背景下的被害人身心情绪及能力水平却完全不具有可复制性。[注]正如唐代诗人卢纶的《塞下曲》所描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李广深夜误将石头当作猛虎而挽弓射去,他在这种特定紧急情形下展现出来的精神、体力和武功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因此,且不说当他于次日清晨试着再度用箭射向石块时已无法再现“没在石棱中”的效果,即便再重复一次当时夜半遇“猛虎”的情景,由于其身心状态已无法与事发当时完全保持一致,故能否重演这一惊人之举也并无十足的把握。因此,假定的合法超车行为能否避免事故的发生,这本身就是一个只涉及可能性大小,而不可能具有绝对确定回答的问题。在医疗案件中,假定因果流程的这种不确定性显得更加突出,因为“许多的疾病发展过程和治疗过程并不完全是为因果规律所决定的。”[注]Puppe (Fn. 〔40〕), § 2 Rn. 24.例如,在奴夫卡因案中,注射奴夫卡因是否也同样会导致具有特殊体质的被害人死亡,这不仅受到被害人当时的身体状况的影响,而且还取决于被害人用药后出现异常反应的具体时间和表现、医生发现症状的早晚以及可能采取何种救治措施等等一系列不可把握的复杂变量。由于这些因素即便在案件事实已经全部查清的情况下也仍然无可避免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故注射奴夫卡因能否避免结果的发生永远是一个只具有可能性,而没有确定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合义务行为始终只能为法益保护提供一种可能性,那么注意义务规范就必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因为合义务行为无法确定地避免结果发生而在这类案件中一概放弃归责;要么在合义务行为能够明显降低损害发生机率的情况下承认结果与义务违反之间的规范关联。若选择前者,则由于医疗事故基本上都由不确定的因果流程所引起,故在该类案件中即便存在对注意义务的严重违反,也无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于是,像我国刑法第335条的医疗事故罪等条文也将几近形同虚设。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该结论并无不妥之处。其理由在于:因为医护工作者的注意义务标准较之于其他职业来说本来就十分严格,所以为了避免使其陷于过高的刑罚处罚危险,有必要在缺少确定因果流程的案件中一律否定客观归责的成立。[注]Vgl. Justus Krümpelmann, Zur Kritik der Lehre vom Risikovergleich bei den fahrlässigen Erfolgsdelikten, GA 1984, S. 508ff.但这样一来,医疗人员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极为偶然的因素。例如,刑法理论一致认为,只要合义务的医疗行为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命,不论延长的时间长短,均应认为义务违反与患者提早死亡的结果具有关联性。若医生违反注意义务实施医疗行为时患者已处于疾病的晚期,则因为科学鉴定往往可以确定地得出合义务行为能够将患者的死亡时间往后推延数分钟到数小时的结论,故容易肯定归责的成立;反之,若医生的违法行为发生在患者尚处于疾病早期的时候,则由于合法行为能否延长生命大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故容易否定归责的成立。于是,医生是否成立犯罪就完全依赖于其行为实施的早晚,这是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因此,使医务人员免予过高处罚危险的正确方法不是把合义务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定为100%,而是将过失犯的成立限定于重大过失,[注]Vgl. Puppe (Fn. 〔17〕), S. 300.即我国刑法第335条所规定的“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由此可见,以危险升高为根据,即在合义务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低于100%的情况下肯定客观归责就成为必然选择。
另外,还有学者把涉及因果关系不明确之情形的经典案例与此处探讨的问题进行类比,并由此对危险升高理论提出质疑:甲与乙分别出于过失不约而同地向丙开枪致其死亡,但无法查明致命的那一枪究竟系何人所发(以下简称“枪击案”)。对此,刑法理论没有争议地认为,由于各个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都无法确定地得以查明,故他们均不成立犯罪。然而,按照危险升高理论的逻辑,既然每个行为人的枪击行为均已明显升高了丙中弹身亡的危险,那么即便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完全查清,也不妨碍甲和乙都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可见,危险升高理论会得出明显错误的结论。[注]Vgl. Rolf Dietrich Herzberg, Die Kausalität beim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 MDR 1971, S. 882. 类似的论述参见车浩,见前注〔3〕,页157。但是,我认为这种类比是存在问题的。因为用于进行对比的两种案件看似均涉及某一待考察的对象与结果之间的关联问题,但实际上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异。在枪击案中,由于子弹射出击中人的要害部位致其死亡的过程属于某一积极力量主动侵入并使对象物发生客观变化的事件,它自始至终都处于绝对确定的物理性因果链条之中,所以在案件事实均已查明的情况下,可以对死亡结果是否为枪击行为所致的问题给出全有或全无的确定结论。但在考察注意义务的结果避免可能性时,以载重卡车案为例,积极引起外界变化的是行为人的超车行为,由于违反法定距离只是依附于超车行为的一种规范属性,它并未直接对因果流程的走向施加积极的影响,故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对此无法通过直接的观察来加以认知,而必须借助于假定因果关系的实验方法才能获得答案。如前所述,在假定因果关系中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而这种不确定性并非来在于案件事实无法查清,而是因为假定因果流程本身就受到各种不可控制、无法再现的复杂变量的影响。所以,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往往只能表现为一定的因果概率。总而言之,“由于对犯罪事实的查明存在局限而产生的不确定性,与假定因果流程的不确定性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注]Günter Stratenwerth, Bemerkungen zum Prinzip der Risikoerhöhung, in: Festschrift für Wilhelm Gallas, 1973, S. 229.这两类案件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对于上述枪击案,即便是危险升高理论也不可能得出行为人有罪的结论。
其次,尽管坚持确定能够避免说的学者对危险升高理论提出了种种责难,但他们自己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却又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朝危险升高理论的思路倾斜。有的学者意识到,对于大量案件而言,想要证明合义务行为能够毫无疑问地避免结果发生确实是不现实的,故对于归责的成立来说只能要求合义务替代行为防止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达到优势性的较高程度,除此之外不宜再提出更高的要求。[注]Vgl. Ellen Schlüchter, Strafrecht AT, 3. Aufl., 2000, S. 184; Duttge (Fn. 〔39〕), § 15 Rn. 175-176.还有人提出,只有当根据个案中的具体线索可以认定在合义务行为的条件下也存在结果发生的具体危险时,才能认为合义务行为已无法保证避免结果的出现。换言之,尽管合义务行为避免结果发生的概率不满100%,但只要这种避免可能性上的亏损尚不足以构成导致同一结果发生的具体危险,则仍应肯定归责的成立。[注]Vgl. Frisch (Fn. 〔27〕), S. 549.以上学者都曾明确反对危险升高理论,但他们此时却在实际上放弃了“只有当合义务行为能确保万无一失地防止结果发生时才可实现归责”的命题,并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危险升高的判断标准。另外,尽管德国的司法实践一贯支持确定能够避免说,但由于严格坚持该说会得出不合理的结论,故帝国法院曾一度借助证明责任的倒置而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例如,在关于山羊毛案和奴夫卡因案的判决中,帝国法院指出:要想认定行为无罪,必须证明结果在合义务行为的条件下也会发生的可能性达到了确定或者接近于确定的程度。[注]Vgl. Roxin (Fn. 〔11〕), S. 423; Duttge (Fn. 〔39〕), § 15 Rn. 174.换句话说,只要无法证明合义务的行为完全不能避免结果发生,那就应当推定它能够确定地防止结果出现。于是,只要合义务行为有一线希望避免结果,都应当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完全是以“确定能够避免说”为名而行“危险升高理论”之实。
再次,应当将归责所需要的结果避免可能性确定在50%以上。在肯定了危险升高理论的基本立场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义务违反对危险的升高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实现归责呢?有的学者主张,只要存在危险升高,不论其程度如何,一律可以成立归责;[注]Vgl. Roxin (Fn. 〔11〕), S. 431-432; ders. (Fn. 〔18〕), § 11 Rn. 89.有的学者则认为,只有“显著的”(erheblich)危险升高才能满足客观归责的要求。[注]Vgl. Jescheck / Weigend (Fn. 〔43〕), S. 585.我认为,合义务行为避免结果的可能性必须超过结果仍然会发生的可能性,即义务违反不仅与被容许的危险相比提高了结果发生的概率,而且它升高危险的幅度本身还必须达到大于被容许之危险的程度时,才能使义务违反与结果建立起必要的联系。因为当注意义务阻止结果出现的机率虽然客观存在,但明显小于结果同样会发生的机率时,义务违反的危险性就仍然停留在行为的属性本身上,而尚不足以迈出行为领域而与法益侵害的结果建立起连通的桥梁。相反,当合义务行为遏制结果的可能超过了结果发生的可能时,义务违反已不再仅仅拥有单纯的危险性,而是明显具备了朝结果方向发展的压倒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将结果看成是义务违反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产物,并据此将义务违反视为法益侵害发生的内在动力和必要条件,从而在规范上将两者联系起来。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合义务替代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超过50%,或曰义务违反优势性地升高了法益侵害危险的事实必须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充分和确定的证明。若对该事实的证明存在疑问,则必须根据罪疑唯轻的原则排除犯罪的成立。Roxin认为,即便在行为是否升高了危险还不能确定的情形中也应当肯定危险升高的存在。“因为如果根据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还无法确定地查清行为究竟是否提高了立法者所容许的危险,那就说明这一行为与被容许之危险的情形是存在区别的。若该行为引起了法益侵害,则应对行为人加以处罚。”[注]Roxin (Fn. 〔11〕), S. 434.毕竟,“对于某个有可能逾越注意义务规范所容许之危险的行为,法秩序没有理由加以容忍。”[注]Roxin (Fn. 〔18〕), § 11 Rn. 96.但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第一,既然危险升高是过失犯构成要件符合性得以成立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事实,那么对该事实的证明就必须达到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确定程度。[注]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做到证据确实充分。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所谓“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标准之一就是: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参见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327。)第二,法秩序对某一行为加以禁止,与刑法将严重的法益侵害结果归责于该行为并予以处罚是两码事。违反注意义务规范的行为本来就与被容许的危险存在差别,也没有人认为法秩序应当对该行为加以容忍。例如,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就明确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机动车驾驶人应科以一定的行政处罚。可是,在刑法上,由刑事制裁措施的严厉性所决定,能够成为刑罚处罚对象的违章驾驶行为必须与严重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存在必要的关联。若这种关联无法确定无疑地得到证明,那就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过失行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并不意味着法秩序容忍该行为的存在,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单独针对过失行为本身对行为人施以行政处罚。正因为如此,危险升高理论阵营内的绝大多数学者也都坚决反对Roxin的上述主张。[注]Vgl. Stratenwerth (Fn. 〔53〕), S. 235f; Arthur Kaufmann (Fn. 〔46〕), S. 277, 281ff; Jescheck / Weigend (Fn. 〔43〕), S. 585; Rudolphi (Fn. 〔43〕), vor § 1 Rn. 69.
四、 余论:危险创设还是危险实现?
最后还有一个体系性的问题需要附带加以讨论,即在客观归责的理论框架中,应把义务违反和结果之间的关联置于哪一阶段呢?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尽管关于客观归责的学说千差万别、异彩纷呈,但将危险创设(Risikoschaffung)和危险实现(Risikoverwirklichung)作为归责判断的两个核心步骤已成为理论界的普遍共识。其中,多数学者认为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属于归责判断的第二阶层,即危险实现的问题。例如,Roxin就是将“合义务的替代行为和危险升高理论”放在“不被容许之危险的实现”之下来加以论述的。[注]Vgl. Roxin (Fn. 〔18〕), § 11 Rn. 88ff. hnlich Rudolphi (Fn. 〔43〕), vor § 1 Rn. 67f; Wessels / Beulke, Strafrecht AT, 41. Aufl., 2011, Rn. 179, 197. 我国也有学者接受了这种体系安排,参见陈兴良,见前注〔3〕,页305;张亚军:《刑法中的客观归属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97。但在我看来,注意义务的结果避免可能性涉及的应当是行为是否创设了法所不容许之危险的问题。理由如下:
第一,通说之所以将义务违反与结果的关联置于危险实现阶段,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危险创设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合理的危险判断标准。多数学者认为,在考察行为是否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危险时,应以一般人能够认识和行为人特别认识的事实为基础、站在行为当时的一般理性人的立场来加以判断。[注]Vgl. Jescheck / Weigend (Fn. 〔43〕), S. 286; Roxin (Fn. 〔18〕), § 11 Rn. 40, 56f; Walter (Fn. 〔18〕), vor § 13 Rn. 92; Schönke / Schröder / Lenckner / Eisele, StGB, 28. Aufl., 2010, vor § 13 Rn. 92; Puppe (Fn. 〔34〕), vor § 13 Rn. 157.根据这一标准,一旦行为违反了注意义务,就足以认定它产生了法所不容许的危险。不过,注意义务在具体个案中是否确实具有避免结果发生的能力也直接影响归责的成立与否,对此必须结合事后查明的所有案件事实才能弄清,故只好把结果避免可能性的问题放在危险创设已得到肯定之后的危险实现阶段来加以讨论。若以事后获知的全部客观事实为基础能够认定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与被容许的危险相比的确升高了结果发生的危险,则可以肯定该行为创设的危险已得到了实现,反之则应否定归责。[注]Vgl. Roxin (Fn. 〔18〕), § 11 Rn. 74, 94; Schünemann (Fn. 〔43〕), S. 217ff.然而,该观点仍有可商榷之处:①通说在危险创设阶段采取的以“一般人认识 + 行为人特别认识”为资料的危险判断方法本身就存在严重弊端,它不仅在客观构成要件的判断中掺入了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从而造成了主客观要素的混淆;而且由于它在选取危险判断的基础事实时需要不断穿梭于一般人认识、行为人认识和客观现实之间,并对三者进行对比,所以既会在实际操作中带来不必要的累赘和麻烦,又可能导致不合理的结论。[注]详尽的分析参见陈璇:“论客观归责中危险的判断方法——‘以行为时全体客观事实为基础的一般人预测’之提倡”,《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②该观点在客观归责中引入了两个危险升高概念和两套危险判断标准,并由此带来了以下疑问:[注]Vgl. Klaus Ulsenheimer, Erfolgsrelevante und erfolgsneutrale Pflichtverletzungen im Rahmen der Fahrlässigkeitsdelikte, JZ 1969, S. 366.其一,既然我们已经在危险创设阶段认定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危险,这就足以说明行为以法所禁止的方式升高了法益侵害危险,那又何须在关于危险实现的判断中再次考察行为是否升高了危险呢?这两种危险升高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其二,为何两种危险判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判断方法,即前者的基础是“一般人认识 + 行为人特别认识”的事实,而后者则是事后查明的所有客观事实呢?Roxin对此的解释是:“这并不能证明我的观点是错的,而充其量只是说明,当以行为制造了不被容许的危险为根据而做出的危险被升高的推测为事后查明的事实所否定时,需要对广为接受的相当性公式(Adäquanzformel)进行一定的修正。新的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具体的危险判断不能脱离那些只有在事后才能为人们所知晓的事实情况。”[注]Roxin (Fn. 〔25〕), S. 138-139 (Anm. 18).换言之,对于危险的判断而言,以“一般人认识 + 行为人特别认识”的事实为基础的判断标准实际上并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权,“站在客观事前立场被认定为升高了风险的行为还必须再经过一次客观事后判断的检验。”[注]Nicolas Börgers, Studien zum Gefahrurteil im Strafrecht, 2008, S. 40.可见,之所以会出现两个危险升高并存的局面,完全是因为前一个危险升高不能真实和客观地反映行为的属性。但是,既然通说已经承认危险的判断归根结底必须以现实存在的事实为基础,既然我们最终无法给予“一般人认识 + 行为人特别认识”以完全的信任而在某些情形下不得不根据现实情况对之加以修正,那就足以说明:以人的认识能力为标准确定基础事实的方法是不可靠的;相反,应从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将事后查明的所有事实作为危险判断的资料。同时,由于危险判断涉及的是行为是否增大了法益侵害可能性的问题,所以理应将其定位于危险创设阶段。于是,实际上就只存在以全部客观事实为基础的一个危险升高概念,其功能就是认定行为是否确实创设了法所禁止的危险、是否具有成为构成要件行为的资格。这样一来,一方面既可以使危险概念摆脱主观要素的羁绊而彻底回归客观,另一方面又能够避免因两个危险升高并存而产生的困惑。
第二,危险升高理论所要考虑的因素均属于行为实施当时存在的事实,而非行为实施完毕后出现的情况。在客观归责理论中,危险创设涉及的是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危险性的问题,故它的考察范围始于行为着手而终于行为实施完毕;与此相对,危险实现关注的则是行为所产生的危险性是否经由一定的因果流程而合乎规律地转化成了现实的法益侵害结果,故它的考察范围应定位于从行为实施终了到结果发生之间出现的各种事实情况。结合本文开头所列举的相关案例,我们不难看出,注意义务的结果避免可能性问题属于归责判断的前一阶段,而非后一阶段。因为无论是公路路面濒临垮塌、自行车驾驶者处于醉酒状态,还是山羊毛中含有无法为消毒剂所杀灭的病菌、患者具有特殊体质以及医生照例会同意开药,都是与违法行为的实施相伴随、直接影响行为本身法益侵害能力的事实。所以,以这些事实为考察对象的合义务替代行为也自然是以检验行为自身的危险性为其目标的。
第三,构成要件行为以现实的法益侵害危险为其实质内容,故某一行为仅在形式上违反了注意义务,这还不足以认定它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危险,也不足以使其成为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只有当这种违背注意义务规范的举动在实质上提升了法益侵害的可能性时,它才真正具备了成为构成要件行为的资格。这与故意犯的情形实际上是一致的。例如,仅根据行为人以毒杀他人的目的朝茶杯中撒入药剂这一事实尚不能断言该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只有在根据行为发生时的各种事实情况(例如药剂是否具有毒性,被害人是否会使用该茶杯等)确定行为实质上也提高了导致他人死亡的危险之后,才能认定它属于杀人罪的构成行为,否则只能认为该行为属于不应予以处罚的不能犯。同理,当事后查明的各种事实表明,即使合义务替代行为也无力避免结果时,那就说明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并不具有规范所预想的侵害法益的能力。换言之,“如果对于相关的法益来说,某个违反义务的行为并未从实质上升高行为人之行为符合义务时所制造的危险,那就应当把它也同样看作是不受禁止的行为来加以对待。”[注]Schönke / Schröder / Lenckner / Eisele (Fn. 〔64〕), vor § 13 Rn. 99a.例如,消毒剂无法杀灭病菌的事实表明,要求工厂主事先对羊毛进行消毒的注意义务规范在该具体案件中已失去了效力,而违反该注意义务的行为也不再具备升高法益侵害危险的能力。所以,无论工厂主在主观上对工人的死亡是持故意还是过失,由于客观行为本身没有法益侵害性,故均不成立犯罪。[注]但是,如果像Roxin等学者那样将注意义务的结果避免可能性归入危险实现阶段,那么由于已经肯定行为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危险,所以在工厂主对结果存在故意的情况下该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未遂。(Vgl. Roxin (Fn. 〔18〕), § 11 Rn. 99.)但这一结论并不合理,因为既然判定行为实际上并未以法所禁止的方式升高了危险,那么该行为与那些完全不具备法益侵害性(即实行行为性)的不能犯就没有任何实质区别,故应完全排除其犯罪性。
五、 基本的结论
由注意义务规范效力的有限性所决定,即使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如果该法益侵害并不在注意义务规范的结果避免能力范围之内,即结果与行为的义务违反性之间欠缺必要的关联,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16条所规定的不可抗力,不能从规范上将该结果归责于行为。对于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关联的判断问题,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对于同时包含了作为和不作为要素的过失行为,只要其中积极作为的要素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就应当首先以作为犯的标准对行为进行考察;只有当作为与结果欠缺因果关系,或虽有因果关系但不符合过失犯的归责要件而不成立犯罪时,才可以补充性地考虑不作为犯的问题。
2.假定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归责判断中,特别是检验注意义务之结果避免可能性时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只是为了避免对假定因果关系思路的运用超出规范目的所容许的界限,故必须对之进行两方面的限制:第一,假定因果关系的考察范围只能限定在处于行为人的行为所涉领域之内、可能影响规范效力发挥的事实;第二,应当将合义务的替代行为限制在与违法行为同属一个行为类型的最低限度的合义务行为之上。
3.只要合义务替代行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达到了占据优势的程度,或曰只要违反注意义务行为升高危险的幅度达到大于被容许之危险的程度时,即可在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建立起为归责所必要的联系。但危险升高的事实必须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充分和确定的证明,否则只能根据罪疑唯轻原则排除归责的成立。
4.在客观归责的理论框架中,应将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定位于危险创设,而非危险实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