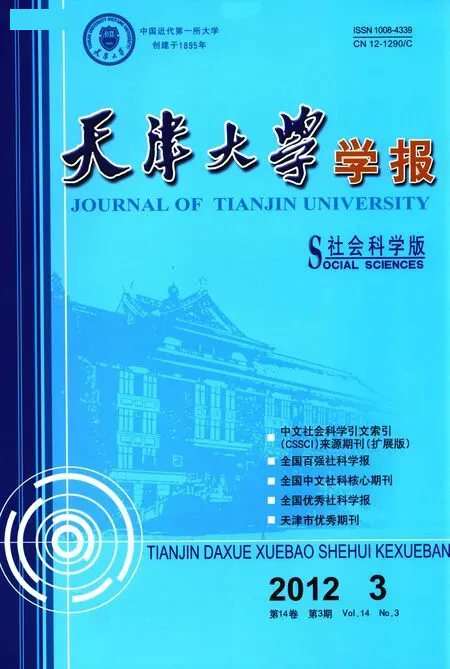论“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称谓的转变
张宇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72)
有关中国近现代“实业教育”转向“职业教育”是一个常言常新的话题,因为人们一般理解的教育都是包含了思潮、制度与办学活动三位一体的概念,无论从思想抑或行为的角度均可进行详细的解读。本文将要谈论的称谓转变则是与学校制度的更迭紧密联系的,从法制史的层面看,当以1922年“壬戌学制”的出台为标志,“职业教育”正式取代“实业教育”成为官方认可的名词。深入分析此次更名的前前后后,我们发现整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中间同样存在着复杂的实践背景、思维线索和社会根源。
一、称谓转变的简单过程
“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名称均出现较晚。据现有材料推断,夏偕复于1901年首先使用“实业教育”[1],“职业教育”更要等到1904年方才见于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只言片语[2]。而在此前,“洋务运动”中创办的造船、器械、铁路、矿山等传授技艺的学堂已经走过了几十个年头,却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用以总括其事的称呼,只是笼统地与同文馆、算学馆等一起视作“西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此类机构数量较少,门类分散,尚无统一的管理与规划;二是由于早期各类新式学堂往往面临着传统文化的激烈排斥,声名不扬。直到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当年的思想家才几乎众口一词地对改良教育寄予厚望。在朝廷重臣、学术权威张之洞看来,“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3],本国则只重视公共之学,只能培养百无一用的学究,为了富强起见,亟需大力兴办各种专门之学,尤其是在已有的兵学、矿学之外提倡专门针对农、工、商业的学堂教育,而“农工商”大体就是当时所指的“实业”。
1.“实业教育”占据主流时期(1901—1911年)
“实业(実業)”及其衍生词汇源自维新后的日本[4],属于“和制”汉字新词。依据该国学者的见解,“实业”应是日语独有,“如果勉强用英语来表述的话,它具有工业化初级阶段‘产业’的含义”[5]。民国初年的学者也曾有类似的看法:“西洋以工商立国,工业振兴,农商业亦随以不得不发达,因不发见有若实业教育之一名词,东洋以耕稼立国,至今犹囿于严士与农工商之分途,故日本别创一实业教育之新名词统括农工商一途。”[1]125
晚清的最后10年,来自日本的影响远胜其他国家。就在“实业教育”首次见诸文本的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并将制订学制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当时拿来参照的范本大抵就是明治后期的各种教育法令,鉴于“实业学校”和“实业教育”已是其中的法定名词,它们也自然地为中国所承袭。尽管1904年的“癸卯学制”以及之前颁布而未曾实施的“壬寅学制”都只有“实业学堂”而未见“实业教育”,但在时人议论当中,“实业”二字已经迅速压倒了一切:无论先前倡导“农工商学”的张之洞、严复,还是鼓吹“专门学”或“艺学”的康有为、梁启超,至迟到1906年,这些思想界的领袖都开始大谈特谈起“实业教育”,而其他类似的名词,如“职业教育”则只能处于“潜流”地位,乃至湮没不闻。
此刻的“实业教育”充满了积极的涵义:“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电报、铁路、邮政、矿务等类学堂”,亦被视作“实业之一端”[6];“实业学堂”由初等延伸到高等,“其教授之法重实习不重理论,由浅近而入精深”[7]。概言之,它既不像后来批评者所认定的那样范围狭窄,也决不过分地偏重理论、专重国家,“其用意与职业教育无殊,不过不以职业教育为言耳”[8]739。
2.“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用、混用时期(1911—1917年)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教育杂志》主编陆费逵发表了《世界教育状况序》一文,提出“吾国今日,亟宜注意者有三:国民教育一也,职业教育二也,人才教育三也”……于是继姚文栋后,“职业教育”又一次被引入人们的视野。
这两位“职业教育”初期的宣传者或许都是在研习日本教育的过程中接触到这一名词——陆费逵曾经专修日文,姚文栋更是有名的“东洋通”,“研究日本著作之多,无人可出其右”[9]——他们开始谈及“职业教育”也都没有专门的立论。然而随着清廷的覆灭,陆费逵有幸参与民国新学制的议定过程,这也使他有必要在公众面前将上述三类教育的联系与区分展示得更具体些。“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三者必当并重。盖无国民教育,则国家之基础不固;无人才教育,则兴办事业乏指挥整顿之人;无职业教育,则在下者生计艰困,在上者辅助乏才……今就鄙见,拟订学制系统。”[10]

在这篇见于1912年的文字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陆费逵所指的“职业教育”基本是一种理念上的范畴,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学制方案,他宁愿继续沿用初等与中等“实业学堂”的名称;第二,就其所划分的“人才教育”与“职业教育”而论,这中间明显存在着针对“在上者”与“在下者”的分工,正因为如此,后一类教育的办学层次便受到了限制,所谓“造就实业界之中坚人物”只能留给“高等专门”教育来解决。
实际上,随后出台的“壬子·癸丑学制”做出的一项显著变革正是将旧制“高等实业学堂”划入“专门学校”,从而将以“实业”命名的学校(这时改“学堂”为“学校”)限定在中学阶段。而与此同时,该法案中又遽然出现了“女子职业学校”的称谓,令其“参照各项实业学校规程办理”[11]。在这里,“实业”与“职业”两方面的名词已然并列地使用了。
需要指出的是,1913年“女子职业学校”的添设并非仿效欧美的结果,它的直接来源仍然是日本的学制。因为20世纪前后,日本妇女也同中国一样大都足不出户,以至有女子的职业“就是结婚,成为贤妻良母”[12]的说法,所以女子职业学校从一开始就突出了裁缝、刺绣、编物、造花以及割烹、洗濯、园艺等家事课程。
倘若民国初年大家认同的“职业学校”仅仅是指这样的特例,那么“职业”与“实业”的教育倒不难在外延上相互分别。历史真相却要复杂许多,那时人们普遍的用词其实处于一种缺乏“正名”的状态,不仅在讨论学制当中有将层次较低的实业学校等同于“初等职业”(学校)之类想当然的说法[13],时而也有“实业”与“职业”交叉使用的情形。例如实业家张謇就经常将二者混为一谈,但对于多数的教育专家,到底是要提倡“实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就不能不争辩一番,大致在1915年前,理论界仍主要是“实业教育”的天下,而后则“职业教育”日趋强势,到1917年已使“倾心于新教育者,大都异口同声,取一致之论调矣”[14]。
3.“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时期(1917—1922年)
1917年是称谓转变过程中关键性的一年。据《中华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记载,同年5月,“黄炎培等48人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实业教育正式改名职业教育”[15],从规范的意义上讲,“正式改名”的提法颇可商榷,因为职教社毕竟只是民间团体,无权变更法定名词,不过自此以后,“职业教育”的流行的确更加不可阻挡,“职业学校”取代“实业学校”在学制中的位置仅过了数年便已水到渠成。
当然,单从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的有关命令、咨文来看,其间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因为行政机构为了管理之便总是倾向于沿用既有的名称。只是到1919年后,官方文件中才较多出现了“职业”的字样,如1919年5月通咨“各省区为女子中学校可附设简易职业科”,1920年1月又“通咨各省请饬发职业教育参考书”,认可“职业教育,极关重要”[16]……而此时已是社会议论学制变迁的前夜。随着1922年11月1日《大总统颁布施行之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将“依旧制设立之甲种实业学校,酌改为职业学校,或高级中学农、工、商等科……依旧制设立之乙种实业学校,酌改为职业学校”,“实业”与“职业”之争终于得以盖棺论定。日后“实业学校”与“实业教育”尽管还能偶见于一些学术著作,但渐渐地它们仍然成了纯粹的历史名词。
二、称谓转变的原因探析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不曰改进实业教育而独提倡职业教育”?早在20世纪20年代,舒新城即撰文归纳了两点:一是各类“实业学校未足以括职业教育而尽给社会分业之所需”;二是实业学校自身办理不良,一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所言,“设置拘系统而忽供求,功课重理论而轻实习”,且“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不能解决生计问题”[8]742。
然则就其表述而言,仍不免失之简略。在本文看来,一次完整的更名过程,必然包含着新名词的兴起与旧名词的消亡,缺一不可。因此以下的论述将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第一,新名词“职业教育”为什么会在民国初年,而不是之前的任何时候兴起?第二,旧名词“实业教育”为什么会全面且急剧地消亡,而不是继续与“职业教育”并用或者混用?
1.“职业教育”流行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
(1)客观因素:办学中的困难。以发展“职业教育”为号召的社会舆论之所以会在民初形成,“直接的刺激因素是清末新教育制度确定后,普通和实业教育都有较大发展……毕业生出路问题却日益严重”[1]137。
在1906年“通行各省举办实业学堂”之前,几乎“所有学校及馆所,均由政府设立”[17],因其通常“特事特办”,即在官方主持之下,能够运用行政力量调配必要的资源,所以各地重点建设的农业和工业学堂往往得以附设或借助农业实验场、制造局和工艺厂作为实习基地,受教育者也能够“实地习练,学有所用”。但是,限于财务、师资等严重制约的“瓶颈”,这些官办教育的一整套经验绝无全面翻版的可能。“自振其业”、“致富图强”带来的规模扩张的要求,与现有支持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实业教育在推广的过程中不得不突破了以往当作国家实业来办的模式,转而成为一种发动政府、民间团体和个人共同参与,且任学生自谋生路的社会事业。于官办则容许因陋就简,对民间更不惜“敷衍门面”,以求一时之缓解。
据不完全统计,从1907年直至清廷覆亡的1911年,全国实业学堂及学生的数量分别由137所、3 693人增长到445所、36 615人[18],超过了同期正规教育总体的增长幅度。可就在同时,“工业不附设工厂,农业不附设实验场”所造成的弊端,表现为实业学堂毕业生“缺乏实习,学非所用”的现象,却也立即凸显出来。随着实业教育被某些公众戏谑地称为“失业教育”,这样一个名词符号所带来的消极意义已经使之失去了进行社会动员的合理性,恰在此时出现新的思潮便有了极大的可能,毋宁说成了一种必需。
(2)主观因素:教育界的反应。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职业教育”而不是其他称谓,例如,蔡元培曾大力推崇的“实利主义教育”,能够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呢?这显然还要归功于一批精英人物的提倡,以及教育界的群起响应。
最初,当陆费逵提出区分3类教育的观点时,整个社会的反响相当有限,至于他本人的思想,日后也没有更多的进展。结果我们看到,一向被视作“职业教育思潮”引领者的黄炎培此刻还在反映“时论注重实业教育”[19],甚至到了1915年,当他随同“游美实业团”考察之际,仍试图勉强地以“实业”之类对应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如《新大陆的教育》开头记载参观过6所实业学校,而经过查证,这些教育机构其实大可直译为“技术或工艺院校”,包括其中最负盛名的“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即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
然而随着考察的深入,美国综合制中、小学校设置的多种面向生产生活的课程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印象,“vocational course”(职业科)、“vocational school”(职业学校)等一系列词汇与其生动的办学实践一起不断冲击着原有的认识。特别是当他与当地教育官员交流,得知“现定之教育方针,在提倡职业教育,期以教育扶助生计”,种种关于本国教育现状的疑惑似乎全都豁然开朗了。通过亲自观察以及阅览美方提供的材料,黄炎培总结道:“职业教育者,在学说上为后起之名词,在社会上为切要之问题,而在教育上实为最新最良之制度也”[20]。由是他不再更多地谈及“实业教育”,而一心一意地主张推广“职业教育”。
1915年的这次游历是一位思想家平生的重要转折,对于提倡“职业教育”的学术思想衍化为社会思潮同样具有转折性的作用。“由于黄炎培与教育界、实业界的广泛联系,由于此时美国对中国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以致许多人认为美国是中国应效仿的榜样,而根本上,由于黄炎培把职业教育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相联系,这给国内教育界极大的振奋——不实用的普通教育、实业教育都应该让位给职业教育。在这种种因素作用下,倡导职业教育成为当时国内教育界最强烈的潮流”[1]139-140。
在这股潮流之中,除了黄炎培、顾树森、蒋梦麟、王则行等众多个人的宣传,一些重要的教育团体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余家菊、庄泽宣都曾高度评价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做的各项工作,据其记载:“(职教社)主持者初办《教育与职业》杂志鼓吹之,继设中华职业学校,继集全国中等以下各种实业学校设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21],“对于理论与实施各方面均有相当的研究实验与介绍……国人对于职业教育也渐渐加以严重的注意”[22]。
这种“严重的注意”很快扩展到了当年最重要的教育团体“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10月,联合会第3次会议便将职业教育列为“紧要问题”之一,会上取消了“实业教育分组”而代之以“职业教育分组”,通过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的“职业教育施行计划案”,大声疾呼欲救学生失业之弊,“唯有提倡职业教育”[23]。其后,该社团历年的会议都在热烈讨论“职业教育”,直到20年代初推动政府确立新的学制。
2.“实业教育”废止的表层原因与深层原因
(1)表层原因无法区分外延。当“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将教育领域的除旧布新与改变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便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与号召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起初着眼学生生计之时,集中批评的决不仅仅是不实用的“实业教育”,而恰恰在更大的程度上针对着“普通教育”。黄炎培在1914年的考察中,即发现失业现象“以中学为最甚……升学者三之一,谋事而未得者占毕业总数二之一”[19]49,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也开宗明义地说到“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失业于社会者比比”。那时的一批思想家未尝不是怀着“普通教育、实业教育都应该让位给职业教育”的理想,可是最终,在“实业教育”称谓消失的同时,诸如“普通教育”、“普通中小学校”等却一直沿用下来,且有“普通教育之终点当补以职业教育”[24]的分工。由此可见,单独的后起名词的流行并非称谓转变的充分条件,“实业教育”之所以会被迅速取代,必然存在着新、旧名词难以划清界限的原因。
其实早在陆费逵设计出“三类教育并重”的学制系统之际,作为类型统称的“职业教育”与那些仍被称作“实业学校”的教学机构之间即遗留下如何彼此协调的疑问。言者本人大约重在阐发理念而非界定外延,但在学者庄启看来,“所谓实业学校者”,已陷入了“不伦不类之地位”[25]。
上述一针见血的批评出自1913年,而在后来呼吁“职业教育”的热潮中,真正试图实现概念的可操作,也就是把它同具体的学校及专业门类对应起来却是1917年以后的事情。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不久于《教育与职业》杂志撰文指出:“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二者皆以解决生计问题为目的,然其范围不同。实业教育之高焉,高等专门实业亦属之;其下焉,仅为职业之预备者亦属之。故论其长,可谓过于职业教育”,但实业教育“亦仅限于农、工、商三种,而医生、教师等不与焉。职业教育,则凡学成后可以直接谋生者皆是。故论其阔,又可认为不及职业教育”[26]。1917年,作为传播“职业教育”影响仅次于黄炎培的人物,顾树森在其出版的著作中更鲜明地给出了二者“虽名似而义实异”的回答。不过他所做的多方比较仍然十分偏重教育功能与目的,关于“职业教育专为多数不能升学之儿童补习关于各种职业上之知识技能”,“范围广而程度浅”;“实业教育专为少数升学之子弟习农工商之专门教育”,“范围狭而程度高”[24]5的见识,也并没有使外延上的区分变得清晰而令人信服。
综合黄、顾二人的观点,“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就其所包含的教育机构而言,应当是一种“交叉”关系:前者可以对口各种各样的职业;后者则需要延伸到“高等专门”,如其不然,相互之间“阔”与“长”的判断都会显得无的放矢。然而说到现实,“职业教育”似乎从来不能将“学成后可以直接谋生”的人才培养尽数囊括(即便上文列举的教师和医生,直到现在一般也不被视作职业教育的培养范围),“实业教育”更是依据“壬子·癸丑学制”的规定被限制在初等或中等,如此则需要开展“职业教育”的机构势必和那些正在承担“实业教育”的机构趋向重合。
(2)深层原因缺乏职业分化。如果“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能够明确地区分外延,情况又会怎样呢?当笔者了解到东邻日本恰好也在同一时期颁布了《职业学校规程》(1921年),既承认了“职业学校”,却又将“实业学校”沿袭下来,使之能够并行不悖。
原来在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6年),传统的工商业急剧扩张,同时新型的服务业也日益蓬勃发展起来,社会上出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工作岗位,为适应就业形势而创办的大量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亦如雨后春笋,其设科除了一些早已有之的家事项目,更有照相、通讯、整容、演艺,按《职业学校规程》所列举的门类则多至30种。于是最初单为女子所设、大抵不出家门的“职业教育”膨胀起来,在一向以农工商为本的“实业学校”之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增量部分。“实业”与“职业”的教育虽有“年限之长短(实校长、职校短)”、“入学资格之差异(实校固定、职校不固定)”和“每学年授课日数及每周授课时数之多少(实校多、职校少)”[27]等不同之处,但以职业分工而论,二者确实形成了外延上的互补关系。
那些年中国的实业也曾一度兴盛,因“欧战发生,欧美之商品来源断绝……日货又以二十一条之要求,而受国人之抵制”[28],从而民族工商业有机会填补外资留下的存量空缺,企业数量与佣工皆显著增长。然其重点多在纺织、面粉、钢铁等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产业,整个社会对于一线劳动者的要求大体仍局限在传统门类,以至于宣传“职业教育”的思想家欲揭露“实业教育”范围狭窄、不敷所需而经常举不出恰当的例子,只好每每言及教师或医生。既然千呼万唤的“职业教育”并非如何扩大了“实业教育”的范围,而恰恰是与原先没有多少差别,那么对于相同事物两个相似的名称很难并存,必然是一个取代了另一个。
3.称谓转变的原因小结
综上所述,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称谓转变尽管受到了国外经验的显著启发,但基本进程、特别是其动因绝不应当简单地看作先仿日本、后学美国那样的“拿来主义”,它实际上是由两方面、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究其必要性,则如舒新城所见,首先归咎于“实业学校自身办理不良”,随之即出现了一个以黄炎培为代表的动员起来解决问题的精英群体,若非他们的努力,“推广职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29]等将不会在当时一呼百应。然而即便如此,新名词的兴起也不意味着原有名词的注定消亡,因为“职业教育”仍可能只是作为一种理念上的范畴而存在(如昔日陆费逵的观点,或者是今天的“终身教育”),从而令“实业教育”、至少是“实业学校”能够在新思潮的冲击下,通过吸收其重视个人生计的涵义而延续下来,直到黄炎培、顾树森等致力于严格地将“职业教育”外延与现实的教育机构一一对应,方才消除了这种可能性。至于实指学校类型的“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究竟能否并存,这里只能根据别国的情况加以推断:假如当时的中国涌现出为数众多的需要依靠学校大规模培养人才的新兴职业,“职业教育”和以农工商为主的“实业教育”或许容易找到一种划分外延的方法,两个不同的称谓或许会一起使用更长的时间。否则,名词间的一取一舍就会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关于称谓转变的评价
发生在20世纪初职教领域的这次更名运动究竟意义如何?积极的方面至少体现在两点:第一,从当时的社会效果来看,采用“职业教育”的名称并突出赋予其“解决个人生计”的涵义,确实比“振兴实业教育”更好地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使人们更加认同此类教育的意义;第二,从最后学制的修订来看,“职业教育”范围的界定摒弃了旧学制对于“实业教育”的列举主义,如农、工、商等,而取富有弹性的概括主义,解决了先前“不依正当统系而设之学校,皆不入学校统系”[30]的弊端。
至于说它的局限性,大致可以总结出两点。第一,称谓的转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职业教育自身的教法不良。就在人们热议“职业主义”,“醉心于美国分科制”的时候,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起人之一蒋维乔即诚心告诫职业教育“不惟其名而惟其实者”,他认为我国实业教育所以成绩较小,原因不在于名称或制度,而在于社会经济事业萧条和课程仍属“纸片教育”[31]。可惜这种声音很快便被淹没了,时论仍然偏重“名词之争”,而相对忽略了研究具体问题,如此也就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职业教育相比以往的实业教育只是“改头换面”而未能“脱胎换骨”。第二,即使单纯着眼这种“名词之争”,当年界定的“职业教育”范围也依然受到了局限。本来按照张之洞描述,教育的类型已经分为“公共之学”与“专门之学”,后者即包含了“农工商学”(实业教育),以及其余各种专业人员的培养,但到了陆费逵,尤其是黄炎培、顾树森那里,“职业教育”实际仅被视作与“专门教育”相对的学历层次较低的类别。倘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一种更为合理的外延划分或许应当是首先区别“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再于“专门教育”之中依据“实用”与否(而非层次高低)分出“职业教育”及其对应的“学术教育”[32]。
[1] 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 周洪宇.谁在近代中国最早使用“职业教育”一词[J].教育与职业,1990(9):47.
[3] 张之洞.劝学篇·学制第四[G]//苑书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742.
[4] 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等.汉语外来语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316.
[5] 寺田盛纪.日本职业教育和训练的研究状况及其课题[J].陆素菊,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 (1):45.
[6] 清政府.奏定学务纲要[G]//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7-8.
[7] 清政府学部.通行各省举办实业学堂文[G]//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11.
[8] 舒新城.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小史[J].教育与职业,1929 (100):36.
[9] 王宝平,黄遵宪,姚文栋.《日本国志》中雷同现象考[G]//胡令远,徐静波.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38.
[10]陆费逵.民国普通学制议[G]//琚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620-621.
[11]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G]//琚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721.
[12]胡 澎.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J].日本学刊,2002 (6):135-136.
[13]湖南省教育会.改革学校系统案[G]//琚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836.
[14]贾丰臻.实施职业教育之注意[G]//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231.
[15]中华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华大百科全书·教育卷[M].北京:中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520.
[16]中华民国教育部.通咨各省请饬发职业教育参考书[G]//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202.
[17]锺道赞.现代中国职业教育之产生与其发展[G]//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532.
[18]王 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J].近代史研究,1987(3):261.
[19]黄炎培.考察本国教育笔记[G]//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20]黄炎培.新大陆的教育:下编[G]//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108.
[21]余家菊.中国教育辞典[M].上海:中华书局,1928:1072-1073.
[22]庄泽宣.职业教育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57.
[23]中华民国教育部.教育部抄发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职业教育进行计划案[G]//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194.
[24]顾树森.德美英法四国职业教育[M].上海:中华书局,1917.
[25]庄 启.论实业学校令与专门学校令议决案[G]//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219.
[26]黄炎培.职业教育析疑[G]//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10.
[27]潘文安.日本之职业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88.
[28]杨 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G]//陈真,姚洛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8.
[29]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G]//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180.
[30]庄 启.实业学校改制论[G]//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229.
[31]蒋维乔.职业教育进行之商榷[G]//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234.
[32]徐国庆.职业教育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