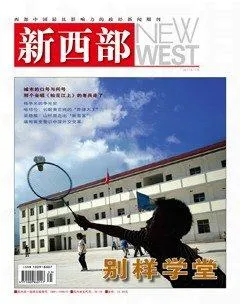杨争光的争光史
从电影《双旗镇刀客》到《五魁》,从电视剧《水浒传》到《激情燃烧的岁月》,从小说《越活越明白》到《少年张冲六章》,他不仅涉猎广泛,而且出手所及屡有建树,属于文化人里的多面手。无聚无类、无宗无派的他,行文行事便显得无规无矩、无忌无畏。他所获得的一切,使他与贾平凹、陈忠实一起,成为中国文坛上的“陕西三宝”。
杨争光一直很忙。
他西安、深圳两头跑,写完小说写剧本,哪有不忙的道理?
不过,杨争光的忙,也与他过于复杂的身份有关。用陕西作家秦巴子的话说,“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他是一个复杂的构成,关于文学、文人、文化的种种时髦或并不时髦的说法,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佐证:先锋小说、寻根小说、地域文化小说、诗人、著名电影编剧、电视剧大腕、影视公司老总、策划人、专业作家……”
在秦巴子看来,像杨争光这样的家伙,必定是一个“异数”。而杨争光对自己的定位却有点儿政治色彩——“第三种人”。
高考恢复的幸运者
1957年,杨争光出生于陕西乾县大杨乡祥符村。他从小喜欢看书,小学三年级就“啃”上长篇小说,12岁便入选县上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但是,“文革”期间,一般农家孩子学习再好,也都是一样的出路;回乡。杨争光17岁回乡务农,但他却一直不甘心,“抓紧一切机会往上爬,想改变农民身份,能把手伸向国家的馍笼子里”。
一回到村上,杨争光就当上了村剧团团长,管着从十几岁的毛女子到60多岁老头子共几十号人。劳动、排戏之余,他从未放弃过读书,从本村到邻村,只要能借到的书,他都借来看。
渐渐地,杨争光产生了写作的冲动。他参加了县文化馆举办的一年一度为期两个月的文艺创作学习班,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作家。
这样的梦做到1978年,开始变得真实。
能参加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杨争光直叹幸运。21岁的他,顺利地成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
终于“把手伸向国家的馍笼子里”,杨争光自然倍加珍惜。上大学的4年里,他几乎没有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学校规定晚上10点之前学生宿舍必须关灯,他就待在厕所里,因为这里有灯。他站在灯下,要么拿一本书看,要么拿几张纸涂抹着诗一样的句子。
那时候,很多年轻人都爱读诗,爱写诗,杨争光也不例外。山东大学有一个云帆诗社,社长就是杨争光。大一大二两年,他基本上都是在读诗,几乎把学校图书馆里翻译过来的外国诗都看过了,中国很多诗人的专辑也都读过。
读得诗86dced9fba7b654911ca90fccddcba8a多了,杨争光就开始写。
他的一首名为《钻天杨》的诗这样写道:你把生命聚成光束/从地心向蓝天射去/当太阳把风熏成红色/在这红色中颤动的/是你绿色的旋律。
还有一首《给法桐》:你来自法国?不,我不相信!资产阶级的树在无产阶级的国度里/竞能抽枝长叶!哈哈!嗬嗬!
这两首写于1979年的诗,很符合当时的社会语境。刚刚走出10年动乱的年轻人,重新思考人生,思考理想和信仰,于是便有了顾城的《一代人》,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杨争光虽然没有这些人名气大,但他的诗显然也是有专业水平的。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乎每年都出诗选,杨争光的诗好几年都有入选。
写诗的同时,杨争光也写小说。他写的短篇小说《霞姐》,获得了山东省大学生文学创作奖。
年轻的杨争光,一天天地向他心中的梦想逼近。
地下室里的小说家
1982年,杨争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
那一年,杨争光第一次去了北京。站在天安门广场,他感慨万千,泪水打湿眼眶。回到天津,便写下了一首诗——《我站在北京的街道上了》:
“我站在北京的街道上了/我流眼泪了/我是从小村里来的/小村很远很远/要过三条大河和很多山/也要过许多小村……小村的人都说/最有福气的人才能去北京/我是我们村最有福气的人了/我流泪了……”
杨争光说,“一个拉架子车种地的农民,竟然有一天能到这个地方,能站在那么宽阔笔直的长安街上,能站在天安门广场,这种感受我无法用语言描述。”
让杨争光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个朋友专门到天津来给我念了这首诗,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选择到天津工作,本是杨争光有意为之。他想走得远一些,扩展一下自己的视野。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走了岔路。“天津是个灰色的城市,我觉得我跟天津没有缘分。”他说,在天津的两年,没有接触到这个城市的体温,没有家的感觉。况且,和妻子两地分居,总不是个事儿。
于是,本来打算在天津干满5年的杨争光,两年后就调回西安,进入陕西政协工作。
回陕不久,杨争光被派往陕北延长县下乡蹲点,这段生活,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农村,杨争光一直在观察,在思考。他发现,中国农民最原始、最顽强的性格和品性,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千上万穿西服打领带的所谓城里人,他们的灵魂深处仍然保留着一个农民的精神王国。这些发现,成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主题。
那几年,杨争光先后发表了小说《从沙坪坝到顶天峁》、《鬼地上的月光》、《一棵树》、《正午》、《干沟》等作品。接着,中篇小说《黄尘》、《赌徒》、《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等先后面世,引起文学界广泛注意。
1987年,杨争光参与创办了《陕西政协报》,后来还成了该报的副总编。有一段时间,他很想把这份报纸办好,但他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天真。“当时随着形势的变化,我越来越感觉到办报纸很难实现自己的很多想法。”
让杨争光苦恼的还有一个现实问题。调回陕西后,他的住房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政协办公楼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十几平方米的地下室,他一家人一住就是很多年。
于是,1989年,当西安电影制片厂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制造真正的西部片
杨争光起初写剧本,还是缘于西影厂一个朋友的鼓励。朋友说,他写的小说画面感比较强,就凭这一点,写电影剧本也没问题。
“我那个时候还年轻,就是牛犊,给个场地就可以乱跑。看了朋友给带来的几个电影剧本,就开始写。”当时杨争光还没调动,他给单位领导撤了一个谎,说得了肝炎,还到医院给开了一个假证明,然后住进西影厂招待所开始写作。
这个电影剧本,就是《双旗镇刀客》。
剧本写完了,杨争光的调动手续也办妥了。他进厂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双旗镇刀客》采景。
杨争光说,他写《双旗镇刀客》时,在西部走的最远的地方是宝鸡,剧本里的环境和场景是在想象中完成的。到了戈壁滩以后,他才知道这世界有多大。
“拍一部好看的,真正意义上的西部片。”杨争光信心十足。
他们跑到甘肃,在兰州租了两辆吉普车,行程万里,终于发现了一个古城堡,叫许三湾城,是汉代留下的,四面围墙,保存完好,但里面什么也没有。经过美工设计,他们在围墙里搭了电影中的那几条街道。
一路上,杨争光都跟导演何平住一个房间。杨争光记得,何平对他非常照顾,每每当他回到房间时,何平都给他放好了洗澡水,他心里感觉很温暖。
《双旗镇刀客》拍成后,由于各种原因,有人给电影局写信告状,希望不要通过这部电影。但是,后来认识到这部影片价值的人越来越多。说起内地的西部片,几乎所有人都会提到这部电影。
在香港,《双旗镇刀客》在一家戏院连续上映72周,创下了内地华语片在港上映的纪录。从1991年起,这部电影连续获得多项荣誉,继在国内获金鸡奖最佳美术奖后,1992年又先后获得香港金像奖十大华语片奖和台湾《中时晚报》商业映演类大陆优秀电影奖。同年,该影片又获得日本夕张国际惊险与科幻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93年,何平因该影片拿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导演奖。
正是因为《双旗镇刀客》,几年后,杨争光被央视挑中,让他与内蒙古作家冉平一起,承担了电视剧《水浒传》的改编工作。
1992年,同样因为房子问题,杨争光再次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我一家三口在那间地下室已住了整整8年,恰好和常宝装哑巴的时间一样长短。”由于西影厂依旧无法给他分房子,他只能辞去工作,自谋出路,加盟长安影视制作公司,总策划、艺术总监一肩挑。
1995年,靠着触电写剧本挣来的钱,杨争光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也从地下搬到地上,一家人从此能看见太阳了。
“侨居”西安的深圳人
1997年年底,杨争光被深圳市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成为市文联的一名专业作家,此后,他先后担任深圳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副主席、影视家协会副主席。
2001年9月,由杨争光担任总策划,解放军总政治部影视中心、沈阳军区影视中心、长安影视制作公司联合出品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一些地方电视台开始播出,谁也没有想到,这部并不被看好的电视剧,竟在各地掀起一波又一波收视高潮。有数据显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播出后的两年时间里,北京卫视应观众要求重播5次,首播收视率达到12%,重播收视率平均也达到4.7%。
不过,在深圳,杨争光很快就从影视剧转回到他所钟爱的小说创作,先后推出了长篇小说《越活越明白》和《从两个蛋开始》。
2003年,《收获》第3期刊登杨争光耗时两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小说以偏僻乡村符驮村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对建国以来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文学化的梳理。“这段历史是很特殊的,有很多东西与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有关。”杨争光说,“对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我最熟悉的就是这段历史生活,能够表达我的很多想法,另外也是因为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作家来完整地写这50多年中国人所经历的生活,那我自己就写一部吧。”
2010年5月,杨争光再次推出长篇新作《少年张冲六章》,把一个“问题学生”活生生地摆在读者眼前,引起文学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有人将其称为关中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少年张冲的故事是杨争光听弟弟杨卫国说的,他随后又断断续续花了4年时间,收集了许多“资料”,走访了老家乾县的几个学校,还在学校熄灯后去男生宿舍里和学生们闲聊。他甚至还专门读过一本关于摇滚的书。
《少年张冲六章》出版后好评如潮,并先后获得“人民文学奖”和《当代》“2010年度最佳长篇小说”。杨争光说,这本书是写给有话语权的人的,为人父母者,为人师长者,孩子看不看无所谓。“我写的是当下的问题,更是未来的问题,也是历史的问题。不能说没解,但不提供答案。”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曾在《杨争光论——对精神太阳的渴盼》一文中说:“在陕西乃至整个中国文坛上,杨争光的小说都是一个变异。他被称为写农村的‘乡土作家’,他自己也以写农民而自命,但他笔下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却迥异于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不仅浑茫和深邃,而且奇异神秘热闹而荒诞,带给人们新的感受和新的认识。”
而杨争光对自己的定位却很是矛盾,他说他“是好人里的坏人,坏人里的好人”、“在浮躁的人中我算不浮躁的,在不浮躁的人里我算浮躁的”。他还自封为“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外的“第三种人”。“可以是奴隶,但不可以做奴才。奴隶是种身份,是遗传、继承的,奴才是自找的。”
虽然已是深圳人,但杨争光很多时间都生活在西安,以至于有人说他是“侨居”西安的作家。
2007年,陕西师范大学聘任杨争光为影视文学专业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他还担任了中国西部电影电视研究中心主任。
离开农村,行走天下30多年,杨争光也学会了用普通话应付一些场面,但他的普通话总脱不掉陕西味儿。他报自己的电子信箱,com常让人听成“烤馍”。在他每次回深圳的行李中,最多的是乾县挂面,他说不仅自己吃,也带给那里的朋友们。
作家高建群说杨争光,“羊绒衫是澳大利亚的,裤子是美国的,皮鞋是英国的,惟肚子是乾县的,黏面和锅盔总也吃不够。”
《少年张冲六章》发表后,杨争光从各种社会反响中找到更多的自信。“这部小说是我与当下距离最近的一次写作,它发表后的反应给我一种很现实的感觉。”他说,“下一部作品是否这样写,我也不能确定。但写作的动力还在,因为我还有以小说的形式说话和交流的欲望,小说艺术还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