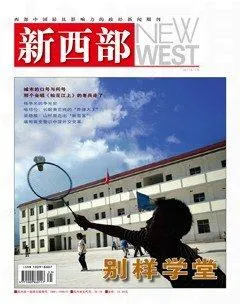张平宜:为麻风村孩子建学校
“他们就像一群被遗弃的孩子,从一出生下来就没有了希望。”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第一次踏足麻风村的张平宜看到除了一群畸残的老人之外,还有一群正要长大的小孩。此后10多年,她着手将一个供麻风村子女上学的教学点,一点点地建成为一所完善正规的学校。
1999年底,张平宜作为台湾女记者,第一次走进四川大凉山的麻风村。
“麻风村里到处都是游荡的孩子,他们不再有父辈那可怕的疫病,眼神里流露出野性的天真。但是他们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一辈子走不出麻风村。”与张平宜一起前往的同事送给一个孩子纸和笔,孩子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让他们感到无言的震撼。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说。
可是,张平宜想做的一切却并不容易。此后的日子,她“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直到麻风村的孩子有了属于他们的美丽校园。
大凉山麻风村里的孩子
到四川麻风村开展救助工作之前,张平宜一直过着幸福安稳的生活。“虽然不是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从小也是吃好的、穿好的,娇生惯养长大的。”
即便结婚生子后,她也没有被生活琐事拖入家庭妇女的行列,生了孩子都丢给妈妈带,因为讨厌厨房的油烟味,从来没做过一顿饭。
张平宜有一份热爱并且引以为豪的工作,作为台湾《中国时报》的专题记者,她经常“满世界地跑,拿到一个专题就消失三个星期”。当记者十几年,她制作的新闻专题获得过台湾地区新闻界最重要的奖项。
人生的转折,往往会来得既富有戏剧性又不知不觉。
1999年底,张平宜作为“世界麻风协会”的随团采访人员,到大陆的麻风村考察。当时的背景是:麻风病已有突破性治疗方式,许多国家将其从一级传染病中除去,对病人不再采取隔离措施,而让其回归社会进行治疗。
第一次走进大陆的麻风村,曾让张平宜产生“再也不去”的念头。12天的时间,她探访了四川、云南的6个麻风村,见到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景象。她原本以为大陆的麻风村和台湾一样,是一个以老人为主的疗养形态的村落,可她在四川的麻风村看到,除了一群畸残的老人之外,还有一群正要长大的小孩。
这些村子极为偏僻,以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都烂了,爬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特别是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大多也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当时的张平宜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小儿子刚满3个月。她想知道在这些麻风村里有没有一所学校,可以让这些孩子读书。她一直打听,终于在2000年得知在四川凉山州越西县一个叫大营盘的地方,有一所专为麻风村子女开设的小学。她非常兴奋,立刻从台湾赶到大凉山。
初到大营盘,张平宜发现这里就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地方。
据她了解,1958年,越西县所有的麻风病人都被集中安置在这里,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麻风病人结婚生子,小村变成了大村。但是,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村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只是感觉到,自己是“令人害怕又讨厌的人”。除了集体户口,他们没有个人身份证。他们几乎没出过村子,而外面的人也从不到村里来。
大营盘的孩子无一例外是麻风病患者的后代,他们一生下来,就被周围村民称作“癞子娃娃”。如果偶尔出村,都会遭到辱骂。村里的老师去县城开会,也没有人愿意和他同桌吃饭。
事实上,麻风病是一种不容易传染也不会遗传的疾病,95%以上的人对麻风有天生的免疫力,只有极少部分人会被感染。张平宜采访发现,整个大营盘共有1000多口人,其中真正患麻风且至今尚存活的病人大约不到100人,其他全部都是麻风病人生下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但是,来自外界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张平宜找到的大营盘小学,其实只是两间盖在水塘边且即将倒塌的土房子,学校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黑板上全是洞。教室里挤着70多个学生,大部分只能站着听课。孩子们的脸都很脏,“脏到只能看见两颗眼珠子”。更危急的是,学校惟一的代课老师王文福因为家庭困难,准备过完年就外出打工。
如果连这所学校都垮了,这些生长在麻风病阴影下的孩子还能有什么希望?张平宜焦虑之中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她向王文福老师许诺:“你留下来,我去筹钱盖一所新的学校。”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
一回到台湾,张平宜发起募捐活动,奔走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她想了很多办法,出书、讲演、义卖,能试的办法都试过了,但筹得的款项却并不多。
她继续坚持。圣诞前夜,她将朋友送的漂亮蜡烛拿到台北一个教堂外义卖,在冷风中站了一晚上,却没开张:第二天再去,又是一晚上,只卖出一份蜡烛。她的举动感动了朋友和同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几位台湾明星助阵义卖,一晚便募得60W元新台币。
还有朋友送来了库存商品,“电蚊拍、洗发水……他们捐什么,我就卖什么。”张平宜笑着说。
2001年,张平宜干脆辞职,专门做这件事情。每个月,她靠丈夫给的一万台币零花钱,打出租车,去拜访资助人,并不断说服那些潜在的资助者。
不久之后,带着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善款,张平宜回到大营盘,开始重建大营盘小学。
此时,她的身份从一个募款人变成了“监工”。在新教学楼建设的每一天,她都要在县城宾馆和大营盘村之间颠簸的土路上来回往返,工程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要给资助的人一个说法,让他们觉得钱捐给学校是对的。”
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张平宜刚到大营盘的几年,与当地官员时有摩擦。“张小姐很难缠的。”当地官员也这样评价她。
学校的通电、通水、修路,都需要当地政府支持。张平宜去找管事的部门,跑过无数次,但几乎没有官员愿意坐下来听她讲5分钟。有时她带着满腔热忱过去,“他们却在打麻将,我就坐在旁边等待”。
张平宜无法和那些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当地官员也不能理解:“这件事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有一段时间,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
张平宜后来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最初经历是“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
2002年,历经一年半的重建,大营盘小学有了崭新的面貌。看着眼前的6间崭新的教室和生活用房,王文福老师像做梦一样。
但让王老师没有想到的是,大营盘后来的变化,更是一次次超越了他梦想的边际。
2003年,张平宜在台湾创立“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专注于大营盘麻风病人子女的援助教育。这一年,她也从暂住的越西县城宾馆搬进了大营盘小学。
住下来以后,张平宜发现,让麻风村的孩子回归社会,光有教室还远远不够,就算给这些孩子马上穿上很好的衣服,但他们的文明、学问是需要慢慢累积的。
从洗脸、刷牙、洗澡开始,张平宜教那些孩子如何“保持个人卫生”。而让她时时痛苦不堪的是跳蚤、苍蝇和头虱。“如果有一群孩子围着你,他们离开时,你身上就被跳蚤咬得一片红了。”
麻风村村民仅仅共用一井泉水,每个村民家人畜共处,生火吃饭睡觉的空间也几乎毫无分别,卫生观念几乎是零。大营盘小学重建后,张平宜特地从山上引来泉水并兴建蓄水池,让学校有了全村中惟一的水龙头。
由于水源不稳定,没有锅炉、热水器等设施,住校学生平均每个星期洗一次澡,而且是几个人一起分着洗一桶热水。尽管如此,学生已是干干净净,比起住在麻风村里的孩子已经好上几百倍了。
住在学校时,张平宜还成了孩子们的课辅老师。她教孩子们讲普通话,也给孩子们修改作文。她熟悉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状况与脾气秉性,几乎可以叫出所有孩子的名字。
假期的时候,张平宜邀请台湾的志愿者、内地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以及外国人到学校来参观。看着穿着制服的学生,朋友说她建的是“麻风贵族学校”。
不上课的日子,学校会放电影,几十个学生挤在走廊上看着小电视放出的DVD。不管是热门电影,还是探索频道,或者迪士尼卡通,都能使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毕竟,那是他们这一辈子从来不曾接触过的世界。
建校史上首次毕业典礼
王文福老师一直遗憾一件事:自己坚守了十几年的大营盘小学,自1986年建校以来,没有出过一个小学毕业生。
当初由于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没有公办老师愿意到大营盘来教书。王文福作为代课老师留在这里,他不会彝语,要教这些不会汉语的孩子们十分困难。多年来,这个学校就像一个扫盲班,一到四年级,学生就越来越少,都被父母喊回家干活去了。而且,村里还有早婚的习俗,不少孩子十五六岁就退学结婚了。
于是,与家长“抢孩子”,成了张平宜在大营盘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一次次“战斗”中,以“凶悍”闻名的张平宜常常能获得“胜利”。她的制胜法宝是:冲到被叫回家的孩子家长面前,“严正”地告诉他们,如果退学,就把孩子上学4年的所有费用都赔回来。
她也试图给村民讲道理,希望他们看远一点。“读书是种天分,并非人人适合,但每个人都应享受义务教育,具备基础素养。这9年里学到的东西,能让孩子一生过得更有尊严。”
2005年,大营盘小学终于迎来了第一届小学毕业生。由于这是麻风村设立半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学生的家长早在一个月前就按彝族习俗替子女缝制背心,然后在毕业典礼那天亲手为孩子穿上。
16名孩子中,最大的23岁,是3个孩子的爹。还有新婚的、订了亲的,有兄妹档、姐妹档。虽然在未来的人生里,这张小学文凭对他们来说未免太过卑微,可在大营盘村民和张平宜看来,却是里程碑式的大事。
因为对在毕业典礼上播放的歌曲意见不统一,大营盘的第一届毕业典礼意外地举行了校方和官方两个版本。在张平宜设计的毕业典礼上,她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感恩的心》,感谢台湾友人一路陪她走过来的辛苦与付出,小虎队的《放心去飞》则是毕业典礼的主题歌。
毕业典礼隆重、热闹又悲情。站在16个大龄毕业生旁边,张平宜忍不住泪流满面。
而在官方版的毕业典礼上,张平宜所关心的则是她的孩子们能否接受中学教育。她询问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孩子们可以到哪里念中学?“张阿姨连问两三次,他们都保持沉默。”第一届毕业生拉且回忆道。2005年9月,经地方政府努力,大营盘的16个毕业生才被邻近的新民中学接收。
也是在这一年,张平宜参加了一项圆梦计划,赢得170万元新台币。加上其他善款,她又开始构想一个更宏大的规划:扩建大营盘小学,把学校办成一所可容纳300名学生的州立希望学苑,让更多凉山州麻风村的孩子都有机会念书。同时,在学校周边建一个能让孩子吃饱饭、让年轻人就业的农场,使大营盘小学具备自我造血的功能。
但是,扩建工程困难重重。在凉山州台办协助下,张平宜拿到了四川省台办批准扩建文件,越西县政府和教育局则希望大营盘小学自行征地。由于五保户的拆迁补偿涉及越西县民政局,张平宜在等待民政局领导两个星期仍不见踪影之后,一下子又犯了牛脾气,让人强拆了五保户的房子。民政局局长一来就跟她吵架,“你以为台湾人就了不起了,跑来欺负我们麻风病人。”
在一次政府协调会上,张平宜坦言:“我是个没有特别宗教信仰的人,也是一个没有政治色彩的人,我来越西,纯粹是一份人道关怀,但这几年在越西真的太痛苦了,其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当做一个敌人来对待……”
在张平宜的努力下,大营盘小学扩建最终完成,建成一个拥有教学楼、宿舍楼、篮球场、乒乓球桌的美丽校园。学校也从最初只有1个老师、70个学生的教学点,变成有12个公派教师、300余学生的正规小学。邻近5个麻风村的子女都来这边上学,其中还有10%非麻风村的孩子,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
但是,经营农场的事情最后却不了了之。“我们主要任务还是教孩子,真的没有精力管种地的事儿。”校长罗桂平说。
为了“最甜蜜的负担”
“慈善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这是张平宜慢慢悟出的道理。麻风村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他们也有自己的运转规则和习俗,面对外来的援助,他们也有自己的选择自由。
她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对于辍学的孩子,她曾认为是“感情上的背叛”。现在,她不再苛求每一个孩子都按照她设计的道路走。“但我也不可能因为有孩子离开而什么都不做。”她开始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渐渐地抓住了对大凉山的感觉。
但问题远未完结。
小学毕业后,大营盘的孩子们必须每天走路3个多小时去新民中学读书。当地对麻风病人子女的偏见还没有消除,他们的住校请求不能被批准。孩子们经常趟水抄捷径。河水湍急,山里的孩子身手矫健,但仍常有落水者,湿淋淋地跑回来。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很少有孩子能够坚持读完中学,“走路又远,功课会跟不上,还常常被同学歧视和欺负。”张平宜咬咬牙,“好,那么我就来盖一所中学!”
越西县邻县的一位县长曾同意批给张平宜一块地,可当她兴奋地带着从台湾募集来的钱款回到凉山时,这位县长却已经调离,而新任县长拒绝了批地的请求。
张平宜失望至极,大哭了一通。她又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向凉山州政府写申请。最终,30亩地批了下来。2 008年,在政府主导下,一座气派的中学在大营盘拔地而起。
同一年,张平宜又利用弟弟在青岛投资的企业,开设“希望之翼学苑”,为想要外出打工的学生们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当年大营盘第一届毕业生拿着毕业证欢喜拍照时,一个朋友说:“他们快20岁才小学毕业,读完大学得多大年纪啊。”朋友的这句话,让她萌生创办这个培训基地的计划。
“如果你接触过‘我们的孩子’就会知道,他们非常活泼、健康、开朗。”张平宜常形容他们是“最沉重的负担”,也是“最甜蜜的负担”。
张平宜的两个儿子每年暑假都会到麻风村当义工,他们和大营盘的孩子几乎是一起成长的。大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如今,张平宜与县上的关系已经改变了许多。她的慈善行动把两岸媒体的目光都引向了这个群山包围下的无名村庄。大营盘也告别“隐形村庄”的历史,成为越西县第288个行政村;人口普查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政府还投资改造了张平宜当年援建的那条路,给村里陆续通上自来水、电、广播和电视网。
2011年5月,张平宜获得首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奖”。领奖那天,麻风村的孩子们对她说:“张阿姨,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你不仅是做了很多的事,而且你也是个漂亮的女人。”
张平宜开心不已:“好,这个OK,这个我喜欢。”
单枪匹马独闯凉山10年后,张平宜在台湾出版了《台湾娘子上凉山》一书。“想用这本书给自己一个交代,想暂时告一段落——我也有我自己的人生啊。”
可一转身的工夫,她又开始操心起孩子们的事儿。2011年9月,因为没有老师和足够生源而闲置两年的大营盘中学,终于迎来首届48名学生。他们从大凉山深处的麻风村走出来,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而这也意味着,未来几年,张平宜还得为这些孩子在海峡两岸飞奔来去,就像她自己所说的,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舍不下了,那个地方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掌控着她的悲欢。
不过,对张平宜来说,这样的牵挂,快乐大于担心,因为“最苦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