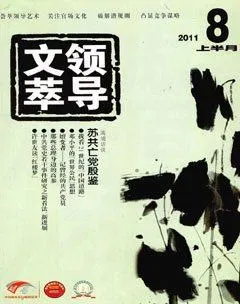香港官员深受“权力之累”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申报拥有8套住房,但是,没有香港人会怀疑他是贪污腐败所得。原因何在?
香港的官员们真的很累。
近来,香港媒体很多头条新闻都是和政务官员的健康问题有关。先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刘吴惠兰因肠癌请辞,然后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林瑞麟接受心脏病手术,接着又爆出教育局长孙明扬患肾衰竭需要定期洗肾。
有意思的是,这些报道的“中心思想”不是表扬官员们“带病坚持工作”,而是批评其“隐瞒病情”并且“拒绝辞职”。这正体现了香港社会所承认的“普世价值”:要把拥有权力者关在笼子里。
为何香港清廉?
2010年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香港得分8.4,排名第13,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排名第二,中国大陆则以3.6分排名78。香港这么高的清廉指数是怎么来的呢?
提到香港的廉政,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廉政公署(ICAC)。
成立于1974年2月的廉政专员公署,最初是为了查处警察内部的腐败行为,其第一个整肃对象是当时担任总警司(警察部门最高官员)的葛柏。当时葛柏被发现个人财产多达430多万港元,但在接受调查期间逃离香港,激起民间爆发“反贪污、捉葛柏”的大游行。
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百里渠爵士在调查后表示,政府需要一个独立的反贪污部门,才能有力打击贪污。
现在廉政公署的职权范围已经扩展到所有政府部门、私营公共事业机构乃至私人机构。廉政公署的功能也从查处腐败扩展到防止贪污和社区教育,分别设有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廉政公署的工作由四个独立咨询委员会严密监察,而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均为社会知名人士,并由非官方人士出任主席。
廉政公署并非香港政府内部唯一的监督机构,比如申诉专员公署也是独立于其他部门之外直接对行政长官负责,其职责是监察政府运作,负责处理及解决因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行政失当而引起的不满和问题。对于处理的投诉,申诉专员公署都会发布公告,对相关责任机构和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此外审计署、警务处等等都从不同层面对其他政府机构进行监督。
而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的相互制约,则是更高层次的监督。虽然香港的立法会还没有实现完全由民主选举产生,但是民选议员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到重大政策,小到“一月洗几次肾”,问责制官员们经常要到立法会接受议员尖锐的质询,而且这些都是全程公开的,市民通过网络就可以观看直播。
“第四权”让草根有力
如果说上述这些都是“体制内”的制约,那么号称“第四权”的新闻监督则是体制外的、草根的力量。
在人口不过700万的香港,仅中文日报就有17份,其中多份发行量在10万以上,电视频道有100多个。激烈的竞争迫使媒体努力去获得能吸引眼球的新闻,除了明星八卦之外,对官员的曝光自然也是重头之一。事实上,前面说到的高官患病、违反利益回避等新闻,无不是由媒体首先披露出来的。
媒体能够发现并披露这些新闻,是基于香港新闻业的充分自由和激烈竞争。竞争迫使媒体去发现新闻,而自由则保障了媒体能够发布新闻。香港的“狗仔队”十分出名,虽然他们时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但是其敬业精神却令人称道,有新闻的地方就能看到他们,而且大到直播车,小到偷录偷拍,他们的设备往往比警方还先进。
更重要的是,虽然香港社会对于媒体侵犯个人隐私、搞“色腥煽”有不同看法,但是基本是针对娱乐、社会新闻的,而对于政府官员的新闻监督,社会都认为这是保持政府廉洁、政治清明的重要基础。也正因为此,政府讨论多年的对新闻报道的监管办法一直无法出台。大部分香港市民也愿意为了保障新闻自由承受一些道德美感上的代价。
在一个你感冒都会被偷拍的环境下,所谓“包二奶”恐怕是天方夜谭吧。
“阳光”防腐剂
在内地热议的官员财产公开,在香港早已实施多年。根据规定,行政长官就任时应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申报财产,纪录在案。同时,由特首、三司十二局主要官员及14名非官方议员组成的行政会议成员,受委任之后要填报《行政会议成员利益登记册》,登记受薪工作、土地及物业等资产及利益。而包括司长、局长、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副局长、政治助理等所有政治委任官员,除了上述资料之外,还需要申报其配偶、子女或其他人士持有,但实质是代主要官员购入的投资及权益。所有这些申报,都不是“内部”的,而必须向公众公开。
去年底,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立法会议员刘皇发,因为没有申报所拥有的公司购入物业而受到专案调查,最后虽免于处分,但是信誉已经受到很大影响。
登录香港政府有关网站,这些申报资料都可以查询。根据最新的资料,特首曾荫权月薪超过35万港币,入住香港礼宾府之后已经将家庭拥有的中西区住宅出租,而此前与妻子共同拥有的英国住宅早已出售。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已经将他在家族公司的所有股份交付信托,此外他还拥有4个物业,包括一个位于九龙城区自用的物业。
除了这些定期需要申报的资料,港府会主动或应香港立法会议员要求,公布主要官员的公务费用,例如今年2月,香港特首办向媒体发放了特首“公费出国”的花费,详细到每张机票,每顿饭的花费。资料显示,曾荫权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4日之间的40次外访,共花费98.7万港币,每次不过2万多元。而其新财政年度的社交及款待宾客预算和去年持平,为32.5万港币。
不仅是特首办,香港政府各个部门的财政支出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查询到,具体到一年用了多少纸、买了多少家具都历历在案,每个部门的财务公开可厚达几百页。这种透明机制下,“公款大吃大喝”以及所谓“特供”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
为什么政府愿意主动公开,除了来自社会的压力,其实透明公开也是减少猜疑、自我保护的方法。比如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申报拥有8套住房,但是没有人会怀疑他是贪污腐败所得。
除了财产、财务公开,在执行公职过程中,如果官员的个人利益可能影响他们的判断,必须要向行政长官报告,而如果官员的投资或利益跟公职有冲突,行政长官可以要求官员放弃所有或部分投资、在指定时间内冻结任何投资交易等行动。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因为在公布提高车税前夕购买豪车,被质疑利用内部信息避税,最后被迫辞职。(摘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