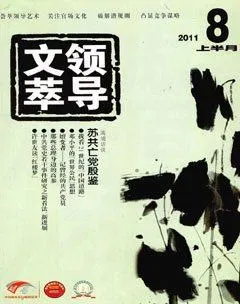铁托:强权维护南斯拉夫统一
回忆起发轫于整整20年前的那一场惊心动魄、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人们不禁要问,南斯拉夫的解体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人为的偶然?铁托究竟有没有机会挽回这场悲剧?
历史没有假设,但仔细观察,人们依然可以发现,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内因长期积累,并被外因一朝诱发的地缘政治灾难。
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国家的面积仅25.58万平方千米,但其民族、宗教关系之复杂,对国际格局变动影响之大,竟不亚于苏联。俄罗斯的幸运之处在于,它足够强大,即便暂落下风,终非美欧所能征服。塞尔维亚人的悲剧在于,它没有俄罗斯那样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即便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也只能留下历史的慨叹。
生来就要面对内忧外患
1945年,铁托领导的民族解放军将纳粹赶出南斯拉夫。与波兰等国不同,铁托及其部下几乎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下的江山。苏军帮他们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但苏军对南斯拉夫的贡献也仅此而已。因此战后,铁托成为这个国家毫无争议的主宰。
此时,铁托一定在考虑,如何统治这个获得新生的国家。对内,南斯拉夫除了主体的塞尔维亚人,还有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民族,虽然同被认为是“南部斯拉夫人”,但其实各民族间的关系并非完全融洽。克罗地亚就一直有强烈的离心倾向。当初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曾经想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国家分崩离析,1934年,他因此遭到克罗地亚极端组织乌斯塔西的暗杀。此外,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及伏依伏丁纳的匈牙利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对外,作为巴尔干上的一个大国,地理位置决定了任何想要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国家都会试图在南斯拉夫插上一脚。远如哈夫斯堡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近如德国、意大利乃至沙俄,都曾试图向这块地区施加影响力。
纳粹占领南斯拉夫期间,乌斯塔西为实现建立“大克罗地亚”的迷梦,屠杀约50万人,驱逐25万人。外部大国的插手加深了内部民族矛盾。
铁托的铁腕是稳定局势的关键
铁托最终还是想出了些办法。对内他效仿苏联,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斯洛文尼亚、黑山、马其顿分别成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科索沃则是自治省,而南斯拉夫成为一个“联盟”的概念。加盟共和国权力平等,且拥有各自的国旗、最高法院、议会、总理。铁托甚至想以此模式,与同为“南部斯拉夫人”的保加利亚进行两国合并的谈判。1947年,布莱德协议签订,眼看大事将成,斯大林的强力插手使得此事作罢。
表面上,各自治共和国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事实上,铁托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权力运作,使得南斯拉夫实现中央集权。他被任命为南斯拉夫的终身总统,在贝尔格莱德向各大自治共和国发号施令。任何对体制不利的人或事,都会被迅速清除。
为掌控局势,出身于克罗地亚的铁托对于任何民族主义思潮都进行压制,无论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还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分子会遭到逮捕,极端民族主义团伙则会遭到最严厉的打击,甚至会遭处决。
对外,铁托则奉行不结盟主义,与苏联、美国保持“等距离”,尽一切可能将外部的风雨推到国门之外。
历史证明,在民族关系复杂、内部裂痕深重的国家,强力人物往往能够稳住局势。铁托对内软硬兼施、对外纵横捭阖,使得南斯拉夫在纳粹被赶走后的30多年间保持大体的稳定。
无奈的“克罗地亚之春”
但深刻的民族裂痕并没有在铁腕压制下消失。铁托在经济上实行中央集权,各自治共和国的外汇收入统一上缴,建立联邦团结基金,来帮助落后地区发展。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经济情况一直要明显好于其他自治共和国。有统计数据表明,南斯拉夫50%的外汇收入来自克罗地亚,但克罗地亚自己只能保留其中的7%。至于联邦团结基金,从1965年到1970年,塞尔维亚使用了该基金的46.6%来帮助科索沃的发展,而克罗地亚只拿到其中的16.5%。
铁托的原意是让各自治共和国平衡发展,但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看来,这是“塞尔维亚人的剥削”。1967年,一群克罗地亚诗人和语言学家发表《有关克罗地亚标准语言的名字和地位的宣言》,宣称克罗地亚语并不属于南斯拉夫语言的一种。
军人出身的铁托可能不会料到,这份宣言迅速在克罗地亚人中间引起共鸣。1971年,南斯拉夫经济处于困境,《宣言》的影响力也被最大程度地放大。当年萨格勒布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示威人群高喊反对“塞尔维亚人霸权”的口号,要求克罗地亚获得更多自治权,这起事件被西方称为“克罗地亚之春”。
“克罗地亚之春”的影响是深远的。南斯拉夫为此于1974年进行修宪,主要是限制塞尔维亚人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提升其他各自治共和国以及自治省的权力。这部宪法还允许各自治共和国脱离南斯拉夫独立。
潘多拉魔盒缓缓地掀开了盖子。
6年后,强人铁托因为血栓被切除了左腿,不久病逝。在他之后再也无人能拥有他的手腕以及威望,继续维护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但这个巴尔干大国依然要再过10年的时间才走到终点。
(摘自《上海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