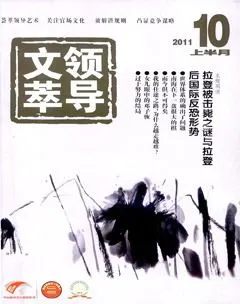皇帝的救赎
康梁之流,本来是变法,偏要说改制,变法可以依靠皇帝权力,一说要改制,皇帝就靠不住了,因为皇帝权力都由体制赋予,若无体制支持,作为个体,皇帝哪有权力?变法是在体制内解决问题,而改制则针对体制本身,不是通过体制去解决问题,而是把体制当作要解决的问题。本来张之洞、翁同龠禾都是变法的支持者,一获悉康的改制意图,即与之划清界限,成为坚决反对者。
可怜皇帝,竟与体制对立,变法伊始,即开经济特科,矛头对准科举制,欲改之。须知,科举制乃官僚的命根子,一改制,便要触及。或曰科举各朝有异,历代修葺,岂非改之?但那都在科举制以内损益,仍以科举制本身为目的而完善之。而开经济特科,则于科举制旁另起一新炉灶矣。
戊戌维新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变法路线,一条是改制路线。变法路线,由陈宝箴行之于湖湘,沿着郭嵩焘以来的洋务思想前进,从造枪炮到办外交,从办外交转向改革内政,这一转向,实以郭氏倡导,而由陈宝箴发为新政。改制路线,则由康梁等人发动,欲以君主专制“定国是”而行之于中央,结果是,为改制而专制,等于自己将自己连根拔起,如斯而已,敢问所专何制?又有何制可专?
仅仅是变法,慈禧并不反对,事实上,有关变法事宜,光绪都向她请示,她并无异议。说变法,除了顽固派,都不会出来反对,多半还会表示支持,袁世凯加入强学会,张之洞与康梁合作,翁同龠禾向皇帝推荐康有为,他们这么做,都是对变法的认可,一提改制,则无不反对。不光翁同龠禾在皇帝跟前与康有为划清界限,就连那时正在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上了一道《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奏请皇上谕饬康氏,将《孔子改制考》自行毁版,以正误息争,知非进德,维持风教。
为什么他们都反对改制?除了看不惯康氏以孔子自居而不可一世外,主要是对于康氏下手处,人人自危,恨得切齿。改制首当其冲为慈禧。康氏欲以“光绪帝+孔子”来改制,就要搞皇帝极权主义,可慈禧还在,皇帝不光每天要向她请安,还要向她请示,皇帝搞专制,搞搞名义的,当然还可以,因为政体本来就如此,如果真要搞,那就该问问她是否同意。
《明定国是诏》她已经批了,但她批的是变法,而非改制。荣禄问康氏,改制要不要改祖宗之制,康氏回答当然要改,又问改不动咋办,答道杀两个一品大员就行。所谓祖宗之制,其实就是家天下,光绪可以为了救国而不顾家,慈禧则不然,必要时,她会卖国以救家天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非失言,而是守着家天下的底线。
这样改制,分明在搞无政府主义,谁还会支持?空想的幽灵,从《大同书》里跑出来,徘徊于京城,盘桓在皇上头顶,皇帝多么青春,何等单纯!为了救国,他愿意放弃帝制,不做皇帝;为了救民,他可以放弃家天下,还权于民。可这是“三千年来一巨变”啊,他怎能想干就干?更何况祖宗之制亘古如斯,岂能说变就变?
李鸿章曾为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作序,序文大谈“民主”,说:我邦三代以前,以天下为公,嬴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自夏以来,从三代开始,天下由公而私,天要中国大一统,其势浸淫二千余年,而今一变。如今中外畅通,看来是要恢复中国三代以前天下为公的局面了。康有为向光绪帝推荐了这本书,李提摩太《在华四十五年》里说到这本书,不仅皇上爱读,恭亲王也称赞,而俄使却对恭王说,这本书是讲民权的,如果四万万汉人都来讲民权,你们六百万满人就只好回老家了。
这话是对恭王说的,会不会传到老佛爷的耳朵呢?老佛爷心知肚明。在政治思想上,意识形态上,谈一谈“天下为公”是可以的,但制度上还应该是家天下。可皇帝居然就这么糊涂,听洋人忽悠,被汉人劝说,就想把天下交出去,搞什么立宪。为此,还设了个变法顾问团,请伊藤博文来当首席顾问,本来家丑不可外扬,她和皇帝争,再怎么争,也是一家人在争,到头来,还要唇齿相依。可皇帝竟把洋人引来,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皇帝还要他作甚?
严复说,最是皇帝不自由。可就这么个最不自由的人,竟然拼将一死,也要打开通往自由的另一个出口——立宪。
……
有了光绪,爱新觉罗氏才无愧于历史,正是这位皇帝,以维新,以受难,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尽了他对爱新觉罗氏的救赎。家族的罪和历史的恶,压住他脆弱的双肩,他忍受了,突然有一天,他站起来说“我不能做亡国之君”,便走出王权洞穴,去领略普世阳光,看世界的真相。
走出去,意味着拿自己去救赎。走出家天下,走向民天下,像匹夫那样以“天下为己任”,是对爱新觉罗氏的民本主义救赎;走出帝制,走向民主制,把皇帝搁在宪法里,是对帝制的民主主义救赎。可他凭什么来救?用什么来赎?就凭项上那颗大好头颅!英雄进当铺,用头颅作抵押,不是押在天命,而是押给真理。
秦始皇开创了帝制,历史学里,称之为“千古一帝”,然而,在我们看来,要终结帝制的皇帝,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历朝历代,不乏雄才大略的皇帝,可帝制终结者只有一位,那就是光绪。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