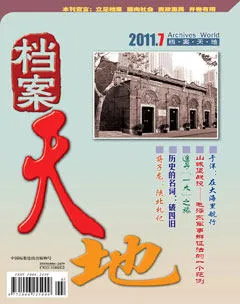追寻“一大”之旅
2011-12-31 00:00:00肖舟
档案天地 2011年7期


拂去岁月的尘埃,打开历史的篇章。90年弹指过去,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耄耋之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由于其地理上的优越位置,开埠不久就形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最早窗口。从这里,我开始了——
一
在上海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数千条马路中,兴业路是很普通的一条。这是闹中取静的所在。这儿离车水马龙的商业闹市圈淮海中路不过几百米,而这条马路上却不通公共汽车,行人也不多。
我一次又一次来到这条马路,步入路北那座在青砖中镶嵌着红砖砌成的典型的上海民居——石库门房子。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小康之家,喜欢住这种独门独户、既有小天井又有小楼的房子。石条门框,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矾红色雕花门楣。这一切都给人古朴典雅的感觉。
虽说,上海现今还有不少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房子,然而,兴业路76号却成为万众景仰的革命圣地——墙上高悬大理石铭牌,上面刻着金色大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我第一次来这里免费瞻仰“一大会址”开始,到后来的1毛钱、3元钱直至2008年3月10日开始的免费领票参观,每次一涉及这个地方,我的心里都会情不自禁地鸣奏起那首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旋律,尽管停驻在心里的,都是上海典型居家的石库门房子,青灰色的砖墙,灰蒙蒙的,潮湿的墙根爬满了青苔,在狭小低矮的装有黑漆铁栏的阳台上,堆着未必可用却永远也舍不得丢掉的“破烂”,描绘着物质生活的贫困;阳台边沿,还可能长着一些杂草,和窄小而陈旧的马路倒也相称。然而,绝不影响那激越得能煮沸热血的旋律在我的心底奏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落花流水的废墟上站起来的“天下”,当然是前无古人的崭新天地。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1921年7月23日晚8时,在这幢房子底楼那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15个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3人。)围坐在长方形的餐桌四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这样开始。
穿长衫的、穿对襟中式纺绸上衣的、穿西式衬衫扎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操英语、俄语的,讲湖北、湖南话的,聚首在这幢石库门房子里。
我追寻着那围坐在大餐桌四周这15个人的足迹。
我在心里默默的计算着当年这些代表们的年龄。我发觉,他们是那样的年轻!15个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在他们之中,最为年长的是“何胡子”。他,45岁,湖南代表何叔衡,因为留着八字胡,得了“何胡子”的诨号。最年轻的是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刘仁静,19岁,担任大会的翻译。
我查阅着代表的履历档案。我发现北京大学跟代表们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代表之中,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的占了5位——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此外,由于公务繁忙未出席大会而被人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南陈北李”——正在北京的李大钊、远在广州的陈独秀,都是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那么密切的联系,因为,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先锋,而“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二
在15位代表之中,有两位外国人——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我细阅着关于他俩的种种档案。
38岁的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约瑟夫·斯内夫利特·马里。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曾在荷京大学读书,能说流利的英、法、德等多国语言,1900年开始在荷兰从事工人运动。1902年加入荷兰铁路电车工人联合会,1904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被派往荷属东印度群岛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14年发起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后改称印尼共产党),1917年著文宣传俄国革命,被印尼当局驱逐出境。1919年1月回到荷兰,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加入荷兰共产党,与怀恩科普等同为激进的论坛派。
依据1935年8月19日的《马林赴华回忆》叙述:1920年6月,他代表印尼共产党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同年8月,列宁任命其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身材硕壮如同工人,而那副金丝眼镜表明他是知识分子。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他从莫斯科经奥地利穿过苏伊士运河,坐远洋海轮来到上海。马林到中国后首先接触的人是孙中山。
而尼克尔斯基却是那么的年轻——22岁。80多年前,他接受设在西伯利亚腹地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委派,风尘仆仆从俄罗斯来到上海,走进望志路106号,出席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会议进行到一半被迫转移,他也匆匆离去,之后便音信杳无。
三
很多年以来,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第三展厅,介绍15位出席者的版面中,只有14人的大幅照片以及生平介绍,唯独第15个人——尼克尔斯基处,却成了一块醒目而无奈的空白,让许多参观者迷惑不解。
在大半个世纪中,这位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重要人物只有一个名字,他的模样不为人知,他的命运无人知晓。曾有俄罗斯学者于1989年在《远东问题》杂志撰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
直到2007年9月,尼克尔斯基的生平之谜终于被揭开了。经过“一大”会址纪念馆20多年坚持不懈的寻找,俄罗斯、蒙古两国学者几乎同时发现了他的照片和档案,并将照片和资料送到了“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听说这一发现后,认为是中共创建史上的“重要成果”。一段历史的空白被填补了。
那天上午,时任“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的倪兴祥向我介绍了这一重大发现的来龙去脉。
多年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从未间断过解开尼克尔斯基之谜的努力。倪兴祥回忆:上世纪80年代,曾通过外交途径,致信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寻找。这封信引起了前苏联有关方面的注意。
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卡尔图诺娃曾撰文说: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华,回国后,他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卡尔图诺娃接过了这项“解谜”工作。尽管她多方努力,也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却一直没有重大突破。直到2006年,她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了尼克尔斯基的传奇经历。
原来,尼克尔斯基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阿勃拉莫维奇·涅伊曼的化名。他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布)党员,长期在前苏联远东地区工作。1921年6月,他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南下来到上海,与另一位来自荷兰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
然而,这位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革命者,命运却以悲剧告终。上个世纪30年代,涅伊曼成为前苏联“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1956年,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
尽管,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渐渐浮出水面,但是,由于他身份特殊,照片一直未能找到。卡尔图诺娃教授曾向媒体呼吁,请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寻找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2007年6月29日,“一大”会址纪念馆有了意外收获。来自俄罗斯的参观者阿列克赛·布亚科夫,要求面见“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领导,称手头持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原来,布亚科夫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2006年,曾经来沪参观过“一大”会址。当时,同胞尼克尔斯基留下的那片空白,给他带来震撼。他决定回国后设法找到尼克尔斯基的照片,送交纪念馆。
布亚科夫先后向尼克尔斯基工作过的数个边疆地区的档案馆致函查询,均无所获。直到俄罗斯有关方面向他建议,根据尼克尔斯基生平的一些线索,不妨向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问询。这封征询信在两个月后,终于有了让他喜出望外的回函。一张光盘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氏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带有其本人头像的履历表。据称,档案馆中还有尼克尔斯基几十页的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其自传中还披露自己去过上海工作。
这一发现,令“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负责人激动不已。2007年9月12日,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著名学者达西达瓦,又送来了在鄂木斯克州的专业档案馆发现的尼克尔斯基两幅珍贵的照片,终于,使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微笑着向我们走来,用他深邃的目光、坎坷的人生,向世人昭告着革命者的曲折经历与牺牲精神。
四
“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词,在以前所有涉及中共党史的教科书里都有出现,而且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统一名称。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最新的权威党史著作里,已经见不到这个名词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接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那么,是谁制造了这样一个谬种流传的名词呢?有学者研究认为:“一般认为最早是由武汉代表陈潭秋提出的。”与此相关的史料是,为了纪念建党15周年,1936年6月7日《共产国际》第7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陈潭秋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只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早在之前就已有了这个名词。从马林1922年7月11日在《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可看到这个名词的完整表述,报告中说:“陈同志在广州……接到国际代表邀请他担任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工作之后,于8月底回到上海。”1926年,苏联的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明确写道:“1920年初,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组成了。”1936年,也是为了纪念中共建党15周年,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发表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也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由此可见,这一名词的最早提出者还是那些“关心”中国革命的外国人。不过,实际上在1949年以前的革命史书籍中,如延安时期,由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就没有出现“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词。1949年后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等教科书、学者研究成果中普遍沿用这一名词,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受了中共“党内一支笔”胡乔木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书的“权威”影响。
大会的组织者是上海共产党代表中的“二李”——李汉俊和李达。“二李”还是代理书记(书记陈独秀当时在广州)。从档案中,“二李”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俩同岁——31岁,都曾去日本留学,李达懂日语、英语,李汉俊懂日、英、德、法四种外语,正是从一本本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当时中译本甚少)。
李汉俊是兴业路76号的主人。他和哥哥李书城(建国后曾任农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1965年8月26日去世。)住在一起,人称“李公馆”。
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我请他的夫人薛文淑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她说:“汉俊性格刚直。汉俊的朋友很多,在一起时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李达(1950年2月,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调任武汉大学,并兼任中国哲学会会长。“文革”开始后,被迫害致死。)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哲学家。我曾在北京寻访九旬高龄的李达夫人王会悟(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寓所病逝,终年96岁。)。她感慨忆当年:“中共‘一大’是秘密召开的。李汉俊家在法租界,法国警官和密探监视着那座房子。在闭幕式那天,幸亏马林警惕性高,发生情况异常,建议立即休会,叫代表们迅速离开。10多分钟后,法国警察和密探就闯进了李公馆。后来,我建议改在我上中学的地方——嘉兴南湖举行,那里僻静,可以躲开密探的眼睛……”
中共“一大”本应由陈独秀主持。陈独秀缺席,“二李”又不擅长交际,便由时年24岁、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党十分活跃的人物——张国焘担任主席。会议的记录是毛泽东和周佛海。
马林在1935年8月19日接受美国教授伊罗生的采访时,曾谈及:“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这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便是毛泽东。这位28岁的湖南青年,在中共“一大”上,很认真地听取别人的发言,做着记录。虽然他言语不多,只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党的情况。然而,他的“能干”,已引起了马林的注意——尽管在当时他还不是“主角”。
我还对“兴业路”这路名发生了兴趣。我知道在“一大”召开的时候,那条马路叫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树德里3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我猜想,一定是在解放后,为了纪念这革命摇篮,改名兴业路——大业兴起之处。我向上海市地名办公室请教,这才查清楚:望志,原是法国上海公董局总工程师的名字,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望志路。因为这条马路当年在法租界之中。后来上海收回租界,改名兴业路,那时上海一般采用中国各地地名来命名路名,兴业是广西一个县的名字。在代表们下榻的博文女校——白尔路(后改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间隔,与兴业路相邻的马路叫兴安路。兴安也是广西桂林市下辖的一个县名。虽说是偶然的巧合,兴业路这路名却给那历史性的会址增添了纪念色彩。
五
我沿着“一大”代表们的足迹追寻,一直追寻到他们人生的终点。当年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最后一个离开人世——1987年8月5日清早,85岁的他持剑穿过马路,照惯例到对面一所大学里舞剑,被一辆疾驶而来的公共汽车撞倒,当即死亡。
在这15人之中,壮烈地牺牲于刑场的是山东代表邓恩明(后改为邓恩铭)烈士和湖北代表陈潭秋烈士。李汉俊虽然后来脱党,也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何叔衡于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附近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1942年4月,马林惨死于德国法西斯刑场。
没有到会的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27年4月28日下午1点,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谈定自若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了最后的一张照片,从容地看了看风中摇曳的绞索,蹬上了绞刑架,从容就义时,年仅38岁。
李大钊牺牲后,身后萧条,当时《晨报》报道说:李死后,“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云云,于是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者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5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同志”(戴季陶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是“盟友”(汪精卫则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如果用我们久已被灌输成习惯思维的历史观,这就是很难认为的历史的事实了。
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那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是刘半农撰写的。
1933年4月22日公祭举行时,参加者中还有教育部长的李书华、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国民党中央监委的黄少谷(都曾与李大钊于“三一八”后遭北洋军阀通缉)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适、周作人、马裕藻等。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1942年5月27日晚上9:40分,病逝于四川省江津县鹤山坪的寓所。),依照毛泽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由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其明确使用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直到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版,正式变更为“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去掉了“投降”二字,显然是考虑到陈独秀一生虽然数度被捕入狱,历尽坎坷却从未投降敌人的因素。
山东代表王尽美为党工作,过度劳累,肺病不愈,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逝于医院,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一大”代表。
毛泽东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的战友、湖北代表董必武,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丰功。
人是变化着的,在炼钢的过程中要不断除渣。张国焘于1938年4月逃往武汉叛党,成了国民党特务,最后于1979年12月3日,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陈公博、周佛海堕落为汉奸头目,分别于1946年6月3日,在苏州被执行枪决和1948年2月病死于南京老虎桥32号“首都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2000年7月4日,监狱的建筑整体被拆除,迁移至雨花台区铁心桥镇。)
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是由于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都记不清“一大”开幕的确切日期,便用7月首日作党的生日。后经党史专家多方面考证,查阅原始文献,已确定中共“一大”开幕之日为1921年7月23日。但“七一”沿用已久,现仍照惯例在7月1日庆祝党的诞生。
代表们在离开兴业路那张大餐桌之后,各自东西,走着不同的人生之路,最后的结局也各不相同。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战斗中成长,在战斗中壮大,由最初的53位党员发展到2010年底的8026.9万名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