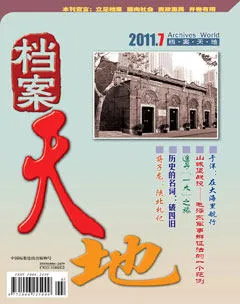写出历史的真
看了你们为写《抗渡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历史警示》一书而搞的灾情摘要,使我了解了很多,深受启发和教育。原来模糊的一些想法,趋向于明确;原来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也向我脑海里聚集。可以说,摘要虽粗疏,还是向我们提供了一把了解当年情况的钥匙。今天,就如何去破这个题,提出几点想法,供你们参考、讨论。
一、要认真研究电报,并以此为切入点,把灾害的坐标定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是一个通俗的说法。从我们河北讲,一般指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从全国来看,起止时间可能不是这样。至于说什么灾,各地情况又都各异。单就我们省来看,地域这么大,各地方的起止时间和具体灾情也并不统一。既以“三年”为限,应指自然灾害相对集中,影响了河北省全局的那段时期。从摘要的内容看,把“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起止,定在1959年到1961年,理由比较充分。当年那么大的灾害,涉及面那么广,危害那么深。从中央到地方,了解灾情、报告灾情、指导抗渡、下达指示命令,往往返返、上上下下,会形成很多有价值的历史记录。那时科技不发达,最先进、最机密的手段是电报。电报有多种多类,省委、省人委给党中央、国务院的,给华北局的,可统称上行的电报;与此同时,河北省委、省人委,给我省各地区、市、以及部分县的电报,可统称下行的电报。这些电报,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要以这些电报为主要脉络,从头到尾地加以梳理。简要地说,讲时间坐标,定位于1959年至1961年;讲抗渡主体,以省委、省人委为中心,为轴心,为坐标。把向上行的报告和向下行的指示,一并一封一封地做一下统计、分类。因为重大灾害发生在河北,我们讲的是河北;也因为已经形成的省委、省人委向上报的材料都是真实而重要的。从省委、省人委向上报的文件,可以看出当年自然灾害的重要实情,看出如何领导人民抗渡的举措;从对各地区、各市以及县的下行文件,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抗渡的具体指示、要求;从党中央、国务院给河北的文件,可以看出党中央对河北的关心、重视,同时也可看出全国面貌的一部分。这样讲灾情,从村,可以一直讲到党中央、国务院,整个灾情的背景很厚。
二、要认真研究“灾”与“荒”的关系。多少年来,灾荒二字,是社会尤其是民间的一句常用语。灾,当然指灾害,荒,指什么?少有人去加以研究。我不是咬文嚼字,如仔细琢磨,灾是不等于荒的,把“灾”与“荒”分开来看,有很大区别。一般讲,“灾”是一个自然现象,相对于荒,它是一个原因、一个起始,而“荒”,是灾的一个结果。任何“荒”的发生,都有其原因,也有规律可循。这个关系,这个概念,希望你们认真研究,不要弄混。也就是说,这个“荒”比“灾”,更能看出结果的严重性。在这里,二者不是并重的。凡灾必有害,但不是什么灾都可导致荒,荒是灾害的严重升级。比如,讲“大涝”,一般用“一片汪洋”,这本身就相当严重了,如汪洋迟迟不退,又是什么结果?退了后,遍地是泥,种不了地,而草,趁机就大量地繁生出来,所以,大涝灾之后最容易形成草荒,而漫地的草荒又继发虫荒,虫吃草、吃庄稼,转而人再治虫。假如这几种荒一齐出现,又是什么结果?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本身的严重性在这里。再如,讲大旱,一般用“赤地千里”。“赤地千里”是什么意思?别说庄稼,地旱得连草也不长。不长草也可发生虫灾,但要看看是什么虫?光说虫灾虫荒又有多种。无论什么灾,当它变为荒,涝荒、草荒、虫荒的时候,必然导致最后一个荒:粮荒。所以你们对“粮荒”务必注意。“以粮为纲”、“南粮北调”,想想那些年,北方尤其河北,吃过多少省市的粮食呀,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以粮为纲”、“南粮北调”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南粮北调,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同志们,请想一想,如果粮荒渡不过去,接下来该是什么?是饿死人!所谓“抗渡”,从根本上说,主要指抗击灾害留下的恶果,解决人如何吃上饭,不被饿死这个天下的根本大事。任何自然灾害的出现,都有一个过程,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单纯的讲过程没多大意义,关键的关键,是讲清灾害殃及了什么。殃及的程度,才是衡量灾害大小的根本依据。希望你们从“灾”与“荒”的区别与联系上,深化认识,进一步构思。千万不要把思路局限在就某个灾说某个灾上。
三、要认真研究“多灾并重”,在此基础上再梳理“几个为主”。根据灾情摘要,按时间顺序,你们概括了几个“为主”,对此,我一是肯定你们的努力,二是,觉得几个“为主”可能不大好概括,也难准确。因为,凡称得上“特大灾害”的,多是多种灾害并发且持续性时间很长、殃及范围又很大的。有的灾,看起来很重,比如,一夜暴降300毫米雨,造成山洪暴发,河水漫堤,人畜伤亡,但“暴”的东西往往有一过性的特征,第二天,可能就雨过天晴了,损失再大,也便于集中精力去处理。请注意“一过性”这个词。“漏房偏逢连夜雨”,灾害,怕就怕多灾交错并发,且持续时间长,从而导致“粮荒”这个极其严重的恶果。所以,只讲灾发生过程的本身,有时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讲灾害的严重,关键要讲出它殃及的国计和民生,如当时死了多少人,以后又有多少人没口粮,多少人患了这种或那种病,死了多少牲畜,损失了多少房屋、财产(包括公产和私产)等等。总之,写这部书,希望你们多考虑一下灾的后果,灾的殃及。你们的提纲里,对财产的损失情况、人的伤亡情况,病的情况、牲畜损失的情况,都做了一些考虑,但我觉得还不够充分,下一步,应在这方面下大气力去搜材,在“殃及”两字上多动脑子。这样,才能说清灾害的全貌与严重。
四、要认真研究“天灾”与“人祸”的关系。“人祸”在这里是指什么?要给它一个清晰的定义并不容易。我的看法,大家应多从政治和领导的高度去构思,似应用八个字,即“决策失误、举措失当”,比较合适。“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讲到“殃及”,这里必须要多说几句话,就是“天灾”与“人祸”的关系。1959年到1962年,在河北百年未遇、多灾并发的特大灾害这几年里,单讲自然灾害本身,恐怕最严重的年份是1961年。1961年,各级组织想的主要是什么?做的主要是什么呢?当然想到了抗灾救灾,采取了许许多多的举措。但历史地、全面地、综合地分析那几年河北走过的路,从生产关系、政治背景、大的社会环境上去看,谁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史实:那几年,正是河北省省会从保定搬到天津时,正是轰轰烈烈的撤县并县时。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又能拿出多少精力关心民生、考虑救灾呢?我觉得,这是与灾害相伴的另一件十分严肃的大事。对这个问题,去年我写的关于撤县并县的一些考虑,可供你们作参考。如这样去把握,这个课题就更加浑厚了。天灾不可拒,人祸可避免。假如(当然历史不可能假如),没有那么一场导致人心惶惶的撤县并县,抗渡三年灾害可能更好些,更快些。1958年,应该说是建国以来生产发展最好的时期,但头脑太热了,先合村,再合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县县全部人民公社化。我看过徐水的档案,按发文件的时间来说,该县从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到全县实行人民公社,一共短短21天,真是神速。人民公社后的第一件事,是吃食堂。每个农户家里不做饭了,还存粮食干什么?还要什么积蓄呀?不说别的,仅一个吃食堂,就把人们的生活秩序全打乱了。食堂存在时间不长,很快解散了,但人民公社没有解散。“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统购统销”,都是那个时期的政治标志。农民本来不富裕,又不让积攒粮食了,又赶上那几年地里不产粮食,可想,粮荒该有多么严重,该有多少人吃不上饭。这就是天灾与人祸的关系。
五、要认真研究如何写“活”的问题。我们的书叫“史鉴”,必须保证使用的材料、数据、情况等,真实可靠。但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写得活一些的问题,让读者爱看。只有读者爱看,我们费心血得出的警示,才能入心入脑;如果写得干干瘪瘪,可读性差,心血就白费了。这题目很大,要写出可读性,大的背景应清楚;主要线索应清楚;“灾”与“荒”的关系应清楚;“天灾”与“人祸”的关系应清楚;边抗边渡,节节升级,最后取得了胜利也应清楚。按这个要求,希望你们,不仅要对书的章、节、目如何设置做进一步考虑,而且使用什么语言,也需要精心考量。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定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时代的特点就是语言的特点。如光使用些现代语言,无论如何不能反映那段历史。讲到章、节题目,又回到你们几个“为主”上,我不主张这样简单地概括,如果非用“为主”的话,我想,可以考虑以哪个地区为主,而不是以哪一年哪一灾为主,因为这几年的灾害,确实是综合的、持续的、各种灾害交错并发的,找几个受灾最重、最有代表性的地区、县,以它们“为主”,去列章、列节,我觉得可能更容易看出河北的全貌来,当然还要附上其它,即以典型带出全局,而不是对全局进行很难概括的“……为主”。今上午,我一边看摘要,一边想,究竟怎么体现以点带出全面来,以重点带出全局来呢?这篇大文章从什么事上起步呢?从何种灾上起笔呢?如何从一开始,就抓住读者的心呢?从摘要来看,以唐山、张家口、沧州,南部再找出一个地区,最多四个,就可以了。以它们为重点,来烘托出全省、烘托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