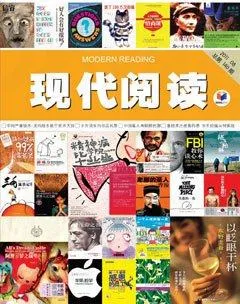中国严重缺水 龙的故乡是个贫水大国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前,城市缺水只在个别地区及个别年份发生。20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和城市建设的发展,缺水城市不断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已有300多座城市缺水。
人们的普遍经验是,水是上帝赐给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世界上最廉价、最丰富的资源。事实上,这笔财富是非常有限的。科学家经过精确计算,得出如下基本数据:
地球表层面积为5.1亿平方公里,其中,海水覆盖面积为3.6亿平方公里,约占71%;陆地面积为1.5亿平方公里,约占29%。地理学家们简称为“三分陆地七分水”。
在这七分水体中,97%是咸水,淡水仅占其中的不到3%,这些淡水的2/3以冰的形式固定在南极洲和北极格陵兰的冰盖中,人们很难利用。人类所能直接利用的淡水,只占全球淡水总量的2%以下。
龙的故乡也是个贫水大国!中国的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淡水资源量仅23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量的1/4,世界排名121位,被列为世界上最贫水的13个国家之一。这么一点雨量,70%集中在4个月内降落,其中2/3以洪水形式白白流走。
地域差异造成了永久性旱区:中国长江流域以北,包括西北内陆河在内的广大地区,总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3.5%,人口占全国的43.6%,而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属严重缺水水平。各地缺水困情成了年复一年的热点新闻。
拥有6500万人口的河北省,数十年来一直被干旱所困扰。境内的滹沱河、大清河、白洋淀等,20年前就先后断流或干涸。2000年大旱,全省372座水库和4.8万口深水井已经干涸见底。300多万人口和70万头牲畜得不到足够的饮用水,20万公顷农田颗粒无收。
河北省水利厅资料显示:近年来,全省每年超采地下水50亿立方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省累计超采地下水60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地下水300亿立方米已无法补充。照此耗费速度下去,石家庄的地下水15年就能采完,邯郸地区的情势更为危困,不用15年地下水就会枯竭。
超采地下水带来的严重后果已逐渐显露出来:地面下沉、海水倒灌、大地开裂。
位于大运河畔的沧州,深达10米的裂缝有数百处,许多房屋已有塌陷趋势。整个平原地区已发现200多条地裂带,涉及35个县65个乡。河北省第二水利电力勘测院的总工程师英若师已经得出结论:原先华北地下漏斗仅有几个,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这些地下盆地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世界面积最大的复合漏斗区,俗称“空心漏斗”,总面积至少在5万平方公里以上,后果相当严重。
提起内蒙古,人们立刻想到那首千古流传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如今的内蒙古大草原,很难找到古诗里那种“水草肥美牛羊壮”的美丽景象了。
资料显示,内蒙古整个天然草地面积有70多万平方公里,而饲草灌溉面积只有400多万亩。这里的降水量为50毫米至450毫米之间。经测定,其水面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0倍以上。亩均水量570多立方米,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4。可见内蒙古的旱情是多么严重!
在这干旱天地里生活,人、畜用水得靠“基本供水井”来提供。说它“基本”,大意是“维持基本生活”而已。地下水很深,有的深达300米才出水。这样的水井,几十公里才有一口。也就是说,人、畜渴了,得跑几十公里才能取到水喝。
近几年连续大旱,有些水井干涸了。牧民们要到几十公里外拉水吃,水价贵到每立方米30元以上。
2000年,内蒙古又遇大旱。7月底,首都北京的各家报刊上,大都登载了这样一条新闻:《天灾人祸,黄羊遭受灭顶之灾》。黄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尤其是生活在中蒙边境中段草原上的长尾黄羊格外珍贵。由于干旱的煎熬,许多野生动物在干渴中死去。有位记者在中蒙边境走了约300公里,亲眼目睹许多渴死路边的长尾黄羊,有的甚至在饥渴难熬中蹬腿挣扎,那情状,真是惨不忍睹。
内蒙古的这场大旱,渴死了上百万头牲口。牧草无收,牧民们无法生活,迫使10万儿童中途退学。这场灾难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提起大西北,人们立刻想起“大漠孤烟直”、“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等古代诗句。大西北缺水历史触目惊心。
干旱埋藏了繁荣的丝绸之路,干旱消失了昌盛的楼兰文化,干旱将一个好端端的西部变成了千里赤地、万里荒漠的荒芜凄凉地带,致使许多地区成了寸草不生的生命禁区。
那些环境条件稍好的地区虽有人居,但也逃脱不了干旱的困扰和高度缺水的威胁。
这里,不说缺水如何制约西北经济的发展,不提干旱如何造成了西部地广人稀的格局,仅就饮用水问题做一简要介绍。
解决饮用水困难,已经成了西北人民近期奋斗的一大目标。
拿宁夏来说,那些距黄河及引灌区稍远的村庄,吃水相当困难。笔者的爱人作为部队派出的扶贫医疗队,到陕甘宁边区扶贫巡诊,亲眼目睹了那里的缺水惨状。
那是一个平水年,但水源距村寨有10多里路。家有毛驴者可以把水拉回来,没有毛驴水车的,得靠肩担、手提、脑袋顶。
水贵如油,人们惜水如命。半盆水,洗完菜舍不得倒掉,用来喂猪喂羊。平时想洗脸洗脚,简直成了奢望。至于洗澡,那是雨天的事了。
男孩没问题。女孩可就麻烦了,例假无水清洗,出现臭味,当妈的不忍心,总要为女儿留点“卫生水”。就那么一点“卫生水”,当爹的也舍不得,因为那是全家的保命水。
条件好的家庭才有水窖,水窖是上锁的,钥匙掌握在一家之主手里,家人渴得无法忍受时才动用窖子里的水。
当地人说,只有孩子出生、青年结婚、人老去世之后,才能动用窖子里的水洗一洗身体。医生们说,那里的女人普遍患有妇科疾病,因为没水洗。
姑娘找婆家,不问存款多少,先问家有几眼水窖。
建个水窖这么难?说难也不难,不就挖个洞吗!再用胶泥和石灰封漏,加上木板盖即大功告成!这在别的地方也许很容易。但在贫困地区太难了。附近都是沙地荒坡,到哪去找胶泥和石灰?所以,那里的水窖大都是从爷爷辈传下来的,所用胶泥都是以金黄的小米从遥远的地方换来的。砌窖也有一定技术难度,弧度要合适,窖壁要夯实不渗漏,这就难上加难了。很多家庭连饭都吃不饱,哪有资金修水窖呢!
2000年特大旱灾,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赤地千里,渠道龟裂,河汊干涸,连水窖里也淘不出水来。于是,50万家庭,300万人口讨水过日子。讨水队伍绝望无助的模样,让观者潸然泪下。幸亏宁夏的“生命工程”,陕北的“甘露工程”,以及甘肃的“121工程”,解决了1000万人的饮水问题。否则,讨水人口会超过好几倍。
中国西部地区至今仍然面临非常严重的缺水困难,其中约有50万户约300万人严重缺水,如果再有30万口水窖,缺水的特困形势就会扭转。
一口水窖需1000元,全部资金缺口为3亿元。旱区经济贫困,自身无力解决。为此,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推出了“大地之爱母亲水窖”捐赠活动。
近些年来,西部地区虽说解决了一户一窖的生存问题,但仅靠这么点水常年度日,母亲脸上会出现舒心的微笑吗?
2004年10月22日的《新华社每日电讯》刊发了这样一篇报道:《会宁水荒:初中生每天定量3杯水》——水荒涉及3万多人和4万多牲畜,这里关于水的故事听了让人心酸。
甘肃会宁县是红军长征时期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也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导致这里贫困的主因就是干旱缺水。1995年,甘肃省为了解决会宁等贫困地区缺水问题,实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即政府出资400元帮助山区缺水农户修建一块100平方米的庭院雨水水泥集场,挖两眼用水泥敷底的水窖,发展一处经济园林。毫无疑问,这项工程使会宁的老百姓找到了一条寻常降雨年份保障吃水的有效之路。但是会宁依然缺水,水窖可以蓄水,但老天不下雨时间长了怎么办?因此,解决缺水问题成了这些地区乡镇干部和会宁县一些负责人的中心工作。
缺水,已经危及到人民的基本生存。
(摘自华文出版社《西藏之水救中国〈新版〉》 作者:李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