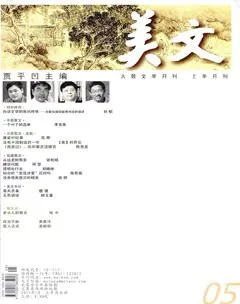1989年初春至深秋的火车
高晖1966年出生,辽宁昌图人。自1988年7月毕业后,先后在村、乡、县、市、省五级组织、四级财政部门分别任村、所、股、科、处长职务。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品兼及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著有短篇小说集《寻人启事》散文集《内部问题》《向陌生人招手》及其增订本,文学评论集《原始阅读》等五部六种。
我最亲爱的人:你在人群中去找他吧!当所有的人都大哭,只有几个人在笑——那笑得最欢的,就是他;当所有人都大笑,只有几个人大哭——那哭得最凶的,就是他……
一个爱你的人(请保留到最后)
小镇的基本含义就是非驴非马。眼里的雪地杂乱而参差,一只只昏黄的路灯就像滴着热泪的烛光,摇曳。这早已不是纯粹的雪野——雪的下面不是黑土地,而是干硬的水泥汀,尽管我心里想象着康家村洁白的样子,仍然无法弥合这满眼的残缺。
两位黑色棉袄的老人,突然跪在我的脚下:“领导啊,你救救我们吧!”我被吓了一跳。没等我问,他们已经开始陈述:为了给儿子找工作,被骗去两千元。我问:谁骗了你们?谁能做证呢?他们说:给一位国营厂长偷偷送的礼,谁也没看见。我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四处说说,但这事儿难告赢。天太冷了,不如你们先回家。慢慢地把钱挣回来吧,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让你儿子揍他一顿。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声音很低,真怕别人听见。
放心地走吧,走吧、走吧——
肯定会有人想你、找你……
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留言板
有一段时间,应该是1989年初春——那时,即使不出发,我也喜欢去车站。那是在我的家乡昌图,离康家村十公里左右就是昌图站,一个像火柴盒那样的小火车站。在那里,我听火车轰鸣声,看来来往往的人上车、下车。那时,车站里面有留言板,供旅客传递信息。我喜欢站在留言板前发呆,看那些写着各种规格、各种字迹的纸条儿。
记得,那是冬末的一个午夜,看完最后一班上车、下车的人,我又走到留言板下端详。突然,我剥下烟盒,抽出钢笔在上面写了几行字,贴了上去。其实,你知道,我当时并不需要给谁留言。
我至爱的人,我已经找了你很久——你到底在哪里?
0∶59一个爱你的人(请保留到最后)
写完、贴好,我又看了一眼它在整块板上的位置,居中。然后,就像往常一样回家睡觉。后来,日子忙了些,我竟忘了这事,很久也没到小站上去。转眼间到了初春,又来到小站,自然想起我那张纸条儿,找遍了所有的纸条,并没有我的。我想,也早该让人扯下去了。然而,当我借着昏暗的灯光,又重操旧业,一一地审查着全部纸条儿时,突然心里一亮,发现了几行工工整整的字:
我最亲爱的人:你在人群中去找他吧!当所有的人都大哭,只有几个人在笑——那笑得最欢的,就是他;当所有人都大笑,只有几个人大哭——那哭得最凶的,就是他……
一个爱你的人(请保留到最后)
当时,我浑身上下,甚至每个毛孔,都感受到一种神秘的温馨,觉得心里装满了好多、好多人。果断地写下了“我去找你了。我去找她了”。然后,贴上去。
那个夜晚,我有些激动,我想: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铁轨
当时,我一个人在昏黄的灯光下读书,样子像座黑陶塑像,只有指缝里的香烟,证实着屋子里肯定有个活物,庄重、紧张、自闭。黑色的烟缸里,只能再最后容下一个烟蒂。突然,我走到书房里一个古老的石膏像前,摸了摸老人的额头、胡子——指上有些灰痕。于是,拿起毛巾擦了擦,有种很细微、很动听的声音,于是,我的心和手,还有毛巾都变得丰富。老人也很寂寞,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心里陡然间湿润了一下,顷刻间又归于龟裂。
夏天,在一间爬满青藤的小屋,屋子里有笔、有墨,还有一位纯白衣少女。窗外,自然有阳光——甚至看得清整个世界的血液和骨骼。这时,我拿起笔,在这女孩的脸上写上了太阳的名字,并且告诉她:我们都把心掏出来碾碎。她没摇头,她没点头,默默地跑出门外;她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灼热、刻骨。我拼命地追上去,因为她的脸上有太阳的名字。前天夜里,我刚刚躺在床上,就做出这样一个梦。我想,我大约是病了,就病在没有童年的夜里。这个夜晚,又想起这个很抽象的梦。这时,却下起雪来,在初春的北方,这是少有的天气。
小镇的基本含义就是非驴非马。眼里的雪地杂乱而参差,一只只昏黄的路灯就像滴着热泪的烛光,摇曳。这早已不是纯粹的雪野——雪的下面不是黑土地,而是干硬的水泥汀,尽管我心里想象着康家村洁白的样子,仍然无法弥合这满眼的残缺。我踩着早已被践踏得面目皆非的雪路,很艰难地行走,鞋子踩着雪地时,有轻微的响动。当我找到那两个朋友时,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出来,然后在雪地里默默地走,这是我们临行前的一种默契。这是小镇里仅存的三个诗人,说不清从哪一天开始,我们老在一起走路、说话。那时,三个男人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的世界,脱下白天的面具,像对待跑街的鞋子一样,将它们扔在门外,都觉得绝对坦诚是唯一能维系我们的东西,尽可能真实得使空气随之颤动。这时,我们排了很长的一串脚印,仍是默默地前行。原来,我朝着铁路走去,那是有铁轨的地方。
“很久没笑了,我们”。
“这世界有什么好笑的,有一个人哭我就跟着哭”。
风雪,迎面打在脸上,我突然感觉有点看不清他们的脸,只是黑黑的一团。光头猛地弯下腰,从脚下扯出个美丽动人的黑圈儿抛在空中。那黑圈儿在雪空中旋转了几个回合,最后终于砸在雪地上,形成一个椭圆形而且很规则。原来,他的裤脚长极至地,日积月累被鞋踩得成了圈套。
“真他妈的潇洒!”我们竟是异口同声地喊。然后,我们在雪地里找到了一张有酒的桌子,高粱酒一杯一杯地掺在血液里,身体就热起来。“很久没有出来了,我们!”“出来就好。干!”三只酒杯,撞出了一阵沉闷的声音。至此,眼睛看见了酒,鼻子闻到了酒,耳朵也听到了酒——浑身自然就有股悲壮。“走吧。当!”
雪越来越猛了,我们发出粘着雪花的喊声,反过来又震动着雪花。我们想沿着铁轨走到山那边去,光头发疯似的跑在前面,我和小个子拼命地追他。马路上,那些身上印烙着号码——像囚犯一样的垃圾箱,一个个地向我们身后闪去。我们一边跑一边张开爆满青筋的手,像要接住什么,嗓子眼里有股滚滚的烧酒辣味。前面,终于看见了铁轨——黑洞洞的两条铁线,在雪地里非常惹眼——只要沿着这两条铁轨奔跑,过不多远,就是真实的、茫茫的雪野。踏上枕木的瞬间,我的心都碎了,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崇高感。
我们停下来,朝着前边望去——远方的白桦林中,似乎有盏红灯笼,在白桦林和红灯笼中间,隔着一带小山,在雪夜里显得不同寻常地幽远、浩渺。我们慢慢地走,本来就没有人追赶我们,那些不写诗的人们正在酣睡。
后来,我们的回忆是一致的:那天正是1989年的3月24日。海子于当天下午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站台
在站台上,人们把一个老妇人,围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圆圈儿。人们茫然地站着,而且低头。老妇人则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手脚几乎同时摆动。她的衣衫明显不够用,遮掩不住应该遮掩的地方,整个脸都是乌黑的,只有鼻子周围的一小条儿,还有些眉目。整个轮廓像个大猩猩,一点人样也没有——四周的眼睛都这么说。
我挤过人群站在里圈,想看个究竟——原来她手里握着的是一张居民身份证——反复地说——不是说,是喊:我是××省××县××乡××村××组的人叫×××。
我突然感到圈儿里发闷,就想挤出去——也不知是没有回去的力气,还是人群越来越紧,我出了一身汗,还是没挤出人圈儿……
老妇人还是在圈里手舞足蹈,不停地说。
我想,她才应该站在圈外。
车来了。在前一站就超员——列车在本站不开门。
那些不同规格、不同性别的人堵着车门,眼巴巴地仰视着门把手。
我急了——手里舞动着车票——我有票,为什么不让上车……
人们侧目看了我一眼,然后果断地,为我闪开一道缝儿,我立刻钻到前面——继续呐喊,而且声嘶力竭。身后的人们,都照着我的样子——手舞车票大喊开门,也许这样就叫群情振奋。这时,我周身一阵血热。
车上的人终于按捺不住,将门略微打开一些,我奋力拽住门把手挤了进去。车里实在太挤。我又将门带上。于是,我心里踏实得很,呼出了一口长气。人们仍在车下手舞着车票,张着大嘴——原来好些人的牙齿不齐,而且深黄……又有一个人舞得最欢,口张得最大。站在前面,也许这人和我刚才一样。我听不见他们喊着什么,也许车厢门窗太厚。
火车改点
开车前三分钟停止售票,而且那天正赶上子夜火车改点。我跳过铁栅栏,猫一样钻进奔向站台上汹涌的人流。这些家伙都急匆匆地乱窜,真的有些像老鼠啊。就在进入人流的刹那,我禁不住发问:这么多人——从什么地方来,又到什么地方去呢?
站台上,都是一些混乱的人,背着或拎着形形色色的包,做出形形色色的姿势。在这里,人本身就是随时装车准备运走的物件,似乎身体的每个零件都在诉说着自己不适应这深夜,还有这改点。我迅速找到六站台十二道,长年累月的奔波,使我熟悉了这城市、这车站的每一处细节。
长长的站台,人们在等待。又晚点十三分钟,不吉利的数字。灯光昏暗,天有些凉,好在我加了一件外衣。
突然,在人群中发现一个熟人,我眼睛一亮,直奔上去和他打招呼。他张开嘴和我喃喃几句,看我一眼,慌张地又挤进人群。他背了好大一个包儿。我木讷地寻着他的背影,这时,有股冷风吹来。
两条铁轨,冷冷地卧在一个槽里,就像两条东张西望的毒蛇,枕木上有个干瘪的易拉罐,空空地躺在那里,被风吹动,偶尔还会发出呻吟声。人们站立在站台上,一动不动,像是在为出发默哀,又像是为了归宿担忧,僵硬的脸上没有任何舒展的表情。这时,几乎所有的眼睛,都同时盯着十三道上停着的那列货车的某一节车厢。平板车厢上,装着几辆深红色的22马力农用拖拉机。就在两个拖拉机之间的平板上,竟蜷曲着一堆人。一、二、三、四、五……是五个。一男一女,两个大人,还有三个是孩子。所有的眼睛都会判断出——这是一个家庭。
“娘……娘……我冷!”是那个小姑娘在喊,她大约十一二岁。脸像花蝴蝶一样。站台上所有的身体都向她倾斜着。女人们开始交头接耳。有人说了一句: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漫不经心地撵了他们两句,然后又拿着小铁锤,敲击着铁轨向前摸索着。敲击声在子夜格外悠远深邃。
她的娘站起来,根本没在意站台上的人。
“喂,小姑娘,你坐到拖拉机驾驶室里去!”我喊了一嗓子。
小姑娘果断地挣脱开母亲,麻利地坐到了深红色的拖拉机的驾驶室里。
人们都望着那小姑娘,再也没有说话。
嘀……滴……汽笛撕心裂肺地响着,我的耳朵眼里一阵奇痒。货车缓缓开动,那小姑娘满脸得意,她当时一定想象着——她正在驾驶着拖拉机,在土地里耕作。她向我们挥着手……刹那间,我眼里有点湿润——好像领略到我们之间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一种悠远的起始感和缥缈的归宿感在我的内心蔓延。
我们的车也来了,有些人没有挤,甚至样子很庄重。我当时想,车里应该有点音乐,然而什么也没有,除了拥挤和嘈杂。原来,车里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个手握方向盘的小姑娘,站在前方不远处。当然,他们也无须知道。后上车的人们,又都忙于找自己的座位,仍然是匆匆忙忙。
当时,我想回去就给小姑娘写封信,问问她是否有了归宿。后来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她的任何地址。
车厢
车厢里灯影斑驳、灰暗,就像人们的心情,只有车厢划破铁轨的撞击声,几乎没有人的声音。 这时,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对话儿。看样子,他们俩有点儿血缘关系。
“好你这个家伙,把糖都藏起来了,给我两块!”男孩先说。
小女孩只好掏出两块给他,他吃了。
“再给我两块!”
她又掏出两块给他,他吃了。
“你还有,再掏出两块!”
她又掏出两块,样子很不情愿。他又吃了。
“你还有”。
“没了”。
“还有!”
“还剩这一块了”。
她要哭,他把糖攥在手里。
“还有!!”
“这回真没了”。
“肯定还有!!!”
“不信你翻”。
哥哥模样的小男孩,把小女孩的兜子都翻过来——什么也没有——一张棕色的糖纸,缓缓落在地板上。
她哭了。
他愣了。
火车仍在一颤一抖地往前走,那种声音仍然刺耳,让人心里发空。
旅途
本次列车严重超员,座位、过道、连接处,甚至行李架上都是人,如果你离开座位或者站位一路挤到厕所,那就别想再出来。我实在不知道那些长途旅客,是怎样解决排泄问题的。我原本有座位,挤出厕所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厕所旁边狭小的过道,像炼人炉一样闷热。我对面那个少女几乎就贴在我的脸上,我们俩谁也别想转身。我只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也只能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空气里有了些许湿润。那女孩的确不难看,甚至可以用漂亮形容。
在车轮遇到铁轨接口阻力的时候,我还可以感受到时间——的确是在前行。就这样一直盯下去,这时,我开始觉得那少女面目恍惚,有些狰狞。稍微转动脖子,我发现原来身边有扇窗,透过车窗望去,顿觉树行河飞云也走,感觉稍好些。
窗外是初夏的麦田,总能闪现几个孤零零的稻草人,穿着人的衣服,摆着人的姿态,僵僵硬硬的样子。这些,让我感受到深秋的肃杀,就是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感觉。就这样,我记不清到底过了多少站。这时,我又想起那位少女,她仍在我身边站着,原来她始终保持开始的姿势。列车一摇一晃,咯咯噔噔地走着……蓦地,我再次盯着这张年轻女人的脸,有些恍惚,我无法判断这张脸,是属于站台上那老妇人,还是身边这位美丽的少女……
就这样,车到了北京。
我要去北京,我该下车了。
向陌生人招手
那时,我时常和陌生人招手。
在一条铁路线旁,我租了间房子。六层,大约四十平方米。太小的房子,又塞满了书,常使我透不过气来。好在有个阳台,我常常站在阳台上,看下面。下面,是农田和农田之上的铁路,铁路总是有火车通过的。总是盯着下面便乏味,乏味到已经看不清农田的时候。于是,我便朝更远的地方望去。远方显得缥缈而不可捉摸,几乎和我没有直接的联系。火车仍然轰鸣,有绿色的、红色的,也有黑色的。色彩的调子太冷,包括那红色的车厢,也会给我这样的感觉。
尽管天渐渐暖和了——从春天到初夏,甚至有一点闷热。就在这样的季节,使我越来越看清了一些动的东西或者说:我原来眼里曾经静止的东西动了起来。对我来说,这一发现有点特别。
那行动着的火车原来紧闭着窗子,也打开了一些。也确实到了开窗子的季节了。透过车窗,我大约能看清车子里的脸,都是很麻木的样子。当然,他们也透过窗子向外望着。
这些天来,来来往往的火车似乎比前些天多,而且是绿色的多,红色的也多,黑色的少了些。能看清人,便觉得有意思。我老觉得车子里的人,在探头探脑地对我做出古怪的表情。于是,我便常常扬起手,和他们招一招手——纯粹是不自觉的动作。人家是无动于衷的样子,我便觉得索然无味。现在,剩下的出路只有两条了:一条是我再也不招手了,就此罢休;另一条是继续招手,也别管为什么,仅仅是招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我仍然是常常向人家招手,木然的旅人呼地一下子过去了。招手时,我似乎被释放,毫无原因也毫无结果的那种释放。我推测,他们看我的样子变得认真起来——我喜欢这样一厢情愿地这样认为。
那时,我刚读完沃尔夫的一篇小说——《远和近》。故事简单得几乎到了透明的程度:一个火车司机在路过一座小山村的时候,总是看见有个女人在向他招手。几十年如一日。这位可怜的司机,退休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座小山村,找到了那个常和他招手的女人。结果是,和我们大家想象的一样——他看到的是一张麻木而苍老的脸。我觉得我的招手和别人的招手意义有很大的不同。只能这样想。不然,我的手就会招不下去。肯定不会有哪位女司机在退休之后,来敲我的门,而且,本国似乎不让女人开火车。激情不在的时候,我愿意依靠理性生活,哪怕是自己设计的理性。
我愿意从另一角度理解这个问题,那就是:火车以及火车上的人只是我的一片风景。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自己也成了他们的风景。只能是这样。虽然他们从来不和我招手,但我仍然和他们招手。这是一种习惯。说不准哪一天,我会改掉这个习惯或者忘了这习惯。
这条铁路在京哈线上。
准备出发
我刚生下来,没哭——这是后来姥姥告诉我的。当时她在场,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得知这一消息时,我就隐约地想过,大多数的孩子一般都要哭几声的,可能是我的体力或者胆量在那一刻出了什么问题。那么,我死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哭吗?当时的答案肯定布满了悲伤。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一些晚上,我愿意围绕这个问题想一些事情,也许那是在和这种预感做抗争。于是,我开始想做个有出息的人,替别人做一些事情——“在更高层次上为人民服务”——早期的功利思想就是这样朴素。无非是在死后让别人哭两嗓子,捧捧场。那时我的想法是,自己会哭,也就能让别人为自己哭。
还是二十来岁的时候,有那么几年,我一直想走出家门,独立地做点事情。走出家门的标志是,暂时丢下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首先最要紧的是挣脱家,也就是天天板着面孔的爸爸妈妈的所有羁绊。当时,这样想的时候心里有种热热的东西……这种念头持续了很久。在某一天,我想起了自己十五岁时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天中午,家里来了三个客人,均男性,爸爸不在家。妈妈说,你陪叔叔们吃饭吧。当时,我心里升起一股热流——那是少年受宠若惊的正常反应。当时,我就告诉自己:我已经是成年男人了,可以和大人们平起平坐。整个午餐稀里糊涂地弄完了,已记不清细节,唯一能记清的就是我没有吃饱。不过,从那时起,我开始上演大男人的心里戏。此戏的演出程序大体这样:想干的事情都要弄出幻觉来,骗骗自己,然后再想办法弄假或成真的,这与马克思阐述的理想有一定的相像之处。我自己的说法是,强大的想象力可以制造现实。直到现在,理想这东西对于我,还好像是借贷的心理体验,付本还息时自然比较惨淡。不管怎么说,从那时起,我相信自己能听见自己骨骼生长的声音,哪怕不是在万籁俱寂的时候。
一旦觉得自己长大,当然就想独立地出门走走。少年刚开始独立的时刻——免不了和周围的亲人抗争些什么,当然,那都是有理由的。我敢和大人吵架了,我瞧不上他们,有时他们还蒙在鼓里呢。那时,我和其他的孩子也有深仇大恨,我竭力地想充当孩子们的领袖,敢打人也敢挨打。曾跑出过几次短途,大都是沮丧地回来。没有远行的经历,我就在一篇作文里给自己虚构一个。
我虚构的地方是龙镇,直到前年我才路过那个地方——还真是很荒凉的。火车停下来的几分钟,我下来了,到了龙镇的地面上,想起那篇作文,心里仍然复杂。似乎虚构这件事时,我将起因放在高考失利后的挨揍。天地良心,当时父母根本没有打我,我怎么虚构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呢?打虽没打,罪还是遭了一些。发榜那个夜晚,天阴,也就确实没有星星。当时我确实承受不住家里沉默的哀悼,终于向他们大吼一声:死人了吗?你们怎么不责备我——不打我?我没有给你们脸上增添光彩,你们就像死人了一样?接下来写到——也许当时我主要是为了增强叙事效果:
爸爸终于举起炉铲——你滚,你混蛋。于是,我真的滚到了一座粮库去扛了二十二天的麻袋,那是惨无人道的麻袋,我无法忍受它的重量又回到了我那有炉铲的家。尽管所有的细节都是天衣无缝的自然,我还是在痛恨这出来进去的根源,因为不明了这根源,也就恨得无的放矢,现在想来,我恨也不那么真切。
再后来,我拿到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文凭——鲜红方正的小本本——我被认定为国家干部。爸爸妈妈看着这片硬纸说:“现在,你可以让人放心了。”也就是说,我可以体面地养活自己了。当时,他们的样子比较意味深长。果然,我在那间被称为机关的屋子里,扫地、打水、看报纸、写写小材料——刚满一个月,他们就给了我一百二十元钱。不错,的确不错。
我上班不久,有一个晚上,他们突然吵了架——那时他们时常吵一吵。不过这次似乎仅仅因为钱,结果是妈妈走了。屋里没有灯。我坐在爸爸身边,拿出两只香烟递给他一支,他燃着了火柴让我先点着。“我妈更年期,你应该知道啊”——我有点不平静。在黑乎乎的屋子里,两颗并肩的火光在闪,他似乎第一次听进去我说的话。他没有说话,我们就站了起来,并肩走着,找人去。外面的云里,隐约的有了点星光。地上两点并列的红火在动。当时,我的想法是找不找到妈妈已经不重要。
从那以后,每月的7日,我都领到一叠人民币。我似乎隐隐约约地在享受一种习惯:上班、挣钱、下班,就这样习惯着。其实,从红小兵、少先队到共青团,他们都会要求我把整个身心都奉献出去,在更多的时候,我也顺势默默地接受着这种习惯。接下来,日子当然是平平淡淡的,我也坦然且无波痕。我和母亲的紧张关系也得到相应的改善,她每次出去还要给我留下几行字,比如:我今天不能回来,你自己做饭,用那小红瓢舀米,你有半瓢就够了。当时,我也为“小红瓢”这样的词语感动。那时,我常常想,我是个平凡的孩子,而且我掌握自己平凡的全部证据——我就该过这样平凡的日子,甚至有些贪恋自己的小镇生活。
那是1988年冬天,那天的确有些阴冷,政府的高墙已经有很多冰棱,而且错落有致,远远望去,甚至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当时,我迈着小干部应该迈的那种步伐,刚进机关大门。两位黑色棉袄的老人,突然跪在我的脚下:“领导啊,你救救我们吧!”我被吓了一跳。没等我问,他们已经开始陈述:为了给儿子找工作,被骗去两千元。我问:谁骗了你们?谁能做证呢?他们说:给一位国营厂长偷偷送的礼,谁也没看见。我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四处说说,但这事儿难告赢。天太冷了,不如你们先回家。慢慢地把钱挣回来吧,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让你儿子揍他一顿。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声音很低,真怕别人听见。随后,我掏出仅有的三十元钱递给他们。他们又跪下了,管我叫“恩人,恩人啊”。当时,我很悲伤,想跪下向两位老人说:对不起,一切都会好起来,不应该这样。不过,我没有勇气说这些——看看周围没人,就走开了。我恨不得自己是县长,想着这些我又笑了,也许那时我会看不到这点小事。如果那位厂长真给老人的儿子找了工作,两位老人就不会来告状。
从那以后,我时常能目睹到这样的事情,而且人们大都很木然,仿佛世界原本就应该是这种模样。在那样的时刻,我也会感受到,自己身上那种久违的青春期就有的暴戾之气,时常在内心深处蔓延。我还会像青春期一样,涌起一股想撕碎什么的冲动——与青春期不同的是,总能咬着唇把这冲动踩在脚下。这时,我会涌起一阵满足感——我仍有血性,我还能做点什么。那段时间,就是常常在这样的目睹中练达我的稳健、沉静,于是,我开始未老先衰。
那时,我总能想起爷爷,一位山东农民,不会写字,只会漏粉。死于痨病——肺结核——现在打上几支青霉素就能救活的那种病。我没有见过他,不过每次见到驴子,我总会想起这位山东粉匠:他在磨坊里,与毛驴一起将土豆碾碎,毛驴被挡了双眼,爷爷扎着围裙,一双湿漉漉的手,始终不停地往粉漏里面添加淀粉,下面是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然后,漏出长长的粉条,他将晶莹剔透的粉条们挂在房梁上,直至晾干的粉条随风飘动。我知道,这些是我的组成部分。
我在姥姥身边度过童年,我学会了这位老人的善良、倔强。在漫长漫长的童年里,我是胆小、拘谨而口吃的孩子,村里的孩子们老是变换着花样捉弄我,打我,至今我的脸上还留着他们的指印。有一天,自卑的童心开始懂得自救,我将姥姥家的风轮搬到了房顶,里面装上土末,对着邻人家的菜锅猛劲地摇,土星四射。“你们再敢欺负我,我就打死你们!”这声呐喊及其重要,震裂了我的全部软弱。当时,我纵身跳下房去。那些欺负我的孩子们被我的举动弄傻了。从那以后,我成为孩子们游戏的领袖。我深深地记着,不公平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屈辱感,于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仇视任何形式的恃强凌弱。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甚至希望整个世界失一场大火,只剩下水和船,那时,也许就会好一些。
我好像自己整天都在坑道里,背上掮着沉重,在爬行前,遥远处有丝微光。我的额头上有汗珠儿,我自己不能擦掉。这就是体制的力量——将个人放在体制里,就像将一颗螺丝钉拧在机器上,螺丝钉如果不问机器的产品,只是拧牢一个零件,日子还会相应好过一些。难就难在螺丝钉有自己的诉求。只有到了晚上,我才有一片真正宁静的东西,我想,我不能随着机器旋转、轰鸣,我要有自己的声音,我不能这样两手空空。那是很纯粹的感觉。当时我想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自己所处的时代。
那次,在夜里,我从水草丰满、热气腾腾的北京回来。火车在家乡小站的一阵撕心裂肺的制动声,唤醒我了的骨肉深处的疼痛。原来,我的小镇是这样的偏僻、封闭而荒蛮。当时,我的感觉复杂极了。那天夜里,电视演着很老的一出舞剧:洪常青救下苦大仇深的吴琼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自由了。吴木然,就是说你愿意到哪去,就到哪去。我突然涌上一阵悠远的悲哀,我就永远地在这个小镇边缘生活下去?我怎么能忘记更远的远方?我睡不着——那天夜里,始终没有月光,我也始终沮丧,而且推测会这样很久。
我躺下来,摘下白天的面具,结束这一天的总账,结算着这二十余年的总账,心中有种难以抑制的躁动。我似乎真切地感到了我这些日子的憋闷是极复杂的情绪:无端的困惑,莫名的烦闷,倦怠和暴怒,还有怀疑,阵痛及至求索、冲动、渴望……我已顺从呼应了好久,生久了就会腐烂。
于是,我想到很远地方去,拂晓就动身。我真的想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生活——不是照样繁衍后代吗?快睡吧。如果天气不适合远行,那么就让你的心飞翔——那时,我决计依靠读书、写作实现这样的梦想。直到现在,我始终是在路上。说不准哪天,我要不辞而别,到更远的远方。也说不准哪天,我还会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