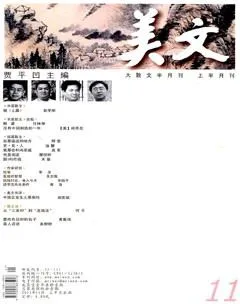发现的智慧
吴克敬
陕西省扶风县人,西北大学文学硕士。出版《梅花酒杯》《日常的智慧》《把窗子打开》《真话的难度》《渭河五女》《碑说》等作品集多种。
喟叹岁月的易逝,是文化人的一个通病。我在阅读李浩老师的新著《行水看云》时,由不得自己又犯病了。弹指二十四年过去了,犹记我在西北大学读作家班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班的时候,李浩老师给我的教诲,是太深刻了,我以为受益匪浅。现在再读他的著作,让我恍惚有回炉西大的感觉,幸福地再次接受李浩老师的教诲。
早些年,李浩老师结集了一部《怅望古今》的书,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在西安一家书城发现了,当即购回阅读,那一次的阅读,与这一次的阅读,隔了快四年的时间,但我的感觉一样的新鲜。我以为,阅读老师,如与老师喝酒吃茶一般,酒依然是辣的,茶依然的苦的,但却从这辣和苦里,有所新的发现。
老师的发现首先是语言上的,不像人们通常的作为,总在吃力不讨好地驾驭语言,那样刻意和饶舌,面对面说了,让我会担心折了他的舌头。李浩老师就不是这样,他使语言回归到历史的长河中,进而又回归到生活的溪水中,不见激烈,不见浑浊,舒缓有度,清清亮亮,仿佛敲窗的春雨,洗刷着历史的尘障,又滋润着现实的生活,牵连着人的思结,阅读起来就不忍放下,直觉舒服!
老师的发现还在于他的叙述角度。一般情况,文字操作者或者习惯了站在理想主义的云端里俯察大千世界;或者习惯了站在大千世界里俯望云端之上的理想,除这两种之外,还有别的叙述角度吗?可能有,但我不能肯定,我在努力地寻找另一种叙述视角。苦苦的寻找,忽然在李浩老师这里寻找到了,那就是,老师坚定地站在现实的土壤上,彼此平等地审视对方。咱们说,这能不是李浩老师的发现吗?承认为他的发现,是很容易的,知道他的发现,而且还要学习他,就绝非容易,这要求我们必须如老师一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葆有一颗波澜不惊的平常心,唯此,不可能以平静的心态去平视历史,去平视现实。
虽然如此,老师却一点都不琐屑,像他写历史,即深蕴着文化的意义,《怅望古今》中是这个样子,《行水看云》亦是这个样子。如《丑的历程》一文,老师从殷商的青铜器,从古典绘画和诗歌以及戏曲人物等方面,文化地阐释了“丑”的存在“不仅是美的补充和映衬,而且有其独特的历史流程和价值指向,是中国艺术史上弥为珍贵的奇观异景”,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研究”。再如《唐代的启示》一文,老师即从盛唐的物质文化成就、制度文化成就、精神文化成就诸方面,向我们的社会明确地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启示,即:树立文化的自主性;涵养文化的多元性;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促成文化的会通性;构筑强势文化与外向型文化。我不能引述太多,但我相信,哪怕仅是提纲挈领的引述,我们也可发现李浩老师的发现是怎样的珍贵和实用。
老师的用笔,沉淀在历史深处是这样,放眼于现实生活也是这样。《禽兽慰灵碑》是他旧著《怅望古今》中的一篇短文,写出老师远赴韩国游学的日子,他在庆尚大学科学院见到一个卵形巨石,其间嵌有一碑,上书:“人与物兮,同生两间。乃禽乃兽,为学资材。我闻古佛,极必于施。物为人用, 苟利万端。顾我大学,感德同涯。视尔来生,莲出金池。”啊哈,为禽兽树碑,在我泱泱中华是不好想象的,韩国的科学工作者做了,他们做的让一位中国教授心服口服,中国教授李浩在文尾不禁感慨,“盲目追赶现代化的中国人,偏执地以为人定胜天、征服自然为科学理念,没有天人的和谐意识,能有多少原始创新与自主创新,能在多大程度上追赶上世界潮流”。他因此还不无激愤地说,“丢弃了所有的人文素养,折断了另外一个翅膀,是悲是喜,孰优孰劣,我不知道。科学的疯狂崇拜者读此碑不知作何感想?”同样的妙文,在老师的新著《行水看云》一书中,可谓俯首皆是,《麻雀、熊猫在休息,请勿惊扰》就是如此,老师起笔即说,“当下的中国,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一副生猛的暴发户气象。到处是新开工的大工地,到处是新开张的阔商铺,到处是新竣工的大高楼盘……”可是,“麻雀和熊猫都在午休,我们人就不要午休了,就可以没有节制的折腾吗?真是岂有此理,都不放眼世界看一看,没人瞧不起我们,不要动辄一惊一乍,天天弄出许多响动来。我们也有五千年的文明,拿出贵族绅士的气派来,低调谦逊,文质彬彬,从从容容地干自己的事,也让环境安安静静”。
呀呼嗨……倡导静穆的老师,可否允许我为您歌一曲信天游,来为您祝贺呢?我心虚的厉害,就只有噤了声,依旧俯首在您制造出来的文字海洋里,去发现您的发现,去感受您的感受。因此,我还要说:向老师致敬!向老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