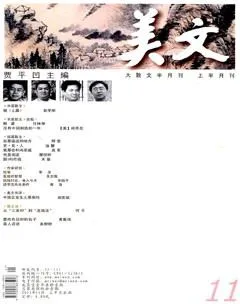信笔
李浩
西北大学副校长,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园林别业考录》等,随笔集《怅望古今》等,有多篇作品入选《中国最佳随笔》年度选集。
关于随笔的坦白
二十世纪的一位西哲克罗齐曾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头脚倒置过来:一切当代史都是历史。你想想看,并不是要你等到白发渔樵,也不要你傻看秋月春风。转瞬即逝的东西像毛毛虫一样沿着你的眼角眉梢蜿蜒不断,不用多久就把你光洁的身体雕刻得丘壑纵横。涓涓细泉汇聚成历史的洪流,侵袭着你所谓的当下与现在,有些浪头高如江潮,猛如海啸,顷刻间就会吞噬掉你精心搭建的那些叫做创造叫做成就的东东。你在惊愕之余,自不免更加黯然,对经过人类夸大的种种创造和成就会产生别样的理解。
这一戏仿的命题也会使我们对生命中的一些庸常和琐屑多了几分怜爱与珍惜。抢救史料不仅仅是上古史研究或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竞标口号,同时也隐含着对当下生活所有细节的足够珍视。
也许,我们对当下的一些判断太匆忙太草率。那些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表述,那些急匆匆塞进中小学教科书的文字,那些不和脑子商量,不假思索脱口秀出的华丽演讲和珠玉文章,其实未必就是定论,更未必能藏诸名山,传之后世。但将当下的一些散碎琐屑的材料有意识保存下来,给未来的史学实验室多存一些活标本,让后人自由评说,则不失为一种理性与明智的做法,也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另一种温情和敬意。
按照诠释学的观点,文学与历史其实都是阐释,这可视为文史既是同源的,也是同用的。按照更时尚的互文性理论,则不光文史可以互相解释,就连我们自鸣得意的那些独立创作,也总是与历史上的名著范本,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有时你越要撇清,越会陷入各种互文的指控中。
我在教书或专业写作之余的这些边脚料,无甚重大价值,弃置也未尝不可。朋友们虽曾不断怂恿,但我尚有自知之明。有些曾在报刊上登载过,也有些草成于信纸或电脑文档中,要不是为编《行水看云》这个小集,过不久自己也会将它删掉。还有些文字写完后仅挂在某专业网站我的那个点击率并不高的博客上。
自打有了网络,出版和发表的门槛被极大地降低,人人是写手,处处可发表。于我而言,把文字粘贴在博客中,就算发表,也懒得再投稿。当然访问者寥寥,链接的朋友也不多,真可谓“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了。在销售率、点击率、票房率决定一切的时代,我却不以为羞,坚持不随队逐群。反倒觉得在乱哄哄、闹嚷嚷的虚拟化生存中,能拥有些许真实的寂寞和孤独,委实就是一分几近奢侈和昂贵的享受。
个体生命中的这些小感触,小情绪,小体会,在时代巨变的大风浪劫掠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犹如在东南亚海啸、汶川地震、福岛核辐射中,我们的低声叹息与高声哀号,都是细微的也是无助的。在大灾难面前,狂呼人定胜天就像无知无畏的少年吹鼓胀的皮球一样,细小的针刺就能把狂妄的自大彻底戳穿。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也曾迷信过枪杆子、笔杆子对解放人类、改造社会的作用,及近二毛之年,开始反思“两杆子”的功能是否被过分夸大?枪杆子姑且不论,单说笔杆子,究竟对世道人心的改良有多大作用?笔杆子是否像核能一样同时还有它的负面作用?我越来越陷入困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阅读、思考、写作虽不一定能拯救或解放全人类,至少可以拯救或解放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人推崇“读书为己”甚于“读书为人”的理念,其实是蛮深刻的。
晚年的达尔文说:“很久没有读诗和欣赏一首乐曲,这不只是我理智上的损失,甚至也是道德方面的欠缺。”东坡居士的看法更新潮:“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偷闲读点旧书,写点抒发小感触的散碎文字,虽谈不到什么大意义,但至少可以让手脑同时运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保证身体和心灵不至于因封闭凝滞变得过早衰败腐朽。
我也有个梦想。就是在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无目的,无功利,无追求,仅为兴趣和感触写点小东西,但绝不会开辟第二战场,也不会把业余发展成为第二专业或第二职业。记得很多年前,我的一位长者很怜悯地对我说,你们这代人很可怜,没有渡过真正的童年,没有过开心的游戏和玩耍过。“文革”的成人化和后“四人帮”时代的成人化,剥夺了这一代人的游戏和玩耍。我对老人的话深以为然,总想找寻补偿缺憾的方式。大概文字游戏是一种老少皆宜的健身健脑活动,应尽量保持它作为娱乐的纯洁,不要被其他干扰和影响。
故我始终没有让这些散碎文字被立项,被评审,被开评论会,被作为成果计入教学或科研工作量。这些刻意的有些做作的回避能坚持多久?能有什么意义?我不敢说,但至少目前我还能坚守,就像一个老男孩不停地捣鼓一个旧钟表一样,就像我在长满芜草的博客上还能守住寂寞一样。
胃里的爱国主义
作别了东升的旭日和彩云,登上返西安的航班。机上早餐竟然还有一盒热气腾腾的白粥,心中一热,长时间对境外航空公司的不满,一下子被软化、被稀释,化成热气,蒸发得不见了。
人的胃真是贱骨头,所谓吃了人的嘴软,其实不是嘴软,是心软了,化成了柔柔的棉花糖。记得几年前也是从境外回来,由虹桥机场入境,首先在候机楼餐厅要了一碗酸汤面,虽然像所有大陆机场一样,食品价格高得离谱,机制挂面也委实不敢恭维,但毕竟是面条,是朝思暮想的酸汤面。人对食物的思念不是基于神圣的信仰,也不是亢奋的情感,而是从胃粘膜传导出的火辣辣的信息。据说胃粘膜是有记忆和选择功能的,儿时的嗜好,故乡的口味,会被长久地积淀保留下来的。
多年前在网上看到一篇《床上的爱国主义》的文章,乍看题目颇有些愤愤然。但文中拉出李香君、羊脂球、赛金花、小凤仙等说事,还真让感到上床不上床,与谁上床,并不仅仅是私情,还关乎爱国的大事体。而胃与爱国也还真有联系,这里有几条现成的硬材料。东吴人张翰见秋风起而思故乡的莼菜鲈鱼,辞了晋朝的官回家,是爱国兼爱乡。更早的伯夷叔齐俩兄弟,宁愿挖山中绿色食品蕨菜也不肯食周粟,是爱国主义的经典文本。可以类比的还有朱自清教授不吃美国面粉,是爱国主义的现代版。生理上的胃粘膜蠕动与否,竟然与伦理学和政治学上的气节有牵连,看来形而下与形而上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统一的。
胃的需求既然与爱国事体相关,所以饮食之事绝非小事。我们常把国家贫困形容为吃不饱穿不暖,“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人们从胃的角度对暴政的抨击。老话要新解,不光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