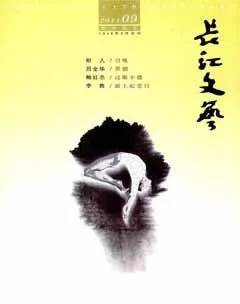和一座山的缘分
从武当回来之后,才知道不仅人与人相识要靠缘分,和一座山相遇,原来也要讲缘分。
出差到一个地方去,只要是时间允许,工作之余总要去领略一下当地的名胜,才算不枉此行。因为是第一次到湖北,长江三峡便自然成为我心目中的首选之地。无奈同行的两个同事多年前早已去过三峡,当我兴致勃勃地提议去大坝时,他们俩都同时摇了摇头,反而动员我一起去别的地方。我虽不太情愿,却也不好过于坚持,毕竟少数要服从多数,不能让他们两人迁就我一个人。由于入冬时节不宜去神农架,于是,武当山便成为当然之选。
不料,在我们谋划出行路线时,却遇到了一些阻滞。首先是路程的问题。同事反对去三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说路程太远,从武昌去宜昌坐汽车要四五个小时。可等我们买来湖北地图打开来一看,发现武当山在远远的西北角,离武昌的距离几乎是到宜昌的两倍,坐汽车至少要六个小时。我当下心中窃喜,希望他们会知难而退,改变主意重走三峡。正在打小算盘时,同事却在网上查到可以直接从武昌坐火车去十堰。我只好又死了心,以为这次武当肯定跑不掉了。没想到,却又碰上了时间的问题。我们前后一共只有不到三天的时间可以支配,而出发的那一天中午,因有一个工作午餐要参加,所以只能选择中午以后的车次。同事查询过武昌至十堰的列车时刻表之后,失望地宣告火车要不是早上的,要不就是下午的,中午没有班次。而下午的班次都在五点以后,到达十堰已经是深夜或凌晨了。这对于我们有限的时间来说,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以为武当之行恐怕会就此流产,未几,事情却再次有了转机。同事发现我们可以坐中午从武昌到襄樊的火车,然后第二天再从襄樊去武当也不迟。那一段全程高速,只要两小时便可轻松到达。
最后,我们并没有从武汉去襄樊,而是坐上了从汉口到襄樊的“和谐号”动车组——原本要六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到了,真正的和谐而舒适。
原本阻碍重重的旅行,却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除了归结于“缘分”二字,怕是没有别的理由能够解释了。
到湖北之前,就知道武当素以道教圣地和武当功夫闻名。此次上山,传说中的太极功夫未能亲眼目睹,道教神韵却是深有体味了。
早就听说武当山有“方圆八百里”之大,为了节省时间,我们选择了坐缆车上山——当然,担心自己爬山气力不济是另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即便这样,到达太子坡时也已是正午了。一旁拿着喇叭为旅游团讲解的导游告诉我们,武当山的景点非常分散,而太和宫(俗称金顶)、紫霄宫、南岩宫、太子坡是必去的四处景点,要我们自己抓紧时间。我们查看了景区地图,知道金顶的主要建筑金殿在武当最高的天柱峰顶端,便齐齐先向金顶出发。
那天不是节假日,上山的游人不多。我们慢慢地拾级而上,先到朝拜殿、皇经堂,再到紫禁城,边走边停,每到一处都挑选不同的角度拍照留念,完全没有了时间观念。在皇经堂,同事驻足仰头观赏堂前道光皇帝御赐的“生天立地”四字金匾及两旁的楹联,我却被陈旧古朴的门扇吸引,上面雕刻着众多的道教人物故事及珍禽异兽图案,技艺精湛,虽褪色残损,却形象逼真,而且每扇门上的图案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每扇雕画的背后有些什么故事和传说,只好把它们细细地拍下来,存留在记忆里。
太和宫不像一般的道观那样,建在一片平坦的开阔之地上,而是充分利用了武当峰峦的高大雄伟和崖洞的奇峭幽邃,巧妙布局,将每个宫观依山就势而建,垂直分布在海拔1500~1612米之间上下约2公里的建筑线上,与山巅峭壁浑然一体,仿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一段地势虽不算陡峭,却仍有攀爬气喘之感。到了紫禁城的墙楼时,终于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可以歇息一下了。从城墙往下望,只见一片参差错落的古建筑群在脚下延绵铺陈,确有“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独特气势;而远处,武当群峰层峦叠嶂,薄雾缭绕,犹如人间仙境,方始领略世人称武当为“仙山”之妙。
把城墙宫殿修筑在悬崖峭壁之上,恐怕只有当年的明成祖朱棣才有这样的气魄。历史上素有“北建故宫,南修武当”之说。当年的永乐皇帝在北修故宫的同时,又远在千里之外南修武当,日役使军民工匠30万人,历时12年。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是为了朝拜心中的仙山圣地,还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后人不得而知,甚至难以想象30万人同时劳作的工程是如何的庞大和艰辛。但可以肯定的是,武当自此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家道场,几百年间被帝王将相顶礼膜拜,并与另一处皇家重地北京故宫扯上了不断的渊源。
终于到了最顶端的金殿,顿有豁然开朗之感。金殿的名气大,殿体却不大,和山下的大殿相比,显得小巧玲珑。这座仿木式宫殿,屋顶采用的是皇家专用的重檐庑殿式,与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形制相同。如此高规格的建筑,全国仅此一座,体现了“万乘独尊”的皇权与神权思想,也让武当山的地位比其他道教之地更为尊崇和超然。
除了殿基为花岗石铺垫,金殿的殿体构件都是铜铸鎏金,不能说金碧辉煌,却也算得上光彩夺目了。殿门洞开,但有围帘供桌挡栏不能入内。掀开围帘,只看见里面供奉着披发跣足的真武大帝铜铸鎏金像,面容慈祥端庄。游人都拥挤在殿前殿旁,或拍照,或赞叹,或兴奋,或手触着金殿外面的铜铸栏杆转一圈,据说这样可以祈福。同事也兴致盎然,加入到转圈祈福的行列中去。金殿四周传来遍拍栏杆的“啪啪”之声,让这个道教的清静之地短暂地热闹起来。我默默地注视着身边走过的游人,他们和我们一样,费尽力气地上山,驻足流连一番之后,又匆匆地离去。或许,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里不仅有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更有恩泽众生的民间神祇。
在这个本该喜悦的登顶时刻,我却不敢有半点的喜悦之心,反有一种惶恐之意。这种惶恐,源于登顶的过程太过轻松容易了。金顶是武当山最高的一座山峰,如同一根通天的大柱屹立于群山之上,所以被称作天柱峰。从山脚放眼望去,它高耸入云,周围的山峰至少比它低100多米。而且,峰峰俯身颔首朝向主峰,仿佛在向君临万方的天帝俯首称臣。2500年前,一个叫尹喜的关令在得到老子的《道德经》之后,弃官归隐,而后不远千里,从函谷关来到武当山。当他看到“七十二峰朝大顶”这一自然奇观时,心中激动得难以自抑,以为那最高的巅峰意味着宗教的高远至境,就像道教中元始天尊居住的最高天界。而从山脚通往大顶的修行之路,就如仙界里由低到高的“三十六天”。在尹喜看来,在与天相接的绝顶修身问道才是最终的理想。于是,在一个草木凋零的冬天,他开始了自己的通往梦想的朝圣之路,一步一步,一里两里,艰难地慢慢地接近大顶。但穿过了一天门、二天门之后,尹喜在三天门的石壁下停了下来,并没有继续前行。金顶已经近在咫尺,可那是尹喜心中至尊无上的圣地,他唯恐自己修行不够,亵渎了神灵,便留在石壁下的岩洞静心修道,默默地守望着心中的那一份神圣。至此,尹喜成了武当有记载的第一位修道者,被尊奉为道教护法神“玉清上相”。
相比于尹喜的艰辛和执著,我们一路上的费力和喘息实在是不足挂齿,不值一提。几千年来,在尹喜之后,通往大顶的神路上来来往往着络绎不绝的朝拜者,他们追寻着前人的足迹前往心中的圣地。然而,在羽化而登仙之前,他们都要经历一个潜心修道、忍耐寂寞的过程。只有一步步地从低到高,不断进取,才能体会登峰的艰难和大顶的神圣,才能到达修道的最高境界。这有点像如今文学青年所走的文学之路。在成名之前,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少不了艰难跋涉、忍受寂寞的漫长煎熬。然成名并非就是登顶,只是一个修道的较高层次。因为登顶就意味着进入了文学修道的最高境界,那就是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生命,是一辈子都在追寻的生存意义。就像众多的山峰都俯身朝拜天柱峰一样,大顶在修道人的心中是至尊无上的,是不可轻易靠近的,一旦靠近,便意味着到达了终点。而我们轻松地乘坐了缆车上来,即便也费了点力气从半山腰攀爬上来,却确实有点不够虔诚的大不敬之嫌了。
怀着一颗心虚的惶恐之心,我不敢在金顶多作停留,拍照留念之后便匆匆下山。下山比上山要难得多,每下一级陡度大的台阶,小腿肚子都要一阵发抖。我们的速度慢了下来,一边走,一边在景点逗留盘桓。到再次经过太和宫时,又被一阵干净舒缓的箫笛之声吸引。循声而去,只见一个梳髻长衫的道士手捏一支竹箫,坐倚在半高的墙边,支起一边腿,在入神而自得地吹奏。他的面前,摆放着一本用塑料文件夹套好的乐谱。这是一个年轻的道士,面相很嫩,发髻虽然没有梳得一丝不苟,衣着倒也算整洁利落。也许是并不熟练,他的箫声显得有点迟疑和犹豫,却不乏清亮恬静,还带有丝丝虚空和哀伤。我第一次在山上的寺庙中听见如此箫声,仿佛在一块净土上遇到了一泓清水,头脑中杂七杂八的念想忽然被洗去一空,忍不住驻足聆听,心为所系。而后又凑上前去,翻看道士面前的乐谱,才知道他吹奏的是道家音乐,难怪曲调清幽缥缈,让人身心虚静,再无挂碍。他吹奏的是《丰都咒》,歌词独具一格:茫茫丰都中,重重金刚山,灵宝无量光,洞照炎池烦/九幽诸罪魂,身随香云旙,定慧生莲花,上生神永安/功德金色光,微微开幽暗,华池流真香,莲盖随云浮/千灵重元和,常居十二楼,急宣灵宝旨,自在天堂游/寒庭多悲苦,回首礼元皇,女青宝灵符,中山真帝君/一念生太清,默念归大元,九幽旋旋生紫虚。如此耐人寻味的歌词,只可惜当时有只箫声,无人吟唱。后来,我才得知这道乐是教道斋醮科仪等宗教仪式上使用的音乐,以吹管打击乐为主,歌词则一般要由高功、都讲担任颂唱。据说,在求乞福愿的斋醮仪式中,道教音乐有感动群生的作用,看来此话不假——我虽还未听到吟唱之声,就已经被小道士的吹管之声感染了,只觉胸廓涤荡,万象皆空,心下顿生敬畏之情。小道士告诉我,他刚到武当不久,吹奏尚嫌粗糙初级,观里其他的道士要吹得比他好听得多。我便寻思,不知那些老道士吹奏出来的道乐,该是怎样美妙的天籁之音了。
初闻道乐,有点惊为天曲,竟忘了时间,一心想这武当既没有华山的险峻,又没有黄山之秀美,却名声在外,看来真应了刘禹锡的那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当年就曾在南岩修道,武当尽沾仙气,再加上山里终日仙曲飘荡,自然吸引络绎不绝的修道之人和游人慕名前来,想不出名,恐怕也难了。这样感慨间,不觉日头已偏西,拿出手机一看,已近下午四点了,而四个必去的景点,我们只去了一个。于是,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匆忙赶到太子坡,坐上环保车往南岩宫去了。
选择南岩宫,是因为早就听说它建在峭壁上,险峻奇巧,值得一看。下了车,一路小跑,一时上坡一时下坡,直赶得上气不接下气时,远远就见到南岩宫矗立在一片悬崖峰峦之上,面临深壑,仿佛在万仞之壁横空冒出一座宫殿,极目眺望,那万仞像一个巨大的鲨鱼口,而南岩宫则像是镶嵌在鱼口之间两颗参差的门牙,雄奇得令人难以置信,反而像积木搭建般不真实起来。及至走近,进入南岩宫的正殿玄帝殿之后,广殿大庭,高堂飞阁,视野开阔,刚才的险峻之感才渐渐消弥。旋尔,穿过正殿步入石殿及右侧的两仪殿后,身临崖边的晕眩感又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只见石殿依岩而建,坐北朝南,上接云天,下临绝涧;殿前有著名的“龙首石”,横空跃出,悬空而立,龙头上置一小香炉,险峻无比。龙首长约丈余,宽仅一尺,上面精雕细刻,巧夺天工,俨然就是鼎鼎大名的“龙头香”了。据说,过去每年都有信众不远千里而来朝拜,为了许下大愿,在龙头的香炉上争烧头炷香,不惜铤而走险,甚至葬身沟谷。信众们的虔诚日月可鉴,但为此而丢掉性命,似乎有违进香祭拜的初衷。如今,这种危险的行为已被禁止,当年的盛况也不复存在了。我自问本是俗人一个,假若哪年亦许下了大愿,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或许也会上山争烧头炷香。但转念一想,这样的朝拜未免又过于功利了,倒不如上山听听仙乐,沾沾仙气,以求神清气爽,还更为明智些。
南岩宫“仙山琼阁”、“丹台晓晴”、“晨钟夕灯”的意境,本该慢慢游玩,细细品味,只可惜我们的时间有限,还要赶坐五点钟最后一班下山的车。在乌鸦岭候车时,我一直在默想自己与武当的缘分,还有对武当没由来的那种亲切感,才恍然悟起,原来自己的居住地佛山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祖庙,里面供奉的也是玄武帝——本地人俗称的“北帝”。祖庙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比初建于唐朝的武当宫殿要晚几百年,但在当时的南方是最早的,故称为“祖庙”。岭南一带的寺庙大多供奉观音菩萨,供奉玄武大帝则少之又少,只因佛山地处珠三角水乡腹地,当时水患频繁,而玄武恰好是传说中治水的神,于是玄武就作为佛山的保护神被供奉起来,此后,佛山便再无水患之扰,百姓安居乐业。每年的春节,当地人都要去祖庙烧香拜祭感谢北帝,虔诚之心不亚于武当每年抢烧头炷香的信众。虽然我没有养成每年去拜祭的习惯,但祖庙也算是经常出入之地,故此,对武当的宫殿油然而生熟悉亲切之感,也是在所难免了。想来,这就是自己和武当的缘分所在吧。
坐上车下山时,天色向晚,很快便暮色四合,除客栈旅馆的点点灯火外,武当陷入了一片昏暗之中,群山连绵,万籁寂静,像是沉沉地睡着了一样。车上的游客都噤声屏息,生怕打扰了入眠的群山和仙人。我心生遗憾,只盼着下次再来,把这次错过的紫宵宫和遇真宫尽快补上。
责任编辑 易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