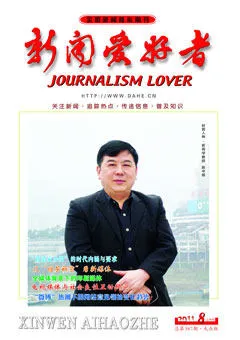两宋时期写真的审美功能
宋代写真的功能从重教化转向重审美,逐渐形成追求意境和诗性的表达,更加关注人的内心主观世界,注重自娱性,强烈抒发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郑午昌指出:“唐代绘画,已讲用笔墨,尚气韵;王维画中有诗,艺林播为美谈。自是而五代、而宋、而元,益加讲研,写生写意,主神主妙,逸笔草草,名曰文人画,争相传摩;澹墨楚楚,谓有书卷气,皆致赞美;甚至谓不读万卷书,不能作画,不入篆籀法,不为擅画;论画法者,亦每引诗文书法相印证。盖全为文学化矣。明清之际,此风尤盛。”善画者多工书而能诗,画家不但画技要好,而且文化底蕴也要深,“画者,文之极也。故古今之人,颇多著意……唐则少陵题咏,曲尽形容;昌黎作记,不遗毫发。本朝文忠欧公、三苏父子、两晁兄弟、山谷、后山、宛丘、淮海、月岩、漫仕、龙眠,或品评精高,或挥染超拔,然则画者,岂独艺之云乎?难者以为自古文人,何止数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将应之曰:‘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这里面就说明了绘画与绘画者之间全面修养的关系。文中所指的人物要么精于品评论画、要么画技登峰造极,后人仰止,文学与艺术相互融合,画品与人品交苒互渗,达到了至善至美的程度。宋代的绘画追求文学品位,推崇士人绘画,贬低画工绘画,苏轼有诗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由此可见,即便是唐代“吴带当风”的吴道子,到了宋代也不得不屈身于画工了。
宋代的文人画家通过绘画,以解胸中之郁结,借以达到愉悦心情之目的。“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爰及万法,缘虑施为,随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书画,发之于情思,契之于绡楮,则非印而何?”一语划破,直抒胸意,使绘画的本体美学逐步挣脱社会伦理的桎梏,进一步升华。
世人寄情抒怀的内敛与外化
借画像作为情感依托,是人们表达尊崇、爱慕、祈福乃至闲情逸趣、自娱自乐的手段。将个人内心情感外化为写真向世人传达。唐代崔徽就以写真为爱情信物,表述衷肠,“唐裴敬中为察官,奉使蒲中。与崔徽相从,敬中回,徽以不得从为恨,久之成疾。自写其真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崔徽为唐代河中歌妓,裴敬中使蒲州,与崔徽相恋,数月后,裴离去。崔思念成疾,便绘制一幅自己的写真,寄给敬中,不久相思而亡。后世遂以此为典,喻指情真爱深的女子,歌颂伟大的爱情。故事真实与否无法考证,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写真可以假借感情的信物,寄托人们无尽的思绪。为此,苏门四子之一的秦观曾写过《南乡子·妙手写徽真》,把崔徽描绘得貌美如仙,加以歌颂。由此可见,宋代写真的审美意味更浓,意义也更深远。
写真可以作为表现人们自娱自乐、闲情逸趣的工具,“君不见潞州别驾眼如电,左手挂弓横捻箭。又不见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耸山。饥寒富贵两安在,空有遗像留人间。此身常拟同外物,浮云变化无踪迹。问君何苦写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适。黄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勋名将相今何限,往写褒公与鄂公”。何充秀才画苏轼像,不过是为了“好之聊自适”,还有赵元俨,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八贤王,“元俨生而颖悟,太宗尤所钟爱,不欲令早出宫,每朝会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封,故宫中呼为二十太保。广颡丰颐,资质严毅不可犯,其名闻于外夷。性喜儒学,在宫中时,孙奭为侍讲,平日与论经艺,尤所亲礼。多畜书,好为文词,颇善二王书法及飞白书,尝自绘太宗圣容”。他爱好广泛,诗文书法,样样精通,对绘画也很偏爱,自己曾亲手绘制其父圣容,这种雅致应和何充一样,自适而已。还有金代王庭筠(字子端,号黄华山主)也曾为其父写真,将其描绘得如仙人雅士,居青松碧水间,清静空闲,如入仙境,赞美之情,溢于画面。“仙人紫霞衣,危坐古松间,玉色映流水,不动如丘山。平生黄华老,得意每相关;九原如可作,与君相对闲。”画中此景,确实令人思绪绕梁,浮想联翩。
写真还可以用来展示内心的宏图大略,金海陵王完颜亮曾通过绘己像于吴山绝顶,彰显豪情满怀,壮志凌云,欲投鞭南下,一统江山,体现其内心强烈冲动的一次宣泄,“金主又潜使画工密写临安之湖山城郭以归,继则绘为屏而图己之像,策马于吴山绝顶,后题以诗,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盖金主所赋也”。由于这次军事冒险彻底失败,其人也横尸瓜洲,他的深思妙想,最终也变成了临安遗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把深藏在内心的情感,诸如渴望、追求、苦闷、纠结、赞美等来之于心,行之于笔,表现于纸,外化为写真,展现给世人,才能得以解脱。
文人审美情态的记录与再现
宋代,文人学士深受统治阶级器重,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或写诗作赋,寄情山水,激情雅集;或为民请命,嫉恶如仇,一身正气;或血流战场,视死如归,丹心汗青;当然这其中也有投敌叛国、陷害忠良,令人厌恶的龌龊之徒。宋代的写真能表现出文人特有的内在思想和生活态度。但是,见之于记载和流传的写真,大部分是表现文人悠闲自适、雅然聚会的情景,用于显示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我们可以看一下传为李公麟现存的写真《西园雅集图》(图1),水墨纸本,白描入画,以写实的方式描绘了李公麟与众多文人雅士,包括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秦观等名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做客聚会的情景。画中之人或挥毫泼墨吟诗赋词,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每个人的表情动态在李公麟笔下皆栩栩如生、动静自然,人物衣纹草石花木,每一笔线条都处理得十分精致,游动的墨线节奏率然朗快、迂回荡漾,整幅画面潇洒、隽逸、嫣然欲绝。
另外,看一下《耆英会图》,文潞公将当时的很多名士绘于耆英堂,“元丰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时富韩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以洛中风俗尚齿不尚官,就资胜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闽人郑奂绘像其中。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文潞公与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议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寿皆年七十。时宣徽使王公拱辰留守北京,贻书潞公,愿预其会,年七十一。独司马温公年末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请入会。温公辞以晚进,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后。潞公不从,令郑奂自幕后传温公像,又至北京传王公像,于是预其会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潞公又为同甲会,司马郎中旦、程太常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绘像资胜院。其后司马公与数公又为真率会,有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惟菜无限。楚正议违约增饮食之数,罚一会。皆洛阳太平盛事也”。当时传写诸公之真像,尽显逸士之风采,“然一时衣冠人物之华,水竹林亭之胜,朝野升平之象,髦老康宁之福,蔼然见于毫素,使人展卷而为之叹息企慕,恨不身生其时而目睹其事,盖有非后世俗史之所能及也”。《耆英会图》与李公麟乘兴所绘《西园雅集图》很相似,此图景物全作初春,同时它也表现了当时文人的生活情态,人物形象鲜明,极尽潇洒之态。
我们再看通过绘像对当时文人学士的描绘,就更容易走进当时的生活。“荆公退居金陵,多骑驴游钟山,每令一人提经,一仆抱《宁说》前导,一人负木虎子随之。元祐四年六月六日,伯时见访,坐小室,乘兴为予图之。其立松下者,进士杨骥、僧法秀也。”金人所绘《苏子瞻游赤壁图》所绘苏轼游赤壁中的情景“扁舟驾浩荡,水月聊相娱。低头俯清冷,照见髯与须,仰视苍苍天,与身同一虚”。他们通过这些写真绘画记录了宋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审美理念,再现了那个时代文人的音容笑貌和时代特征。
文人赞美他人与自我评价的依托媒介
“赞”是一种文体,赞文一般简洁、明了。“像赞”则表现出对所绘人物的赞美,它往往与当下的社会思潮、经济发展、人文历史、人情世故等密切相关,是文人学士生活情态、道德追求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有自写赞和赞他人两种。汉代,像赞就已经出现了,如“初,父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到了宋代则非常流行,通过它可以了解到所绘对象的很多信息。文人学士往往利用自写像赞来描述自己的经历、成败等,抒发对理想与现实的憧憬、苦闷,甚至超脱。苏轼则曾这样评价自己:“予过金山,见妙高台上挂东坡像,有东坡亲笔自赞云:‘目若新生之犊,身如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今集中无之。”苏轼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是一位为人耿直、刚正不阿、才华横溢,颇受争议的人物。一生都郁郁不得志,在改革派和元祐党之间,他都不被认可,备受打击。发配、流放相伴相随,一贬再贬,饱经风霜,最后陨落于常州,可悲可叹。和苏轼相对的黄庭坚也因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最后笃信佛教,以禅入诗,以诗释禅,寻找到了精神安慰,自写禅味十足诗一首:“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这是他淡泊自适的内心写照,也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态度。
我们再看一下对他人的写赞,像陈亮,他在《辛稼轩画像赞》中,称好友辛弃疾:“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戴四国之重。”他淋漓尽致地歌颂辛弃疾照映一世、流芳百世的英雄形象。国家之栋梁,英雄盖万世,而却无用武之地,隐含对南宋朝廷苟且偷安、屈膝投降政策的唾弃。宋代曹勋曾对赵伯驹(字千里)、赵伯骕(字希远)兄弟的写真写下了这样的像赞:“此尊者双瞳瞭然,奋髯虬然,志趣丘壑,风神□仙。昆季燕处,华萼相鲜,芝兰庭户,笔墨山川。此特妙发天藏,为金马之隐尔,讵知高视物表,居玉牒之贤。甚抱负磈礧,凌砾万象,雕龙海陆,顾丹青不可得而传也。”“天潢流派,濯秀玉潭,丰姿英发,神宇粲然。彼天下能事,琴书笔墨,固不可写,而难兄难弟,一丘一壑,亦安得而传。霜松雪竹,宗籍之贤。”赞美之词,洋溢于表。
像赞这种题材有时也会成为相互吹捧的手段,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圣其父过于孔子也。雱死,荆公以诗哭之曰:“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儿子比孔子也。父子相圣,可谓无忌惮者矣。”这里的王荆公指的是王安石,儿子对父亲写真进行赞美很正常,此处异乎寻常的是父亲对儿子的赞美有点出格,父子二人皆不遗余力地吹捧对方为孔子,较为滑稽。
参考文献:
1.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
2.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3.李福顺:《中国美术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4.宿白等:《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室壁画》,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5.杨辛:《文潞公耆英会图考析》,《文物》,1999(12)。
6.单国强:《古书画史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7.朱志学:《两宋“写真”的社会功能研究——根据两宋史料对宋代绘像重构》,2007年版。
(作者为中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