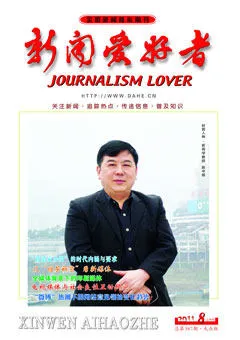新媒体与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
摘要:弱势群体由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在大众传播语境下缺少话语表达平台。目前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还不健全,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传者和受者的线性传播关系,使得网络等新媒体成为弱势群体寻求话语表达的主要途径之一,但近年来发生的“酒鬼妹妹”等网络事件也暴露出新媒体在弱势群体话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弱势群体除了可通过制度内途径进行话语表达外,还可以借助媒体进行利益诉求。
关键词:新媒体 弱势群体 话语表达 话语权
从我国进入改革和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以来,由于文化根源、心理根源、社会根源,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法则、城乡二元结构和市场经济中的失范行为等经济根源,造成了社会阶层分化日趋严重,由此产生的弱势群体及其话语表达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关注,“在利益逐渐多元化和博弈的时代,弱势群体由于普遍缺乏能为他们代言、发声的渠道,不拥有相应的话语权,从而影响了其利益的表达”。①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保障,既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给予弱势群体政策上的扶持,又要提升弱势群体媒介素养、拓宽话语表达的途径,大众传媒特别是新媒体应该履行媒体的社会责任,发挥媒体力量,为弱势群体话语表达提供有效途径。
弱势群体及其话语表达
“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在智能、体能以及权能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人群;社会弱势群体又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它不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老弱病残群体,还指在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全球化浪潮中随时陷于失业、贫困、孤立、边缘化状态中的人群。”②弱势群体同样享有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自由,但他们既没有掌握应有的话语权,又缺乏畅通有效的话语表达渠道,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常常被社会忽略。
新媒体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以数字技术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媒介,它的核心特征在于“它的互连性;它对于作为传者又是受者的个人受众的易得性;它的交互性;它的多功能和开放式终端的属性;它的普及性和‘去地域性’”。③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改变了广播、电视、电影的播放型传播模式,“在当下的媒介化社会,媒介所有者不再是社会中的强势角色,媒介平民化使得普通民众也能分享舆论表达自由。而且新技术的使用可以使得舆论声音得到最大限度地复制与放大。”④但其在弱势群体寻求媒体救助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新媒体语境下弱势群体话语表达的困境
总体而言,弱势群体在整个社会分层中处于底层,缺少社会资源,因此呈现出“利益表达与实现上的边缘性、获取其利益机会上的稀缺性、应变能力上的低适应性和心理承受能力上的脆弱性”。⑤新媒体虽然给弱势群体带来了话语表达的机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矛盾,陷入了话语表达的困境。
媒介素养与话语表达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弱势群体主要包括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虽然“弱势群体”与“贫困人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弱势群体往往是社会的低收入人群,而且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2010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总体网民达到4.2亿人,从网民的城乡结构来看,农村网民占27.4%;从收入结构来看,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网民占34.0%;从学历结构来看,初中和小学以下学历网民分别占到整体网民的27.5%和9.2%;从职业结构看,无业/下岗/失业、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产业/服务业工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共占网民总数的25.7%。可以看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多从事体力劳动、经济收入较低的弱势群体接触网络的总人数仍低于高学历、高收入的社会主流群体。
在2009年1月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还对中小学生、大学生、办公室职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四个重点群体进行了网络应用行为研究。该项调查显示,在网络媒体、信息检索、网络通信、网络社区、网络娱乐、电子商务和其他类型的网络应用行为中,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网络应用普及率最高的前三项分别是网络娱乐(网络音乐)、网络媒体(网络新闻)和网络通信(即时通信),网络社区应用中的“拥有博客”和“论坛/BBS”的普及率在四个重点群体里均属最低,而在这些网络应用行为中,博客和论坛是话语表达的最佳途径。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弱势群体使用网络的人数仍然较低,同时使用网络的弱势群体较少借助博客、论坛等方式来进行话语表达特别是利益表达。弱势群体媒介素养水平整体较低,最终形成媒介弱势,更影响了他们通过媒介来发声的可能,也失去了有效话语表达的机会。
网络议程设置与话语表达之间的矛盾。媒介的议程设置指的是“媒介的一种能力,通过重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⑥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由三部分组成,即媒介议程、公共议程和政策议程,它们共同影响着信息的传播过程和取得的传播效果。
网络环境中的议程设置与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议程设置权由媒介适当让度到网民手中,网民议程设置成为可能;二是网民构成的复杂性使议题多样化;三是网民参与度更高,互动更快捷,扩大了议题的影响力。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新媒体为他们拓宽了话语表达的途径,但是如何从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以引起网民关注,进入公众议程甚至是政策议程,这是一个难题,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网络事件也暴露出弱势群体话语表达与网络议程设置之间的问题。
麦库姆斯和韦弗认为,受众的导向需求是决定信息能否进入议程设置的重要因素。在网络传播中不再以传者为中心,受众对于信息的需求成为他们使用媒介并从中获得满足的前提。波尔斯和考特赖特(1993)列出了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以电脑为中介的传播可以满足的需求,如放松、娱乐、忘掉工作或其他事情、寻求刺激、消磨时间(尤其是无聊的时候)等。因此为了迎合受众,传者会有意识地将符合受众需求的信息置于媒介议程中,以引起受众的注意。尤其是在如今大众文化日益娱乐化的趋势下,公众表现出猎奇、寻求刺激、宣泄不满情绪等倾向,因此越是刺激、显著的事件越容易进入公众议程之中。这也正是“酒鬼妹妹”等网络事件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在网络传播中一般性的求助信息很难在众声喧哗的网络中受到关注,因此弱势群体在新媒体中如何做到有效表达是利益诉求成功与否的关键。
媒体刻板印象与话语表达之间的矛盾。不少学者对媒介中呈现出来的农民工、女性等弱势群体形象或者关于弱势群体的媒介报道进行的量化研究发现,“在有限的弱势群体报道中,一些传媒呈现弱势群体形象也表现出妖魔化倾向”。⑦在媒介呈现中,有些新闻媒体用“跳楼秀”、“自杀秀”等字眼来报道弱势群体因遭遇社会不公的无奈抵抗;有些新闻报道用诸如《连体婴儿之谜》等充满猎奇色彩的标题来吸引读者。媒体对弱势群体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而是将负面的特征赋予他们并通过刻板印象加以强化使之污名化。这些对于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一经形成,就如李普曼所说的,“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⑧
通过媒体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会将弱势群体的媒体刻板印象在受众心中固化并形成负面的成见,必将影响弱势群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这不仅是对弱势群体的漠视和伤害,更加剧了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新媒体赋予了弱势群体一定的话语权,而且弱势群体有话语表达的需求,并且掌握了传播的工具,也很难突破和改变社会对之已经形成的负面刻板印象,“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失去了传播能力与传播工具,就等于失去了说话与表达的能力,甚至导致自我本质的丧失,并且将自我形象的诠释权,拱手交于媒介掌控者的手中,而这样的权力关系,亦会落入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中”。⑨媒介可信度与话语表达之间的矛盾。媒介可信度实际包含了三个方面,即“来源/信源可信度(sourcecredibility)、信息/内容可信度(message/contentcredibility)、渠道/媒介可信度(channel/mediacredibility)”。⑩在传播技术不断更新的21世纪,媒介可信度研究开始关注网络可信度和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媒介可信度比较研究,弱势群体话语表达的媒介方式会影响利益诉求的有效性。
1.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来源可信度比较。“‘来源/信源可信度’指的是传播者(commun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