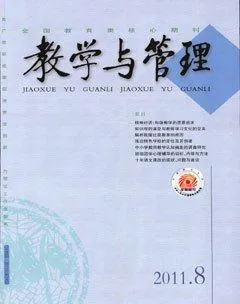论课程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性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无疑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认为其中很多歧见和争论是出于对公平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笔者认为,课程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即:无论是没有公平的效率还是没有效率的公平均是虚假的,它们二者应该是和谐地统一于学生的公平发展之中。
一、课程公平的实质是为学生发展提供其所应得的课程支持
由于课程是“学生发展的最核心支持力量”、“公平就是给每个人以其所应得”,因而,课程公平主要就是指“为学生发展提供其所应得的课程支持”。这个说法内在地包含了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即“学生应得什么样的课程支持”和“学生应得的课程支持如何实现”。其中,前者涉及的是实质公平问题,后者则是程序公平问题。
课程支持是泛指支持学生发展的支持系统,是一个包括内容、目标、实施、评价等一切与课程相关的因素支持系统,因而能否促进学生获得“公平发展”就自然成为学生应得课程支持的判断标准。个性发展是学生公平发展的实质,强调个性发展也成为了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共同趋势,学生应得课程的实质是得到“能够促其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促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课程支持”。
“公平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设计出了“给每个人以其所应得”的基本原则,还需要有“怎样给每个人以其所应得”的方式与程序。一般来说,“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靠道德的自觉约束力量,一是靠制度性的外在约束。其中,道德的约束力量具有强弱两重性,因此,要实现课程支持有序的“给”,除了人的道德自觉以外,还必须有一种外在的力量与方法,制度就是这种外在的力量。当然,课程制度要成为实现课程公平的必要手段有一个前提,即制度本身体现公平原则,不然它就极可能会沦落为赤裸裸的强权的工具。例如纳粹德国的法,那么这种制度的控制约束力越强,离公平就越远。
二、效率的多种理解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而经济学对于效率一词的使用又源于自然科学。效率最初原来是物理学中的概念。物理学中“效率一般定义为有效输出量对输入量的比值。”从定义可以看出效率主要涉及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这深合经济学家的口味,使其成为一个衡量生产活动的指标。
经济学对效率的另一种解释是在制度层面上进行的。受古典理性观念的影响,现代经济学中效率概念通常被赋予最优的含义;在此层面上,效率亦即经济制度效率,指一种经济制度达到了不减少给予某个人的好处就无法增加给予另一个人的好处的程度,即著名的帕累托效率,它描述的是一个特殊的均衡点,就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的结果。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十分重视对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且马克思本人有关经济效率问题的论述,是我们研究和探讨经济效率问题的基本理论依据。马克思写道:“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那么,如何实现对劳动时间的节约呢?与符合社会需要相联系。因此,我国学者给经济效率下的定义是:“经济效率是指社会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生产所提供的效用满足的程度,它是需要的满足程度与所费资源(成本)的对比关系”。它不是生产多少产品的简单的数量概念,而是一个效用概念或社会福利概念。
三、课程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性
1.课程公平与效率根源于社会实践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根源于社会实践的发展。课程活动也是一种实践,它自然也就一样会产生公平与效率问题。社会的发展使教育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显然,接受教育对每个个体具有必要性。而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时期,作为重要教育资源的课程支持总是相对稀缺,社会必须制定合理分配课程支持的原则,这样课程公平问题就产生了。
同时,由于课程支持的稀缺性,使得人们必须考虑怎样配制课程支持最有利、有效的问题,这样课程效率问题必然出现。因此可以这样说,课程公平和课程效率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2.学生的发展规定了课程公平与效率追求价值的一致性
从前面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课程效率本身不是一种独立自显的价值,它应是相对于学生的发展而言的,如果学生的发展受到了压制或产生了异化,即使课程方面的投入再少,也不能说有课程效率。因此,课程效率就是指单位课程投入所发展人的质量达到最优,也可以理解为以最恰当的课程投入促使学生获得最恰当的发展。而课程公平的实质就是给学生其所应得的课程支持、实现学生最佳的发展,因此,在学生发展这一共同价值追求上,课程效率与课程公平有着天然的联系与统一。
从“效率=产出/投入或效率=结果/投入”这一传统的定义公式上来看,效率的高低与产出或结果的多少、质量成正比,而与投入或成本成反比。考虑到课程效率是事关学生发展的效率,“人的价值”应在其中处于核心价值的地位。因此,课程效率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产出或结果与投入的比值”,它与投入、产出的数量、质量关系更为重要;它应至少要求我们明确这么两点:
第一,必须保证课程生产出来的“产品”——学生的发展是合格的,才能说是有“课程效率”的。如果学生的发展出了问题,那么,即使课程投入很少,课程投入与表面上的“课程产出”的比值还比较大,但这也同样不能说是有课程效率的,至多只能说是“畸形的效率”或“假效率”,不是“真正的效率”。
第二,必须保证“学生应得发展”的课程投入,才能说是有“课程效率”的,否则,因课程投入不足,虽然从表面上看“投入与效率成反比”,但学生发展“不合格”这一无效结果便就决定了“无课程效率”;课程投入太多,当然更是浪费,也是“低效率”的。
因此,“课程效率”都是相对于“应得的课程投入量”而言的,而这种“应得的投入、追求学生的应得发展”实质就是课程公平的另一种形式表现。效率不仅是最小投入最大的发展,而且更是最恰当的投入最恰当的发展,对于人来讲,最恰当的发展应该是他的潜力基础上的最恰当的发展。比如:通过恰当的课程支持提供,使得巴金发展成为了今天的文学巨匠、姚明发展成了今天的篮球明星、刘翔发展成了今天的田径名将等就是最有效的。
从“效率就是帕累托最优”的界定来看,课程公平与效率更是一致的。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指“若不使其他人变得得差一些,就不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平衡状态,因此,“课程效率”也就是“课程支持提供最优”,每个人的发展到达了一种“若不牺牲某个(些)人的发展权利就不会继续有更好发展的平衡”,这也意味着我和别人实际上都刚好得到了“各自应得的”,也即我们彼此正好获得了“公平”。因此,“帕累托最优的课程效率观”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的“课程公平观”,追求这种效率的课程效率,实际上同时就是在追求一种理想的课程公平。比如说如果以牺牲农村落后地区儿童发展的权利为代价,集中有限的课程资源提供在发达城市极少数的精英儿童发展身上就是一种破坏“帕累托最优效率”的方案,也是对课程公平的一种损害。
3.当前教育课程领域“公平与效率”争论的实质
目前经济学界的“效率与公平不可同时兼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底线公平基础上的效率优先”等观点以及相关争论,实质都是蕴含“公平与效率是相互冲突的”这一结论,并且,受此影响,目前教育界也有不少研究公平的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矛盾的”,于是引申出:面对我国教育亟待发展壮大的事实,可以“效率优先”,依靠行政手段形成的“重点与非重点”“城市与农村”等不公平的教育现象便应运而生,并成为其他新的不公平的源泉。
其实,“研究公平和效率问题,必须十分重视不同时代、不同范畴、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学科的界限,不能以此时代、此范畴、此层面、此学科的概念去解读彼时代、彼范畴、彼层面、彼学科的同类概念,否则,只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经济学界更多是单纯从“投入量与产出量的比值”这一经济效率标准进行探讨,而较少从“产出质量”这一角度阐述;而教育课程领域面对的就是正在发展中的人,我们不能只讲“单纯的比值”,我们更应要看重产品——人的发展质量,并且,注重人的发展质量,并不要你课程投入过多的支持,只要求恰当就行,应当就是最有效率的。
至于,有人混淆了“公平与平等”,以致出现将“追求平等与追求效率的冲突”等同于“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冲突”,那更是不应成为“课程公平与课程效率相冲突”的理由。很明显这与人的个性差异性相冲突,因此,课程平等所要求的平等分配自然与课程效率要求相违背,表现出激烈的冲突。但“课程平等”不是“课程公平”,“课程平等与效率的冲突”不能说成是“课程公平与效率的冲突”,课程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任洪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