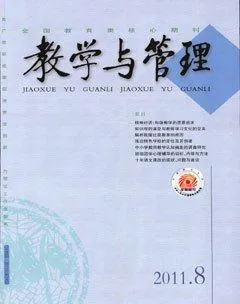论孔子德育思想的践行途径
德育本义应指道德教育。在我国古代,“德”、“育”二字是分开的。《说文解字》释“德”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外得于人’说的是要正直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内得于己’,讲的是内心修养,也就是无愧于心。”[1]可见“德”即道德。“育”在《说文》中的释义为“养子使作善也”,即熏陶涵育子弟使其为善,“育”同道德教育。事实上,“德育这一概念的出现,从教育史上看,是起始于中国近代教育,多半是作为道德教育的简称和同义语”。[2]
一、主观努力的“为仁由己”途径
在孔子的论域里,“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中的“仁”就是一种“爱人”的品德,一种“爱人”的同情心或“仁心”。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这种“仁心”,才会做到“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乃至做到“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要培养这种“爱人”的同情心,使自己具有“仁”的品德,就要从道德教育入手,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进行内在的道德修养,这就是所谓的“为仁由己”。
在实现“仁”的问题上,孔子特别强调主体的内在自觉。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这里的“己”和“人”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己”是主观方面,是内因;“人”是客观方面,是外因。也就是说,实行仁或做到仁主要在于自己,而不是在于别人。在孔子看来,“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和根据,实行“仁”完全是人的内在要求,而绝非任何外力的强迫所能奏效的。所以,“在道德修养亦即为仁的问题上,主观内因是最主要的”。[3]
在孔子的心目中,德育本意中的“仁”处于非常崇高的地位,是必须终生为之奋斗的大事,虽然表面看来达到“仁”很容易,其实不然。“仁”的目标诚然高远,但是,高,并不是高不可攀;远,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仁”的实现总归要落实在人的行为上,需要从点滴做起,这并不太难,更重要的是,“仁”本来就在自己心中,所以贵在有行“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只要心中总想着这个目标,才可能有相应的行动,这样,才会实现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仁就一点儿也不遥远了。可见,“我欲仁,斯仁至矣”绝不是说不考虑现实条件,或完全排斥实践,只在那里一味空想。它只是强调德育过程中的主动性即内心总要牢固树立道德修养的这个目标而已。
正因为孔子特别重视德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他对缺乏主观能动性的人深表惋惜,甚至给予严厉的批评。他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仁”本来就是植根于人心的内在本性,在“仁”上用力,自然就不存在主观力量够不够的问题。“一日”言其短,如果谁说“力不足”,那不过是他的主观托词罢了。孔子的弟子冉求问:“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论语·雍也》)孔子批评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论语·雍也》)所谓“画”就是自己给自己划了界限,停止不前。如果是半路上走不动了,别人可以给鼓鼓劲,帮帮忙,这样还有可能赶上;但如果是主动放弃前进,那么就永远没有达到目的的希望了。
二、反省改过的“自省自讼”途径
“自省自讼”(《论语·雍也》)的德育途径与孔子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的思想紧密联系。“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其意是说,君子总是求自己,向内求,寻找自身原因;小人总是求别人,向外求,找外部原因。因此,“求诸己”还是“求诸人”,便成为是区分君子还是小人的分水岭。“自省自讼”,就是向内求,经常不断地反省自己。
“自省”的概念,出自《论语·里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这里的“思”与“内自省”指一个人面对贤人或不贤的人时,将自己和他们相比较,在内心反省自己、评价自己,努力做到象贤人一样。见到不贤之人,就应反省自己,看自己是否有类似的缺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分开说,自己反省自己,可以叫做“内自省”,而自己评价自己,可以叫做“内自讼”。如果合而言之,也可以说就是“内省”或反思。孔子所说的“内自省”、“内自讼”都是自我反省的德育修身方法,是实现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孔子的弟子曾子发扬他“内自省”、“内自讼”的道德修养原则与方法,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三省”说,逐渐成为人们品行修养的重要原则。[4]
“闻过必改”是“自省自讼”的目的。孔子认为,在德育过程中,应教育学生注意改过。他说:“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即一个人有了错误,要及时改正。一个人不怕犯错误,最怕文过饰非,没有勇气承认和改正错误。孔子说他本人是不怕改正错误的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天生不犯错误的“圣人”,而是一个会犯错误的“常人”。不过,他认为他有一个长处,就是能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如别人指出他的过错时,他即表示改正,不但不埋怨,反而高兴。他有闻过则喜的精神,学生倘能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并坚决改正,那就不算缺点、错误了。因此,他认为教师不应老算学生过去缺点、错误的陈帐,而应朝前看,看学生现在的表现如何。孔子本人正是这样看待自己学生的缺点和错误的。比如:“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已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就是说,互乡这个地方的人“习于不善”。有一天,这个地方有个少年要求见孔子,并受到孔子的接见。孔子的学生对此甚为不解,认为老师不应接待这个“习于不善”地方的人。而孔子回答说:“唯何甚?”(《论语·述而》)何必苛求于这个少年呢?“与其进也”、“与其洁也”,(《论语·述而》)应该看到这个少年现在的进步和现在品德渐趋纯洁;“不与其退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而不应回头看,看重他过去的缺点、错误如何。
三、就近学习的“能近取譬”途径
“能近取譬”(《论语·雍也》)就是能够以切近的事物或行为作范例,进行比较学习,从近处着手,一步一步去做,是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孔子“能近取譬”的思想见于《论语·雍也》中:“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能近取譬”的“近”字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意思是,近就是自己,即以自己的感受来推己及人;一种意思是,近就是同自己最亲近的人,按照这一意思,则应指的是自己的家庭成员或其他亲近之人。[5]一般说来,一个人是爱其父母、兄弟、妻子的。以爱父母、兄弟、妻子之行为作例子,以爱父母、兄弟、妻子之心去爱他人、爱一切人,这就是“能近取譬”。“能近取譬”的意义就在于以孝悌等道德为基础,由爱家庭成员及其他亲近之人扩展到爱一切人。
“能近取譬”的德育途径,与孔子所主张的“亲亲”原则、爱有差等是完全一致的。“能近取譬”,也就是“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替别人着想,这是孔子开创的一种开放式的思维方式。他要求学生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研究和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孔子正是试图借助这一有效途径,实现“至仁”的理想。你自己想要的,人同此心,大家都想要,都想得到;你自己不喜欢的,别人也不喜欢,所以你也不应该把它加在别人身上。自己不愿干的事,不要叫别人干。“推己及人”就是以自己的好恶作为别人的好恶。
也就是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立,树立,指立业,所谓“三十而立”之“立”;达,达到,指某一目标的实现。就是自己想立的业,也帮助别人立;自己想达到的目标,也帮助别人达到。这种推己及人的胸怀,便是仁人的胸怀。按照这一胸怀去行事,就是“为仁”。当然,这种以己所欲推及他人所欲,并帮助他人实现所欲的“为仁”,会受到个人能力的局限,亦即一个人的“为仁”能力,总是有限的。帮助他人“为仁”,不强加于人也是“为仁”。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如果说“如见大宾”、“如承大祭”(《论语·颜渊》)还是表现形式,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实实在在的内容。“无怨”,就是“为仁”的结果。子贡问老师,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生奉行的?孔子便告诉他:“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一次,孔子不仅讲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将这一句话的意思进一步作了概括,提炼为一个字:“恕”。人跟人相处就是一个恕道,能够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假如我是你,必有宽佑他人之心,这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即“仁”的境界。如果终身奉行“恕”,自然就是一位仁人。但难就难在坚持上,而做到“坚持”就要求必须心中有“仁”,且须将“仁”时刻存在人心之中。这样,推己及人才能自觉,才能自如。
概而言之,从文化学的视角来说,孔子的德育思想是一种文化理念,它认为道德教育是个人自觉地将社会的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人内在行为准则的过程,其途径主要是内在修养;它既有基于人性的对道德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伦理价值规范的正当性等诸多问题的理论论证,又有把抽象的道德理念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礼仪规范并使之能够操持执守,付之日常生活的实践品格。
参考文献
[1] 沈善洪.中国伦理学说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2] 鲁洁.德育新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3] 冯天瑜.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 汪国栋.孔子哲学新论.南宁:广西师大出版社,1990.
[5] 刘宝楠.论语正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陈国庆)